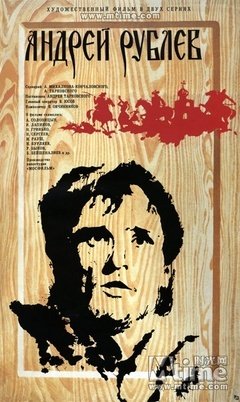《伊万的童年》是一部由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 爱德华·阿巴洛夫执导,尼古拉·布尔里亚耶夫 / 瓦连京·祖布科夫 / 叶甫盖尼·扎里科夫主演的一部剧情 / 战争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伊万的童年》影评(一):一时失语的颓然
朋友借了我一大堆碟,先挑了这张看。说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俄罗斯的战争电影,对于塔柯夫斯基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之前从未了解过。影片通篇黑白色调,戴着冷硬的时代感;炮灰渲染出战争的残酷;沼泽、泥水、零星炮火、破败的废墟、吊死的军人......一幕幕颇具视觉冲击的画面倾泻而来。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剪裁,如黑白纪实摄影般的镜头感,带给我们一种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感受他人痛苦”的语境。黑白的流畅中,伊万漂亮的脸蛋让人印象深刻;然而看到影片的最后,伊万和他姐姐在海滩上快乐地奔跑,迎向夕阳(抱歉,因为是黑白的,所以不确定是朝阳还是夕阳,但我想孩子们一般都是喜欢下午玩耍的吧。。),影片就在这里落幕,留下一时失语的观众......塔柯夫斯基把话语权交给观众,没有一点的多余和煽情。就像拿着相机的摄影师,冷眼旁观着芸芸众生;然而,纳粹的罪行,对如花童年消逝的扼腕,却又于无声之处悄然奏响弦音,颓然,凄冷,而又坚定。
《伊万的童年》影评(二):暂且记下感想
第一句话,提纲挈领:因为看了雕刻时光第一章的关系,我看了电影伊万的童年,作为不懂艺术的普通人,暂且记下感想。
伊万的童年的开头、中间穿插、和结尾都是男孩子的梦境。梦的解析里面,老弗神神叨叨念了一整本的梦境是愿望的改装,儿童时期的梦境则更加真实的反应其愿望的本体。12岁的少年的愿望非常简单,在母亲的身边玩耍,和妹妹一起吃苹果打闹。那些景色就好象是牧歌一般,安静美丽。即便是黑白电影,也似乎能看到小男孩金色的头发,晒在大地上的金色阳光,和水面下星星的影子。这是最平常不过的生活,童年难道不应该就是这样的么?战争年代这样的生活只能是个奢望。
看到小男孩少年老成的跑去了指挥部,说出自己的代号要求联络总部,用蘸水笔写下敌人的信息。眼神坚强刚毅,站姿坐姿甚至吃东西的样子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比我们当年的小兵张嘎更加觉悟更加革命,只有在梦境里和面对特别的人的时候,他才稍许回复到真实的自己。他寻求的是保卫伟大的祖国和家园么——肯定不是,没有家人的家园不过是回忆的坟场。当战争夺去一个人的所有的时候,人不会强大到去反思,去觉悟,只会找一个敌人去憎恨,去毁灭它们,也毁灭自己,不然就无法活下去。生与死的渴望是一个哲学命题,今天不想谈……伊万的想法,应该也逃不出,我已经在地狱里面了,你们也要来,我跟你们没完!
中间那一段伊万在房间里面想象着面对敌人的场景,不知道后来他又没有实际做过。小男孩小的时候都喜欢玩打仗游戏,就算长大了也会偶尔沉浸,不然那些游戏公司的人都得去喝西北风。差别是那种临场的真实感,游戏之所以为游戏,就是死亡不过game over,我们还可以改日再战,而真实的战争则是one or never,挂了的话下辈子投个好胎,这辈子没戏了。伊万在那个自己的“战争游戏”里面表现出来的紧张,杀意,恐惧,让人觉得真实,却情不自禁的皱眉头。
老塔的电影追求的应该是诗化的世界,不会和一些美国片那样有过多的撒血浆挥大刀,当然以当年的技术也做不了那些。所以轰炸的时候拍着太阳没入乌云和十字架的倒塌,牺牲的战友尸体被挂在沼泽里也没有加入近的特写。最后突然一个急转入攻陷柏林,四处欢歌,伊万最后留下的,是纳粹在行刑前给他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里面他含着憎恨的目光。
欢歌的音乐非常的耳熟,是父辈们都会高唱的喀秋莎,赢了,胜利了,又怎么样呢。孩子们已经死了,或是被行刑,或是被家人宁为玉碎的杀死,留下惨白的尸体或是一张照片,让人对着一排排绞架不忍想象。
我们还是需要用做梦来慰藉自己么?
战争是成年人的残忍游戏,小兵张嘎虽然搞笑,但是说难听了就是洗脑,童年是宝贵的不该被如此利用。大多数时候,我讨厌战争片,很多都是立场片面,毫无美感的东西。同样的二战题材,我国的抗战片一般都是:鬼子真TM不是人,全是杀千刀的畜生。老美的一般是,日本人偶尔也是人,不过我们更人性,啊~。日本人的一般是,虽然呢……但是我们也是有爱的,尽管呢……其实我们反思了,对吧……恩你们懂得嘛……别老是那么看着我啊<-少将体模仿不成功真对不起。
《伊万的童年》影评(三):【转】萨特影评
萨特谈《伊万的童年》
作者:萨特 文章来源:文学 点击数:297 更新时间:2006-11-1
背景:1962年,塔科夫斯基的处女作《伊万的童年》在威尼斯获得了金狮奖,并引发了评论界的争论。当时正旅居意大利的萨特,给《团结报》的编辑阿利卡特写了这封信,并谈了他自己对影片的一些看法。
阿利卡特,你好:
在不少场合,对于贵报评论家在文学、雕塑和电影(领域)所做的工作,我都不止一次向你表示过由衷的敬意。我发现(在他们的评论中)严谨与洒脱并行不悖,而这意味,他们把握一件艺术作品独特具像的同时,还能直中问题的要害。或许,我要对此重复派萨.塞拉的赞扬:没有因循教条的左派,也没有思维僵化的左派分子。
而这,也就是今天我要向你抱怨的原因。《伊万的童年》是我近些年看过最为出色的电影之一,而《团结报》和其他左翼报纸对此片的评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不就是一种因循的、模式化的责难吗?评审团给了影片代表最高荣誉的金狮奖,不过在意大利左派偏狭的眼中,这恰好奇怪地证明了该片是“西化”的产物,而塔科夫斯基则是个具有小资嫌疑的导演。事实上,正是这种不禁推敲的臆断,使得我们的中产阶层与这部深刻、革命的,以一种典型方式表现苏联年轻一代情感的俄国电影失之交臂。因为当时在莫斯科,不管是小范围的首次试映,还是之后的公映,我都是同年轻人们一起观看这部影片的。我知道这电影表达的对于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意味了什么,作为俄国革命的接班人,他们从不怀疑这一荣耀并随时准备将其进行到底: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对这部电影的认同里,没有半点属于“小资的”反应。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家在面对所评价的艺术作品时要毫无保留地接受其全部,但对于这部在苏联受到热情讨论的电影如此之轻蔑是否合适呢?不考虑这些讨论和其中深刻的意义,而把《伊万的童年》只当作苏联现行体制下的一个范例来批评,又是否合适呢?亲爱的阿利卡特,我当然知道你并不认同评论家们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向他们致以真挚敬意的同时,我希望你能让他们了解到这封信的来意,或许在这场讨论为时未晚之际,公开其中的内容。
这些评论家把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看成是过时的,因循守旧的。照我看,他们这种形式主义的框框本身才要被报废。的确,在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那里,象征主义被巧妙地掩饰了,但实际上最后的效果却更明显。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并不能更多地避免象征主义。其实,有必要谈谈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具有的象征功能,不过这里限于篇幅不宜展开。评论家们指责塔科夫斯基的,是这种象征主义的特质。他们说,塔作品里的象征符号是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而这点,正是我不能接受的。首先,这里同苏联的一样,对这位年轻导演有一种学院式的责难。那里的某些评论家,就象你的这些一样认为,塔科夫斯基一知半解地接受了一些过时的西方艺术形式,并且不加批判地加以运用。他们因影片中伊万梦境的戏指责他:“瞧那些梦!在我们西方,早就不用梦来表现了!塔科夫斯基落伍了,这种手法二战时期用用还凑合!”以上这些,就是官方评论家的定语。
塔科夫斯基今年28岁(这是他本人告诉我的,而不是有些报纸写的30岁),可以肯定,他对西方的电影缺乏足够充分的了解。他受的教化本质上必定是苏联式的,同资产阶级处理电影和相关材料的方式没有任何关系。
伊万是疯的,是只怪物,也是个小英雄。现实世界里,他是战争最无辜、最可怜的牺牲品。这孩子,让人不禁怜爱,却早被暴力所内化、锻造。村民遭屠洗的过程中,纳粹杀掉伊万母亲的同时,也扼杀了他。然而,他活着。在那个残酷的时刻,他目睹身边的同胞纷纷倒下。我自己曾见过一些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不堪大屠杀的折磨而时常产生幻觉。对于他们而言,清醒状态下的噩梦与夜睡时的梦魇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被人杀,也要起来杀人,并开始习惯屠戮。他们惟一具有勇气的决定,就是在面对这难受的苦痛中选择仇恨和逃避。他们战斗,并在战斗中逃离这种恐惧。而一旦黑夜卸除他们的警备,一旦他们入睡,就又恢复了儿童的稚弱,这时,恐惧再次出现,而他们又重拾起想要忘却的记忆。这就是伊万。我觉得有必要感谢塔科夫斯基如此出色地展现了,对这个随时准备做出自杀式举动的孩子,这世界是如何日夜不分的。无论怎样,他都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世界,不同于我们,行动与幻觉咫尺相近。请注意这种关系,他同大人们呆在一块:他住在军队里;那些军官——英勇的人们,勇敢但“正常”,没有悲剧的童年——保护他、爱他,尽可能地使他“正常化”,并且到最后,送他去上学。很明显,如同契柯夫小说里写的,这孩子能在这群男人中找出一个来取代他失去的父亲。只是,这一切来的太晚:他不再有双亲相伴的需要;(比痛失双亲)更为深沉的是,大屠杀所带来的那种难以拭去的恐惧使他陷入孤独、隔寂。最后,军官们认定,这孩子是温顺、让人惊异、和产生痛苦的不信任感的混合体:他们把他完全看作是只怪物,美丽而又令人厌恶,对他,敌人所激起的完全只是屠杀的冲动(比方说,刀子),而无法在战争和死亡间产生联系。伊万现在,需要这丑恶的世界来过活,需要在战斗中逃离恐惧,需要在苦痛中战栗死去。这小牺牲品知道什么才是必然的:(创造他的)战争,鲜血和仇恨。不过,那两个军官爱他,而他能做到的,只是不讨厌他们。对于他来说,爱是一条永远不通的路。他的噩梦、幻觉总离不开这三样东西。它们无关勇气,也无关对这孩子“主观世界”的巡视:它们完全是客观的,我们从外部来看伊万,就象那些“现实主义的”场景;真相是,对这孩子来说,这世界整个就是场幻梦,而对于旁人而言,这世界里的男孩、这怪物和烈士,则是另一种幻梦。正因如此,影片开首的场景就向我们巧妙地介绍了这孩子和战争中真和假的世界,向我们描述了一切,从伊万穿越树林的现实过程到他母亲假的死亡(他母亲的确死了,但那是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其意味隐藏之深到我们无法知晓)。疯狂?现实?两者兼而有之:战争中,战士都是疯狂的,而这怪物般的小孩就是他们疯狂的客观证明,因为他就是疯的最厉害的那个。所以,这里关系到的,并不是表现主义或象征主义的问题,而是这一主题所要求的特定叙述方式,就如同青年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超现实主义“。
要了解影片主旨的确切涵义,就有必要对导演的意图挖掘的更深:即便最后存活下来,战争还是扼杀了那些制造它的人。同时,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每一次运动中,历史都需要(这些)英雄,它创造他们,并且通过让他们在自己所塑造的社会中受尽磨难,来毁灭他们。
他们在赞扬《烈火男儿》(L'Uomo da Bruciare,塔维亚尼兄弟62年的电影,描写一个工团主义者同黑手党之间的抗争)的同时,却向《伊万的童年》报以睥睨。他们偏对这部处女作给予了褒奖,褒奖它的价值,即重提了正面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复杂性。的确,导演给让片中男主人公有一些缺点——比方说,爱夸张。同时,他们显示出这个角色的牺牲其实源于他的自我中心和保护。不过就我而言,没觉得这电影有什么新意。最后,出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总给我们以微妙、复杂的英雄形象:他们在强调英雄身上缺点的同时也提升了其优点。其实,问题不在于衡量英雄的善恶得失,而在于把英雄主义本身作为探讨的主题。不是去否定它,而是去理解它。《伊万的童年》正点明了这种英雄主义的必然和含混之处。这男孩不善不恶,他是历史造就的极端产物。他被不由主地抛入这场战争,并为此而生。要说他在周围的战士中引起了恐慌,那只是因为他不再习惯平静地活着。源自痛苦与恐惧的暴力,留在他体内,并生了根。他靠它存活着,于是不自主地去接受那些危险的侦察任务。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会怎样?即使活下来,他体内那股岩浆般炽热的东西也不会让他安生。这里,在这个词最近的意义上,不正是对正面英雄人物的一种重要批判吗?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哀伤而高贵;他令我们看到其力量悲哀而颓丧的来源;他揭示,这战争的产物,是何等贴合这好战的社会,又在走向和平的途中,被后者所唾弃。而这,就是历史造就人的方式:它选择他们,践踏其上,并最后碾碎他们。在愿意为和平而战、而献身的人中间,只有这好战而疯狂的孩子是为战而战。他活着,纯粹是为了这个,因此在爱他的战士中间,他显得无比孤独。
然而,他是个孩子。这孤寂的灵魂保持着孩童的稚弱,但却难再体验它,更别说表达它。即便是在梦中回归于它,或是从日常的喧嚣中轻身而退,这些梦仍是无可避免地化成了夜魇。那些表现赤子欢乐终结的画面让我们害怕:我们知道到这种终结。这稚弱虽脆弱而抑郁,但却活在当下的每一刻,用这稚弱,塔科夫斯基小心地把伊万包裹住:无论战争,甚至有时是出于战争,它都是一个世界(我想起那些火球划过天际的美妙场景)。事实上,这电影里的诗意、刻意的天空、明澈的水、无尽的森林,就是伊万的至极生命,是他失去的爱和根,是他曾有的模样,是他已然忘却的,是内在、围绕与他,别人能看到,他自己却不再意识到的东西。我知道,这电影里没有什么比这一连串长景更动人的了:河流悠长、迟缓,为之心碎;抛开他们的痛苦和疑虑(让一个孩子冒这些危险合适吗?),陪伴他的军官们被这种可怕、孤寂的稚弱所深深打动;男孩一身尘土,无言渐逝:在满野的尸体中走向敌方;小船从河对岸归来,水面上一片死寂:祷文残短凋零;一个士兵对着另一个说:“这死寂,就是战争…”
就在那瞬间,这死寂爆发:尖叫、怒号,就是平静。狂喜中,苏联战士遍布柏林的领馆:他们奔跑着,冲上楼梯。其中一个军官在一处暗格中找到一叠名册;这曾是第三帝国的作风:名单上有每个被绞死的人名,照片。年轻军官找到了伊万的照片,上面写着:12岁,绞刑。在追求建设社会主义的举国欢庆一片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黑洞,就象针扎般的刺眼:一个孩子,在仇恨和绝望中死去。没有什么东西,即便是未来的共产主义,可以补偿这些。他向我们展示,没什么东西可以打通集体的欢乐同这种个体的、微不足道的苦难间的隔阂。这时,甚至没有一位母亲为此而伤痛和自豪。人类社会朝着它的目标前进,生者将运用他们的力量实现这些目标,然而这渺小的死者,就象一株卑微的稻草被历史碾过。它将永远成为一个问号,不提供答案,却又如一道崭新的昼光将一切照白:历史是悲剧的。黑格尔曾这么说过,马克思也是,并且他还说,历史往往通过它的阴暗面来获得进步。不过我们通常不愿意这样讲,最近的这些时代,我们追求进步,而忘却了那些失去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伊万的童年》用一种暗暗的、平柔的,但又极具爆发力的方式提醒我们这一切。一个孩子死了。看着他无法再活下去,这几乎是个让人高兴的结局。我想,在某种意味上,这个年轻导演要讲的,是自己和那一代人。不是讲这些骄傲而坚强先驱的牺牲,是讲他们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童年和命运。一个孩子被他的父母亲毁掉,这是资产阶级式的悲喜剧。而百上千万的孩子因战争而死,或因其而活着,则是苏维埃的一种悲剧。
于是,这部电影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一种别样的俄国。技术是俄国式的,尽管它本身是原创的。我们西方人,知道如何去欣赏戈达尔那种快速又简略到晦涩的节奏,以及安东尼奥尼般自然原生的悠缓。但在一个从未受此影响的导演身上看到这两种风格同时出现,实在是新奇的的体验。塔科夫斯基以无法忍受的迟缓来让人亲临战时的岁月,同时,又以历史简略的快速从一个时段跳到另一个时段(我特别想起影片中两组场景的绝妙对比:河流与国会大厦)。这期间,电影不靠情节的推动,不展现角色生命的特定时刻,而是在另一种时刻、或是死的时候再现他们。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影片的特色并不在于这两种节奏的对峙。那些绝望的时刻尽管不多,但足以毁掉一个人,我们知道它们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我不由想起1945年的一个犹太男孩,同伊万差不多大,当他听闻双亲死于纳粹的毒气室和焚化炉时,往床单上倒了酒精,躺上床,点着,把自己活活烧死了)。但是我们没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去从事一种宏大的工作。我们太了解恶是什么。在那种时刻,在善恶对抗处,善之中永没有极端的恶。这正是打动我们的地方:自然,苏联人无须为伊万的死负责,犯罪的是纳粹。但是问题不在于:恶来自何处?当恶如同万点针尖般刺破善时,它揭示了人和历史进步的悲剧性事实。当然,这里没有任何悲观主义的因子,但也不是什么廉价的乐观主义。有的,只是斗争的意志和对其代价的清醒认识。亲爱的阿利卡特,我知道你比我更清楚这点,痛苦、汗水和鲜血,常常是人最不愿意计入社会代价的东西。我能肯定,在死者的历史缺失这点上,你将同我一样地赞赏这部电影。我对《团结报》评论家的敬意也促使我请求你让他们读到这封信。如果信里的一些内容能使他们有机会做出回应并重提有关伊万的讨论,我将非常高兴。对于塔科夫斯基而言,真正的褒奖并不是金狮奖,而是电影能在那些反对战争、争取自由的人当中引发起讨论的兴趣。
仅致我全部的友谊与敬意
《伊万的童年》影评(四):梦境之诗-----献给老塔的诗行
(一)
奔跑与意义
奔跑着的你呦
究竟是什么刺得你
双脚流血的奔跑
爱情还是死亡
一种神秘不可知的莫测的力量下
你径自跑向自由的新大海
直指最后的黑漆灌木中直指的
死亡---永恒的神秘之梦幻王国
哦,哀鸣的太阳,黑漆的枯树
瑰丽死亡幸福岛的大门等待着
高低凌乱的枯枝
群鸦尖利的啼哭
哦,死亡正从大海上升起
太阳已从黑漆枯树的哀鸣声中
慢慢走入走向林间黑夜的沉沦...
附注:这首诗灵感起于影片《伊万的童年》的最后结尾。
最后一个梦境开始的是关于沙滩上的无常游戏,爱情,神秘,自由与死亡及奔跑的意义!是小伊万跟很多同伴在沙滩上玩游戏,其实将的就是人生,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如沙滩上的快乐游戏是人生的本质,众多孩子小孩子中那的小女孩则象征着存在真理的遮藏,(或如海德格尔的“存在”的被传统形而上学中众多的存在物的遮蔽)尼采也曾说过真理如一女子,他躲藏,诱惑嬉戏我们,她只暗示,引诱却从不明白显现,伊万发现和后来的奔跑做一种诗意的追问!
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讲过个人生的譬喻: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的游戏性,我们的人生其实不过是在沙滩上搭建房子城堡的游戏,其中就是死亡的冒险性,有着死亡的毁灭的痛苦和大欢喜是一般人所不能体会的,尼采也曾说过,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在大地的桌子上掷骨子。当一浪花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堆的东西一下子全没了,我们犹如孩子般看到自己的建造的东西被无常的浪花(生命无常的象征)给毁灭,吹打走了时候,我们不知觉的都哭了起来,却突然不知道浪花给我们又带来那么精致的贝壳和其他的好看的各种各样的美丽的小石头....当然这个游戏的前提是以死亡为参照的,就是大家都在玩,但有的人是在玩命式的去游戏!是以死亡冒险为代价的。其中的生命的无常的本质所带来的毁灭的大痛苦和意外的大欢喜也不是常人所能体验到的.... 当然这可能还涉及到老海的死亡存在哲学,比如伊万是象征的此在(dasein),那小女孩子象征存在(sein)做指引着伊万,伊万的奔跑可以象征的灵魂,心灵在以死亡为参照下以彻底追问存在的形式而向虚无中作诗意的敞开的存在(being)....
另付其他:
第三个梦境,爱情的萌动
云端上的咏叹
总似在冥冥之中
何种不可知的奇力
神明般莫测的玄秘
似天宇的轻风
流水的淙淙
柔柔伸出纤纤手臂
绚丽如紫金色的彩虹
刹那已把你我勾勒在一起
划落在大自然恋爱的琴键
似九月的凉风,摇落了一秋的金黄
似云上的雷电,瞬间击中爱的萌动
抚动了曲曲爱的乐章
不停颤栗着心玄的忧伤
瞬间融汇于狂喜与痛苦之中
最后里有一个无常的丫丫藏在沙滩游戏的后面
啊!你变幻,无常的美
本就是生命最本真的底片里
最纯净的蓝色
在轻柔触及到生命的
奔涌激流的大浪花的一刹那里
在永恒的流逝的时间长河之中
所遗留下的一片美丽而忧伤的剪影
哦,这染发着诗意,梦境一般的美幻与忧伤
神秘的永不可重复!
啊!古今又有多少诗哲们
曾为不能捕捉到你痛苦的焦灼而忧伤的叹息
并瞬间转为为你永久沉迷的痴狂.....
啊!这神秘的,无限用不可知的美呵
且就为我停一停
哪怕就是最短暂的一瞬
我生命的强大自我意志
最终也将你驯服为我的奴隶!
并在万古的永恒轮回中
永久的支配和占有你!
我一朋友的回复:生活祥和静谧,里面包含着不义和毁灭,亦包含着巨大的爱和和平。肉体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灵里的死亡!在日常中突然爆破出来的死亡又好像河水一般默默,流去。盗去,不要让坚贞被盗去,在那渺小的一刻。
光呵,夏日雷雨让道路旁的果园沉浸在一片银白的梦幻中,还有一个清纯的黑眼睛小姑娘在近旁心心相吸。。。真美好!俄罗斯是上帝的恩赐,圣像和铁十字架在烽烟中屹立,始终注视着大地,毁灭、杀戮、仇恨、真挚的爱、呼喊和祈祷都包括在目光的注视中,要相信上帝悲悯,上帝爱人类,上帝爱你,有光!我想这就是塔尔可夫斯基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念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3ce99010009l5.html
《伊万的童年》影评(五):怎么讲和讲什么
让人难以置信处女作即获得了金狮。明白了安塔为什么和费里尼、伯格曼合称圣三位一体了。
安塔最后流亡法国,也死在了那里,在他身上最能看出一个体制下导演的复杂。
伊万内容明显是我们说的主旋律,可他在电影技术和更深的内涵上都体现了自己的思考。技术和深意已经被分析了太多,看那些就好了。
电影的结尾设计让人震撼。伊万消失在敌后,女军医被暗恋她的年轻上级调到后方,压抑的上校愤怒砸烂了椅子。上校的愤怒有迹可寻,当他和女军医在白桦林时让女孩挨着他,又赶走女孩。战争中,他知道爱情是虚妄的且不能承受的。从河边回来,上校失去了伊万、先前死去的朋友,带回了两个被绞死的战友,现在有眼看着军医离开。虽然他知道让军医离开正确的,上尉也爱着他。紧接着的画面是占领柏林的庆祝,上尉的喃喃自语告诉我们科林上校已经死去,接着他找到了处决伊万的档案。档案中,伊万直视着镜头。
其实这电影最大的触动是:任何故事都分怎么讲和讲什么。
《伊万的童年》影评(六):摘要
(一)一些细节
1,死亡暗示:开场伊万的面部特写(7:59)与末尾档案中的伊万照片如出一辙。
2,三种居所:疯老人的居所(树立的烟囱);玛莎的居所(树立的白桦木);伊万的居所(树立的十字架)。
3,跌倒场景:上尉的跌倒(战壕中,谈及玛莎);贺林的跌倒(河边,谈及伊万)。出现在人物理由缺乏、底气不足之时。
4,蛛网:第一场梦境中的蛛网;废墟的蛛网意象;玛莎在白桦林中发现的蛛网。
5,井中的双重视角(18:18):既可看作“井底→井外”视角也可看作“井外→井底”视角;同一性的分裂。
6,时间与水:梦境-伊万喝水-井水-雨水-海水-生命与循环-时间;现实-河水-静止与死亡
(二)悲剧性
1,并不仅仅是伊万的死亡。
2,一种解读是伊万无法分清现实与梦境,但问题不在于伊万无法分清,而在于梦境治愈功能的失败:现实侵入梦境(枪击声、德国士兵的低语)。
3,伊万的分裂:孩童的习性/成年人的激情。伊万必须死亡,或者说,伊万无法成长——复仇信念将伊万困在“过去-现实”牢笼中,战争是伊万的绝对需要,同时是其认知、评价他者的唯一途径,“战后”的、未来的生活对伊万是不可想象的。与其他角色不同/不可弥补的创伤。
说实话我觉得塔的选角除了《索拉里斯》的男主哪里怪怪的之外其他人都赞爆好吗!上尉和玛莎长长的睫毛真是动人心弦!
《伊万的童年》影评(七):《伊万的童年》:为了妈妈什么都无所谓
睁开眼睛就是复仇,闭上眼睛就是与死去妈妈的美好回忆,这就是少年伊万的全部生活。他可以孤身潜入德军战区去收集关键资料和情报,通晓全部的侦查技能,不畏所有的艰难险阻,深夜游过连大人都敬畏的渡河,穿越鬼影婆娑的森林。就算上级领导一再要求他到后方去过正常的孩童生活,去学习知识接受教育,伊万还是毅然决然的拒绝掉。让上前线就去,不让去也要去。这就是伊万的生存信念,为了日思夜想的妈妈,伊万可以完成所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比大人们完成的还要出色,尽管只凭借形只影单瘦骨嶙峋的弱小躯体。最终,现实的命运是残酷的,当抗战胜利以后,军人们在德军丢弃的材料中发现了伊万的档案,被执行绞刑。也终于,伊万与思念的妈妈团聚在天国。
《伊万的童年》影评(八):Childhood Regained
Childhood Regained
y Aimée
In Ivan’s Childhood (1962), Tarkovsky incorporates four dream sequences into a war narrative of a twelve-year old Soviet solider Ivan whose childhood is brutally shattered by the war. While the reality of war produces only fear and horror, an oneiric space in contrast offers an alternative universe of comfort and joy. After the Nazi massacres Ivan’s mother, his life becomes filled up with pain and rage. Determined to avenge, Ivan refuses to attend military school and insists on fighting on the front line,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his murder by the Nazi. In my paper, I will focus on the opening and ending dream sequences. I would argue that these two sequences visually materialize a blissful childhood that Ivan can reside in on the screen but could never have lived. Furthermore, Tarkovsky’s revelation of world through poetic and oneiric imagery thus accentuates a visual counterpoint to a bleak and harsh post-war reality of pain and loss, offering consolation to Ivan and the viewer. However, while affirming the cathartic and healing power of cinematic imagery, Tarkovsky articulates the instability of the oneiric space and refuses to render fictional resolution on the screen.
tylisticall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st of narrative, the two dream sequences present a warm, dynamic world that offers Ivan security and joy.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 is characterized by changes in the choice of lighting and in the rhythm of camera movement. By using natural lighting instead of staged chiaroscuro lighting and freely moving hand-held camera instead static framing, Tarkovsky effectively presents the viewer with a dynamic world full of lively, luminous imagery different from the harsh, disenchanted reality of war. As the camera pans up the torso of a thin tall tree marked by its femininity and tenderness, the viewer is elevated from the ground to the top of the tree. In an extreme long shot, the viewer finds Ivan standing in the meadow and bathed in sunshine. As Ivan turns around and looks back in the direction toward the viewer, a world of affectionate and luminous imagery unfolds on the screen before the eyes of the viewer. The camera swiftly cuts to a close-up of the animated face of a goat staring at the camera, as if the goat has returned Ivan’s gaze. Here, the consolation is primarily enabled by the act of looking. The viewer is directed to look closely at the physiognomy of animals and patterns of things to form a meaningful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he hand-held, wiggling camera also leads the viewer to visually track the movement of a butterfly in an experience of liberation. Nature not only surrounds and embraces Ivan; it also protects Ivan and provides him with happiness. In this alternative oneiric space, Ivan regains a blissful childhood that he could never have lived during the war.
Intriguingly, the point of view that many of these shots provide is ambiguous: the viewer is unsure through whose perspective he or she is seeing. The ambiguity is exemplified by a disorientating panning shot of earth followed by Ivan’s flight. The fast-moving camera pans from left to right at decreasing speed, as if the camer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fter the exhilarating flight. It may naturally follow that in this shot one gains access to seeing things by identifying with Ivan. However, as camera pans further to the right, the viewer discovers Ivan standing by the side of the earthy surface and curiously listening to the sounds of nature. The images thus suggest that there is someone or something else that is also looking at the lively, beautiful things. It is implicated that, in a more ambiguous way than that in the shot where a goat stares back, nature may be returning the gaze of Ivan and the viewer. In the exchange of gazes that precipitate an increasing degree of appreciation for beauty, the orphan is able to immerse himself in the luminous world of joy and alleviates the painful experiences of solitude and loss. The viewer, who is also engaged in the act of looking, is offered such consolation as well. The extended image of the thick earth and residuals of aged tree branches also grounds Ivan as well as the entire film in the comforting natural world that distances itself from the world of human-inflicted atrocities and pains.
Taking his cinematic mission even further, in the ending sequence, Tarkovsky offers the viewer a deeply tactile, consoling experience that goes beyond the visual and aural engagement. The viscous exchange between the film and its viewer gets to beneath the skin and reinvigorates the body. Tarkovsky locates the majority of his images in an unkind nocturnal space: the expressionist mise-en-scène that persists throughout the war narrative is as psychologically unsettling as the reoccurring harsh sounds of diegetic gunshots. The oneiric space, in contrast, is saturated with sunlight spilling over the imagery. After a series of unnerving war images is delivered to the viewer in a mixture of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footage, the viewer exists the ghostly and spine-chilling Nazi office where Ivan is brutally murdered and immediately enters the dream world that is illuminated by exuberant amount of natural light. In a long tracking shot reminiscent of the ending of Truffaut’s 400 Blows, Tarkovsky’s dynamic hand-held camera adds invigorating energy to Ivan’s running and alleviates the melancholy caused by Ivan’s longing for freedom and happiness. In a long shot, Ivan runs away from the shore toward the sea as the splashing waves spread out around his feet. The viewer, as if are invited by the shining sea waves, can almost feel the warmth of sun and water as Ivan does beneath his or her skin. The tactile camera eye thus affirms the cathartic power of images. These shining images in contrast to the gloomy images of war and death offer solace to Ivan as well as to those who may have ha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during the war and to those who have not had direct war experience but are nevertheless affected. In effect, Tarkovsky’s camera transfigures a bleak reality into a luminous world.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arkovsky rejects the escapist approach to post-war filmmaking that is evident in post-war pictures such as German Heimat films. While affirming cinema’s healing power, he nevertheless casts doub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erfectly constructed cinematic space and denies the pleasure of fictional resolution. Ivan’s Childhood does not promote pure escapism or supply propaganda to gloss over the war. Often times, the serenity of the alternative cinematic space is mercilessly disrupted by the sound of gunshots, as the gunshot recurs and repeatedly murders Ivan’s mother in his dreams. In one of most serene moments of the film, Ivan regains a lighthearted childhood after his death and plays with his friends on the sand by the sea in sunlight. However, in the game that Ivan is playing, after Ivan points at his friends who form a circle around him, the friends consecutively fall down as if they are shot by an invisible gun. As the bodies of Ivan’s friends collapse down and encircle him, the bodies become stand-ins for Ivan’s deceased families and friends who are visually absent. The circle of bodies also metaphorically cast a web of death over Ivan, which resonates with the spider web that blocks Ivan’s face in the opening dream sequence. Thus, the oneiric and luminous space is nevertheless permeable to external dangers and potentially unsustainable.
Despite that the indelibly beautiful cinematic space has the power of catharsis, whether this oneiric world is ultimately untenable remains ambiguous. While Tarkovsky wholeheartedly affirms the healing power of poetic images, he refuses to abuse this power. In fact, the flight that Ivan takes substantiates potential peril lurking behind the shining oneiric world and evidences Tarkovsky’s discretion. While Ivan enjoys the blissful freedom of flying, the camera that accelerates in its downward movement foreshadows a potential pitfall and impeding death upon hitting the ground of reality. Tarkovsky’s cinema is thus a realm of ambivalence that exists in a liminal space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The descendent flight that Ivan takes would be explicated four years later in the opening sequence of Andrei Rublev where the peasant-inventor Yefim’s exhilarated flight is cut short when he violently crashes into the ground. After the camera accentuates his tragic death in a freeze-frame shot, however, Yefim is cinematically resurrected in the subsequent images where a sprawling horse gets up and trots off in free spirit.
《伊万的童年》影评(九):属于导演的温暖和纯净
塔尔科夫斯基说过:“电影的纯净和其与生俱来的力量,不是表现于其影像之富于象征(不论其如何大胆),而是在于这些影像表现具体、独特、真实事件的能力。”极其信服这句话。
老塔经典之作《伊万的童年》尽管以二战作为背景,但整部片子全无刻意,包括讲故事的节奏,太节制了,太自我了,太不煽情了,各种平面蒙太奇,大量的空镜头,对白没一句废话,演员也没有表演的痕迹。
60年代的片子,却用了黑白胶片,冷色调,从头到尾色彩阴锐,但导演在这个电影里注入很多温暖的元素,伊万没有童年,战争毁了他的童年;但伊万又有童年,那是和母亲一起在海边欢笑的童年,那是和妹妹一起苹果满地的童年。
从希望开始,以决绝结束,德军司令部的文件宣告了伊万的结局,他那愤怒的眼神已没有孩童的滋味,最终他还是在天国和家人团圆了,最后的镜头是想象的回忆还是梦中的想象,已经不知道的,这也是属于导演的温暖和纯净,也是我最后会流泪的原因。
《伊万的童年》影评(十):有一种宁静
有时人会痛哭,哭过以后会平静。若这时恰好,在夜色茫茫中,便仿佛,古往今来,这世界上只有你这么一个人。
你抬头看看天,突然有亮光。
是星星,或者月亮,或是烟花。
或是战争潜伏时,从天坠落的照明弹。
那一刻,这缕光会无比清晰。遥远得温柔,像是抚慰你的伤口。又明亮得残忍,似提醒着你的黯然。
看这电影时,无端想起《灰烬与钻石》来。
伊万和科林他们潜伏在林子里时,身后的照明弹,在夜空中坠落。这画面,让人想起《灰烬与钻石》中,那一幕烟花。看后者时,是几年前,剧情都已几乎遗忘,却不能忘记,里面盛放过一场绝望的烟花。
于是我在想,人在绝望时看烟花,为什么总有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麦克白杀了人,听不得敲门声。
人在绝望时,总需要那么一抹亮,用这样一种仪式感,却提醒你:是了,你原来是站在暗中。
伊万是痛苦的。他的精神创伤让他无处出逃。他不能接受温文的善意。他用热水洗澡时,会让人想看热水如何抚过他的皮肤:是个孩童的身体。他瘦骨嶙峋,他舀着食物,也会怔怔。他在黑暗中出现幻象。仅这段幻象,便使此片不朽。
关于死亡、战争、屠杀。
水滴让他回想母亲告诉过他的井里一颗星。
人都是奇怪的生物。再苦再痛,也不会哭。难过时给你一丝温暖,反而就不行了。亦舒说的,受伤野兽最怕突然有了抚慰,一口气上不来,也就过去了。
而伊万,便是一直死死咬着这一口气。
直到最后,才敢放开胸怀,跟着死去的母亲,在阳光灿烂的海边,笑着抬头。和伙伴玩耍,和女孩嬉戏。
但战争里,创伤中,他能做什么呢?
惟有依偎着那枯槁的树皮,看照明弹从夜空中落下。
这么亮,这么明白。
晃得眼睛又疼,又要掉泪的。
大概是宣告你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