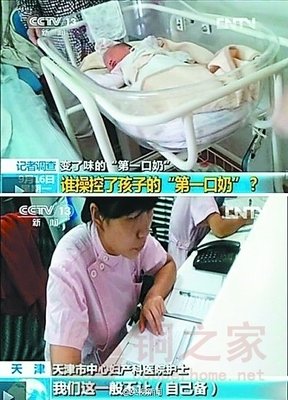《泯灭天使》是一部由路易斯·布努埃尔执导,西尔维娅·皮纳尔 / Enrique Rambal / 克劳迪奥·布鲁克主演的一部喜剧 / 剧情 / 奇幻 / 悬疑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泯灭天使》影评(一):荒诞的强力
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构想了一个失明会如疾病般传染的社会,以此回望创世之初,但他仍然需要将人物隔离在一个摆脱社会的空间之内,以重塑人与人原初构建的关系。布努埃尔则毫不费力地建构起一个类似的空间——客厅,完成了相同的审视。(我们只能怀疑萨拉马戈的创作是否受此片影响。)
一群客人在晚餐后莫名地睡在客厅,看起来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但布努埃尔由此推进,预设下一个绝妙的陷阱:第二天,所有人都走不出客厅了。没有原因,就像被施与魔咒。这一预设让我们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一开头,读者便明白无误地被告知格里高利·萨姆沙变成了一只甲虫。没有原因,就像那群客人不再能走出客厅。
如果变甲虫的故事仅止于此,卡夫卡充其量也只是一位童话故事家,但当他把一个不可能的事写成可能之后,他就成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同样,布努埃尔当然不会只有这么一点天赋,他必须将荒诞的强力彻底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接着看到的一系列堪称漫长的折磨——抱怨、焦虑、面对死亡、疾病……以至于为了生存砸开墙壁取水、烤羊充饥,其间所探索的人性焦灼都在这一困难时刻、密闭空间暴露出来了。而那位充当调停次序的医生无不让我们想起《失明症漫记》中唯一的明眼人——妻子。
当影片照着逻辑发展下去,剩下的便只需一位合理的结尾。《失明症漫记》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此,让人物复明就像是把一场革命的胜利之果拱手相让对敌——一种强力的破败。在此,布努埃尔再次爆发出他的天才之处。他使用了一个回响的结构来巧妙地化解这一莫名奇妙、却效力十足的预设:让所有的人都回到陷入魔咒之前的状态(弹钢琴、鼓掌、赞颂……),于是,魔咒被化解了,就好像当初只是在一个50/50的选择中错误了一次。
其实至此,电影是可以结束了。但布努埃尔说“不,要升华!“于是在教堂我们又见到了故伎重演。可谓妙哉!
《泯灭天使》影评(二):布努埃尔的超现实之旅
今天在塞万提斯学院先看了毕加索的盘子罐子,再看了这一部《毁灭天使》,虽然小厅加DVD投影很不爽,不过看在免费的份上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布努埃尔——这位达达主义的旗手是名副其实的“达人”,他善于捕捉社会人的非理性状态,在银幕上讲述一个个荒诞不经又发人深省的奇妙故事。
经过默片的洗礼,有声电影自然驾轻就熟,看似一板一眼的对白布景却让观众进行了一次不可理喻的银幕囚禁。影片讲述的是一群上流社会的人在欣赏完歌剧后被一对夫妇请到家里共进晚餐,但酒足饭饱加上天色不早客人们反倒没有一个要离开的,都横躺竖卧的在屋内休息了。翌日,众人不解,又想不出任何解决困境的出路,仍旧在屋内搞着社交,随着时间的延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性,最终几近发狂。几日之后,他们共同回忆并重复着这一切的开始,最终解开了“魔咒”,离开了房子。但怪事没有终止,更多的人被困在了教堂之中。
影片主要对这群人被困在屋中的心理及行为的状态进行了详细地展现,一方面揭示了人的普遍的伪装性,人们隐藏着自己的欲望,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另一方面影片中的羊和熊暗示了人的动物性,他们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还要满足性的需求。可以说本片生动地将社会中的人进行了“活体解剖”。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在观影的过程中,由于长时间的表现着这个封闭空间,观众似乎也同样被关了进去,在观看这群人的心理、行为的变化的同时,观众也在无形中“煎熬”着,布努埃尔的这个“实验”成功的将观众拉了进去,中间偶尔的几次外景似乎是在开恩让观众透口气。
影片的结尾,一个街头暴乱的镜头后,人们在教堂内重复着迷失自我的过程,暗示出这两者隐喻的对应关系:社会的本质是疯狂,但常态却是虚伪的谎言与忍耐。
《泯灭天使》影评(三):但是时间注意时间
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母题,小写的与大写的。小写的故事在私域的消遣的场所展开,大写的在公共的严肃的(某种程度上神圣的,当然布努埃尔消解了这种神圣)的场所展开。但是小写的故事占据叙述的大部分,大写的故事时长很短,从这个角度看大写的故事又成了小写的故事的缩写,形成一个在结构和意义上均衡的互文。
除了对中产阶级的一贯讽刺——布努埃尔的老三样(已经是十分平庸且无聊的点了没必要抓着不放),“没有任何壁垒里面的人却无论如何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的隐喻的适用范围远比批判布尔乔亚广泛得多。懒得解读政治和宗教喻意了,太明显。
闪光点是对“时间”这一概念的展现,“电影是从真实时间中倒出的时间模具”(塔可夫斯基),困在别墅里的人们无法计算天数,在过去了不知多久之后,来到和问题发生的当晚的同一时间,每个人无意识地回到自己当初的位置和姿势,有意识地说出一样的话,镜头中多次出现的钟敲响一样的次数,一段轻快干脆的奏鸣曲之后(音乐,音乐在这里十分重要),所有人顺利走出了房间——看到这里我惊喜得屏住了呼吸,一种类似当初看到最后一个奥雷里亚诺在风中翻动的书页中快速解读命运谶语时的激动与快感的清凉激荡全身——时间是静止的,或者时间不存在,中断的音乐在卡壳的节点接上又继续顺畅的演奏下去。
至于其他的细节,作为秩序维持者的医生被关进柜子;羊进入客厅与羊进入教堂;是一个小女孩而不是大人能够向别墅迈几步,我能理解他们有所指。不过把所有细节都当做导演用心良苦的暗喻就上了超现实主义的当了,有时他们就是想到了随便这么一玩。
《泯灭天使》影评(四):泯灭天使
当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里借布努埃尔之口说“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时,正是看这部电影时我们的想法,也正是在此处,我们与电影里的人物产生了类似“互文本”一样的交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跳出“房子”、不能跳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困在了里面”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其实也就被锁在了电影的最浅层。
摘选来自“吞火海峡”的热评一条:为了逃避了人生苦痛和对自然的恐惧,人类遁入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领区。我们本可支配天然赋予的灵活手脚,却在社会规范的皮革中变成了僵死的鸡脚。想要破茧而出的唯一方法,是反思生命本原的追求和意义。
《泯灭天使》影评(五):太晦涩了!
Luis Buñuel的这部超现实主义作品实在是太过晦涩了,直至影片结束前的一刻,(一批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街上肆意抓人时)我才自认为理清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头绪。
影片实际上是影射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弗朗哥独裁时期的政治生活状况,人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肉体和精神的牢狱中,(象征:影片中那些“屋子里的人”)不然的话,就会像影片结尾处那群在街头示威与反抗的人士一样,受到逮捕或滥杀。
但是,这些反抗弗朗哥独裁统治的中左派人士(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并不是一股团结的力量,(象征:屋子里的人时不时就要互掐一顿)他们时不时的还要互相争斗。
当然,在当时的西班牙,仿佛还是有一些能够过着平静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无关的普通民众。但是他们所作的呢?就是像影片中的那些“屋子”外的看客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结局:“屋子里的人”最后似乎想明白了什么(想起了自己被“关押”前的生活),仿佛一下子一切都豁然开朗了,纷纷勾肩搭背的结伴走出了屋子。回到了平静如水的生活中去。( 可以看做是这些“社会精英分子”,“中产阶级”最终放弃了对独裁统治的反抗)。
最后再谈影片中的两个隐喻:
仆人们早早离开了“屋子”:社会中下层阶级显然对于社会变革与动乱,不像那些所谓“社会精英份子”那样麻木与迟钝。
宗教:在这部电影中,它是受赞美的,也是受批判的。它既保护了民众,却又无法领导民众反抗独裁统治。(象征:“屋子”里的大量“宗教画”与电影结尾处的才出现的一些有关教堂的镜头)。
《泯灭天使》影评(六):心灵桎梏
觉得电影很别具一格,含沙射影,有很强烈的喜剧色彩。可以看出来,电影并不一定非常真实,因为如果按正常不加思考的生活情况来看,会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景突出了极端化的色彩。但,也许很多映射就是从这种极端里体现出来的吧
开始的时候客人想要离开,这时聚会呈现一种意犹未尽的气氛,客人留下的时候尽管不情愿但是仍觉的有趣,但是又放不面子。
这种情况持续一定的时间后,焦躁不安迫使所有的人急切的想要离开,然而这种情况下。越是迫切,越是期待有一个人能够先离开,而每个人都不愿意成为那个第一个离开的人。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鬼胎。也许就是这种纠结的心情,困住了大家,让大家在有限的空间里,心理逐渐的扭曲,抛开了理性的面纱,道德的底线,走进了一个混乱的 世界。
可是,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个“混乱”的世界,事实上毫无改变。
《泯灭天使》影评(七):宗教的寓言
这部电影还是针对宗教来的,大家不要忘记不努埃尔的反宗教虚伪的一贯宗旨,而且影片已在告诉观众他的用意何在,人们走进宗教的屋子不愿意出来,由于人性的内在懒惰以及外部世界政治的混乱无序,人们逃不出所谓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迷宫。即使很简单的来路也想不清楚。不努埃尔的反宗教性实际上针对了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的荒诞不经以及当时西班牙国内政治的警察统治黑暗现实而发,即便是超现实的电影也还是针对了当时的现实不放,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反讽精神。至于人性的阴暗,那是必不可少的,典型的对白透露上流社会的无聊和猥琐,人性的虚伪和脱离大众。在批判的方面有点左派的味道。毕竟是大师的作品,想像一流,画面的超现实手法独具一格。
《泯灭天使》影评(八):走出魔障
走不出去的困境,魔咒?更是魔障。
最后一镜:枪声林林下,顺从的羔羊避入教堂。
顺从到了极点则吃掉顺从/goat羔羊,忍受到了极点则吃掉忍让/bear熊。
一切都已吃光,推诿已然无望。
其实并不是重复,每天都在发生微小的改变。
于是回想从前,刚开始进入这房子的景象。
留心钢琴曲。音乐灵粮,有唤醒生命树的力量。
影片写实荒诞,探讨人性的软弱与希望。
有些电影有着惊人的生命力,比如情节上晦涩难懂,人们就热衷于解读、热衷剖析,如果内容上荒诞无稽,人们便热衷提出解读的方案、欣赏的角度。我敢说像《穆赫兰道》这样的电影,无论经过多少年都会被人无尽地剖析下去而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泯灭天使》则会以另一种方式被人传颂,那些过去的,以及即将发生的历史、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无不更新着解读这部电影的“方法大全”,大到国家意识形态,小到个人心路历程。这些电影,和那些不朽的杰作一样,不会被时代湮没,甚至永远在变换着形象,以鲜活的姿态向观众展示着人类思维的局限。
之所以《泯灭天使》这么有“魔性”,我想主要原因也不是布努埃尔为人所念叨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而是那个始终没有给出的“答案”——为什么他们不走出那个房间?是啊,这个有趣的问题之于这部电影就像“我是谁”、“我为何存在于此”、“我将去向何处”之于这个世界中的我们一样无可奈何又诱人深陷,正是这个未曾给出的答案,让影片产生了无穷多的可能性。对阅历不同、信仰不同、认知不同的人们而言,它自然有着数不尽的样貌,就算把布努埃尔本人请来,相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伍迪·艾伦就在《午夜巴黎》里恶搞了布努埃尔一下下)。
隐去的原因,使得一切解读《泯灭天使》的尝试沦为一种可能性的比拼,它像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每个盛装打扮站在它面前的人,但谁是最美的?无人知晓,因为没有标准。于是后继者们依循着《泯灭天使》的脚印,纷纷将“为什么他们不走出那个房间”变成了“他们将怎样走出房间”。于是乎,有人将一群人抓到密室里玩“生存游戏”逼迫他们离开,就拍成了《九人禁闭室》,“在这间密室的成功逃脱却是下一间密室逃脱的开始”这样的结局和《泯灭天使》的最后又是如此相似;有人将这个荒诞的故事用高科技包装一下,再消去那些讥讽的情节,然后加入一些血浆,就成了《心慌方》;又有人让故事里出现怪物、把角色统统换成女人,就又造出了《黑暗侵袭》……
观众们在《泯灭天使》里看见自身,创作者们在《泯灭天使》中看见的是无限多的电影。它是面神奇的镜子,我想知道没有东西在它面前的时候它是个什么样子。
2014.02
http://i.mtime.com/fabzany/blog/774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