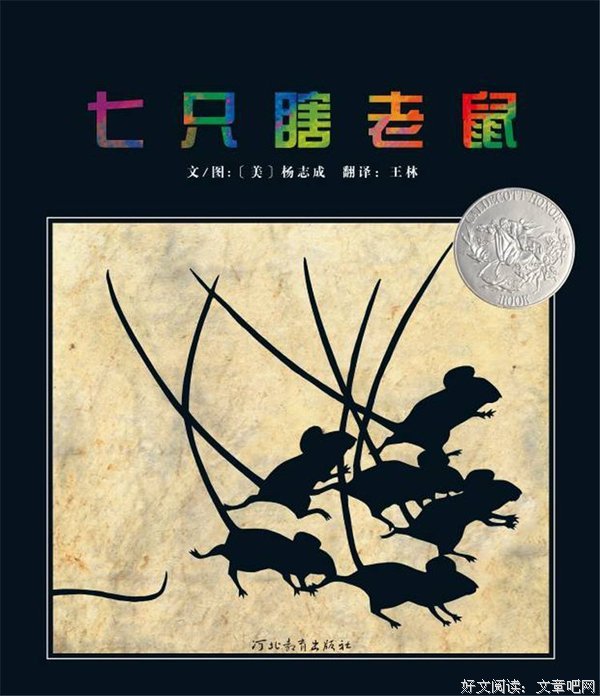《盲人奥里翁》是一本由龚祥瑞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虽然我还没有买到书,也没有阅读,但基于对法治的信念,写点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大家,仅仅有的是一些浮躁.阅读可以让我明白很多事理,从旧事中去体会法治的道路.
寄希望于法律共同体的建立,寄希望于依法治国不是口号而是切切实实的法治现实。宪政理念的控制论,管理论,平衡论将在这里找到答案。
龔祥瑞先生對青年之期待“剋服求知過程中的懶散懈怠”,以及對二十一世紀的嚮往“社會現代化,法律正義化,言論自由化”,值得我們學習。
其中一個章節《兩代人的對話》,有深刻的意義所在。本人猜測,該文爲龔先生自擬的“兩代人對話”,所謂的古人之“賦體”創作,比擬“主客問答”,以申明自己的意思。
龔先生對生活的信心,值得我們學習。當我們是無名小眾的時候,我們要“發憤”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培養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然後等機會來到的時候,我們再努力的實現自己的價值。
要之,本書非常值得閱讀。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四):自序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时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我因此而焕发昔日的青春,像一个手工业者那样不倦地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我想,这种执著追求实践智慧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那源于我家乡的江东父老乃至芸芸众生繁衍生息、死而复生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外部世界的变迁,而在于内心世界的体验。人的本质乃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繁衍生息的精神“亦此亦彼”地相互作用的一种综合的产物。 1923年,我以一个免费走读生的身份进入美国浸礼会宁波北郊路末端的一所中学,这是我童年的终结,少年的开始。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五):敬意
读完整本书,我应该收回我之前说的那话,因为他"信仰"毛泽东,因为他开枪杀了人而对他敬仰度下降,毕竟他不是神,两种情怀始终贯穿他的一生,超然的理性(中立)以及基督教中的忍耐乐观的精神,伴随着他度过了在我们外人看来是何其悲惨的遭遇,但我相信如他自己说所的那样他是幸福的,因为在他心中有着有恒的不灭的希望,因为他自己承受的遭遇坚实了他的宪法学理念,以至于,浩劫之后,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了重燃起生命的那个学者,满怀热情地致力于希望传递给下一代人。有的人很年轻,心却老了,有的人老了,却藏着一颗年轻人的心。当老人在被学生问到“不会让步”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回答“我们的政府是不会让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是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老师-我们永远没有民主的希望了”老人怆然落泪,慢吞吞走回讲台,自言自语的说,似乎是向全班同学说“你们还年轻,无需有丝毫的悲观。”他等不到这一天了,但此时,我想他已把这颗种子埋入了想我一样的诸多法律学子的心中,我敬仰你,前辈,我会追随你的理想!
他说,你们可以举把我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六):后记
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的生活时代的悲剧。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題記:盲人Orion是一顆星座,他摸索著向着朝陽前進。當太陽出來時,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著他的是無窮無盡的晝夜。我非常的像他。
龔先生說他非常地像盲人Orion,其實我看到後的第一想法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多少書生都像盲人Orion一樣默默地追尋著陽光,卻最終消失在無窮無盡的黑夜中。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能看到幾顆這樣的星星?有一些星星在追尋的途中被無情地摧毀,有一些星星中途隕落,有一些星星墜落在無窮無盡的黑夜之中,一些星星照耀著這片土地。我們看得見那最明亮的幾顆,卻看不到那滿天的繁星。這個時代的人們的內心就和這個時代的星空一樣空虛。思想讓位於實務,傳統讓位於現代。
-------------------------------------------------------------------------------------------------------------------------
龔先生出生在作爲中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他的家庭依然保有著中國的傳統觀念,重視家庭,注重傳統。然而他的母親卻將他帶往了美國浸禮會設立的小學識字,並且就讀了英國聖公會辦的小學。彼時是1914年,中國剛剛經歷辛亥革命,革命一直在進行。而龔先生的就學生涯其實一直都在英美教會學校之下,他的大學是滬江大學,後來到清華大學——這所由庚子賠款退款所設立的學校。他的人生背景本身就與近代中國的發展史綁在一起了。
龔先生說他自己的人生是摸索著向着朝陽前進,事實上,他在書中一直提到自己對於政治有的是超然的興趣,所以他並不被其所干擾,而是保持著一顆單純的超脫政治的心。雖然他的內心依然爲中國之命運所牽動,然而他卻篤定了先學知識,再來求變革中國的想法。他在自傳中所流露出來的誠懇讓人爲之感動。龔老確實有良知,肯反思,只是無論是何時,龔老的選擇都顯得太過軟弱,太過中間。我不知道這是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的緣故,還是龔老超脫政治的緣故,在我看來,他的許多選擇不過是選擇對自己最無害的中間道路,這更像是一種妥協,而不是一種選擇。國共內戰時期也好,反右也好,大躍進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我實在看不到太多的擔當與主體性。
---------------------------------------------------------------------------------------------------------------------------
無論那些星星選擇何種方式結束自己的命運,至少他們曾經在星空中閃耀,你擡頭懷想時,低頭思索時,他們便在這近代中國的天空裏默默閃光。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八):We are not to write history,we are still making history
读《盲人奥里翁》是和重读三联马国川的《共和国部长访谈录》混在一起,缘何?大致书中采访的人和龚先生年龄大致相仿,经历或许类似,二者结合起来读,颇有感触,故借用了钱正英的几句话作为标题。
龚先生心无旁骛,一心求学,经清华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可谓学贯中西,且又在实务部门有所历练,留心时务,学有针对性,一脱所谓学院派的窠臼;而马书采访的共和国的部长们,大抵年少时对政治抱有热情,积极投入其中,因而诸部长们多是中途退学,少有高学历者,多是做中学,或依靠家学的沉淀,当然也有成功名就担当“院士”者。部长们也是呕心沥血,爱其岗,认真专研,在各自岗位都有所成就;当然,领导们都有能力,即便涉猎多个岗位都可以胜任,且能做出成就为世人瞩目;而像龚先生这样,仅仅黯淡于法学、政治学,两种某些时候,甚至多数时候杂合在一起的学问时,就难以彰显了,或许当初他们的许多人,彼时的经历都不如他,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时代选择了他们!
坎坷的法学,充实的人生。龚先生的自传读来,有点像长辈在循循讲述一个世纪的变迁乃至法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辗转起伏路。法学作为限制权力之学,素来为当政者所鄙睨,尤其在50-70年代,运动层出不穷,长官意识高于一切,学法学被打倒,也是题中之旨,1959年,司法部不是也被撤销?曾经看到一本《法学界右派言论集》,个中苦楚,不言自明。返观龚先生,下过干校,遭过批斗,但是心中自有坚持,或许教会学校的经历有助于人的心理的慰藉。虽然法学坎坷,但先生的充实,我觉得很充实,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天下”,再不济,先生也曾经20多岁就受聘西南联合大学,有个美满的婚姻,且曾参与蒋经国的青年干校设计,又在考试院、行政院历练多年,于实务工作与学术研究皆有所得,相较一些劫难,也是难得,毕竟一场场劫难不是自己所能躲避的,是世情国情党情所致。
尴尬的宪法,不屈的奋斗。书第21章,关于《宪法理论问题》的纠结,处于八卦的心态,一一google了各自的作者,仔细拜读了他们的批评性文章,但是心中有个纠结:辨证格式的固定,每个人都事先预先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然后不说为什么,只说应该如此如此,就是如此如此,缺乏合理的让人信服的逻辑;或者作为政治表态文章,不免的随大流了。而龚先生的反思与答辩,有理有据,今天读起来,仍让人赞叹不已。末了,厦大的龚先生提及的刘国和究竟是谁,真是难以寻觅啊。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九):天空中的猎户座
奥里翁,猎户座,是冬季星空中最灿烂的星座,他摸索着向朝阳的方向前进。当太阳升起时,他则黯然的隐灭在空中。龚祥瑞老先生在这部《盲人奥里翁》自传的题记里,把他自己比作了奥里翁,那个给我们昭示了方向,而最终又隐灭于黑暗中的灿烂的星辰。
曾经,城市的霓虹,厚重的烟尘,阻隔了我与星空的交流。今天,翻着这本《盲人奥利翁》,听着宗次郎的《天空中的猎户座》,我才明白,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竟是如此简单。我没找到世外的桃源,但是我找回了头顶的那片灿烂星空。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们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发强烈。这两样东西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话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他在书中提出,道德不是以符合个人或他人的幸福为准则的,而是绝对的。就是说他认为人心中存在一种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道德法则,道德应该符合正义而不是个人的幸福。作为道德义务论代表之一的康德将道德法则和灿烂星空相提并论,是因为他认为虽然自由意志是道德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道德法则是刚性的,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突出了道德原则的坚硬性、独立性。
其实,不只康德,很多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道德法则,并为了维护和践行这一道德法则,而不惜一切代价。以此来反观《盲人奥里翁》的作者龚祥瑞,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法学老人向着心中的真理艰难跋涉的身影。
龚祥瑞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他将英美法系中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介绍到中国。1993年7月,他开始写作《龚祥瑞自传》,历时三年完稿。这本自传,是龚祥瑞先生对其一生经历的回顾,也是20世纪中国法、政、学界的缩影。龚老生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年,作为民主革命的同龄人,也就伴随着革命的艰辛,体验着革命的震荡。
龚祥瑞的这本自传,于他而言是当作回忆录来写的,这本书闪耀着一个法学家思辨的光辉,充盈着独立而理性的思想。
当《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直言:“一个法律人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他的抗争是以道德律和正义感为标尺,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
文革时有次他被人批斗,他腿上被活生生踢掉了一块肉。他说:“我活了那么多年,竟然从未知道人间还有如此残酷的行动,虽然脚被踢掉了块肉,但获得了西方书本中学不到的真知。只有实践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这就是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
因为龚祥瑞优美的文字,很多人也可以把这本书当成抒情散文来读。这不是一本单纯的传记,也不是一本散文,更不是一本法学著作,他是龚祥瑞以优美的笔触审视自己,审视20世纪中国法学界的点滴记录和心得。不同的人阅读它,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启示和思考。
猎户座是冬季天空最亮的星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有两种颜色,那是勇敢的猎人头顶的翎羽,那代表着勇气和坚忍。龚祥瑞,就像奥里翁一般。
《盲人奥里翁》读后感(十):写给祥瑞先生的一封信/袁岳
几周前,好几位您生前器重的年轻朋友告诉我你的自传出版的消息,也从《南方周末》上读到对于自传出版的评论,今天得以手捧你的自传《盲人奥里翁》,深感无比亲切,尤其看到你手书的书名,就想起你最后几年写作时候的神情。我有幸在那个时候,见证了你写作时候收集历史资料的不易,也目击了你几易文字的费神,看到方备先生为你誊抄书稿的认真。外人很少知道,你的书稿最早的时候叫做《倒悬》。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几乎完全按照原稿内容出版了你的自传,这部手稿的很大一部分按照现在的政治观念应该是有争议的,所以在你生前也曾有朋友建议在境外出版,而你思索良久拒绝了,今天此书的样子可以告慰你的心愿了。在你最后的日子里,中关园502楼一层的房间里,你常常夜书自传书稿,我在周末留宿您家中沙发的时候常听到你夜半的长吁短叹与老年支气管炎折磨出来的阵阵气急。我现在偶尔走过那里,看到房间里面厚积的灰尘,你与方先生早已不在的荒芜,让我深深心疼。你走的时候,我与刘晓春等兄去八宝山送别,那么多你的学生除了共同的痛苦之外,我还记得亲你额头感到的冰冷与僵硬,也在几年后亲去世的方先生一样的冰冷与僵硬,才确切地感到你们俩的离去。就是一直伺候你们的无为保姆在方先生去世以后决定永远离开北京,她说,“两位不在之后,我觉得北京已经惨不忍睹了,我完成了龚先生托付我的照料方先生的责任,现在可以走了。”
1987年,在下有幸得听先生家中授课,与先生交往,在以宪法思想从事《民事诉讼法》研究方面另辟路径,因此我的硕士论文《诉权理论的再研究》得以自成一说,以今天的目光回看,那时的硕士论文恰也可作为今天诉讼平权主张的基本。此后我在国家司法部工作,以一公务员身份而不曾演变为小官僚思想,受先生的经常影响与教诲颇深。1992年创办零点调查,早期辅助先生在成都做《行政诉讼法》实行成效的调查,也辅助先生修正更广范围的社会调查问卷,在那个时代有此民意调查观念者寥寥无几,先生实乃先锋,也是鼓励我的关键人物之一。今天回看,有人说在中国零点调查开创的民意调查乃是中国条件下的民主元素之一,我想有先生鼓励之功。蒙先生不弃,常与我分享自己的教学观念、旅行感受,在你与方先生最后的岁月里,先生的家就像我自己的一个家,不只与先生有交流良机,也能为两位先生每周末做上一点江浙口味的菜肴,尤其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与冰糖肘子,那是我的幸福所在。在我一生交往的朋友中,能周周见面、长日饮红茶而对坐、几乎次次争辩、常常以书面文章对话、夜半与餐桌上能开研讨会者,唯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学贯中西,我是时不过一黄口小儿而已,能不吝对话,这是我进步的压力与动力。
先生此去十五载,但先生与方备先生的遗照一直压在我的办公桌的日程表下。先生在日曾勉励我辈,“人就应该为理想而活着,虽则你未必会收获理想,但你必定会收获很多没有理想者所没有的东西”。在我们讨论灵魂有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屡有争辩,我主张在人最不起眼的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条件下,最宝贵的灵魂应该是不灭的。先生最后以自己的方式接纳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我现在更希望这不是一个理念,我期望您与方备先生的灵魂垂看苍生,接纳我们的感谢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