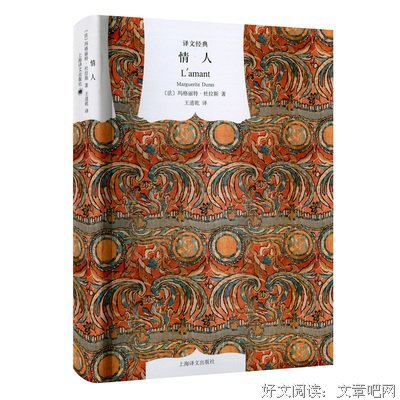
《甘地的武器》是一本由[美] 威廉·夏伊勒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一):喜欢的都不出声了,为嘛?
好几个朋友得到了,有位打劫了别人的,又被打劫。我总是收到电话,说很喜欢,不是喜欢我,是喜欢书。这些人的意见,我先代表了吧。
看了这本书,才懂得怎么看电影甘地。夏伊勒是我喜欢的作家,又在译他的另一本书,讲作者的青年时代,主要是在欧洲的经历,很喜欢。昨天有位小提琴家要去欧洲演出,我就告诉他去巴黎街头的咖啡馆吧!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二):圣雄甘地
甘地曾说:暴力是动物界的法则,非暴力是人类的法则。甘地忠诚践行真理的精神,对每个人尤其是修道之人,是极为重要的。若在广州的话,此书可以去希圣书馆借阅,希圣书馆是文史哲共享型书馆。书馆及借阅详情见:http://www.douban.com/note/301941935/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三):“通向自治的道路会很漫长”
——《甘地的武器》读书笔记
购买这本书不是缘于这是本写甘地的书,而是因为它作者叫威廉•夏伊勒,上高中时我曾读过他写的大部头三卷本《第三帝国兴亡》,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书里面描述集中营中活体实验的那些细节,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对于甘地,我则兴趣缺缺。曾买过一本商务出版社出版的《甘地自传》,可能买的早了点,当时读得味淡如水,一直搁置到现在。也有看过曾获奥斯卡八个奖项的影片《甘地传》,对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是云里雾里,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的形式怎么可能如此具有煽动性和生命力,很是怀疑他是不是又一位被神话的人物,如孙中山之类。在阅读这本《甘地的武器》时,到网上下载了影片《甘地传》重温了一遍,仍然没有特别的感觉,这片子让我想起另二部同是奥斯卡获奖影片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和《莫扎特传》,似乎拍得都不咋地,只除了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这个话我留到最后再讲。
有些中国人蔑称印度人叫“印度阿三”,这个名称起源于上海还有英国租界的时候,当时印度仍是英国的殖民地,雇佣了不少印度人到上海当小警察,这些印度人缠着红头巾,所以也叫“红头阿三”。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印度排到小三的位置,连当汉奸的二鬼子都不如,百度告诉了我一堆答案,我还是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英国人更擅长以夷制夷,他们统治香港时,也从内地招人到香港做警察,现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父亲似乎就是早期从山东被招到香港去的。扯远了。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彼此藐视,我们称呼小日本叫倭人,直指人家的生理缺陷,日本人称呼中国人算客气了,叫东亚病夫也还是承认中国人并不总是这样子,对吧?还有那个什么支那人,其实支那二字是梵文cina的音译,大概等同于CHINA的发音。这样看来,中国的英语称谓实际来源于印度。等等。我要说的意思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村落的家与家之间的关系一样,长期以邻为壑,相互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彼此仇视,又彼此纠缠,但幸福永远是魔鬼词典里说的“看见邻居家失火”,谁也不想谁的好。
我对印度也没啥好感。一说起印度来,首先不是想到它是佛教的发源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是左右手怎么用的疑惑,想起《流浪者》里面永远蹦蹦跳跳的那股子傻劲,哪好玩么?心理上觉得印度永远竞争不过中国,就如同印度板块永远在亚欧板块下面一样,认为他们越跟我们拱我们的珠峰就越高,他们就会陷得越深,等等。去拉萨时,我特意去到荒芜凄凉的拉萨烈士陵园寻找中印之战的烈士陵墓,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里面转了三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任何一尊标有中印之战标记的墓碑,后来在去山南返回的车上,望见那里也有个烈士陵园,那边更靠近当时中印交战的战场,也许所有的烈士都葬在了那里。可惜当时无法下车进去祭拜。我想不明白,难道那时的中国在别人眼里就那么的弱不禁风么?你知道,印度1947年才独立,1962年刚刚建国不过15年就妄图用武力把中国给收拾了,真搞不懂那位印度总理尼赫鲁同学是咋想的。那位尼赫鲁同学就是主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袖甘地的嫡传弟子,也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和甘地一起,共同领导了印度的建国运动。
通读《甘地的武器》这本书,我没找到一点有趣的结论,也没觉得有啥受益。作者作为长期近距离接触甘地的西方记者之一同时也是他的铁杆粉丝写下的很多话也许更适合于放在励志教材里,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真实客观的地方。比如下面这几段:
“甘地是我伟大的老师,不止是他说的话、写的文字或者做出的事情教育着我,他给我作出了榜样。虽然我不是个好学生,我从他那里还是学到了不少。”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追求真理,摒除伪善、虚假、肤浅,努力对自己和他人真诚,怀疑常规的价值,尤其是在物质方面,培养内在的力量,对他人宽容,宽容他们的行为和信仰,不管他们与你有多大的分歧,但是绝不宽恕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永远不要为了利益或出于怯懦而出卖它们,而要维护它们,并且敢于凭借经验和智慧去改变它们。”
“甘地还教会我这些:冥想的重要,以及怎样在20世纪的压力和忙乱生活中坚持冥想。他还教会我如何使身心有节制,时时抑制自己的贪心、欲望、自私和世俗的妄想。他教我去爱、去宽恕、不怨恨、不使用暴力、去了解非暴力的力量,并且懂得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大的勇气。”
甘地坚持过贫穷的生活,身上永远裹着块缠腰布踟蹰而行。他的铁杆粉丝也是政治盟友奈杜夫人曾说:“你永远猜不出,为了让这位圣人——奇妙的老头生活在贫困中,我们花了多少钱!”看来甘地无疑首先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一直试图将信仰和政治结合起来的人物。
书中还有一段话值得一晒。“在甘地走上舞台之前,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相当容易。继东印度公司之后,少数英国人继续统治着两亿五千万印度人,只用两千名公务员、一万名士兵、六万常规部队,以及其所辖之下二十万本地人组成的印度军——他们常常被用来镇压自己的同胞。”按照这个比例粗算一下,如果我们国家也按这个比例配比公务员,也不过仅仅需要一万名而已。我们现在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简单按比例这样分到每个县里的大概就是4名公务员。你能想象出那会是什么样子么?
写到这里,连影片《甘地传》中那两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都懒得写了。就此打住吧。
最困难之时,就是离成功不远之日。——拿破仑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四):神坛背后的甘地
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那样,谈论甘地一直是时尚。然而,当大家谈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只注意他反对中央集权制和国家暴力,却无视他的思想里重来世、反人道主义的倾向”。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是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因报道纳粹帝国兴衰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此之前,他还曾在印度报道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的两年里,夏伊勒基本与甘地生活在一起,记录甘地的运动现状,也记录下了甘地的生活细节。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其作为外国记者的观察,短距离的祛魅效应让他看到一位真实的甘地,也让我们在他的观察之下读到了一位未被神话的甘地。
毫无疑问,夏伊勒没法看到年轻时代的甘地,而是正值运动期间的甘地。在《甘地的武器——一个人的非暴力之路》一书中,夏伊勒第一次对甘地感到惊讶的是甘地对于现代文明的敌视。甘地在一九零九年写下《印度自治》,此书对现代文明充满了敌意,指责科技、机器和医药使人们沦为奴隶,并将西方文明社会称之为黑暗世纪,宣称理想的印度应该没有工厂、海军、陆军和铁路等。20世纪30年代,夏伊勒在采访中问及甘地对其当年言论是否曾做改变时,甘地说:“我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种种罪恶,这种观点没有改变。如果我的书明天就再版,一个字也不会改动,只是背景要改到现在。”从此可以看出,甘地对现代文明的敌视一贯如此,未曾改变过。若考察甘地所在的印度,以及他的私人阅读史,对甘地敌视现代文明的态度不会感到惊讶。朱生坚曾在《读书》杂志梳理了甘地的阅读史:一九〇四年,阅读约翰·罗斯金的《时至今日》,该书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的劳动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一九〇七年,阅读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其中心思想是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们——甘地的萨蒂亚格拉哈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而发展成熟的。两年后,在伦敦,甘地又读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卡彭特的《文明:它的起因和矫正》,作者将现代文明斥为腐化堕落,赞美体力劳动的快乐。更为打动甘地的是托尔斯泰。大量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始于一八九四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给甘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甘地也曾把自己的《印度自治》寄给托尔斯泰,两人有过通信。除去甘地的阅读史之外,甘地所在的印度刚好处在西方文明进犯印度社会的时候,这就导致甘地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
继续让夏伊勒诧异的是,甘地竟然完全赞同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断为之辩护。种姓制度在印度决定了印度人在印度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印度人出生之后应当从事什么职业、家庭的解构以及与其他家庭的关系,还决定了印度人在社会中需要遵守不同的规范。并且,这种制度使得印度群体之间成为单独的、封闭的集体,互相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社会交往,比如不同种姓之间不能结婚,甚至不能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当然,这种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凝聚印度民族统一和印度政府统治社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夏伊勒所言,“在20世纪,当印度再次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候,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价值”。在对待种姓制度上,尼赫鲁的观点与甘地截然相反。甘地对种姓制度的态度,又可以从他的陈年往事中寻找到原因。1888年甘地前往伦敦学习法律之前,本族长辈以种姓等级的规矩而禁止他远行。当他前往伦敦时,甘地被扫出摩德班尼亚等级。而当他回到印度,家人也被禁止前来欢迎他的归来。在印度教徒看来,被扫出等级的耻辱比被处死还要糟糕。
夏伊勒在于甘地的接触中,他完全没法理解其他媒体将甘地塑造成瘦弱的老人。在他的观察下,甘地像钢铁一样,“六十一岁的他身体保持得像运动员一样轻便”。而且,甘地在国大党内部会议上,表现得更像是不折不扣的精明政客,他善于运用煊赫的权威地位来压制反对的异见,甚至极度专制。对于决议的通过与否,甘地毫不受限,对制衡的权利或权力不屑一顾。再者,当他的妻子因急性支气管炎即将死于自己怀抱之时,甘地竟然拒绝英国特派飞机运来的青霉素治疗,因为甘地认为医疗注射是暴力行为,他要以拒绝的态度来维护自身的非暴力理念。结果,他用自己的非暴力简介地对妻子的生命进行了暴力掠夺。而甘地与他妻子之间,更是充满了家庭暴力,甚至禁欲之事也撇开妻子不与之商量。而据夏伊勒观察,甘地却与甘地的追随者玛德琳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晚年的甘地请求年轻女子与其裸体抱眠。多年来,甘地一直隐瞒与裸女抱睡的事情,直到后来才出来解释说,他如此为之,不过为了证明自己是否信守禁欲的誓言。
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向食盐进军”到几度被羁押,从办报到劝解民族团结,都是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也正是甘地这些作为,才塑造了圣雄的神话地位。但是,在印度皇家警察任职过的乔治·奥威尔,在《战时日记》一书中却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做出了另一番的解释。他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而使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更为容易,而非抗争带来压力,因为甘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争执的行动”。无论是英国对狱中甘地的宽容,还是对甘地的绝食作出让步,都是因为“英国官员担心他会死去,担心他会被某些不太相信‘心灵的力量’而更相信炮弹的人所取代”。虽然甘地自身非常诚实,但甘地也未能“觉察到自己正在被英国人利用,而他个人的诚实使他总是有用的”。
二战期间,德、日逼近,地缘政治发生巨变,美国也对英国施加强大压力。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工党政府取代了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长期的战乱使得英国陷入在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的泥淖。英国国内外都受到重创,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和资源使印度继续臣服于英国统治之下,工党首相决定放弃印度。这才是印度独立的主要原因,而非取决于甘地的抗争。而在权力交接期间,甘地作为圣雄,却怎么也无法以非暴力理念来缓解印度德里的暴力、暗杀、强奸等社会仇恨。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局限性?
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否可取,鲁迅曾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甘地是“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乔治·奥威尔更是在《论甘地》一文中设问:“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这正如徐贲所言,“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五):被夸大的甘地
被夸大的甘地
总有人痛心疾首地批评商业文明,认为它导致世人沉醉于物质享受而迷失自我,他们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学习甘地好榜样。朝圣者们,浩荡奔赴印度的各种精神修炼所,领略神秘的印度文化和甘地的心灵鸡汤,再回国发扬光大。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不管有多么复杂和专业,探索者一概以甘地语录自勉,在咀嚼大师智慧的同时被反复感动。
1925年到1932年期间,威廉•夏伊勒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负责欧洲、近东、印度的报道。他同情印度独立运动,与甘地交好,近半个世纪后,出版了一本对甘地的近距离观察细录。来自西方的眼睛,在东方的圣者身上,看到了不少荒诞与难以理喻。
甘地头上的光环,是远距离观察者想象的结果。事实上,甘地身上的抽象理念和浪漫精神,并未受到印度精英阶层的多少青睐。鉴于甘地所拥有的道义资源,他们一边不得不打着甘地的旗号,一边做着与甘地的构想相悖的事。若理性观察印度之现代化转型,却又不得不幸庆没有照听甘地的话,而是跟着尼赫鲁、安培多伽尔的路线走,印度才能有今日的崛起。
那么,甘地是救心丸,还是迷魂汤?
甘地的局限:反智
留英回来的甘地,对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看法完全是不合时宜。《印度自治》一书 阐述了他的建国和施政理念,不仅雷倒了夏伊勒这个外来者,也让国大党的其他领袖不以为然。夏伊勒回忆,作为接班人的尼赫鲁多次公开表达对甘地的恼怒,老头子又犯糊涂、又在装神弄鬼。
甘地对印度传统文化充满自豪感,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性,同时蔑视现代化。根据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的实质即西方文明是邪恶的,一个理想的印度大陆不应该有铁路 、工厂、军队等产物,医生和律师人数要尽可能少。与红色高棉的看法一样,城镇生活意味腐化,唯有乡村才是神圣的。三亿国民靠着非暴力、求真理这般抽象概念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非暴力精神并非甘地独创,而是来自印度教、耆那教。出身于刹帝利的甘地,身体力行地倡导取消贱民制,却希望保留剥夺人平等的种姓制,他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安分守旧。这自然让夏伊勒吃惊。
奠定建国方针的尼赫鲁,跟安培多伽尔站在一起,抗拒了甘地追随者要求建立村社统治制度,抛弃文官制、英式议会制、工业化的乌托邦诉求,他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国家。甘地眼中代表美德的苦行僧和乞丐,在尼赫鲁心目中是“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所以一句话概括,甘地的局限性在于他对现代化的抗拒,如鸵鸟将头埋进沙子。
在私德上,苦行僧、清教徒形象的甘地被人批评是愚蠢和荒淫。甘地为了他的非暴力信仰,认定皮下注射是暴力行为,拒绝让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的妻子注射青霉素,妻子遂病亡。父亲弥留之际,他贪图床榻之乐而错过了父亲断气的一刻,便终生自责不休,36岁时未与妻子商量就开始禁欲。晚年甘地宣称为了考验自己的禁欲毅力,与年轻貌美的多名女子裸身同寝,有一位还是侄孙之妻。双方都宣称没有发生任何事,但瓜田李下,任何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甘地为远离罪恶而食素,食物仍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精心制作。他穿的手工纺织的土布衣服,未必比工业化产品便宜。同时,身边簇拥众多的秘书和女仆,算上修行地的开销,都靠商人的慷慨资助。曾在他身边服务过的一个人说:“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中花费了不少金钱。”
甘地的成功:不可复制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何以能成功?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敌人。很幸运,甘地的对手是有宽容、公正制度的英国,这就足够了,其余的一切成功因素都是为了英国而配合的。
尽管甘地多次入狱,但都受到了当局的文明对待,在狱中有特权,更未受皮肉之苦和思想改造。自始至终,甘地都享受到基本权利,他始终是西方新闻界的宠儿,英国大众对他也是宽容的,即便是因他抵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
1931年,夏伊勒全程陪同了甘地的英国之行,近距离见证甘地受到的待遇。火车一到伦敦,就有数千名支持者来欢迎他,印度事务部的官员给他当司机,汽车刚到旅馆,即发现几百人伫立雨中等候,旅馆大厅里更是聚集了来自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新闻界的1500多人。除了在圆桌会上自由辩论外,他会见了从议员到纺织工人的各界人士,甚至以恢复棉布贸易来煽动英国工人向政府施压支持他。
在印度,甘地在内的国大党一直与英国保持亲密关系,随时和总督进行亲切交流,夫人们则和总督夫人对应联谊。两位英国法的律师甘地和尼赫鲁在骨子里都是热爱英国的,不列颠空战时,甘地说他为圣保罗大教堂遭到轰炸而感到极度悲哀;尼赫鲁在监狱囚室里保存着母校哈罗公学的照片,更何况他是费边社的铁杆粉丝。
内因上,甘地有极高的表演天赋。赤裸上身,腰上系一块土布,坐在一架小纺车面前,素食、禁欲、静修,他用东方元素装扮一身。在信息传播尚不够便捷的时代,遥远、神秘的东方大陆上所有一切事物都能吸引西方人。当西方看到一个风俗习惯、生理习性与自己不同迥异的东方人居然也能将普世价值参杂着玄学出口成章,当然是大为惊讶和欣喜。他还可以穿着缠腰布去见英皇乔治五世,在会议上能突然中断讨论,兀自做让英国人陌生的祈祷,高唱《薄伽梵歌》。
同时,甘地善于利用媒体,夏伊勒一接触甘地就意识到。除了使甘地个人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外,每一次非暴力行动都会由媒体来放大效应,如著名的向食盐行军活动成为与新闻界互动的大狂欢,之后进占达拉萨那盐厂行动更是在美国1350家媒体上刊登。
所以,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得很刻薄: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甘地背后:被光环遮蔽的力量
甘地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他是印度的立国精神之本,本土精神资源之一。许多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教诲,甘守贫穷;也有人将遗产提炼出“坚持原则、自我反省、劝人向善”这类修身养性的内容来吸纳。不过在民间,边疆的分离主义势力、纳萨尔武装分子、宗教仇杀以及种姓间的私刑从没消停过。如今的印度政府在面对有人效仿甘地绝食抗议时,会以强制鼻饲对付。
很多人写到甘地的时候,都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衣服血肉之躯。”保罗•约翰逊解释了时势何以造英雄:“甘地的怪癖对一个尊崇灵异的国家非常合适,但是他的主张对印度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
成稿于2012-07-20
《新京报》2012年7月28日
《甘地的武器:一个人的非暴力之路》
(美)威廉•夏伊勒 著
汪小英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6月版
相关阅读
《帝国斜阳》
(英)布赖恩•拉平 著
钱乘旦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4月版
印度独立史是本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印度是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
《告别甘地——现代印度的故事》
(瑞士)贝尔纳德•伊姆哈斯利 著
王宝印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4月版
欧洲记者沿着甘地的行踪一路走访,与基层人士交流。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
(英)爱德华•卢斯 著
张淑芬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英国记者、印度通笔下的印度社会,文笔幽默。
《印度史》
林承节 著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林承节是国内研究印度史的权威,尚有《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
《甘地的武器》读后感(六):圣雄甘地,大英帝国与非暴力不合作
一、暴力还是非暴力?
我朝官方的书上(中学教材提到了印度么?),关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传统见解是甘地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既要争取印度独立,又害怕唤醒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采取了这种斗争形式,而不是暴力革命。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总之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被用来证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居然在印度提什么“资产阶级”,还把甘地封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此只能呵呵了。
这正是甘地不遗余力地宣传"真理坚固",宣传"爱与非暴力",宣传"神即真理",宣传宗教和解的原因(之一)。他感到人们的宗教情感是难以放弃的,于是希望将“神”加以泛化,从一族一教的神,推广到普遍的神,希望人们上升到宗教的本质“爱、宽容与非暴力”。甘地时常表现出一种“印度教的固执”,固然与他深刻的宗教背景有关,然而,或许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亲近民众的方式;真正涉及到贱民问题等敏感议题时,他是从来不会执拗于宗教教义的。
甘地被尊为印度国父,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本质上,他失败了。印巴分治是非暴力的失败,是爱与真理的失败,是普世价值的失败。它暂时地被狭隘的宗教情绪和民族情绪给打败了。
仍然不会,不会忘记圣雄的那句话:“我相信,爱能战胜恨,非暴力能战胜暴力,由剑取得的,终将由剑失去。” 纵令失败,理想主义的光辉依然闪耀,虽败犹荣。
二、仁慈的大英帝国?
此外,国内一直有一种见解,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所谓“英印政府的文明、法制与进步”。至少,在中国,甘地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迅哥儿就曾经讽刺道“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就毫无成效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甘地如果在中国的狱中绝食抗议,在鲁迅看来,结局一定会是这样:“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Ibid.)”
相反地,人们往往要把大英帝国吹嘘一番,说它如何“文明、法制”,以此来反衬“某些国家”。下面可以引用一段文字来说明这种普遍的看法:
”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不管对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毕竟是有规则可循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被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而不是一旦拖出牢房,就被割断喉管;甚至他也可能被判除死刑,但在枪杀之前,绝对没有人敢把他的肾强行挖去,枪杀之后,也没有人敢收他家属的子弹费。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实际上倒是殖民政府的司法部门越来越不希望甘地被收监,因为多一次收监,就意味着多一次审判;多一次审判,就意味着甘地的“非暴力”技术多一次宣传。“非暴力”运动能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取得成功,并由这位熟悉英美宪政体制,而且在英国的大学里读出法学博士的甘地来领导,绝对不是偶然。 “
然而读过夏伊勒的报道,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对于英印政府的民主法治,多少是一种附会和误解。固然,在当时,英国甚至印度的法治环境比中国要好,但也并非某些人吹嘘的那样完备。个人以为,英印政府之所以面对甘地表现出克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甘地太有名了。一旦甘地死亡或者”失踪“,不仅英国在国际上要背负巨大的舆论压力,而且更现实的,很有可能引起印度的动乱。 而甘地刚好是”非暴力运动“的提倡者,例如乔里乔拉袭警事件发生之后,甘地就感到运动超出了非暴力的限度,而自行停止了运动。留下甘地,英国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控制住印度,而甘地一死,英国人恐怕就要面临三亿暴徒了。
不错,1922年艾哈迈达巴德的審判,的确是按照正规程序由地方法院法官主持的公审,检察长提起公诉,记者在场。但我敢说,英印政府之所以敢于公审甘地,只是因为轻视了这个人。之前甘地领导的运动也一直是”非暴力“的,客观上具有对英印政府的迷惑作用,以为他没什么能量。直到公审上甘地的申辩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被全印度、甚至全世界广为传颂,英印政府才知道悔之晚矣。
于是到了8年之后的食盐进军,甘地于1930年第二次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英印政府直接依据1827年东印度公司宣布的第35条法案,未加審判地监禁了甘地——虽说还是“有法可依”,但依据这种东印度公司时代留下的莫名其妙的法令,依法监禁和非法监禁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什么“多一次收监,就意味着多一次审判;多一次审判,就意味着甘地的“非暴力”技术多一次宣传。”这种论调,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以后的历次收监甘地,没有一次经过了審判。然而,英国人不可能杀死甘地。他已经太有名望了。如果他们不想让全国都变成乔里乔拉,那就只能客客气气地对他,印度总督欧文男爵亲自跟他谈判,签署了《德里协定》,还要邀请他到伦敦参加圆桌会议。
英国人当真不想杀死甘地?1942年甘地因为第四次复出领导“退出印度”运动而被捕时,丘吉尔就指示英印政府说,如果甘地要绝食,就让他饿死。可是,英国人毕竟不敢这么做。来自印度总督和各方的压力压得丘吉尔这样的强人,也不得不同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甘地最好还是死在监狱外面”。丘吉尔只会在伦敦发脾气,抽着雪茄纸上谈兵,印度总督才明白,一旦甘地死在监狱里,整个印度都会沸腾。
可见,这绝不是什么“民主法治”,这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大法官”来搞什么“违宪审查”,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考量。
事实上,我以为甘地看准了这一点。甘地是个精明的政客,这千真万确。他完全利用了这一点。他说,英国的几千万人不可能统治印度的三亿人。在伦敦的圆桌会议上,他也反复指出了大英帝国的外强中干。他也知道英国人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他背后有着三亿印度人。甘地的国大党和英印政府,配合着维持着印度的稳定,又在这种配合中相互角力,相互争取利益。但至少,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印度的稳定。英印政府当然希望维持印度的稳定和非暴力,而甘地也这样希望——这原因在前文已解释过了。
不必说什么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只有在大英帝国的“民主法治”的土壤上才能结果。大英帝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回印度——并不是以法律为框架,而是以印度的稳定为框架。英国和甘地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也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了解甘地,这位圣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