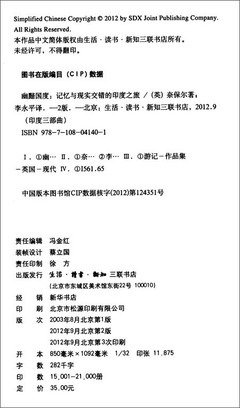
《印度之行》是一本由[英国] E. M. 福斯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 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20元,页数:4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印度之行》精选点评:
●210♛ 本来我还以为是作者的游记,原来是小说啊...不过被殖民的国家国民真的卑微可怜,甚至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男主已经是医生了】,殖民者都是绅士淑女别傻了...就因为一个英国女人的幻觉就可以判定一个印度人强奸,要脱罪只能英国女人承认自己幻想...
●致D。它合适的出现了......刚好也很大!
●要看多少印度相关我才敢真正提起勇气去印度呢
●还看过电影 我喜欢福斯特的小说
●本来被印度的神秘所吸引,可这本小说深奥的内涵把我搞晕了!
●不是一般的好.
●看得出这本书的价值。我还是太浅薄,喜欢他那些普通男女间的故事……
●殖民文学
●整本书就如结尾印度教的祭祀活动一样,喧闹、浑沌、神秘
●大一读过,记得这本书很有趣呢~
《印度之行》读后感(一):这本书写的挺好的
这本书写的挺好的 很真实。反应了印度的另一面。印度QQ高级群133142428。 印度的服饰 印度的歌舞还有印度电影都给我非常深刻的映像。我们在可能不是很了解印度,通过这本书,大家可以了解印度的另外一方面。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印度走走看看。印度同中国一样,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感受一下印度当代的风情。让你体验不同的人生!
《印度之行》读后感(二):印度之行
对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观点来说,一类显然是吉卜林,认为这是大英帝国的光荣,给殖民地带来了文明(《吉姆》);另一类应该就是奥威尔(《缅甸岁月》)。那么究竟是怎么样呢?要是以前我可能会说奥威尔的更“正确”,因为我毕竟是个半殖民地的后代。但看完此书后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没错,但都偏颇了。东方人(书中是印度,我则是中国)的思想如同戈德博尔教授:一切皆可能是,也可能是否,根本没有标准。而西方人则是就是,否就是否。东方人生活在混沌之中,周而复始,如果不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恐怕永远固守僵化。但西方文明过于功利。两者都优缺共存,倒是能够融合,兼容并包才是未来之福。从此点来看,福斯特要比奥威尔更深邃些。
作品以一个看似荒诞但又完全现实的“案件”为线,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印度人阿齐兹邀请两个英国人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去山洞游览。在黑暗的山洞中,阿德拉小姐感觉似乎有人侮辱了她。于是阿齐兹先生被捕了。故事就此展开了。
故事内容倒是其次,文章通过故事阐述的思想非常有意思。那黑暗的山洞非常类似于东方的混沌思想。而阿德拉小姐的幻觉倒是很具有西方文明的特征(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这场荒诞的官司中,东西方人的表现带有着鲜明的各自思想特征。
此书内容相当值得深思。
《印度之行》读后感(三):印度之行
E.M. Forster 英美文学史上不输于海明威,毛姆,也是一样畅销作家。 他的《印度之行》也被拍成了电影,场面恢弘,角度精妙,是展现印度风情的绝好窗口,个人感觉和《甘地传》同看, 可以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风貌了解较深了。 而这本书至今也还是印度大学里面文学课程的重要篇目,现在Youtude上一搜一大堆印度老师讲解其中段落情节。 书的情节其实倒也简单,剧透都无妨。 就是两个英国女士,一老一少,结伴到英国殖民地下的印度来找未婚夫,认识当地热情的本地医生和校长两个朋友,结伴同游。 但是其中引起了重大误会,后虽然得以和解,却没能拉近英/印两个种族的隔阂。 一番波折之后,带着对于印度似懂非懂的感悟,女主人公回去了英国,印度族群和英国统治者越走越远。 由于故事的背景就设置在英国统治印度末期,而福斯特也是两次前往印度,所以小说的主线其实落在了印度族群和英国统治者之间, 以及印度内部各族群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之上。 在每一分部的开篇,都会有一章是提纲挈领的景色描写,英文言简意赅,中文也翻译出神入化,读下来恨不得抄一遍。 幸运凑巧,刚在二手书店淘到89年出版的硬皮版本,对照中英文读来之后,非常佩服译者的功力。 唯一的缺点就是电子书的通病,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把注释直接做个链接?本来举手之劳,真搞不懂。
《印度之行》读后感(四):无政府主义的分野之行
《印度之行》不愧于福斯特最有传世影响的小说,在保留传统式的情节走向叙述和外部世界的宏观描写的同时,角色内心世界描写的分量大大加重,并大量地辅之以象征手法。因此有不少人把《印度之行》视为现代主义和现实小说之间的过渡品。其实无论什么殖民政治文学还是什么前现代化的过渡品都是别人扣的帽子。整篇小说的精髓依然是福斯特一直在探讨的人际关系问题。而小说真正是有“殖民”而无“政治”的。即便代表本土精英的阿齐兹多次与英国教授菲尔丁争论印度出路,也只是在个体公民在爱国问题的左右倾斜上浅尝辄止罢了。文中登场人物,无论贫富贵贱、白皮黑发,更像是超脱出政府管制的自由份子。他们不关心军事暴动带来革命,也不受制于国家机器的运作。警察局长时常在口中叨念着如何惩罚印度贫/平民,但是对于该行为无论是其施动者还是受动者,小说从来没有正面描述过。相反,担负起社会运行角色的人,反倒是制度之外的当地居民们,他们以自己千百年来固有的生活模式与评判标准使社会运作起来,被隔绝在印度之外的,反倒是那群远道而来的英裔人。即便阿齐兹的入狱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结果,但警察从立案到逮捕,我们不能感受丝毫标准化操作程序的存在,唯一的一次法庭审判更像是一出闹剧。
这里原因有二,其一,是在于印度的特殊语境,19世纪初的印度,还处于前法治化时期,与风俗道德相比,在不少社会生活领域,法律还显得苍白无力;与社区自发组织相比,暴力机器还不能扫除犄角处的余尘。“他(阿齐兹)的习俗是属于社会的,只要社会没有发现你违反规范,那就是你没有给社会带来危害,因为只有当社会看到你违反规范的时候,你猜算有危害社会的行为。”诸如此类舆论力量胜过法律法规的描述,文中还有很多,这也就并不出奇了。
其二,福斯特本就是信奉审美为上的原则,追求自由平等,用格兰斯顿的话就是“艺术美的研究和人际关系的培育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因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都坚信并依赖自己的内心直觉和美德,并且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对国家机器有种天生的反感。阿德拉刚走下海船,踏上印度的土地时就对早一步侵入印度,敌视印度人并且想要以此为模板教化所有后来人的英国人提高了警惕,行文至半时,更是干脆让她自己开口讲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很善良,也不很坚强,我要靠这些去和我的环境对抗,去避免成为她们一类的人。我有不少很严重的缺点。这就是我喜欢阿克巴尔‘普遍宗教’的原因,也就是说我要继续保持我清白和明智的本性。”
另外一方面,福斯特对政治并不积极热心,这决定了他无法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出超前的政治构想和斗争纲领,自然也就无法赋予小说这个里世界中人物任何提纲挈领,又何况《印度之行》本来也不是为政治或泛政治化而作?1914年的印度,还没有出现甘地,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使反抗外敌过于虚幻只得流于空谈。所以即便福斯特旅居印度多时,也无法从现实中收集到有关反殖民的革命斗争素材。
像上文提到的,在福斯特的小说中,他历来的探索方向都是指向人与周围人事、世界的联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冒险遇到了各色宗教的掺杂其间,并且把话语的分析放置在了一个不同源也不同质的跨文化情境里。虽然小说存在时间流动,但是基本的叙事框架是不变的——与生机一片的热带气候不相协调的萧索破败的殖民大陆和各种教派相互箕斗的宗教国家。由此引发的混乱是必定的。世间本无善与恶,混沌与秩序才是永恒。当混乱出现时,人们自然就想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观,一条定理,一种秩序。
讲到形而上的哲学对人的影响,自然离不开宗教对人的洗礼。宗教给信徒设定一种抽象秩序。秩序的本源是官能感受到的世界,最后却返回来赋予这个世界以能动活力。印度是个实实在在的宗教国家,大不列颠的民众历来也有信仰耶稣的传统,当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不期而遇,更像是一场传教宣演的比试,最后谁能获得胜利?为此,小说给三大宗教各安排了一个象征代表,穆尔夫人、阿齐兹和戈德波尔分别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最后三个角色各自的结局使作者的感情趋向不言自明。
仁义宽厚的穆尔夫人无法认同混乱不安印度大陆。异域多元化的宗教存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路历史传说与文化艺术鳞次栉比都使信仰一神论、追求绝对知觉而不容失序的穆尔夫人无所适从,产生信仰危机,仓皇而逃出印度只是以否定自我所见来追怀遗失的精神信仰。一意孤行、不合时宜的航海计划更像是回归天父的举措。
分野的最后一位代表,印度教的戈德波尔则是关注轮回,忽略现世。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花大量篇幅来写印度教祭祀活动。通篇充斥着喧哗与混乱,是一种与寻常生活状态相异的行为模式。人们欢庆爱神黑天的降临,却浑然不知领主早已病死的真相,更让这场狂欢变得无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印度教更像是印度本身的代表——混乱繁芜,让人不得要领。
在宗教分野之外,还存有本国与他国的对抗。阿齐兹确信印度的发展不需要英国的参与,就算客观上后者带来了先进的器物与制度,并打碎了印度本身的桎梏。而菲尔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封建制度下的必然衰败和西方人工和理性的必要性。这次在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分歧。两位挚友几经决裂,在最后重归于好,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分道扬镳。他们试图寻在一个使朋友平等交流的秩序,使两国和睦相处的秩序。然后这是一次讽刺性的寻找,无论是个人关系的还是国家群体的,也无论是借助宗教冥想还是理性思维。任一一方,都无法圆满。
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忠诚?福斯特在读《神曲》时曾发问过,是但丁把贝娅特丽丝描写为从天国下凡的天使,还是李尔王把缢死的三女儿科迪莉亚抱在怀中?对小说中的忠诚而言,是阿齐兹的“国家利益过于个人”,还是菲尔丁的左翼的、犬儒的爱国主义?这种认识的混乱就是终极,应该如何消除,小说并未能给出答案。就像小说结尾那样。
“如果我们摆脱你们,需要五千五百年,那么我们就用这五千五百年,我们将把每个该死的英国人都统统赶到大海里去,到那时候”——阿齐兹骑在马上飞快靠近菲尔丁——“到那时候”,他轻轻吻了菲尔丁一下,做结论似的说:“我和你一定会成为朋友。”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成为朋友呢?”菲尔丁满怀深情地抓着阿齐兹的手说,“这是我的愿望,也是你的愿望。”
然而他们的坐骑并没有这种愿望——他们会转向各奔东西,大地没有这种愿望,它在路上布下重岩,使他们不能并辔而行;他们走出山谷的时候,脚下的茂城一览无遗;那些寺庙,那个大湖,那个监狱,那个神殿,那些飞鸟,那个兵营,那个宾馆,所有这一切它们都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你们现在还不能成为朋友!”苍天也在呼叫:“不,你们在这儿不能成为朋友”
一场畅游印度的旅行,到头来成为了作者以印度为舞台,向人们展示宗教、文化的分野。
《印度之行》读后感(五):印度•文本•旅行家
秋高气爽的日子总让人骚骚然生起一股拔脚往外跑的冲动。你看那外面的世界:“突然一阵微风,微弱而温热,充满了奇花异木芳香的暖风,由夜色的静谧中扑面而来……它费解,又沉溺,就像被施了巫术,就像在你耳边窃窃私语,向你许下了未知而神秘的乐趣。”一个世纪前约瑟夫•康拉德展现的异域诱惑,又何尝不在向当代的背包客们频频招手?只是这“未知而神秘”的靡靡之音,在不同人听来便是各具意味的回声,或聒噪或幽寂,或玄响或深沉。手头几本游记书,即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关于游客,关于世界,关于如何行走与观察的记述。其中有小说也有随笔,事涉印度又不全然是印度,因为在地缘政治与文化传统之外,我们分明看到记录者们的特立独行与其笔下的异质文明一样丰富多彩。
守规矩的游客和不守规矩的“土著”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05)为我们树立了关于游客的最佳典型。在印度的寺庙、河流、田野和火车站,到处都有怀揣着相机拍个不停的外国游客。他们相信所见即真实,于是便有“坏心”的印度警察或城管欺负贫弱的本地小孩,好心又愚蠢的美国夫妇施以援手的一幕。对踏上这片土地的观光客而言,探索异域文明的特出之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而于这片土地上世代居住的人来说,活下去才是王道,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如何在观光客面前“表演”的艺术。“表演”正是一个仰望着世界“强势”民族的相对“弱小”的民族的本能反应,你尽可一掷千金邀得满堂喝彩,也可满地打滚作摇尾乞怜状,而个中缘由只为作此“表演”的民族心领神会,至于模范游客,则只当是精彩纷呈的异域情调而成为其相册中千百珍藏中的一帧,过目即可忘怀。
因此,我对那些不太守规矩的“土著”打心眼里抱持好感。他们往游客身上抛掷垃圾(奉劝他不要做模范游客),或者在自己人脸上打上一拳(破坏他的表演欲),意在给游客展示一个真实的国度。《白老虎》(2008)的叙事人向即将踏上印度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写信,以一天一封共七封的“攻势”揭露印度近二十年的进步“神话”,将印度传统文化中“未知而神秘”的一面统统剥除,甚至连《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金元的叮当声响也剔除殆尽。叙事人把活生生的日常性端出来,几乎直贴客人们的眼睛:喏,这才是你们应该看到的。《白老虎》向游客们提出一个颇诡异的问题:我们在给乞讨的小孩一个美元的时候,是否应该感到一种内疚?简言之,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们能否介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个人的伦理道德,而又不伤及他人的自尊(遑论他国的主权)?我们能不能在“游心”与“良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徘徊在“游心”与“良心”间的异质文明
其实早在《印度之行》(1924)中,E.M.福斯特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白老虎》是一个印度草根以一种尽量不妄自菲薄的姿态写给中国总理的旅游指南,那么《印度之行》则是若干英国知识分子试图以“平视”之姿检视印度文明的寓言之书。两书堪可对照的一点便是叙事角度上的“装”,在前者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张声势,在后者则是对待不及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刻意尊重。《印度之行》的故事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游客与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之间。在“山洞”事件发生之前,这两类人在一种近乎甜腻腻的友好状态中交游;而在事件发生后,旅游主题中客人与主人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质变——英国女孩指控印度男士侮辱了她,而这纯粹出自这个女孩的臆想。何以发生这种臆想?或者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追问:在黑乎乎的山洞中,为什么英国女孩一口咬定是这位印度男士侮辱了她?
游记记录一种认识的过程
福斯特看破了人们在对待异质文明上的暧昧态度。而V.S.奈保尔则一点也不含糊,他在1962年甫一踏上孟买时便苛刻“印度人还没有学会漂白新闻纸。”在“印度三部曲”第一部《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1964)中,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以令人咂舌的毒辣描写了印度的贫困与丑陋,嘲笑中印冲突中印度的全面败北。咋看之下这仿佛是猎奇的游客的循香逐臭之举,实则是有着印度血液的外来客在寻根过程中的纠结与失望。奈保尔令人激赏的一点在于他洞察了其所寄生的“高等文明”的脆弱性,同时亦没有拔高与之相对的“低等文明”的道德优越感,在他看来,牛津剑桥的高材生与他家乡特立尼达中学里的同胞一样“愚蠢”,而支撑父辈们“保持正常心态”的印度传统文明早已分崩离析。在随后的《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1990)中,奈保尔继续其融历史与当下的印度书写,只是年少时的轻狂为一种更为深沉的风格所取代,他对印度所作的冷酷的现实批判在在隐含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爱恨交织的饱满情感。这种对异质文明既贴近又疏离的观察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最优秀的旅行家。
尽管硕果累累,但奈保尔对异质文明的朝圣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他无法在自己的内心与印度的现实之间搭起一座能使之在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上回归的桥梁。这一目的倒是在无任何印度背景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身上奇迹般地“达成”了。在她的《在印度》(2011)中,一个执着于“内心一直存在的某种清洗和过滤的愿望”的游客,惊叹于印度的历史是如此辉煌,现实是如此烂漫,“这些看起来贫穷日常的人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优美和优雅”。可以讲,她把我们再次拉回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关于异质文明的滥情而又苍白的叙述。这一情况发生在一个中国作家身上堪称怪异。究其根本,正是“小资”的自得其乐与浅薄的认知使她的印度之行始终立足于一种封闭的视域之内。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更无涉“平视”,而是一种“无视”,使你没办法对其眼中的世界下任何判断,因她的眼中根本没有世界。
伊塔洛•卡尔维诺曾说:“游记是一种有益,不起眼但完整的文学……虽然世界日新月异,但正因如此,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保留的是其多变的本质,而且传达出的不止是对眼前实景的描述,而是你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一种认识的过程。”当世界为安妮宝贝这样的模范游客所充斥之时,我们便要为有像奈保尔、福斯特这样的旅行家,以及如“白老虎”那般不安分的存在而感到庆幸,他们所勾织的关于旅行的文本大大扩展了这个因技术、资金和全球化而浓缩成“地球村”的世界,让人对安妮宝贝赞为童叟无欺的印度机场旅游宣传品之外的天地,心生无限向往。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维卡斯•斯瓦鲁普著 作家出版社2009年3月
《白老虎》[印度]阿拉文德•阿迪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
《印度之行》[英国]E.M.福斯特著 译林出版社2003年5月
“印度三部曲”[英国]V.S.奈保尔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8月
《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
《印度:受伤的文明》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在印度》(刊于《大方》No.2)安妮宝贝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