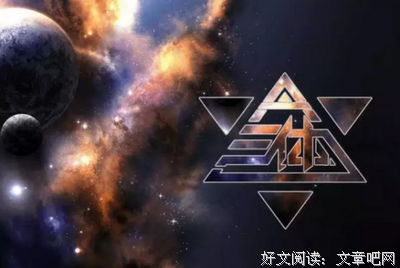《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由张典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8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一):太平轮 一九四九
太平轮是什么样的船?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两千零五十吨。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个月七千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开始航行于上海、基隆间Ⅲ。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间,客船、货船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公司当年已有两艘定期船只往返上海、基隆。一是华联轮,为一九○七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另一艘安联轮为加拿大制造的商船。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启航,投入上海与基隆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最后一班,共计行驶了三十五个航班。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是在同年秋日过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选,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二):一個倒掉的世代
每一個世代的倒掉,具有象徵意義的並不只是君主自縛、銜璧出降,更多的是屬於舊時代的一群具體人在生理意義上的倒掉,迴響出舊時代本身的喪鐘聲。
太平輪的悲劇便是這樣一種倒掉的體現。紅旗插上總統府的那一刻,天安門廣場升起五星紅旗的那一刻,蔣中正座機降落台北機場的那一刻,都不如太平輪的沉沒具有的象徵意義濃厚。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七日的那艘船上,搭載著舊時代的典型知識份子、士紳、商賈和官員,這些人擠在超載的輪船上本身就已經昭示著舊時代末期、昔日榮光全都被打碎堆放的夕陽光景。舟山海域的沉船,帶走的是一個世代的身份認同、一個世代的價值觀念和一個世代的生活方式。自此以後,中國再無士紳,再無知識份子,再無舊式商賈。
一個世代的消逝,具體人肉體上的消滅,往往是最好的註腳。
多到随便弄出来一点点就会让你的眼泪掉光的地步。所以,太平轮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场悲剧,而是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我是在《巨流河》看到太平轮的描述,加上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印象,加起来促使我在单位一楼的中信开的书屋里,用八折的价格买下了这本书。
花了几天的零碎时间读完,发现里面讲的大部分人与事其实和一九四九年沉没事件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因为那会儿幸存下来的人太少了,而逝者的家属多半不愿再回首那沉痛的往事,种种原因吧。
书中也有令人快乐的颜色,那就是吴金兰的故事,在一本充满了沉重压抑的书里,给人一点点温暖的感觉。也有令人泪下的悲惨遭遇,那就是黄似兰的故事,亲情在这里也失去了效力,整个世界都是漠然的黑色,但是故事的结尾还是好的。
总之这本书是一本受众范围很小的书,我们从打分者和书评的人数上能看的出来,区区二百多不到三百的打分和22条书评,少的可怜。按理说,这种书与《巨流河》有相通之处,都是台湾情结,都是悲惨遭遇,然而由于一段经历和一个事件的区别,有了不同的关注度。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四):完全不亚于泰坦尼克号。
这个学期开学,朋友隆重介绍了《太平轮1949》,在她的介绍和一些段落剧透中,我已觉得是本好书。现在离开学校,刚把网上所能找到的文看完了(有人吐奶没上船后面一点),是今年以来的读书中,除了《废都》最爱看的书。回学校之后会借书看完。
历史本就比任何小说都惊心动魄,这应该是个常识,而把历史事件费劲心思地整理还原,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辛苦过程。我曾读《为历史流眼泪》而被伊拉克战争虐得内伤,这次的太平轮,虽然作者文风平实克制,娓娓道来,很不夸张,但这些真实的故事已经够让我学到很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属于“开卷有益”类的读书。这样的书的作者也分外令人尊敬。虽然,很能理解也很遗憾的,这种书注定不会和一些快餐书一样红。
我们都很爱电影《泰坦尼克号》,爱情,亲情,人性的光辉和丑恶是一出最经典的悲剧,而中国的太平轮,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书中采访当事人,整理出来的故事,丝毫不比电影逊色,人生百态,有时候令人唏嘘,有时候令人悲伤,有时候又令人庆幸。
在这艘船上,除了直接遇难的乘客,还有政府、两党、商人、义士……他们纷纷出场,国难飘摇中的一艘悲剧的沉船,足够上演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看完此书,我觉得最触目惊心的句子居然是那句“怀素的字也在船上!”
这本书至少不会让头脑简单不谙世事的读者更加愚蠢,它直接告诉了众人沉船的遇难各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为了加紧运输财富不顾超载,船员为了消费不断放人,事情发生之时,救人性命的救生艇居然不能也不允许被放下……而出事之后,世道的艰难更是可见一斑——保险公司推卸责任,公司倒闭赔偿不多,国民党征用民船之后撒手不管……
这本书还看得出人生百态——出生的船上的小太平被一个老奶奶的剪刀救了一命。妻离子散中的丈夫还在木板上捞起其他落水的乘客。善于游泳的哥哥遇难了,不会游泳的妹妹却侥幸活命。许多人不愿意上木板,怕太重了大家都沉下去,宁可在冰冷的海水中沉浮。国人同胞的船见死不救,澳大利亚的船只觉给了大家最人道的待遇。附近的岛屿上的人民连夜组织救援,而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这是一场悲剧,这是无疑的。但作者娓娓道来,非常克制,这也是我非常尊崇的笔者的立场,一位作者,如果不懂得在行文中克制自己的感情,那他就不算好作者。
德艺双馨的父亲遇害了,失去家庭和至亲们的女儿一生继承父亲遗志,辛勤育人,笔者也只是用那挂着遗像放着钢琴的屋子里仿佛流淌出阵阵琴声,好像父亲没有离去这种淡淡的句子一笔带过。而大难不死的人虽然百种无一,但万幸大部分都有后福,太平妈妈每次被孩子气得够呛的时候,会骂人都怪你当时吐奶,如果当时沉船了,就一了百了了!还是很有暖色的。
哀而不伤,这是对历史悲剧最应该有的态度之一。
再浅显的人,读完此书之后,也会有一点基本的收获——船超载了不要坐,出事了不要大意,迅速准备救生工具,遇见可以帮助的人要帮助,投保要找靠谱的保险公司等等。
这就是好书带给人的教益。
我想我很难忘却这艘太平轮了。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五):太平轮
说来惭愧,第一次知道太平轮还是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当时,齐邦媛的“惊骇悲痛”四字和那艘没能靠岸的轮船,就都深深烙上我心头。
幸运的是,三联不久又出版了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在这本书中,张典婉用扎实的采访和丰富的资料向世人展示了太平轮的时代背景、沉船事件始末、还生者的自述、死难者家人的命运因之发生的改变以及曾经乘坐过太平轮的人们的点滴追忆。
太平轮的故事与“太平”毫不沾边,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载的都是离散和逃亡。1949年1月27日,它从上海启程去基隆。当天是旧历除夕前夜,全船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多少人盘算着搭乘这一班船去台湾与亲人团聚。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刻,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两船相继沉没,近千人丧生。太平轮永远未能靠岸。
如果是和平年代,太平轮沉船会引发多少世人多少关注多少眼泪呢?可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每个人似乎都自顾不暇,在太平轮船难事件审理期间,海峡两岸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不久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在时代的急剧震荡中,这次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可是和沉船事件相关的人,悲伤却是永恒的。船难让多少人从此孑然一生,半生孤苦,让多少家庭破碎,孤儿寡母失去生活的依靠。因为母亲在太平轮沉船事件中遇难,7岁的黄似兰如同从天堂掉入地狱,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即使六十年过去,回忆起童年丧母的辛酸,她仍然止不住流泪。
即使是这次船难的幸存者,伴随着他们也是永恒的阴影。担任军职的陈金星和葛克是幸运的还生者,他们都在船难中失去了妻子和儿女,两人在台湾恰好住在附近,几十年来,每到周末,他们都在葛克家中,默默对望,几乎不说一句话,直到天色暗下来。
读着《太平轮一九四九》,我无数次留下眼泪,也无数次想起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在庞大的国家面前,渺小个人的生死哀乐是那么无足轻重。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书写者都只记得宏大叙事。充满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1949,本是被泪水浸透的一年,可关于1949年的官方历史却总是一片胜利在望的喜气洋洋。
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折射。我想,当权者哪天能把目光和研究重心投向历史大事件中普通人的坎坷命运,或许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才能懂得给予普通人真正的尊重和权利吧。
最初听说“太平轮”,是听说吴宇森要拍一部新片,主角就是这太平轮,奈何几度搁浅。好奇的去粗浅的了解了一下大概就是说“太平轮是中国的泰坦尼克号”,哦,一艘沉船的故事啊,吴宇森不要把它弄成了翻拍的中国版泰坦尼克号就好。却不知泰坦尼克号满载的是美国梦,沉下去的令人唏嘘的爱情。而中国的这艘太平轮满载的是对生的向往,沉下去的是希望和梦想。
“他們聽說,台灣四季如春,物產豐隆,於是許多人變賣家產、攜家帶眷,擠上這艘航向南方的船舶,尋找一生的太平歲月......”
偶然间读到了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才真正解开了我心头对于“太平轮”的疑惑。也让我深受撼动。知晓是因为吴宇森,感动却是因为张典婉。
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运行在上海——基隆的一班货轮。
初读这个名字——太平轮。我暗自猜测,所谓太平,是当时那个动乱年代对安定和平的一种向往。就像是小时候,蹲在地上,一手猜丁壳,一手执木棍,赢的就可画一笔,最终先完成“天下太平”的为胜利。许多孩子还不会写别的字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包含了多少先辈的血与泪,从心底更深处发出的渴望,世代相传。
天公不作美,事与愿违。十分遗憾的是,从它投入运行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它波澜不息的命运。作为运输货轮度过了十分艰难的那段二战岁月,转眼,却又深陷内战的漩涡,。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上海到基隆,由大陆到台湾,乱世没有时间好等。它载过政客名流,载过撤退的国军士兵,载过底层的老百姓,载过的更多的是对于宁静祥的日子的希望。
太平轮,太平轮,它上所承载最多的,是向往太平。
翻开本书,起初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相关记载,报纸杂志,涉事人员的口述,分析太平轮失事原因,从而谨慎的列出种种可能:超载,晚点,船员疏忽,为了躲避“敌人”不能开灯……看起来偶然的事情,在他背后都有着必然性。而太平轮背后的必然因素就是——战争。太平轮事件是时代的悲剧,是战争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
在浏览器搜索“太平轮遇难者”,相对具体的答案无非是“太平轮随船遇难的众多旅客中,各界名流众多。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等国民党政要均在该船;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也在这艘船……”这类。他们仿佛离我们很远,再华丽的名声,如今也只剩一声叹息:不愧被称作“黄金轮”,单不说上面有多少财宝,只看这些人才也足以担得起“黄金”之称了。而最常见的往往是用一个数字就概括了的——1000多人遇难。在后世的旁观者看来,再怎么震惊,也只是一个冰冷冷的数字。让我们唏嘘的也只有人命卑微,天道无常。
但是直到看到张典婉把每一个能找到的幸存者,每一个能找到其家属的受难者的相关故事,一一记录下来,真实的再现在读者面前。我才真正的感受到,那白纸黑字是由人命堆砌而成的。那1000多人汇成的血与泪浸染了东海,那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不再是一个个无甚人知的名字,而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们满怀憧憬的经历千辛万苦的挤上了这条船,海的那端有着等他们回去共度佳节的家人,曾经的苦难与低迷都已经抛却在了身后,而前方是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期望。
看着书中对于活下来的幸存者的采访,发觉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领域都是十分成功的。最初,我觉得这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使其经受苦难的洗礼。但是当看到那位一直坚持着跑马拉松的叶伦明老人,我才意识到,他们成功的动力,不单单是生的愿望,更多的是死的责任。那位老人说:我要为他们奔跑。只要奔跑就觉得肉体、心灵都满足,也从不感觉孤独。
看着这些幸运的人儿的故事,心中无限慰藉。但这份好心情却在看到后面更多的遇难者家属的回忆录时回归沉重。被命运眷顾的人总是极少数的,而更多的则是那些不幸的人,那长眠于东海的人。书中无数次描写到,在基隆的港口,或是各家的家门口,或者是旅店未熄的灯下……等待乘船从大陆归来一起吃年夜饭的父亲,或者是新婚的丈夫,或是年富力强的儿子……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同样的心情——盼归。无情的海水淹没的这一切,所有的爱与希望都化作了台湾海峡的泡沫。
文中触动人心的不止一处,而令我潸然泪下的是一位遇难者的女儿的一句话“人皆有父母,为何我独无?”我以身为人女的感情体验去尝试着理解她,但我发现不能够,面对这令人崩溃而又无从宣泄的情感,我只能远观,只能同情再同情,祝福再祝福。逝者已逝,徒留活着的人从内心不断地涌出无尽的思念和泪水。
看完《太平轮一九四九》我满腔感慨,却无从诉说,总怕拿起笔,除了泪水和叹息写不出别的东西。书中出现过得每一个太平轮的乘客,有记载的所有太平轮的乘客,没有记载的却上了太平轮的乘客,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书,每条生命都是一个传奇。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七):好没分量,失望至极
太平轮1949,这本是一个多么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坐标。
太多太多的悲喜交加、生死离别,以及国仇家恨,处在那么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大幕下,它就是一个旷世的悲剧传奇。自然,它其中也隐藏着太多的无法言说的隐衷与哀痛。
因《巨流河》读它,带着相当的期待。但作为作者同行,窃以为,倘若看作一篇报道,这无疑是相当失败的案例,离及格都差了很大一截。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全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一部分。其中对太平轮的基本背景,出事时的详细状况、事发原因、现场情形等相关情况有大概介绍。郁闷的是,从中不仅看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佐证资料,且作者的采访量明显不够,导致文中既缺乏有力的文字史料,又见不到可以补述的细节,最明显的漏洞是,从头至尾我都没看到太平轮的出身。
作者也说,有关这段历史的可查记载,实在寥寥无几。但既然要做这个工作,当然不能仅仅从资料室抄那么一点可考之事,嚼嚼现饭而已,多少得花点精力,做点独特的贡献吧。
其次,书中90%的文字为人物采访。用新闻行业的俗语来说,这部分内容,根本没有拿到核心材料,即处于漩涡最中心的一手素材。
所有的采访对象中,与太平轮失事事件离得最近的,是第一个采访对象叶老伯,依然健在的事件亲历者。作者也明白他的重要性,可惜的是,这一段描述,与我们日常见诸报章的一篇普通人物通讯无甚差别。现状当然要讲,但我们的主题是1949年的太平轮哦亲。哦,花费80%的篇幅粗粗地写写叶伯的现在,到了关键的部分,就简单一句“不想说”“不愿讲”,你当这是给交代你任务的领导汇报呢?
写不出来核心事实,或者拿不到一手事实,那绝对是当记者的水平不够,突破能力不够达不到哦。对领导,尚可有理由解释一番;对掏钱买单的读者,这样应付一下,着实不地道。
至于其他采访对象,基本可以不说了。印象中,有极少几个受害者的父母、兄弟等直系亲属,有两个未曾谋面的受害者的遗腹子,几位自身经历较坎坷的后代,以及几位只和太平轮有关而与1949无关的普通人,作者绝大部分文字都在概述他们的人生,但,他们与太平轮的交集,实在是没有几毫米关系。因为采访对象集体情绪的疏离,作者的文字也显得十分生涩,当然也感染不了读者,生生浪费了一个好题材。
大概是对这个厚重的题材抱有太大的期待和好奇,这本书让我失望都很彻底。这么一次失败的尝试结果,若是有同行竞争非得如期刊出,那尚可理解;而时隔60载,若是真正用心去做,怎么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空空洞洞,又何苦要匆匆以此面目示人?
我想,掏钱看此书的,大概都是奔着“太平轮1949” 这场悲剧本身而来吧。其实,这几个字,这无端消逝的近千个生命,以及不计其数的人世悲欢,也的确值得你我永远带着敬意,去好好阅读。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八):乱世之下的“太平”一念
《滚滚红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既非三毛执笔,也非影射张爱玲,而是那场残兵溃将,与无数肩担手提的民众困作一处,蜂拥抢路,怆然上船,相形之下,林青霞和秦汉的松手再是凄然又如何,因为被裹胁其中的每一个人无不如此地深陷绝望,根本就无高下之分。
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起航,往来上海与台湾之间。一九四九年,它成为运输撤退军民到台湾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一九四九年除夕前夜,太平轮与另一艘轮船相撞,导致近千人丧生,最后仅几十人脱难。太平轮沉没事件这些年来即便有少许报章提及,也是被迅速地湮没在那些猎奇的旧事当中,直到台湾女作家张典婉捧出了一本《太平轮一九四九》,成了书,至少这回它就是不会再被轻易地遗忘了。
众说纷纭之下,导致这场灾难的致命原因仍未有定论,而太平轮却确定无疑而又不幸地成为彼时乱世之下命运之手用以展现人间悲惨的典型道具,太平轮上空笼罩的绝望与忐忑如影随形,如蛆附骨,直至命运当真地就使出翻云覆雨手,无数活生生的人顿时就化作冤魂亡灵。
很自然地,太平轮总会被联想到泰坦尼克,其实,又何苦要和后者拉上关系,借后者之名?彼时彼刻,一方是气势如虹,即将描绘美丽新世界,另一方是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太平轮自身难保,又岂能撑起“太平”二字?和极尽奢华、扬帆起航的泰坦尼克又有哪点相似之处?
据说,吴宇森曾想拍“太平”轮事件,却因种种原因搁浅。如若真要拍出来,会不会又是一部卡梅隆的《泰坦尼克》,编一段虚幻的爱情,重现一番沉船场面,但这样的场面越是逼真,就越反而显得背后炉火纯青的电影技术的趾高气扬,对灾难的一味模仿,对人的忽视。
叶明伦被救起后重回大陆,与已到台北的妻子音信两隔,妻子后来重嫁,他为此仍是无法释怀;陈金星与葛克同为生还者,都是一样地失去了妻子儿女。“每到周末,这二位生死与共的朋友,总是默默地对望,直到天色已暗”;陈金星后娶了小姨子为终身伴侣,每到妻子祭日,总会为她烧上几件新衣服,因为在船上曾经答应过妻子到了台湾,过新年要为她添买新衣;童年似小公主般被父母宠爱有加的黄似兰的人生更是如过山车,母亲遇难后,她又被从台湾送回大陆争家产,这一去就是直到几十年后才得以离开……
书中,对遇难的孩童用的是“他们都来不及长大”的字眼;生还者记得老人劝说的话语是“乱世没有时间好等”;有人要从这个改变一生的事件起写回忆录,却被儿子劝阻,“会把眼睛哭瞎呀”;更多的却是不愿意陈述太多当年往事,宁愿沉默着把它们带进另一个世界。
《太平轮一九四九》展现的是惨剧过后,对幸存者余生的追踪,太平轮事件在幸存者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更是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也恰恰比单纯描述沉船事有了更为悲烈的内涵。太平轮上的乘客,在这艘小小的商轮上有了一个小小的交集,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而这一次却是齐齐没顶,在一阵巨大的漩涡之后,江面重又恢复平静,只剩无数漂浮的行李和生还者哀哀哭声。再看到如今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人做成公仔站在一起,更是生起无数感慨。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九):太平轮1949:永远无法靠岸的船
如果没有当年安全抵达的太平轮,世上也许没有张典婉,如果没有当年沉没在海底的太平轮,世上也许没有张典婉的这本书。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于张典婉来说显得有些复杂,从未见过太平轮的张典婉,却听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听“厌”了关于太平轮的故事的张典婉,若没有在某一日偶然看到母亲的几件凝淀着对家乡对过往的留恋与思念的遗物,怕是也不会花费10年时间,忍受着许多直接或是委婉的拒绝,忍受着有心的或是无心的白眼,忍受着响亮的或是低声的呵斥,把那个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太平轮的故事一点点从早已将其湮埋的历史尘埃中挖出来,甚至试图用“水”冲干净,让世人知道,在60年前,因为一场内战,还有一群屈死的亡魂和一群虽然幸存但人生轨迹却被完全改变的人们。
张典婉要讲述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太平轮,其实不太平,因为即使是在出事之前,这艘承担从大陆运载乘客与货物赴台湾的货轮,每天也是在一个不太平的年岁里往返上海与基隆之间,每天勾画的也是离散与逃亡的图景,然后终于在那一天,搭载着那个班次的乘客与货物沉没在舟山海域,上千条生命随着这铁壳的大船,被海水埋葬在冰冷的海底。这一埋就超过了60年。
西历1949年1月27日,农历小年夜,其时解放军的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政府”已经是风中残烛,飘摇的时局使得“国统区”的人们惶惶终日,上海外滩的十六铺码头上,那艘搭载着1000多名急切的要离开大陆奔向台湾的包括政要富商名流以及普通百姓在内的乘客的铁壳船就要出发。
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能赶上这班船,或用权势或用关系,更多的是用金条,谋得了一张他们认为是奔向自由的船票,在很多人心中,这次登船,何尝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
这场与命运的赌博以人们的失败而结束,后者输掉了他们最后的赌本,像是一个绝情的玩笑,这艘载着1000多名旅客和许多货物严重超载的铁壳船,尽管曾经幸运地熬过了二战,这一次却未能打败那艘与它迎面开来的运煤船,剧烈地碰撞之后,太平轮在舟山海域沉没,此时距离它离开上海码头,只不过几个小时。
故事情节的太快转换,让很多人无法承受,他们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入深海,永远没有机会活着踏上台湾的土地,也再不能回到大陆家乡。
而幸存的30多人,从海难发生到现在,他们用了超过60年的时间来告诉自己,一切都已经改变。
在漫长的60年中,集体记忆随着太平轮的沉没而沉入历史的深海,被掌握话语权的人们有意无意的忘记,但是罹难者的愁苦,他们亲属的悲哀,幸存者的伤痛,却不会像出事那天的海上的雾一样在天亮之后便消散,用60年来抚平伤痛,显然远远不够,在太长的一段岁月中,他们在各自的角落里舔舐着历史留给自己的伤口。
政治家们眼中的两岸分治,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教科书上的一段话,但是之于构成这历史的最微末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尽头的离散与数不清的哀愁。
对于当年迁徙到台湾的几百万“逃难者”来说,太平轮是他们也许未曾经历过的旅程,却也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当年它常常停靠的码头已经从地图上消失,而成为繁华城市的一部分,曾经报道过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报纸也早已被封闭,想要查阅它们,只得到图书馆或者档案馆里去,先用手抹去收藏它们的纸夹子上落着的历史的灰尘。
超过60年过去,这历史的灰尘已经沉落得太多,人们已经开始习惯用“旧事”来为那场海难定性。
但是作为历史的一叶,张典婉不相信太平轮的故事已经结束,因为历史不是一页纸不是一张画不是一段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大人物小人物的实实在在的悲欢离合,即便不再写在他们的脸上,也一定深埋在他们的心底。只是已经不习惯在人前谈起,独坐的时候,总会想起往事念起故人。
张典婉开始行动,她要把这些人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以记录那一代人的流亡历史,于是有了《太平轮1949》。
张典婉透过各种管道寻找当年海难的幸存者与罹难者家属,把他们的故事拍进镜头里写进书里。尽管当年他们或者他们的亲属舍得花金条购买船票,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们都算不上多么“大”的人物,甚至都算不上成功,当年一掷千金的豪举,在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孤注一掷的赌博。
张典婉坚持认为即便是小人物,即便从空中俯视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被淹没,但是仍旧不能被轻易地遗漏,因为他们是真实的存在,而历史的洪流也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各自命运汇聚而成。“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她说。
沉船事故发生之前的一个月,张典婉后来的养母搭乘太平轮平安抵达台湾,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随身携带一只皮箱,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即便后来嫁入一户客家人,尽管后来过着并不优渥的生活,这个曾经的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在上海时的生活习惯,穿旗袍,自己制作吐司配红茶,用白纱布代替煮咖啡时“缺席”的滤纸,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这些已经韶华远逝的老太太们穿着旗袍,用吴侬软语轻唱“夜上海”,当年在南部乡下生活时,她会与同样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坐人力三轮车到镇子上的电影院去看《魂断蓝桥》,偌大的影院中只有她们两个观众,俨然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的专场,而她们两个看到伤心处,便就在影院中,抱头痛哭。养母喜欢讲太平轮,丝毫不理会张典婉对这个听过无数次的故事的厌烦,直到养母去世,张典婉才渐渐明白,母亲与同伴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曾经的生活,纪念那段历史。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说自己当时跌坐在地上痛哭失声,之后便决定搜寻太平轮,搜寻那些与太平轮一起沉没的家族故事,而这些的最终目的,是讲述那一代人的离散与流亡。
张典婉往返于大陆、香港与台湾,流连于图书馆档案馆,只为了找到关于太平轮的更多线索,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而罹难者的亲属们想也多是高龄,张典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只为了收集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张典婉一直说自己有贵人相助,寻访的过程中,每次遇到山穷水尽,最后总会有柳暗花明,她甚至在一家餐馆偶遇到当年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经在大陆的一家档案馆翻到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而这被遗忘了60年的档案中有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在她寻访到的那些故事中,最多的是关于等待与改变。
上海小姑娘黄似兰8岁的时候与母亲短暂分离被提前送到台湾,1949年春节,她欢天喜地地等着渡海过来寻她一起过年的母亲,结果等到的却是母亲罹难的消息。
之后的黄似兰目睹的便是家族中最丑恶的争产闹剧,黄似兰被亲属们送回大陆并留居于此。
黄似兰去台湾之前曾经在上海有着快乐的童年,在一张照片中,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但是幸福随着母亲与太平轮一起沉入海底,被送回大陆的黄似兰日后遭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
一场海难改变了黄似兰的生活,从云端跌到谷底,人生际遇的改变成了那次海难带给每一个当事人最大的人生烙印。
王兆兰还记得母亲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抓好妹妹”。家道殷实的王兆兰跟随母亲与弟弟妹妹一起到台湾与父亲团圆,为了能够早一天见到丈夫,母亲买到了太平轮的船票, 几十年后,王兆兰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当年16岁的少年已经满头银发,当年因为祖父的重男轻女而从未念过书的王兆兰在台北与周美菁、吕秀莲成为校友,尽管已经坚强并勇敢地度过了大半生,王兆兰讲起当年太平轮上发生的事情,仍旧像是一个情感失控的少女,双手捂住脸,痛哭失声。
太平轮上1000多名乘客,哪一个不是黄似兰,哪一个不是王兆兰呢,他们在登上那艘开向死亡的永远靠不了岸的太平轮时,心里一定有些许恐惧,因为不远处已传来枪炮声,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期望与想象。他们以为自己要去的真的是“宝岛”台湾,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将蹈入死亡之海。
1949年的那次与太平轮有关的海难,改变了1000多人的命运,使得比1000这个数字更多的人的心永远无法靠岸。
《太平轮一九四九》读后感(十):《太平轮1949》:无法停泊的船,无处安放的心
电影《太平轮》的上映,引起了众人对发生在1949年的“太平轮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为一本早已出版的书赢得了一波回顾——《太平轮1949》。
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大约是在一年前,也许只是被太平轮“沉默的黄金船”、“东方的铁达尼”所吸引,或者是期待着战火纷飞里的旷世爱情。读完这本书,默默的放弃了这样的揣测——在这样的一个关于生命的叙述里,还有什么不会变得无足轻重?
公元1948年12月,上海的富家女司马秀媛乘太平轮离开上海,驶向台湾。一个月后,小年夜,这艘太平轮在黑暗的海上与另一艘建元轮相撞,乘客沉入了冰冷刺骨的海水——千余乘客仅生还36人。而上海小姐司马秀媛,正是本书作者张典婉的母亲。
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巧合——如果司马小姐早登船,还会不会有张典婉?如果没有张典婉,还会不会有《太平轮1949》?如果没有《太平轮1949》,“太平轮事件”还会不会重见天日?
会的。历史一直都在,只是时间早晚或记忆深浅的区别了。若干年后,身世的浮沉,山河的破碎,民族的伤痕也许都化为茶余饭后的谈笑。是的,太平轮上,有文件国宝,故宫的珍玩,中央银行的机要文件,东南日报社的全套设备;太平轮上,有名流绅士,他们有高级将领,有省主席,有国大代表,与蒋经国的好友……但太平轮上,更多的是用仅余的金条换来一张船票,进行一场命运的赌博,期待一段真正的太平年月。
太平轮沉没六十余年后,张典婉奔波于海峡两岸,国内国外,只为寻找到当年太平轮事件的亲历者,还原1949年,那个真实的黑夜。
王兆兰,和母亲弟妹登上太平轮时16岁。巨轮沉没,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抓好妹妹”,但她没有做到。
黄似兰,8岁时被送往台湾,等待着小年夜与前往台湾的母亲团圆。年仅8岁的女童,满怀的欣喜等来的是母亲罹难的噩耗。
叶明伦,往返于上海台湾,贩卖羊毛。登上太平轮与台湾的妻子会和。落水获救后,只身回到老家,后辗转到香港。再未回到台湾,再未见到妻子——妻子早已改嫁。叶伦明终生未再娶。
……
还有,郑家小小的婴儿因吐奶而让母亲放弃了已买好的船票,这个婴儿就是学者郑培凯;李家年幼的男童因父亲的罹难而失去了原本优渥的生活,被迫去警校读书,后来他成为了国际刑侦专家,他叫李昌钰;49年,22岁的李国深仓促间未能登上太平轮,后来,因其在佛学上的造诣,被称为“星云大师”。
……
“爱或不爱,幸或不幸,命运,哪里说得清?”张典婉如是说。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荡气回肠的别离。天地间,唯有冰冷的海水里绝望的哀嚎,和渐渐沉入海底前迷茫而不甘的眼神。
张爱玲妙笔,可以倾一城以成全两个人的爱情。那么,那些因倾城而破碎的家庭呢?那些因倾城而永诀的亲人呢?那些因倾城而消陨的生命呢?在宏大叙事的视角下,传奇、伟人、英雄激荡着历史的洪流,但那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确是由平凡的生民的命运构成——正如漆黑的天幕,明星闪耀。但明星虽耀,那永恒不息却仍旧是无垠的夜空。
我喜欢这本书。纪实风格,语言平稳克制。除却开篇介绍太平轮事件始末,终其全书,再没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人物——也许他们的故事破碎、惨淡,但是,这就是一场内战蹂躏过后的真实历史,这就是去国离乡只求太平的真实历史,这就是动荡年代一个人的真实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人类的坚毅、勇敢和男子汉气魄,就非得在血肉飞溅中熔铸不可吗?战争结束了,正义胜利了。但就人类而言,没有胜者。”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的话。心惊。20世纪的中国,19世纪的中国,上下五千年烽火不曾熄的中国。无穷无尽的离乱,成就了什么?毁灭了什么?也许这艘沉入深海的太平轮和那些无声的遗骨最有发言权。但他们都沉默了。只等待时光为他们做永恒的弥撒。
2010年5月25日,两岸61年来首次合祭在太平轮沉没的舟山外海举行。相关记录片上,鲜花被洒向深海。年迈的王兆兰哭倒在丈夫怀里,跪在甲板上,读着写给母亲、弟弟、妹妹的信;叶伦明,几十年来坚持马拉松,90岁的人,干干瘦瘦,还满口“我还能跑”。他说,“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在书中,看到幸存者李述文撰写的《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文章最后,只留了一句:“征集下联 太平洋上太平轮不太平”刹时,心凉如海。希望这样的下联,永远无法对出。
季子平安否?
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
记不起,从前杯酒。
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