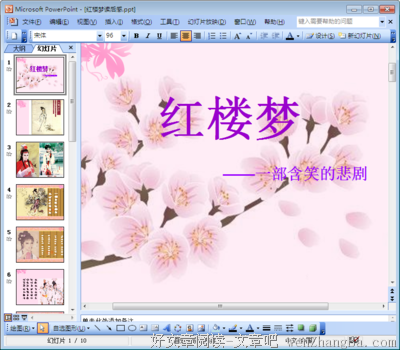《项狄传》是一本由(英)劳伦斯·斯特恩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68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项狄传》读后感(一):乱发牢骚:当我们读项狄传的时候,我们在读什么
在经受整整一个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狂轰滥炸后,十九世纪如托马斯·哈代,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古典小说大师的魅力已经渐渐被小布尔乔亚文艺青年们常挂在嘴边的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奈保尔、雷蒙德·卡佛、普鲁斯特、卡夫卡等名字取代,更不用说作为小说先驱的十八、十六世纪的塞万提斯、拉伯雷和薄伽丘了。然而,同为早期小说家的劳伦斯·斯特恩,却在两百多年后与意识流、现代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炫目名词扯上了关系。当我们在读《项狄传》的时候,我们在读什么?
当一本小说跟相隔了两百年时光的一大堆晦涩名词牵扯到一起,那是对它的赞誉还是误读呢?它的作者该作何感想?
在一个小说艺术还刚刚起步的阶段,当“小说”还未成型,还未发展成一个博大的文学领域时,跟拉伯雷一样,斯特恩写小说只为了愉悦自己。然而,在追求快乐这条道路上,斯特恩走得更放肆,更随心所欲。他不按顺序铺展故事,随意穿插冗长啰嗦的长篇大论,信马由缰放纵自己的笔东扯西扯,甚至专门画图来说明小说的情节进展,“从道德上来说,”随处出现的黑页、引文、各种特别符号,让《项狄传》完全脱离了严肃的文学作品范畴,成了他的信手涂鸦。
然而这种玩乐和涂鸦不是人人都作的。斯特恩博闻强识,涉足历史、军事、地理、生理学、美术、音乐、哲学、伦理学多个领域,同时他行文的功力也实在高超。这本“涂鸦”而成的巨著所囊括的方面和知识之丰富广大令人咋舌。
这本小说最令我欣赏的是,斯特恩玩世不恭的态度,它闲扯一般的行文风格,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和气息,当你读多了严肃的大部头名著后再看《项狄传》,你一定会惊讶,一本小说能写得这么儿戏,这么随意,这是与后来的小说迥乎不同的轻盈潇洒而幽默诙谐的清新气味。它让我耳目一新。而这种混乱,跟现代小说故意装出的混乱相比,自然率性,真正富有魅力。这时我才理解昆德拉在《巨人传》里感受到的古代小说的幽默魅力。
事实上此时居住在英格兰乡间的斯特恩正是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和消遣,他以每年两卷的速度写书,就是把他当成了他的长期爱好。这本书也成了他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和名利的工具,他把它送给著名歌手和政要,请他们推荐,待小说大卖,自己便吃喝嫖赌,坐享其成。斯特恩是一个最不像小说家的小说家。
就是这么一部信手涂鸦而成的小说,这么一个闹着玩的作者,竟被后世尊为现代小说先驱,维基百科更称《项狄传》“意识流的始祖”。无独有偶,《堂吉诃德》也被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人们这类头衔加之十八、十七世纪的早期小说竟毫不觉得别扭,我只能说文学艺术已经陷进了现代的圈套里了。在这些概念充斥着的评论分析里,我看不到我在原著中感受到的那种随意幽默的魅力。二十世纪以后,当人们读一部小说,谈论一部小说,似乎就只能用上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手法来填塞,当一部小说还没有这一切的头衔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无话可说了。法国大学毕业论文涉足最多的是普鲁斯特,显然《追忆似水流年》有太多的头衔和主义可以谈论,随便抽出个“意识流”、“潜意识”、“弗洛伊德个亨利·柏格森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就足够写长篇大论了。可对巴尔扎克,对司汤达,我们还有这么多话可说,那么多概念可填满一篇论文吗?更不用说拉伯雷的时代了。因此,面对斯特恩混乱随意的文字觉得语塞一时的评论家们,不假思索地找上了现代小说衍生出的“意识流”、“结构现实主义”、“心理分析”、“时空交错”这些概念。因为只有在这些华丽的概念里,我们才觉得舒服和熟悉,才能在这些概念上建构对一部小说的分析。
作者用怎样的态度写,读者就应用怎样的态度读。
这是现代病。从二十世纪开始,艺术就开始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创作艺术,先要创作宣言。象征主义宣言,达达主义宣言,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复调小说,原样派荒诞派,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新小说,文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流派。于是,抽掉主义的虚架子,文学就似乎变得无比空虚。不仅是文学,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不论是绘画上的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至上主义,还是音乐上的现代主义表现主义,我们被各种主义轰炸了一个世纪,以至于透过一个世纪的屏障回望十八、十七世纪的小说时,我们发现这些语汇都无法用上,于是不可避免的无话可说。
二十世纪的艺术,已经成了主义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家的艺术。艺术的本质被不断的定义再定义,最终沦为形式下的奴隶。后现代艺术在把自己套进晦涩的概念的同时,也越来越为难着读者。曾几何时,使人读不懂已经成为了一部优秀小说的必备素质。二十世纪的文学看似热闹非凡,但真要论水平,其实不及十九世纪的托翁、司汤达、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师们。二十世纪以后,艺术已经日渐式微。对主义的过分强调,艺术其实在走向穷途末路。
当我们在读《项狄传》的时候,我们是在读小说,还是在读主义?
昆德拉讲拉伯雷,什么主义也不套,单讲一个词:“幽默”。
不可否认塞万提斯对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等作家有巨大影响,而斯特恩也对伍尔夫夫人,对意识流,对现代艺术有巨大影响。它们都是如此高超的作品,塞万提斯和斯特恩是文学大师,他们必定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人们能从他们的作品里寻到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结构现实主义的味道和手法,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就足够高超,足够宏大。你能从中发掘出无数的东西。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把概念强加进一部小说的理由。把一件二十世纪的大衣给十八世纪散发着自然活力的少女穿上,就会变得无比蹩脚。
当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你欣赏的是艺术,不是主义。
《项狄传》读后感(二):转: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从巴赫金的体裁诗学看斯特恩的《项狄传》
作者:蔡熙【内容提要】
文章以巴赫金的体裁诗学为理论视角,从体裁面具、讽刺性模拟,杂语性、小说性等四个方面探析了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在文本领域里的革命性创新。它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以及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放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成分,从而革新了审美趣味。
【关键词】
体裁诗学; 体裁面具; 讽刺性模拟; 杂语性; 小说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S·伯特在《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将18世纪爱尔兰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ence Stern,1743-1768)列入其中。尽管他在该书序言中声明,这个排行榜不排除主观成分,但他为斯特恩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杰出人物进入最令人敬仰的文学伟人行列而感到高兴。当代走红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把《项狄传》(全称《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纳入欧洲最伟大的小说行列之中,认为其写作的无序性,散漫的没有主题却具有复调性质的文本,实在是成了西方小说朝意识流方向发展的源泉宝库。确实,250年前的斯特恩就展开了小说写作技巧的革命,他那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堪称“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
俄国著名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明确指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体裁诗学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1] 他一贯重视文学体裁,认为文学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诗学“应从体裁出发,因为体裁是整个作品整个言谈的典型形式。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2]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主要是作为文学体裁的传统产生影响的。狂欢化小说最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小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体裁,它能利用其修辞和体裁上的异质性颠覆居统治地位的体裁观念。本文拟从体裁诗学角度探讨《项狄传》在文本领域的创新及其颠覆意义。
一 体裁面具——傻子、愚人形象
在巴赫金看来,小丑、傻瓜、愚人形象是狂欢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形象,这种与民间创作有深刻联系但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却常遭鄙夷的“怪人形象”却是具有世界性的形象。研究这类形象才是小说史极为重要和最为有趣的任务。愚钝“既有贬低和毁灭这种否定性因素,又有更新和真理这种肯定性因素。愚钝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这是官方的统治性真理的反面和下部。愚钝首先表现为对官方世界诸种法规和程式的不理解和背离,同样也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关怀和严肃性。”[3]
在《项狄传》中,斯特恩选择了一群疯疯癫癫的人物(不包括特里斯舛),搭起舞台让他们对话与表演。脱庇(Toby)叔叔是一个腹股受了伤的退股军官,他有着成年人的嗜好,要喝酒,要抽烟斗。但却那么愚钝,幼稚,不谙世务,连男女之情都茫然无知,一天到晚只知道在滚木球场操演自己经历过的战役。他是天真、蒙昧、厚道、善良、诚挚单纯的原型,之于哈姆莱特是优柔寡断的原型一样。脱庇叔叔的仆人——下士特灵(Corporal Trim),可谓是他的影子。特灵同样愚钝,他之于脱庇,一如桑丘之于堂吉诃德。为了布置战场,他把主人的长统靴改造成了大炮。如果说脱庇叔叔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那么我的父亲瓦尔特·项狄(walter Shandy)则生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他学究气十足地试图以种种假设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却全然不顾现实和常识。他那关于特里斯舛的出生,关于鼻子和名字的宏论被现实戳穿后,他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讽刺意味。以傻子、愚人的眼光看世界,能使日常世界陌生化。这类形象以其无私的天真和忠厚,以亵渎偶象和神灵的咒语,使文本话语摆脱了高调的令人窒息的重压,摆脱了僵死而又虚伪的语调,使话语变得轻松幽默起来,并且使形象趋于多义,一如象征,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阐释可能性。诚如巴赫金所言,“人的史诗般的完整性在小说中瓦解,人向另外的路线方向发展,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特征出现重大的不协调。”[4]
二 讽刺性模拟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小说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最重要的小说典范及其变体都是在讽刺性模拟地摧毁先前的小说世界的过程中创建的。”他还指出,“所有这些对各种体裁和体裁风格(即不同语言)的讽刺性模拟,都属于嘲笑各种直接的严肃话语(包括所有体裁的变体)的语言形式”[5]。所谓讽刺性模拟,就是把一个人嘴上的话通过另一个人之口说出来,内容依旧,但语气和语调却迥乎不同。讽刺性模拟的语言和叙述带有双重倾向,含有两种声音,且话语里的两种声音明争暗斗,从而造成涵义的“一体双身”。也就是说,作者对本体和讽拟体二者的关系不直接诉诸于文字,不加阐释评论,靠读者自己去玩味,去领味作者的孤心苦旨,调动读者的艺术想象去填充文本的艺术空白。
斯特恩被称之为“英国的拉伯雷”,他创作《项狄传》的本意是“通过嘲讽那些我认为值得嘲讽的事——或者有损严谨学问的东西,为世人做件善事,我将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拉进来,再用笑声使他们甩掉自己的荒唐。”因此,该书充满了讽刺性模拟。其手法大致如下:
(一) 拉伯雷式的双关语
当了21年神职人员的斯特恩谙熟爱尔兰诙谐的民间文学,他又博览了欧洲文学,因此,常运用语言的双关性,大做文字游戏,并且喜欢暗涉肉体的不登大雅的玩笑,如hobby-horse(游戏木马)在俚语中指妓女,鼻子既与拉丁文中“智慧”一词的词根相近,又暗指男性生殖器,Parts有角色的意思,也指两个城市的淫乱。另外,衣裙叉口,黄油面包,祛火方法,绿长袍,旧帽子都有双关意义。再如,“走”字,报丧的信送到项狄宅,托庇先看了信,说鲍博“他走了”,但正在研究地图思考大儿子出国旅行的瓦尔特·项狄却以为托庇在说他上路了,于是两人就“走”字牛头不对马嘴地扯了一大通。这些双关语的涵义是“一体双身”的,即具有双重声音,二重指向。诚如伊瑟尔所说,《项狄传》中的双关语以触目的方式把“被排除在外的生活从幕后推到了理想的前脸上来。”[6]
(二) 降格
降格指的是在话语或叙述中巧妙地沟通身外那些崇高与卑俗的联系,使崇高降低为卑俗,卑俗上升为崇高,昭示出狂欢式的亵渎不敬,对神圣之物的讽刺性模拟。在《项狄传》中,小说的叙述人兼主人公对重要而“严肃”的事物,如生死,宗教机构,种种学问和理论体系,一概加以嬉戏嘲弄。“在这个世界上机智和判断从来不会合为一体的;它们可是天差地远,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儿——洛克是这样说的——我说,就像打嗝和放屁一样不同”,这里把“推理”等同于“放屁”,既辛辣又有调侃的味道。相反,对鼻子,胡须之类的东西却采取貌似郑重的态度长篇大论地阐述,冠之以“精神象征”,“讽喻含义”,“神学讨论”。对下士特灵的议论推重之至,对他的演说姿势描绘尽致。柯勒律治认为这是“让渺小成伟大,伟大变渺小,使两者都被贬损。”[7]
斯特恩尽管自称是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继承人,但与后二者相比却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把讽刺的锋芒对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而斯特恩从未涉足重大的思想上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弊端。他嘲弄的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已经过时的经院式的思维模式。因此他的讽刺不是出于对世界的一种蔑视,也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出于对生活中滑稽可笑现象的敏感和警觉。所以,斯特恩只是把嘲弄无聊的思想观念——荒谬本身当作目的,而且《项狄传》的文字更显得轻佻,更富于“游戏”意味。
三 杂语性
在巴赫金那里,史诗话语只是单一的作者话语,史诗人物缺乏语言创造性,而小说却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部的。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小说,即最具有小说性的小说是杂语小说。杂语小说是从社会杂语的深处进入的,它抨击独白式的高雅语言以展示其喜剧性,它利用杂语合奏自己的思想;它讽刺性地模拟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语言和高雅的体裁,对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语言表示怀疑。因此,杂语小说更能体现小说的本质特点。
通观《项狄传》,斯特恩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组织社会杂语,以折射自己的创作意图的。
(一) 语言杂交
为艺术目的而有意识地杂交是塑造文学形象最主要的艺术手段之一。巴赫金说,语言杂交“这是指在一个表述范围内混杂两种社会语言,让由时代或社会差别(或兼而有之)划分的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个表述的舞台上相遇。”[8]在《项狄传》中,作者故意混杂了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谚语、、模棱两可的俏皮话、短暂用语、塞万提斯式的语气、拉伯雷式的双关语,还有许多自创的幽默的词语,如按发音拼写出一个让人作呕的拉丁名字福大托利呜斯(phutatorius)来丑化一个人物,有时把拉丁语和英语的音节拼贴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库纳斯托洛鸠斯(kunastrokius),有时又将英语词音译为拉丁词,如齐撒溲斯(kysarcius)等。斯特恩让不同的语言众声喧哗,互相交锋,从而使单一的语言土崩瓦解。
(二)插入不同的体裁
巴赫金指出,“原则上,任何体裁都能包容在小说结构里”。《项狄传》可以说是包容诸种小说结构成分的典范之作。这里有古代文体,如希腊文,拉丁文,有布道文,有演说,有献辞,有放肆的故事。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插入了大量的非文学体裁,如第一卷第20章关于分娩的医学知识,有对绘画理论绘画历史的介绍,提到了大量的艺术艺术述评批评标准,罗列了很多艺术大师及其作品,还有对音乐知识的介绍,混杂了传记、历史、政治学、神学、哲学和军事著作。总之,五花八门的知识被斯特恩饶有兴趣地混杂其间。但是插入非文学体裁不是为了使之“高雅”,具有文学性,而恰恰是为了它的非文学性,为了使非文学语言进入小说的殿堂,使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相互指涉,以一种新的关系彼此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难怪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说,“在艺术史中,遗产不是从父亲传到儿子,而是从叔父传到侄子”。他强调了对非文学体裁的兼收并蓄是小说创新的源泉。在这方面,斯特恩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简而言之,杂语性使平常难以兼容的因素合到一起,消弭一切界限,使各种文本相互渗透,各种语言众声喧哗,平等对话,使小说文本永远具有开放性。
四 小说性
巴赫金认为,小说不仅是一种文体,而且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力量,他称之为“小说性”。小说性具有巨大的颠覆力量,能瓦解和动摇官方的、形而上学的一元权威和话语霸权。因为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反规范的。按照巴赫金的说法,《项狄传》是一部极具“小说性”的小说。
《项狄传》问世之初,虽给作者带来了荣誉和喝彩,被认为是特大的文学奇迹之一,但在不友好的评论家那里,《项狄传》只不过是低级下流与多愁善感的混合液,安放在古怪而又有悖常理的艺术形式里。沃浦尔(Horace Walpole)认为它平淡乏味,戈尔德斯密斯(Oliver,Goldsmith)认为它粗俗、唐突、空洞。理查森认为它跑题、不连贯、不得体。大文学家兼词曲家约翰逊博士特别强调“没有什么怪胎会长期存活,《项狄传》没有生命力。”[9]萨克雷指责斯特恩是一个懦弱、虚伪的约瑟夫·瑟菲斯(谢立丹的喜剧《造谣学校》里的伪君子),一个“不中用的老流氓——自负——险恶——诙谐——虚伪。” 斯特恩虽然是个风流才子,然而他之所以赢得了不友好的评价甚至于恶意的攻击,是因为他的小说《项狄传》具有“小说性”,在于他那对传统小说具有颠覆性的挑战。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的起步较晚,它的历史比史诗、诗歌、戏剧要短得多,到18世纪才初步成型。没想到《克拉丽萨》和《汤姆·琼斯》问世才十来年,这种尚处于幼稚状态的新文学样式让斯特恩来了一个地毯式的讽刺模拟,给掀了个地朝天。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验,《项狄传》展示了以下独到之处:
(一)新颖的版面设计
书中不时出现黑页(第1卷)、白页(第9卷36章)和各种图解,大量的星号,无数的破折号,任意的标点符号和半截的断句,整段整页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合常规的斜体字和黑体字,有的段落全是大写字母,有的段落全是小写字母。
(二)琐碎
在《项狄传》里,我们绝难发现习以为常的戏剧情节,讲述者固执地抵制了条理化的事件组成线索分明的情节,有的只是主人公枝枝节节、妨碍小说向前发展的一页又一页矛盾而又含糊的胡话。斯特恩把斯威夫特的“琐事万岁”变成了自己的写作口号。
(三)精心策划的题外话
第三卷写到特里斯舛的鼻子受伤,叙述由鼻子而一发不可收拾。从项狄家祖父祖母的婚事开始,到瓦尔特从“精神象征和讽喻含义”的层次探讨伊拉斯谟谈鼻子的拉丁文句(第三卷37章),第四卷引入一长段关于陌生人鼻子的寓言故事。再如关于脱屁叔叔和苍蝇的题外话等,也是如此。他的手法是在人物的联合观念中加入自己的话语。斯特恩似乎对题外话情有独钟。第一卷的22章可以说是题外话的专论。“题外话就是阳光——它们是阅读的生命,灵魂。”
(四)古怪的时间顺序
18世纪的英国小说在笛福、理查森、菲尔丁的笔下按时间顺序展开叙事,经渭分明。这一传统在《项狄传》里给颠了个个儿。作者前言在第三卷20章,献辞于第一卷第八章才出现,小说结尾讲的是项狄家庭一伙人的闲谈,与标题毫无关联。收束全书的是约里克牧师一段半开玩笑的话,但该牧师早在第一卷第七章就已经死去。该书题名为《特里斯舛·项狄先生的生平与见解》,但对项狄的描述既无生平亦无见解,直到第四卷他才出生,此时全书已近一半。小说大部分讲述的是别人——他父亲、叔叔、特灵等人的言行和姿态。斯特恩不是从出生开始,而是根据人的意识组合原则来结构小说的。显然,这是对人们已经习惯的过于条理化的18世纪英国小说的抵制,昭示了斯特恩对理性的挑战,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
理性曾是人类的一束启蒙之光,在战胜蒙昧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理性并非万能,它扼杀创造潜力,窒息蓬勃的生机和自由。因此,斯特恩受到传统捍卫者的中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上所述,《项狄传》从四个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叙事实验,颠覆了亚里斯多德、布瓦洛等人奠定的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摒弃了条理化结构故事的方法,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自由的写作风格,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脱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笔调,从而革新了文学趣味,在文本领域制造了一场文学革命。斯特恩是地地道道的“文本领域里的罗宾汉”。文学评论家巴巴拉·哈代指出,“称职的作家在其选定的体裁范围内工作,而伟大的作家改造文学体裁。”[9]用这句话来指称斯特恩是恰如其分的。
参考文献:
[1] [俄]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8.
[2] [俄] 巴赫金.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方法[M].李凡辉,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174.
[3] [俄] 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287.
[4] [俄] 巴赫金.史诗与小说:论小说研究的方法论[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80.
[5] [俄] 巴赫金. 小说话语史前史[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422
[6] Wolfgang Iser.Laurence Stern: Tristram Shandy [M].Cambridge up, 1988.83.
[7] 转引自:Van chent,Dorothy.The English Novel:Form and Function [M].New York:Harper&Row,1967.118
[8] [俄] 巴赫金.小说话语.[M]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5.170
[9] [美]丹尼尔·S·伯特.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序言[M].厦候炳译.海南出版社,2005.
《项狄传》读后感(三):《项狄传》:第二句便指望全能的上帝了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1861.html如同鼻子为鼻子,胡子也仍是胡子一样。
——《项狄传·第五卷》
第四卷的鼻子,和第五卷的胡子,却在18世纪的时间里被分裂成两个部分,第四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761年1月,而第五卷和第六卷出版于1761年12月,拉丁语开始,“我不予置评”是鼻子的传说而已,《什牢坑驳鸠的故事》要给你讲的是鼻子的生老病死,鼻子的现实和象征,以及鼻子的生理结构和用途,真鼻子还是冷衫木做的?那松脂的味儿溢满了第四卷的开头,但是还有人闻不出来,那么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一定是不带鼻子的,“它是个死鼻子”,没有人摸一下,也就像没有人认得那一页页满满的拉丁文。奇怪的鼻子带领着生客走向陌生的斯特拉斯堡城,所以大家趋之若鹜,像看一部巨著一样围着鼻子转,“的确,看到斯特拉斯堡人,男女老少倾巢而出,去追随那生客的鼻子时——总是站在门闩旁边的法国人便一个个追随着自己的鼻子长驱直人。”
是的,这是一扇被打开的门,靠着鼻子长驱直入,是法国人侵略了进来?这历史深处的一个战争问题因为鼻子而显得可怕而荒诞,而其实早在《第一卷》的时候,在宛如拉丁文里面的鼻子一样,追溯那个遥远的传说之后,劳伦斯·斯特恩便把门关上了,前后的一连串破折号把故事一分为二,里面是冷衫木和松脂,而外面是蜂拥的人群和丢失在法国人手里的城池。如果再回到鼻子,那也一样是失守的城市和身体,《什牢坑驳鸠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虚幻的故事,“Hafen Slawkenbergius”自然是斯特恩的创造,如果从语义学角度来解读,“Slawkenbergius”是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门都关上了,还有什么可以撤退的?德语“Schlawkenberg”意思是“炉渣堆”,或者“垃圾”,或者可能是“粪便”,而Hafen”在德语口语中指“便壶”——这便是讲鼻子的“一部巨著”的作者的专名——什牢坑驳鸠。创造的专名,创造的鼻子,创造的那扇门,而从鼻子跨过一年的时间,看到的却是胡子。
“鼻子的长度和好看仅在于奶妈乳房的柔软”,那么生客一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哺乳故事,这个暧昧的猜测却和什牢坑驳鸠的名字无关,和便壶以及一切创造无关,而那胡子,自上而下,离开了鼻子的部位,一定是和上帝有关。“从圣安东尼到圣乌尔苏拉,从她(卡尔那瓦莱特小姐)手指头上经过的圣徒没有一个不长胡子的;圣弗朗西斯、圣多明我、圣贝内特、圣巴西勒,圣布丽奇特全都有胡子。”这是圣徒的标记?还是王宫的象征?老绅士在说胡子的时候,把老太太的手抓住轻轻捏了一下——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但是老太太说,我想听,你往下说嘛。然后王后、后宫,以及和这有关的人都听到了“胡子”的发音,在法兰西和纳瓦拉王亨利四世的时代,在《第五卷》的1761年12月,胡子可以净化他们——无乱男女,无论毛发长短,胡子的故事只是“我留做永久管业里的一项遗产给正人君子和伪君子们去取乐,去利用呢。”是的,当高雅的极端与好色的开端合二为一时,下流语言就是被裁定的一个身体,像那个时候的宗教裁判所一样,还有一头“张牙舞爪怒吼咆哮的狮子”反抗者贞洁。
鼻子和胡子,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回归到身体的本义,我知道在这中间一定还有一张嘴,一张说话的嘴,一张表达的嘴,就像《第四卷》和《第五卷》中间横亘着的12个月,劳伦斯·斯特恩一定在说着什么,甚至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说话的欲望会将一部作品带向一个真正的迷宫。“使人惴惴不安的并不是行为,而是关于行为的见解。”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手册》第5章的一句话不是明明白白写在书的第一卷,开篇宗义,只不过引用的是希腊文,而不是拉丁文,当然也不是劳伦斯·斯特恩的母语英文。行动的见解一定是先说出来的,然后才写下来,在关门之前,劳伦斯·斯特恩便变成了我,那个叫项狄的“我”,从ab Ovo开始的故事,都是用嘴说出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我已经用自己开头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而且我还能够往下追踪其中的每一件事情,正如贺拉斯所说,ab Ovo。”贺拉斯的开头是一个有关女人的生命体,也是拉丁文,从卵子开始;即从头说起。这种暧昧和混乱恰如鼻子和胡子一样,是“高雅的极端与好色的开端”。我来了,项狄来了,特里斯舛·项狄,“特里斯舛!他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就叫特里斯舛了,而且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将一直是特里斯舛。”这是打在我身上的烙印,直到死的名字,无法更改,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特里斯舛,Tristram,源于拉丁文tristis,世界上所有名字中,这是有“最难以抑制的厌恶”,因为“认为它在rerum natura中产生出的只能是极端卑贱和可怜的东西”,卑贱和可怜的特里斯舛带着鼻子、胡子以及一张嘴,述说他的生平和见解,但是作为父亲和母亲在乡下生下的孩子,一定还有对于世界最厌世的东西存在:“我,绅士斯特里舛·项狄,被带入了我们这个卑鄙龌龊、灾难深重的世界。——我倒希望自己降生在月球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上(木星或土星除外,因为我绝对忍受不了寒冷的天气),因为在其中任何一个星球上(不过金星的情况我不好说),我的情况都不会比在我们这个邪恶肮脏的星球上糟。”出生是一个错误?而且一直要为这种错误寻找借口?那么错误从何而来?起初是钟,那准确敲击时间的钟竟被父亲遗忘了,“请问,我亲爱的,我母亲说道,你该没忘了上钟吧?——老天——!”因为多年来,父亲已养成了给钟上发条的习惯,而且都会在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的夜里,而这次忘了钟,特里斯舛的出生变成了一个意外事件,而“我的思想行为都跟他人的孩子迥然不同”的最大原因是,“我的特里斯舛的不幸在他出世的九个月前就开始了”。这是宿命?不同的轨道序列当然会、造成不同的人生,无论头脑清楚还是思想糊涂,不管是飞黄腾达还是一败涂地,。这是注定好的出生规则,轨道序列里没有什么意外。
所以,从ab Ovo开始,到后来变成了从HOMUNCULUS开始,拉丁文:小人儿,就是指精子。在一个轻浮的时代,HOMUNCULUS就是父亲的愚蠢和偏见,就是父亲的钟,和那个轨道序列。作为自然哲学家的父亲,几乎什么读懂,但似乎就是不懂生命的出生的真实意义。那么就从出生说起,那种君主式家长体制也是上帝的第一个造物主中的原型,父亲“沿袭这种令人折服的家庭和父权模式和原型”,我还有个哥哥博比,就像父亲还有个弟弟叫脱庇,原文为Toby,在雅语里有“屁股”的意思。脱庇本身含有低俗的意味,就像我是哥哥的弟弟,特里斯舛的名字里含有的卑贱一样,我们背叛了“上帝的第一个造物主”,也就背叛了“君主式家长体制”,所以在缺少钟的警示中,母亲怀上了我,而在出生的问题上,选择接生婆,选择在那里生,都变成了一项必须要讨论的决议,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条款,在那张“审议榻”上完成了,而“实际情况是,一七一七年九月末,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母亲带我父亲进城大大地有违本意”,违反本意,就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将特里斯舛变成了一个孩子,“我就由婚姻条款注定,让我的鼻子挤压得像我的脸一样平,仿佛命运旋成的我实际上没有鼻子似的。”面对没有鼻子的隐喻,我也失去了神学意义上的施洗权力,因为“人们不能对还处在母亲子宫里的孩子施洗”,而施洗正如神学家“所教导的,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以耶稣之名再生一次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施洗这种“精神出生”被取消之后,我最好的精神出生,则是命名,而我也拥有了成为“最难以抑制的厌恶”的名字:特里斯舛·项狄。这个名字对于父亲来说,是“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好像由魔术造成的偏见”,这种偏见不如说是归咎于神学,所以作为自然哲学家的父亲,对于宗教其实存在着一种隔阂,而这种隔阂却让父亲提出了关于命名、关于出生的“项狄假说”:“将双脚先拽出来对灵魂有好处。”并以哥哥博比的出生为例,来印证这个假说:“就是脑袋率先进入人世的,——后来长成了一个才思迟钝得出奇的半大小子。”所以父亲坚持自己的观点,极力劝说我母亲接受斯娄泼医生而不是那个接生老太婆的帮助。
荷兰著名内科医生兼妇科医师海因利希·冯·德文特的《关于分娩指南的重要意见》一字不差地摘下来的,然后便是关于孩子的命名,这是忧伤的生命,这是卑贱的生命,这是“一个悲伤而古怪的人”,取名特里斯舛完全是父亲的偏见:“是特里斯——什么来着,苏珊娜嚷道——除了特里斯舛,助理牧师说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教名是以特里斯开头的——那就是特里斯舛—吉斯忒斯了,苏珊娜说。”不是特里斯,也不是特里斯舛—吉斯忒斯,后面被删除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人生观,一种项狄假说支配的人生观,就像我的叔叔叫“脱庇”一样,低俗而卑贱,因为在父亲看来,“他所谓的好名字或坏名字,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和行为。”“人生短暂,医术无聊!”对于父亲来说,命名是一切意义的开始,而人的健康则“取决于人体基本的热量和基本的水分的适当竞争”,也就是对于生命体液的自由流淌决定了生命的轮子的转动时间,这是爱,这是真正的“项狄主义”:“它敞开了心和肺,就像所有那些带有几分它的性质的爱,它使血液和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体液自由地在它的渠道里流淌,使生命的轮子长期转动,快乐循环。”而这些爱成为父亲《特里斯舛全书》的内容,这是一本“为我而写的一部教育大全”,仿效色诺芬的样子写的书,而这也是父亲“在我身上下的头三个赌注都不幸输得精光”之后的孤注一掷的行为,我的出生,我的鼻子,以及我的名字,都不被接受,当然包括我。所以实际上,我是父亲在宗教之外的一个试验品,是返回他自身的一个象征物,而身上刻满“项狄主义”的我自然成了“项狄家的当然继承人了”,而这样的继承也意味着“我的生平与见解的故事也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这是第四卷第三十二章,308页倒数第三行,“生平”和“见解”用黑体标注,就像这一页上面的“教名”和下一页的“事情”、“胡子”一样,在通篇的字体中分外明显,这是不是也标志着特里斯舛的符号意义?不在子宫里施洗,家族制的破坏与新生,题目“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中的“生平与见解”才是真正要打开一个陌生的门的关键,詹姆斯·A·沃克在《序》中说:“在‘生平与见解’小说中,事件并不重要,甚至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系和相互作用中,实际的时间顺序变得无能为力。”事件和时间变得“无能为力”,甚至在解构着最传统的时间序列,《第一卷》第一章开始就写父母造人,那个钟的寓言,而到了第四章开始考究生命得胎的具体日期,第五章确认其出生的日子,“我是我主第一千七百一十八个年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和第一个星期一之间的那个夜里怀上的。”而这样的“怀上”作为一个事件,必须在“生平与见解”中成为隐藏在深处的线索,就如鼻子和胡子,在第四卷和第五卷分裂开来,而中间有12个月的过度,除了可以印证劳伦斯·斯特恩所说“慢慢来,每年写作出版我的两卷生平”的写作计划相吻合外,时间也成为劳伦斯·斯特恩有意留下的另一种结构迷宫,“可是请问,先生,你父亲十二月,—— —月和二月在做些什么呢?——噢,小姐,——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受坐骨神经痛的折磨。”这是父亲的回答,怀上孩子其实并不在计划之列,也不在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之内,所以一切的项狄假说、项狄真理,以及命名、教育、写书,和鼻子、胡子一样,都是身体的一种象征,包括“坐骨神经痛”,也只好坐在那张“审议榻”上商量一个孩子的卑贱出生,和脱庇叔叔和他的情人坠入爱河的婚姻问题。
都是身体的一种隐喻,坐骨神经,鼻子、胡子,以及脱庇叔叔的那个腹股沟之痛。“那是围攻那慕尔城时一颗炮弹从角堡的胸上炸下来一块石头,正好砸在脱庇叔叔的腹股沟上,结果就形成了他的这种习性。”围攻那慕尔城是脱庇叔叔的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他和下士特灵一直保存着那次战争的记忆,那是一六九五年的事了,仿佛是脱庇叔叔的“爱巴马儿”,围攻那慕尔之后,在草地滚木球场上发动战役,沃德曼寡妇便立即爱上了他,但直到一七一三年底敦刻尔克拆除,他一直都没有闲暇来应付她那短暂但让人心明眼亮的进攻。脱庇叔叔具有谦和的性格,不和女性交往,直到寡妇沃德曼爱上他,他才体会到身体里的那些故事,“脱庇叔叔对这个世界不甚了然:所以当他发觉自己爱上沃德曼寡妇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件事跟沃德曼太太用把打开的小刀在他的手指头划上一道口子一样,要搞得神神秘秘的”,这是必须保持的节操?连同下士和漂亮的贝居安修女的爱情一样,都是神学以外的爱情,可是这和身体有着太多的关系,寡妇对于身体也有着太多的敏感,因为寡妇的前夫就是因为身体而死去,所以即使最后脱庇叔叔找到了爱情,但是膝盖不同的“腹股沟,老爷您知道,就是那个地方的帷墙。”
对于这一面重要的围墙,下士只能挥舞着手杖,而那手势“似乎像18世纪的精子运动图示”,就像“阿曼杜斯——他”和“阿曼达——她”的“两个痴情恋人被残忍的父母和更加残忍的命运拆散”的故事一样预示着没有结局的爱情,而对于这个身体残疾、没有情欲的脱庇叔叔而言,那扇门是始终关着的,父亲母亲在审议榻上审议完了之后,也只能“从钥匙孔里偷看”,而其实,这种偷看的背后是一种渎神的行为:“钥匙孔成了罪恶的渊薮,比世界上所有的孔洞加在一起还要恶劣。”这是对于神学体系来说,也是一种赎罪的行为,但是真的能从这种身体的残缺中抗击宗教的秩序?从“ab Ovo”开始,到“无非是公牛、公鸡之类的荒诞故事”,情欲完全被禁锢起来,而不管是鼻子还是胡子,不管是“高端的极端与好色的开端”,也都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就像特里斯舛的出生和命名,也只是假说恶而已。
宗教是身体里的弹簧,而身体化解在残疾中,弹簧也没有意义,那么,“爱就如同当王八”。很明显,在劳伦斯·斯特恩的文本里,对于宗教完全是解构的,他的出生是在颠覆“上帝的第一个造物主中的原型”,他的命名是在寻找那一扇通向世俗的门,而有关的鼻子、胡子、腹股沟都是宗教的另一种隐喻,尽管“我”要声明这些见解都是不针对牧师、教士、神学家,以及一切宗教典故:
在有关我父亲及他有关的教名故事中——我并无意糟蹋弗朗西斯一世——在有关鼻子的事情上——我也不想糟践弗朗西斯九世——在脱庇叔叔的性格上——我也无意刻画我国的尚武精神——他腹股沟上的伤,无论怎么比方,也是一种伤,——书中的特灵——也不是指奥蒙德公爵。
但是谁都看到了昂杜莱修道院院长和玛格丽塔Bou,ger,fou中发出的这些和“交媾”有关的象声词,看到了牧师约里克死去的那块墓碑上的铭文:“哀哉,可怜的约里克!”,以及作为“伟大的教会律师”,意在影射讽刺弗朗西斯·托法姆博士,当然也看到了脱庇叔叔经常吹着的《利拉布勒罗》,而厄努尔夫主教作《罗切斯特教堂文告》也是谴责反对教会的叛逆者或将他们逐出教门的咒语,和查尔斯二世那“上帝的肉”和“上帝的鱼”的咒语一样,是对于宗教的颠覆,而反过来,自己的身体所有的官能也都受到了诅咒。
而在这种隐藏着满是咒语和解构的文本中,劳伦斯·斯特恩似乎就想为自己关上一扇门,在不可消解的出生、命名,甚至穿裤子的反抗中,也在无限接近那个“四面八方被神秘和哑谜包围着的世界”,实际上他逃回到了自己迷宫般的文本里,“我的作品既是打岔离题的,又是直线向前的,——而且两者同时进行。”是的,这里有“混乱的神明”,从第一卷就开始了旅行:“然而,对于不想追溯这些过于遥远的事情的读者,我能提供的最好的建议无非是,跳过本章剩下的部分;因为我有言在先,这一章仅仅是为那些爱刨根问底的好奇之辈写的。”然后便是“把门关上”,而这扇门从此就没有打开过。约里克死去之后的两页全是黑色的,仿佛墓碑;第105、113、185、291、394的手指的符号,指向一个未知的领域;112和266页的插画,闪现着古典主义的绘画技术;第四卷278-287页的空白,“缺了整整一章——造成了十页的空缺”;第九卷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又是空缺,却在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之间以“第壹拾捌章、第壹拾玖章”的名义又被插了进去;还有无数的乐谱、星号、省略号以及大理石纹路,组成了文本的另一种符号。在解释“※※※※”这个充满性隐喻的符号时说:“画上这个短断音指示号,——这是一种欲言又止的表现。——去掉这个短断音指示号;写上屁股二字——那就失之下流了。——把屁股画掉,加上掩蔽廊道,这是一个隐喻。”没有了屁股,“※※※※”就如那些被禁的书上的“■■■■■■■■”一样,当然欲言又止,当然对于秩序的反叛,“我痛恨老一套的死板文章,——尤其是把一连串夸张、晦涩的字眼,一个接一个排成一条直线、横在您和您的读者的概念之间,从而把您的假说搞得昏昏沉沉,这是我最痛恨的一种事情中最愚蠢的事情之一。”
而对于文本的情节推进,劳伦斯·斯特恩也用了图例来解释,“第一二三四卷中进展的四条线路”几乎没有过程没有终点,当然也没有时间或者事件的推进线索,而在“第五卷中我一帆风顺”,在这条线路里,劳伦斯·斯特恩说:
这条线路表明,除了在标有A的曲线处,我到纳瓦尔旅行过一回,——还有锯齿状曲线B是我在那儿和博西耶小姐和她的男侍一起,暂时外出换换空气外——我一点儿也没有跑题,直到约翰·德·拉·卡萨的魔鬼们领着我绕过您看到标有D的圆。——因为就ccccc而言,它们只不过是插入成分,是国家最高的大臣们的生活中常有的浮沉、升降;和人们的经历比较的时候,——或者和我自己在ABD走过的三段弯路相比——它们就算不了什么。
ABCD的符号是一个事件,但又不是事件,而推进的也不是一条“既不向右拐,也不朝左斜”的直线,这条直线是有不同的含义和指向的,神说,这是“基督徒步入的道路”,西塞罗说:这是“道德端正的象征!”而阿基米德说,这是“最好的线!”还有既非宗教也非科学的种白菜的说,这是“从所给的一点到另外一点所能画的最短的线”。线索打乱,时间打乱,时间打乱,所谓生平和见解也都是一个个迷宫,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叙事中,劳伦斯·斯特恩是有意而为之的:“我从我讲述的正题上飞走,远离的程度和次数堪称大不列颠作家之最”;所以,他告诉读者,“您读到下面的句号时就翻回去,那一章从头到尾重读一遍。”或者在这种天书般的结构中,给读者制造阅读的麻烦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就我自己而言,我将永远向读者表示这种敬意,竭尽我的全力让他的想像跟我自己的一样忙碌。”
其实,在这个宛如天书般的文本里,除了对于这种实验性保持热情之外,劳伦斯·斯特恩也在进行着反宗教、反秩序的努力,他认为,写一本书最虔诚的办法,便是在先写第一个句子之后,“第二句便指望全能的上帝了”。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开头之后,带进那扇门的就是作者之死,就是全能上帝的游戏了,这种讽喻也是小说中不断强化的主题,我的出生是个错误,我的命名是卑贱,那么就将一切还给上帝还给那些被诅咒的神。就像身体上的隐喻一样,永远带着残缺在赎罪。但这似乎是宿命的,正像书中所说,“我一直是世人称之为命运的那种东西的玩物”,而从文本出来,那个现实也一样是无法摆脱的残疾,劳伦斯·斯特恩按照计划,“每年写作出版我的两卷生平”,而从1759年开始创作出版《项狄传》第一、二两卷起,直到1767年1月出版第九卷,差不多就是按照计划每完成两卷出版一次。但第九卷是例外,书出版不久,斯特恩就因肺部大出血而去世。《项狄传》第一卷第十三章写到,如果顺利,那么这本书就是二十卷,而随着劳伦斯·斯特恩在1768年死去,《项狄传》不过是原来计划中的一半还没有完成。
“特里斯舛·项狄”意为“一个悲伤而古怪的人”,也是劳伦斯·斯特恩命运的写照,是个“命运的玩物”,而到第九卷结束的时候,“生平和见解”就像父亲曾对脱庇叔叔说的那样:“我们在时——死亡不在;——死亡在时——我们不在。”不在是个悲剧,而在文本的寓言和游戏中,留下的何止是遗憾,我在604页读完这个“无非是公牛、公鸡之类的荒诞故事”之后,也慢慢合上书,发现我的阅读又一次被他在《第五卷》上所预见了:“书合上以后他的拇指压在书皮的上方,其他三根指头垫在书的下面,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表现。”
《项狄传》读后感(四):神书
这是一部奇书,更是一部“神”书。 我看过《巨人传》,也读过《琼斯》还有《尤利西斯》。本来以为对这种书已经有点习惯了。现在看来我太高估自己了。 在《巨人传》中的各种玩弄学问的风格又再现了。可是好歹它还有一条主线。可是这部书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特里斯舛·项狄先生到第四卷才出生。还好比戈多好,至少是出现了。还有它玩弄不仅是学问,还有排版方式,不仅有插图还有空页(杜尚的现成品),甚至还有****。天呀,它以为它是《废都》呀! 可是等等。这本书写于何时?176*年。怎么可能,我还以为在看法国后现代文学呢。我此书中看到了《巨人传》的卖弄学问,看到《堂吉诃德》的意味,还有《似水年华》飘忽的联想力。以及林林总总的后现代艺术感觉。作者不会是穿越的吧。 整部书就向一幅画。 一张白纸在画框中。 问:这是什么? 答:画,牛在草地上。 草呢? 牛吃了。 牛呢? 吃完草走了。 所以作者是神人,这部书是神书。还好他只写了九卷,感谢上帝! 耐心太差的人我不建议去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