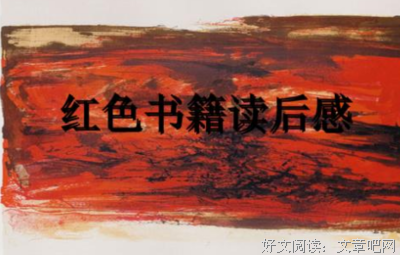
《苦难的时代》是一本由[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著作,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5.00,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苦难的时代》精选点评:
●经典!但是题目似乎翻译不太妥当~
●在谈论本书讨论的奴隶境遇时有两个必须注意的外因,首先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被禁止,这意味着奴隶的成本开始大幅攀升,其次是之前的海地奴隶起义极大的震慑了白人的心态。
●没有附录,精华尽失。
●lq课看的
●居然删了附录!!!
●4/5,经济学真是有力到可怕的工具,算是解释了奴隶制何以在美国如此顽固、美国奴隶的低反抗率以及废奴后美国黑人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原因。肯定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的经济成就确实非常危险,因为这一研究太容易被错误地运用和解读了,斯坦普的踌躇反而是正常反应,毕竟单从经济效益入手很难将黑人的辛勤劳动与美国奴隶制的管理在贡献上做出清晰区分,尤其在当今美国黑人处境的对照下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对奴隶主和奴隶劳动方式的重塑,种植园主以资本家式的运作和黑人流水线式的生产揭示了美国奴隶制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新式而非旧式的生产方式。这与制糖业在美国种植园的缺位,进口奴隶比重低、自然生长率高,奴隶在技能职业与低层管理有相当比重,以及低死亡率共同造就了美国奴隶制的特殊性,当心不要将这一重估泛化。
●自己以前的一些观点在崩塌的边缘…这本书客观得可怕
●道德判断尽量不要去误导事实判断,人类社会很多看似合情合理的观念经不起严格的推敲。我们心中可以秉持着正义高尚的情感,但不应用错误含糊的论据去攻击那些显而易见的罪恶。
●计量历史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结果,都让人深深震撼。
●非常有价值、有启发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接近伟大的著作。可惜中文版本无论是翻译还是校对都太差了,既不熟英文、也不熟中文,导致阅读的通顺性很差,充分显示出"自由人"的素养。
《苦难的时代》读后感(一):危险的路径
可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类书,尽管他提供了大量似是而非的“证据”,但是他们极力要阐明的不过是黑人奴隶制的生产效率不是如想象的那样低。而实际上这用脚趾头就可以想明白。
试想一个成年男性每周工作超过八十个小时,即便是生病了,通常也不敢请假怠工。五岁以上的儿童没有教育经历与妇女一起参与田间劳动。这样的效率又为什么会低下呢?假如,将这些奴隶带入现代社会的大机器运作中,可以说他们依然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
作者对奴隶在那几百年里所收到的苦难几乎选择一笔带过的方式,哪怕是奸淫黑人妇女(哪怕比例不是特别高,哪怕白人妇女也同样受到白人的奸淫,那么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么?)况且他们存在众多将黑人妇女当生殖工具,将他们的孩子贩卖各地的残忍行径。有多少母亲这种苦难中抑郁终生,那么白人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卧室,一个完善的营养结构配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仁慈还是恩德呢?更有甚至,作者习惯性将百分之十的比例视为一个可以不计的数字,这显得可笑至极。我想任何群体中,一百个人有十个人是痛苦的,受尽磨难的,是可以不必在意的么?
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福格尔不停的在论证黑人奴隶在失去“奴隶制”这一制度性“保障”以后,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和惨烈,无论是健康,寿命,生育水平,生活水平都在大学一百年后才得以恢复。我以为,这应该并非是可以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也只是奴隶制的创伤结果,而不是奴隶制的成功的例证。在两百五十年的历史中,这群黑人从黑人来到这里,他们除了生活在农场就是生活在小城市的商人家,无论在哪里身份都只是奴隶。他们从未得到机会去认识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社会,不过是低头劳作。那么,在失去这个圈套之后,一无所有的人们,没有更加娴熟的技能,和装满知识与智慧的头脑,请问,他们靠什么过的更好?难道一个在监狱里呆了四十年的人,一出来就会像华为员工那样奋斗么?请参考《肖生克的救赎》。
所以,福格尔不断试图论证的效率和价值,乃至金钱又说明了什么?五千年后的人拥有登月技术和原子弹,这又说明了什么?是进步么?进步到底是什么?是试图为一种效率和价值而立教的言论么?只要他是人,除了他愿意,没有人可以奴役他,如果有,我们就应该砸碎这些人的脑袋。而如今,奴隶仍存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仍旧是(更加是)苦难的时代。当有人为自己家住在富士康隔壁而自豪,当有人因为看到深夜十点半的大厦灯火通明而欣慰,当有人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而兴奋,我想这不是什么关于进步的问题。因为,所有人眼中存放的是一个虚无的虚有之体,而不是任何人。这样看来,一个人愿意被奴役,似乎比两百年前的奴隶制要令人绝望的多。但是,我们无可奈何。
《苦难的时代》根本没有关注任何苦难,而是讴歌!作者的思维绝对没有错乱,所做的工作绝对具有价值,但路径是危险的,像过去的希特勒和如今的中国一样危险。我们绝不是没有可能逃避出这个圈套,但所有人已经甘愿过着被奴役的日子,理由是他们没有办法!
《苦难的时代》读后感(二):深刻的剖析,伟大的著作
福格尔的此书,是对"存在即合理"的优质注解。现代革命者喜欢说两句话:一句是"先进生产关系必然取代落后生产关系",一句是"落后的东西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两句话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有人看出了革命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才会为林肯点赞。有人看出了其中的悖论,从而有了这本堪称伟大的著作。
根据本书所述,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主(即农场庄园主)中,存在有、并且不是例外地奴隶主,在以优化(或者说改良)的方式调整奴隶的管理、使用方式,从而或有意(出于利他动机)、或无意(纯粹利己动机)地实现了本质上科学、外在上相对文明的新管理模式,赋予奴隶制以生机和活力,其突出表现,即为稳定、可持续、有竞争力地发展,从而具有相对北方农业更大的竞争优势,并带来南部社会总体上的繁荣,由此也带来一个非常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存在有相当一部分奴隶的自我发展。作者并进一步论述,奴隶制的这一优势,根本在于奴隶人身的私有性,从而使得有些奴隶主可以从"资本"角度进行优化配置,并与市场一起分享这一红利,即马克思所批判的"剩余价值"。换言之,这一现象是最直观、最典型、最赤裸的"剩余价值"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产业工人就是事实上丧失了人身所有权、不是奴隶却相当于奴隶的自由人,并取名叫"无产者"。当然,颇具讽刺意味地是,在奴隶制下,相当多奴隶并不是糟糕到绝望无助,甚至还有一些奴隶是有产者、比产业工人还好。当然,马克思会给这些有产奴隶一个专有名词,叫"异化"。从这个角度,19世纪美国南方的某些奴隶制形式比当时主流的工厂制更文明。而作者也论证,工厂制与奴隶制并不对立。看完本书,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推论:当主流工厂制的文明程度超过最好的奴隶制时,依靠经济的主动力,再辅以政治、宗教、教育等力量,实现奴隶制的自然消亡,既是最佳的、也是可行的。
由此再回到开头的两句话,我的观点是:
(1)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不能仅凭其先进的基因,就有资格要求落后的生产关系让位、退出,强行这样做,只会带来持续地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文明倒退。
(2)落后的生产关系,可以通过内部的不断改良,从而向先进的生产关系靠扰,最终平稳过渡,换言之,通过自我的不断革新,最终成功成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实现落后生产关系的主动退出。这是从静态来描述。从动态看,自我革新,就是实现从落后到先进,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就是所谓的"自我重生"。
人类文明的进程,对前两点都有很多鲜活的事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内战意味着北方和平演变南方的失败。根据本书论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北方的生产关系虽然先进却远不成熟。虽然从价值观和结果维度,美国内战堪称伟大的战争,但代价却是远非必要的巨大,事实上是一场风险极高、代价巨大、而又并非迫在眉睫的豪赌。这不过是人类群体不理性的又一个事例罢了,只不过因为林肯的存在,使得这一远非必要的巨大代价没有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避免了让人后怕的局面(即北方的失败)。林肯固然伟大,但这才是让他在历史上永远被铭记、取得凸出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正如火焰让背影更巨大,是社会背景让卓越成为伟大。
《苦难的时代》读后感(三):在某些层面,我们超越了美国南方奴隶制——读福格尔《苦难的时代》(《Time On Cross》)
如果你以为看看《被解救的姜戈》《为奴十二载》或者《飘》就了解了奴隶制,那你将和那些看着横店出产的抗日剧以求获得抗日战争史知识的人们的谬见同样多。
当然,这并不代表你不聪敏,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20世纪之前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一点儿都不比你的偏见少。
我们通常会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非常大的影响,奴隶制显然不如封建制,而封建制又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这样教导我们的。
对于奴隶制,一般的理解是,奴隶们作为牲畜一样的存在隶属于主人,他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常遭到鞭打,虐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被随意的买卖,很难保持健康,也不能维持完整的家庭,常常妻离子散,由于不能分享劳动成果,因此他们会倾向于懒惰,只在监工之下工作,因此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也是低下的,远远比不上自由农民的出产,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除了道德上的考虑,对于南方经济也是一大促进。
但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这本书,通过计量史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大量的史料,并用大型的电子计算机去处理数据,得到了许多颠覆性(但是足据说服力)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渐渐被以后的研究者所证实,成为了对于奴隶制看法的主流。
引书中的一些结论来看,你一定会感到吃惊:
1.奴隶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奴隶主对奴隶的购买是一种有很强盈利能力的投资方式。
2.南北战争前夕,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而且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行将就木。
3.南北战争前夕奴隶主对奴隶制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态度。
4.规模经济、有效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
5.典型的黑人农奴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
6.奴隶制和工业体系并不矛盾,奴隶在工业部门的勤奋程度和效率均不逊于自由工人,只是因为农业对奴隶的需求更加强烈,更无可替代,奴隶才更多的流向大种植园。
7.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庄园主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大部分奴隶也的确做到了家庭的稳定。许多奴隶交易都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是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8.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起码对于19世纪前期的底层来说,奴隶并不比自由工人物质生活更艰难。
9.对于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农奴来说,终其一生,他能获得其产生的总收入的90%。
10.南北战争前,南方经济并没有停滞,在人均收入上,可以排到全世界第四,已经成为了高收入国家(地区)。
11.超过25%的奴隶男性是经理,教授,手工艺人和半熟练工人,认为所有奴隶都是人力劳工的想法是错误的。
12.奴隶制下形成了灵活且无比高效的激励机制,诸如奖金,休假,年终奖,对“劳动能手”的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拖后腿者的惩罚,班组制和劳动分工,流水线作业等等。认为奴隶主仅仅靠着鞭打奴隶来保证服从和效率的印象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传言。鞭打确实存在,但那是为了防止奴隶受伤或者反抗,只在冷静的惩罚时才会被允许施行,而奴隶一般也会认为这样的惩罚是公正的。
13.奴隶摄入食物的营养水平甚至超过自由人,配给最少的是肉和牛奶,他们也能达到每人每天4两肉和1杯牛奶的水平。
14.他们的住房基本上是独门独栋的,而当时的工人还住在群租房里。
15.每个种植园几乎都会配备护士,负责一般的疾病和接生,医生会定期光临,同样的医生不但治疗奴隶的疾病,也会治疗奴隶主和其家人。奴隶主特别关心奴隶的身体状况,如果他们生病,即可得到一天的病假(有时候甚至装病也能得到这样的优待)。
16.奴隶婚姻在国家层面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但是在种植园里却被强有力的保护和促进。原因是,这样有助于稳定人心,增加逃跑的成本,给奴隶以安慰。而无论种植园主还是监工不会去破坏奴隶家庭,或者奸淫女奴,因为这样会激起奴隶的反感,消极怠工,逃亡,成本太过高昂。
看到这儿,有人要大叫了,wtf,这是在给奴隶制洗地吗?奴隶制能这么好?奴隶制经济效率这么高?是不是搞错了?当然也有人这么指责福格尔,不过后来大家渐渐达成共识,即便奴隶制并非一无是处,有许多好的方面,它依然是可耻的。正因为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南北战争似乎变得更有必要了。
接下来我要详细的说一下第六章的内容,并且分析一下这本书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奴隶制之所以能够高效的近似流水线式的生产,是采用了三种途径来维持:
一,通过选择最强壮最有能力的犁地员和耙地员领导种植过程。
二,通过不同种类劳动力的协作(因为在一个流水线上,这样的协作给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造成一种必须要跟上领头者脚步的压力)。
三,通过安排监工和工头,去劝诫领头者、威胁落后者,以及采取必要行动以保证队伍内所有劳动力的工作节奏和质量。
将奴隶组织成高度自律、协作的队伍,以胜任稳定且紧凑的工作节奏,是农场大规模高效运作的核心。
但是要问的问题是,这和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一样啊,工厂里可以用自由工人啊,为什么农村不能用呢?
福格尔他们得出两个发现:
1.南方农业的规模经济必须依靠奴隶劳动力才能实现。
2.城市的生产则既可以使用奴隶,也可以使用自由工人。
原因是什么呢?是农场主(企业主)在获得劳动力身上的劳动时所适用的方式不同。从自由人那里取得劳务,是采取工资协定的方式,从奴隶那里获得劳动使用的则是武力。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分析道,在流水线上或者以小组制度耕种土地这种类流水线的方式,对于劳动力来说是不那么舒服的一件事,实际上是产生了负收入的(这个负收入在奴隶制当中不会表现为现金收入)。
什么意思呢?就是农场主如果和一个自由人签契约,要求采取小组制度来劳作,你就要给一个非常高的工资,高到超过作为奴隶所得的100%,也就是说,自由契约是签不成的,我宁愿少赚一点儿钱,也不去受那个累,就是这个意思。
而城市里之所以能够达成在流水线上作业的自愿契约,是因为在城市生活有一些其他的便利,补偿了在流水线上的负收入。大家算一算虽然工资不高,但是还可以接受(得到了城市生活便利的补偿)。
而在农业劳动中,则只能依靠奴隶,既然自由协定的工资太高,那就用武力强制奴隶去采取小组制来工作。小组制工作提高了纯现金收入,而奴隶承担了非现金的损失,这样奴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现金性收入,奴隶主也得到了更多,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加神奇的推论,那就是奴隶主得到的好处是小头的,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了更加廉价的棉花,而棉花的消费者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也就是说,人人的手上都沾着奴隶的血汗。
而当废除这一奴隶制之后,南方奴隶由于没有相应的跟进制度,又无法自由的达成劳动合同(如前所述成本太高),就导致了奴隶成了边缘人,不再能够分享原来的一些好处(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现金收入),不再能够学得手艺,完全被抛弃掉了。
奴隶制在用大棒加胡萝卜逼迫奴隶高强度劳动上确实存在着剥削和不人道,但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一种脉脉温情和共生关系,当制度改变时,如果不仔细考察原来的经济关系,很可能使两者的处境都变差了,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就世界大同一片光明了,显然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并没有做好这一点。
当我们看到奴隶所处的极端环境下时,自然的想到了秦晖先生所说的,低人权优势,以及富士康的流水线,十三连跳。
虽然我们没法直接得出结论,但是可以提出问题。
在制度转型的时候,市场是不是一定是公平的,是不是说按照供需关系给劳工提供工资和劳动环境就是正当的了。
当大量的农村人口到城市里打工,导致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时候,企业能不能说就以一个非常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来招工,并且称其为“自愿”的,因此是正当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2017.2.18补充,这一点可以参考刘易斯对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研究)
我们同时也可以思考高考制度,像衡水一中这样的超级中学,成绩好就一定是好学校吗?
首先,如福格尔所指明的,效率和文明,和好并不是一回事儿,奴隶制生产率更高,但它依然是奴隶制,衡水一中有更高的录取率,未必就是更好的学校。
其次,在显性收入,显性的效用背后,还有隐性的收入和损失,奴隶制获得了更多的现金性收入,但是奴隶却承受了更多的苦和累,非现金性损失。(2017.2.18,补充,关于收入的论述可以参考费雪的《利息理论》第一章)
考生们收获了更好的成绩,他们付出了什么呢?身心健康,创造力想象力,学习兴趣,对生活的体验?如果都算进去,好成绩到底是赚还是亏呢?
这都很值得想一想,如果有人去做定量,定性分析就更好了。
最后,从整体制度上来讲:
奴隶没有迁徙自由,我们也难以离开这个国家。
奴隶终生被剥夺劳动成果的10%,我们的税负更重,接近收入的一半。
奴隶没有民主权利去支配这些劳动成果,我们同样没有,如果把这本书看成为奴隶制度洗地的就太简单了,它实际上是泼我大社会主义脏水的,比较起来很多地方似乎奴隶制还要好一点呢!
《苦难的时代》给人的最大教益是,经济效率并不总能证成制度上的善,当有些人说,我们的GDP发展很快,我们帮助了6亿人脱贫,我们的经济很好,所以我们国家很好时,我们的人权大大改善的时候,你对他说,不错,你的经济确实很好,可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经济也不赖呀。
补充:一直以来,我们接受了马克思的主张,常常把历史的进步归因于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福格尔对于奴隶制的研究则申明了这一观点:废奴运动,首先是基督教平等理念所引申出来的,是极具道德感的运动,它并没有顺应经济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效率的,然而这一运动不因它在短期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效率而失去了道德正当性。
当追求自由民主制度可能减缓经济发展的时候,当大量的工人不再被迫签订契约,因为环境和产权问题而减缓工厂的建设和城市建设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代价?
在废奴战争当中,恰恰是那些最关心奴隶的人们,采取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看待黑人,认为他们的能力和天赋不同于白人,这也是值得警惕的。
2017.2.18补充:南北战争的确付出了生命和物资的代价,但是在美洲彻底的废除了奴隶制,避免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扩大墨西哥甚至整个美洲,这个成本收益的核算是很难说清楚的,以常识和长远来看,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依然是值得的。——我们人类多么可怜悯啊!
《苦难的时代》读后感(四):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金子,经济史家会为奴隶制辩护吗?--纪念罗伯特·福格尔诞辰九十周年
一、Time on the Cross:一场史学地震
今天,毫无疑问,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奴隶制意味着野蛮、落后与暴力。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也就是计量历史学(New Economical Hsitory,or Cliometrics)的领军人物,罗伯特·福格尔(Robert.W. Fogel)在40多年前以计量史学方法得出结论,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的经济效率要比北方自由农场高出34%,奴隶制更具效率且有利可图,奴隶的生活条件也比北方工人优越……
这项研究即福格尔在1974年出版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Fogel R W, Engerman S L. Time on the Cross :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M]. Little, Brown, 1974.福格尔是第一作者,故一般将此书研究主要归功也是将质疑导向福格尔。国内常译作《十字架上的岁月》、《艰难岁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苦难的时代》,中译本为罗伯特·福格尔等著《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笔者认为题名不妥,福格尔此书本身就是对奴隶制经济是一个苦难时代的颠覆,故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在文中采用《十字架上的岁月》这一译名。],这一年正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获胜的《民权法案》之后的第十年。此书一经出版,简直是石破天惊,它挑战了奴隶制史学的传统叙事,首先让历史学人眼前一亮,当时即被认为这是计量史学的最新也是最好的成果[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Passel说,他不知道最近十年出版的美国史著作中还有任何一本更好的书了,见Thomas L. Haskell. The true & tragical history of ‘Time on the Cro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 October 2,1975.],可以给传统史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因而获得了当年即1974年的班克罗夫特奖,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但是,作为一项在奴隶制这样一个焦点问题上极具冲击力的研究,很快引来巨大的争议,引发了从经济史学界到整个历史学界再到整个大众媒体的一场奴隶制问题“地震”。[ 余英时在日后评论黄仁宇的计量史学倾向时候,也是提到此书作为隐喻,认为在福格尔引发的争议中,黄仁宇显然是导向福一方,暗含“臭味相投”之意,见余氏《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一文。]毕竟,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历史学著作可以同时在经济学专业期刊、历史学专业期刊再到《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引发热议。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对于经济学家的一句戏言,“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黄金,那么经济学家也会为奴隶制辩护”,正是在对此书的热议中产生。
《十字架上的岁月》代表了1960年代到80年代盛极一时的计量史学潮流[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J]. 历史研究, 2015(2):113-128.],可以说也是至今为止计量史学带给传统史学最震撼的一部著作。当时的计量史学基本上掌握在有着良好数理方法和计算机数据处理基础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史学家)手中,传统的历史学家既不能参与也无法予以辩驳,因而计量史学本身暴露出经济史家的很多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但是最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计量史学的技术方法也有了全新提高,并更容易为历史学学人所理解与接受,特别是在国内,量化史学日益火热起来。
在1993年,福格尔和另一位我们更熟悉的人物,同样是制度经济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的旗手——道格拉斯·诺斯,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今年,《十字架上的岁月》才被首次翻译成中文,在计量史学不断被重提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诺奖级经济史家的最具影响力也是最饱受争议的作品中学到什么呢,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够抽打出金块,经济史家真的会为奴隶制辩护吗?
二、美国的奴隶制研究传统
南方奴隶制是美国史研究中最重大问题之一,奴隶制不仅与南北战争直接相关,奴隶制史学更是长期是南方史学的主体。长期以来,美国史学界认为奴隶制是一个垂死的制度,在南北战争之际已经趋于消亡。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U·菲尔普斯的“传统解释”,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奴隶制史学。菲尔普认为奴隶制极大限制了南方工业化的发展,奴隶制束缚了劳动力,束缚了本可以成为工业资本的奴隶资本,而战前奴价相对于棉价的增长,使得奴隶制经济趋于崩溃。C·拉姆斯德尔认为奴隶制的衰亡更多的是一个资源问题,随着奴隶制从旧南方扩展到新南方(大西洋沿岸到墨西哥湾沿岸),适宜奴隶制的土地已经消耗殆尽。这就使得棉花经济也就是奴隶制经济会到达一个极限,然后走下坡路。[ 参见曾令泰, 卢明纯. 效率、自由及其他:奴隶制衰亡的原因探讨[J]. 理论界, 2006(7):148-149.]
奴隶制真的到达极限了吗?在福格尔之前,已经有一些经济史家作出反驳。最著名的即A·康拉德和G·迈耶在《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中就超越了传统单一从棉花的角度来考察奴隶制经济的方法[ Conrad A H, Meyer J 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66(2):95-130.],而是将奴隶也作为人力资本加以考量,从而得出来内战前南方种植园资本和利润处于一个增长状态,并没有走向衰亡。
康拉德的研究挑战了原有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单纯研究奴隶制种植园是否有利可图,并不意味着奴隶制经济是有效的,还需要考虑更多社会经济和道德经济因素,因而,历史将这场奴隶制史学革命的人物交给了集大成者的福格尔以及他的合作者恩格尔曼。
三、罗伯特·福格尔与计量历史学
福格尔于1926年出生在纽约城的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在童年时代经历了大萧条,据说因而产生了对经济学的兴趣。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经济学,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1948年本科毕业后的八年内是一个职业共产党活动者者。但是他之后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追求他的学术事业,并于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于196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库兹涅茨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回顾长期经济数据的实证性研究,去考察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内在变迁。库兹涅茨的深深影响了福格尔,福格尔在新经济史或者说计量历史学就是遵循这一实证传统[ 参见福格尔为纪念其师库兹涅茨的遗著《政治算术:西蒙·库兹涅茨和经济学的实证传统》,胡永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不仅是追求数据的精密性而且是数据来源和背景的准确性。
他在学术思想和方法路径上是受到当时最为兴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或者说他本身就是经济史层面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当家人。简单来讲就是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为零的观点,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交易成本,而为了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就需要明晰产权,这就需要更符合绩效的正式拘束和非正式拘束,也就是所谓的“制度”。福格尔在经济史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去重新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而在奴隶制问题中,也是考虑这么个理论,一个制度是否是有绩效的,就看它是否能够有明确的产权,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提供资源适配和市场流通能力,也就是能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问题。从这几方面入手,由此,《十字架上的岁月》构成了一部瞠目结舌的修正主义史学。
福格尔也不是第一次做出这种修正主义的历史研究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所言,他的获奖是由于“在经济史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重新解释了经济和制度变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颠覆性的,也因此成为计量史学的一代宗师。其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最具开创性的成果--反事实度量法就充分展现出计量史学的强大与活力,即假设某一事实不存在或者情况相反,估算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结果,由此来度量该事实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最著名的即是福格尔对于铁路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作用的研究[ Fogel R W.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J]. Technology & Culture, 1967, 31(313):611-612.],即把铁路看成是一种“社会储蓄”,假设在1890年铁路完全消失,多少对于美国的社会储蓄减少了,由此福格尔估算出铁路在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只占到3%的作用,即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经济状况最多会落后两年,完全颠覆传统对于铁路作用的观点。福格尔在对于奴隶制绩效及奴隶制是否会消亡问题的研究中,也用了这一方法,“假如南北战争没有发生”……
四、十字架上的奴隶制:福格尔的研究
福格尔《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主要分为六个章节,首先回顾了国际背景下美国奴隶制的起源与废除,指出奴隶制的废除是一个加速的、非常态的历史过程,由此福格尔通过计量史学方法重新研究战前的南方奴隶制,从奴隶和奴隶主两方面入手,考察了奴隶的生育、寿命、家庭、生活条件、职业、奴隶贸易与地区流动,探析奴隶制种植园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特征、奴隶主的乐观指数、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与压迫,并研究了美国奴隶制的观念史。他最终总结出他对于奴隶制研究的十大修正,简单而言,就是从以下三个问题挑战传统奴隶制认知:
(一)奴隶制是低效率和落后的吗?
福格尔认为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的种植园主维持的非理性制度,奴隶主对于奴隶的购买和拥有是一个具有高盈利能力的行为,资本利润率甚至高于同时期北方的工厂。奴隶制种植业生产效率比北方自由农业高,更无论南方自由农业,战前奴隶主对于奴隶制经济乐观指数和对于没有南北战争的反事实度量都表明奴隶制经济并没有衰亡的趋势,反而会在19世纪下半叶越发巩固。
(二)奴隶过得非常悲惨吗?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制度,奴隶制应该尽可能降低奴隶制经济交换双方的交易成本,所以需要明晰双方的产权(也就是契约权利与义务),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福格尔从奴隶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中论证了这一点,他估算出无论是出生率、死亡率、营养状况还是生活必需品条件,奴隶均优于同时期北方工人,而奴隶主为了尽可能提高自身利益,也会努力保护奴隶利益,奴隶主如果使用暴力而不是现金作为激励手段,反而会提高奴隶主的生产成本,因而奴隶主轻易不使用暴力,拆散奴隶家庭也是少见情况。奴隶得到了其90%的生产效益,也即是剥削率仅10%,因而奴隶则还报以高水平的生产效率,奴隶有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和高效的团组工作机制(gang system),奴隶的平均生产效益高于白人农民和工人。
(三)废奴主义者是一种种族主义者吗?
那么,既然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益的制度,并且奴隶主和奴隶均处于一个有利状态,奴隶制经济是怎么灭亡的呢?福格尔依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他从经济上对奴隶制控诉的早期两大源头入手,发现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低效的、奴隶是懒惰的、南方是糟糕的观点均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是低等的黑人导致了南方出现奴隶制并拖累南方经济社会。福格尔认为无论是为奴隶制辩护的还是抨击奴隶制的,都是种族主义者,废奴运动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帮助下更为乘风破浪。那为什么之前的历史学家从来不这么认为呢,福格尔指出种族主义是美国史学界乃至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条红线,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从当时到现在,抨击奴隶制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甚至有利可图,但是为奴隶制辩护则要付出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巨大代价。
福格尔是以一个制度视野和比较视野来重新审视奴隶制经济,他并不是说奴隶制有多好,而是在另一个意义上指出,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也就是法律和社会层面双重的种族主义歧视,如果没有奴隶制,奴隶将会生活得更糟糕。而相比而言,奴隶制经济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理性制度,不管是与同时代的北方工人还是自由黑人相比,奴隶都拥有更明晰的产权制度,更有利和有保障的个人收益。这当然不是说奴隶制有多好,而是说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压迫和日益加重的种族主义歧视会有多糟糕。南北战争后自由后的奴隶反而生活得比之前更为糟糕。
非常不幸的是,福格尔的这些结论,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情况下,也即是这样一种制度制约下,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理解为“福格尔认为奴隶制很好,甚至是在推销奴隶制”要比“福格尔抨击奴隶制的废除是将黑人进一步带入种族主义的深渊”成本低的多,人们也更容易或者说,更愿意站在道德高地批评福格尔“为奴隶制辩护”。这也是《十字架上的岁月》带来计量史学地震的直接原因,福格尔必须要为他“为奴隶制辩护”而辩护。
五、争议与回应
学界不少人还记得福格尔刚刚开始其经济史学生涯的样子,1964年晚冬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召开的计量史学会议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头发凌乱、衣服皱巴巴,站在黑板前巧妙地回避尖锐的问题的一个不能更像美国青年学者的典型美国青年学者。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他在铁路经济效益问题上的里程碑著作,已经声名鹊起,虽然也带来一些方法论上的争议,但是人们不会想到十年后他竟然会出这么一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著作:“什么,为奴隶制辩护!?”
针对福格尔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福格尔是带着怎样的历史观念去看奴隶制的,和福格尔对于奴隶制经济的各种估算有没有问题。前者的批评大多认为福格尔估算出奴隶制是有利润的,但是这个利润要看是给谁,而且奴隶制经济社会运行中也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个人压迫等道德问题。后者则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还敬计量史学,区寻找更多的或者是与福格尔相异的证据,用相同或者不同的数理方法区推算奴隶制及奴隶的经济状况。
批评的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罗伯特·福格尔和杰弗里·埃尔顿带有争辩性的合著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Fogel R W, Elton G R. Which road to the past? : two views of history[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和赫尔伯特·古特曼的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s[ Gutman H G.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埃尔顿是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并且坚持最为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他与福格尔的合著就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埃尔顿更看重历史学家长期坚持的历史正义,而福格尔则更倾向于用价值中立的手段去研究历史。古特曼在书中则直接批评福格尔玩的是一种数字游戏,福格尔有限的证据只能说明奴隶主的鞭子没有打在这些奴隶上,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他奴隶的情况,而且福格尔把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放到奴隶主和奴隶身上,古特曼认为是尤为可笑的。
福格尔在15年之后,用其另一部书来总结和回应他对奴隶制经济的研究和由此带来的质疑: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Fogel R W.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M]. WW Norton & Company, 1994.]福格尔首先是对之前的计量结论作了重新计算和检验,认为之前的结论并没有太多差别,并在书中回应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强调他同样了解并也发现了大量存在的奴隶主暴力和奴隶悲惨命运的史实,但是他没有写入《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中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是如何被制度因素所瓦解的,而这种制度随后又对于瓦解后的经济系统内各要素产生负面影响。正如福格尔在获得诺奖后面对记者的谈话中所言,“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这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我并不认为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 张宇燕. “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J]. 读书, 1994(3).]奴隶制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系统,但是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轻易将其废除而没有妥当的善后安排话,道德并不给人面包,或者说,道德本身会变成不道德。
六、四十年以来
福格尔随后的研究虽然不再关注奴隶制经济学,但是他对于奴隶制特别是奴隶个人生理与营养状况的研究,使他的兴趣主要转移到健康经济学以及技术生理演化理论(technophysio evolution),即讨论技术进步与人类生理机能改善的机制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技术生理演化,即研究人的身高、体重、能量摄入等,广泛地出现在人口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对于考察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显著意义。福格尔开创性地进行一种系统研究,即尝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物种进化(演变)的关系。[ 如Bengtsson T. Life under pressure: 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1900[M]. Mit Press, 2004也是继续此种探索。]
而在于奴隶制经济本身上,福格尔的颠覆性研究虽然饱受争议和质疑,至今也已成为该问题上的主流认识。笔者找到了国内翻译的四种流行的美国经济史论著或者教材,分别是杰里米·阿塔克等著《新美国经济史》(第2版)、斯坦利·恩格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乔纳森·休斯的《美国经济史》(第8版)、加里·沃尔顿等著《美国经济史》(第10版)[ 即杰里米, 阿塔克, 彼得, 等. 新美国经济史[J]. 罗涛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斯坦利. L· 恩格尔曼, 罗伯特· E· 高尔曼著, 蔡挺 ,李雅菁译. 剑桥美国经济史[J]. 2008;(美)林斯, (美)凯恩, 邢露. 美国经济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美)沃尔顿, (美)罗考夫, 王珏. 美国经济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在奴隶制经济问题上基本上都接受了福格尔的观点。阿塔克版原封不动地以福格尔的几个修正性观点作为奴隶制一章的小标题,恩格尔曼本来就是福格尔的合作者,他的书中保留对于奴隶制经济的几个客观结论但不作进一步结论,休斯一书中非常有意思地展现了福格尔引起的争论,并客观地表示福格尔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沃尔顿将福格尔的结论作进一步引申,即正是由于奴隶制的有利和顽强,才更需要一次外在的南北战争将其灭亡。
福格尔的《十字架上的岁月》一书曾经一度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随着争议之硝烟散去,我们在今天也许可以回答标题中的问题,如果奴隶主的鞭子能抽打出金块,经济史家会不会为奴隶制辩护:假如金块也属于奴隶的话,或者说这个“奴隶制”是在另一个意义层面上的话,经济史家还是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