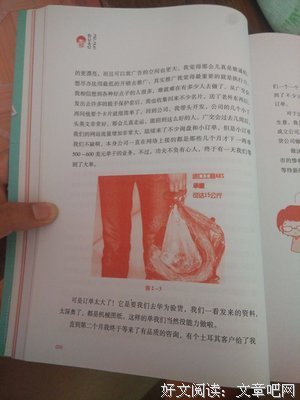
《大小舞台之间》是一本由钱理群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30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07-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小舞台之间》精选点评:
●盼望的“日出”到来了,可曹禺却没能走出恐惧的城堡阴影,甚至主动放弃了赖以成名的普遍的人性怜悯。当剧场中雷雨、日出、原野的郁热乃至北京人、家的沉静统统被广场的喧嚣所取代时,背叛了亚里士多德的曹禺只会走向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遗憾地错过了又一位本可继续攀登高峰的大家。论证史料翔实,目光老道,彰显大师功力
●6/10,主要注重的是曹禺写作上的变化,接受史,所以涉及很多导演、演员了
●1.从中窥见了许多与吴晓东相似的话语痕迹,发现了钱吴师徒二人间的渊源关系,重视从生命意义上进行文本分析,相比较而言,吴晓东的文本分析要更为细致;2.诚如评论中所说,钱对知识分子精神史太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自己的论述框架,因此部分分析有些生硬了;3.九十年代初的著作,可以视为钱的学术生长期的一个小节点。
●钱先生论曹禺的妙处,尽在他对于作者初衷、转变与凝滞的抵牾,体会之深、感叹之切、厘析之彻~有多少犹如万先生这般被时代和舆论蒙住双眼与声喉的天才啊,他们胆怯、敏感而懦弱,但同时,他们对于人的洞察,也是最为犀利的~
●我的潜在期望里是钱老把“大小舞台之间”诠释地非常迷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境况?然而没有,略遗憾啊。振奋我的依旧还是黄永玉画家的那封信,“你多么需要一点草莽精神”。
●钱理群老师真可称得上是用生命著书,治学到此境界,唯有崇敬二字。
●“真实与真诚”反而要到“假”的戏剧里才能寻找到,真的人生社会却充斥着作戏与虚假。想起了我的毕业论文素材
●比较难读,但是好书。
●钱老的书,曹禺的剧。以及当代的文学史。
●观学究的文采展现。
《大小舞台之间》读后感(一):未解决
跟随曹禺先生的创作历程,也似跟随近代中国的社会历程、戏剧发展历程。生命从郁热到沉着,从诗一样的美好向往,到丧失早年的堂吉诃德气。时代成就着一个人,也局限乃至摧毁着一个人。 回过头来看,书的阅读线索竟是从最初的词条好奇,梁启超的功利文学观与王国维的超功利文学观开始串联起的。相对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处于一条线的两种极端的思想在同一时代熠熠生辉,没有相互消磨,反而共同丰富了我们当下能够接触到的文学创作。 当我们站在当下的视角去俯视追溯历史时,理解观念的博弈是为了创造新知以丰富世界而不是强调对错以狭隘视野,幸运的我们就已拥有了对多元话语包容、保持平和的权利。(如果视而不见是多么可惜呀) 未解决疑问: 1.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如何找到平衡?面对共性中的个性,是否有人做出不同的选择? 2.作品生命形态与作家生命形态,作品生命形态与读者生命形态,生活事实与感觉与表现是怎样达成对立统一的? 3.不同时代下同一作品,不同社会情境引导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结果,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倒推,从对待剧目设计的方式推及大致的历史观念情境?现在我们在演什么?演的方式?这背后是否也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取向、意识内核与时代故事? 附最近很喜欢的一首诗,戏剧剖析的整理,合情合景。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共勉。
《大小舞台之间》读后感(二):折翼的鹰
记得去年寒假读了《北京人》,战线拉了一年,到这个寒假,总算把曹禺专题读完。 前后读了剧本《北京人》《日出》《原野》《家》,加上数年前也算读过的《雷雨》,再加上理论著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对曹禺戏剧有了大致了解。 读得粗糙,剧本走马观花,书看到后面,对前面的观点就有些模糊,后来才对没有做笔记后悔不迭。 理论著作有解释梳理,提纲挈领的作用,对理解剧作家、剧本乃至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史大有裨益。看到钱理群先生写的后记,也对这本书写作的脉络有所了解,更能掌握书的内容。 简单来说,钱老提到写作该书的重要思路——一是从作者本身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他、理解他的戏,二是透过曹禺这一代表剧作家,折射整个中国近代戏剧发展史。 作者用春夏秋冬的季节代表曹禺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夏”是《雷雨》《日出》《原野》,春秋是《北京人》《家》,中间夹杂着受政治影响间断创作的其它戏。创作过程中,剧作家也经历着从郁热到沉静的转变,不断追求新的创作高峰。 读完书,我对曹禺这一早有接触却距离遥远的剧作家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印象深刻的是,曹禺说自己的戏“一贯是很浓”,然而演绎的演员要尽量收着演,挖掘内心的复杂深刻,观众也要保持一定的观演距离,不要被浓烈的情感裹挟着走,而要在上帝视角上,体会到戏剧的深意。这浓烈也是和他郁热的性格贴合的。浓烈中包含着中国人的情感成分,读起来让人亲切,也酣畅淋漓。 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天才的创作能力和卓越的艺术追求。他在喝彩声中不断追逐创新,有结构上的、题材上的、语言上的,让剧作不断达到新的艺术成就。 他的剧本读起来如诗如画,大段的小说般细致、渲染力强的描述常常让我担心怎么搬上舞台。到关键处,语言和氛围的统一,让剧本的内涵意蕴似乎强烈得喷薄欲出。我想这也是曹禺文学成就的表现。 而这个戏剧天才创作生涯的后半程,却实在令人深感痛惜。有个人的原因,但占绝大部分的是时代的摧折。思想的枷锁留下深重的烙印,让天才萎缩乃至湮灭,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书中曾说《日出》中的陈白露不是习惯笼子的金丝雀,是折翼的鹰。纵然可翱翔长空,却不得不委顿困囿。曹禺最终也走向和他的人物一样的命运。 但无论如何,曹禺无愧为中国近代戏剧大师。 什么时候重读一遍《雷雨》吧!
《大小舞台之间》读后感(三):被淹没的声音
曹禺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对来探望的吴祖光先生讲:我这一辈子,太听话了。初初在《读书》上见到这段文字,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读完了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才真正体会到曹禺先生话里心里的沉痛。
这本“新论”,新就新在它不是像钱谷融《〈雷雨〉人物论》等那样详细分析作品本文,而是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曹禺的创作生命和时代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纵深的考察,描述曹禺的创作是怎样在自身成为规范的同时也逐渐被纳入时代的戏剧规范,他内心的“小舞台”是怎样逐步和时代的“大舞台”溶为一体的。
起初,曹禺自己的声音是相当强大的。《雷雨》和《日出》就与那个炽热的时代当下的主题相距甚远,这在现代文坛上最善于紧跟时代风潮的戏剧门类中几乎绝无仅有。这两出戏体现的完全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禺自身对艺术的追求,这时候,他对“时代对戏剧的要求”还一无所知。
应该说,曹禺是幸运的。他没有去走学医从政一类的弯路,一开始就选定了戏剧为终生不渝的事业。而且由于他的天才,最初两部作品便大获成功并迅速进入经典。这些本来都非常有利于他对自我的坚信和坚持。可惜太高的起点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曹禺已经习惯于做“时代的骄子”,甚至难于忍受哪怕是一时的冷落。所以,在过于“超前”的《原野》受到的评价普遍偏低之后,曹禺开始按时代的路向调整自己的步伐了。
为了表明对“广场艺术”的认同,曹禺写出了《黑字二十八》、《蜕变》这样近乎幼稚的政治剧。不过此时的曹禺仍然保持着充分的自信。他自己的声音仍然在时代的声浪中若隐若现。《家》削弱“反封建主题”转而礼赞青春和爱情,《北京人》对抗战主题的远离,都表明曹禺并不愿意做一个席勒式的传声筒。与周扬等左翼权威评论家的宏论相比,他更看重观众对他的剧作的欢呼,将之视为自己创作生命的支柱。
所以,当五十年代被告知他的得意之作并不能为新时代的观众主体──工人、农民所接受时,曹禺受到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他天真地相信了那些自称代表人民的评论家发出的声音确实代表了观众。他的自信心终于完全丧失了。除了战战兢兢的《明朗的天》,曹禺所能做的只是带着忏悔的心情对旧作进行大规模的“自戕”。鲁大海成了共产党员,方达生变了地下工作者……曹禺努力地修正着每一个音符,让它们合上新的拍子。他自己的声音终于完全淹没在时代的合唱之中。
据曹禺女儿万方回忆,曹禺最后一次看《雷雨》后急切地问她:怎么样?怎么样?万方说:“他想听的不是评论家的批评,而是普通观众的评价:'还行!''不错。'”联系他对吴祖光说的话,我们不难体会这位现代戏剧史上唯一可以称为大师的剧作家晚年的复杂心境。整整五十年,在大时代的喧嚣声中,年仅23岁就能写出《雷雨》这样惊世之作的曹禺竟不曾拿出一部真正像样的剧作,发出一点儿自己的声音!甚至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无法完全拾回当年那种“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的自信。
然而这一切是不应怪责曹禺的。像他这样一个热爱观众的天才艺术家,他怎么敢、怎么能去对抗定于一尊的“时代的声音”?
“人已彻骨,天尚含糊。”今年也已是老舍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了。这三十年于曹禺先生意味着什么呢?呜呼,哀哉!愿曹禺先生安息。
《大小舞台之间》读后感(四):曹禺之殇
春节前以出乎我自己意料的速度看完了钱理群20年写成的一本书《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于生命的复活。”
曹禺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但是很可惜并没有达到他本应达到的高度,他因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被政治运动束缚住了思想。
他的作品一方面在红红火火地上演着,另一方面却被不断地曲解/误解,不断被人为地重新解读、全新演绎。政权的更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官方审美标准不断形式化与公式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排斥慢慢使得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曹禺一点点失去了自信,直至全面、彻底、心甘情愿地否定自己。曹禺为了适应新的接收对象——工农群众的需要而自戕,可悲的是,他并不了解工农群众的真正意愿,只能按照自称是工农群众代言人的理论家对与中国社会矛盾性质、革命对象、动力、前途的分析去修改自己的旧作。曹禺所特有的极其光彩的个性化、形象化的语言消失了,代之以时代的、逻辑的、公式化的语言;他用自己的手,自愿的、不无真诚的,将自己的戏剧生命的创造砍杀了。
五六十年代,曹禺的戏剧表演完全被纳入到时代意识形态体系中,被高度政治化、时事化,打上了深刻的社会和阶级烙印,原本活生生的具有复杂心理面貌的戏剧人物纷纷被去个性化、去欲望化、英雄/妖魔化、简单化、浅薄化、庸俗化、程式化,至此,曹禺的戏剧已经完全去艺术化,变成了官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宣传工具,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直接助手”,处处显示“善良与阴毒,纯真与丑恶,正直与邪私”的鲜明对照,爱憎分明。
极左思潮是一种对作家外在束缚的紧箍咒,更可怕的是,经过长时间有计划的灌输,极左思潮逐渐内化为曹禺和他同时代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自己的观念,以至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内在要求,不用别人念咒语,自己也会念,成为一种自我限制。这是曹禺心灵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最悲凉的一页。曹禺说:“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法西斯思想专制的可怖、可恶与不可宽恕正在于它以似铁的无情力量将人的尊严、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它以宗教般的幻术,把犯罪感渗入到自我意识中,不仅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残杀,而且制造人的精神分裂,让人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审判、自我否定,以至于想曹禺那样否定了自己做人的资格和权力,仿佛自己只配动物般地活着。而这类精神折磨首先施加于曹禺这样最杰出、最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脆弱、最需要小心保护的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摧毁一个民族的精英可以摧毁整个民族的,曹禺的悲剧,正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大不幸。
曹禺从根上就不是鲁迅那样的强者,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天真,以及他的人道主义过分善良,使他不能彻底“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总是不断地沉迷于自造的梦境中;他也缺乏鲁迅那样彻底的自我否定精神,他太爱护自己,更确切地,他怜悯自己,也就无力战胜自己。曹禺是个弱者,又是天才、艺术家——他的悲剧就在这里。
使人成为人
把文学还给文学
让艺术自由呼吸,追求纯粹的美
让“工农群众”甩掉理论家,自己代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