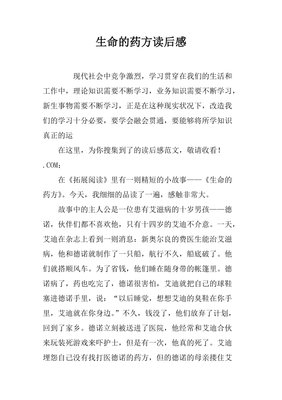
《复杂生命的起源》是一本由[英] 尼克·莱恩(Nick Lane)著作,后浪丨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4.00元,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一):复杂生命的起源
1. 什么是生命
写的没什么章法,感觉作者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任何有条理的思路,且很冗余,看完了感觉并没有解释,到底什么是生命,目录结构应该拆分的更细致,来表达清楚结构与条理。看完总结一下就是,作者也不知道什么是生命。
2. 什么是活着
2.1 能量,熵和结构
人体内不断的在发生反应: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等。一切变得越来越有序,自身的熵变低,并向环境释放热量,让环境的熵变高。
2.2 生物能量奇特的狭窄范围
ADP + P_{i}+ 能量 ⇋ ATP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二):願質子動力與你同在
花了一周,認認真真把Nick Lane的「複雜生命的起源」讀完,誠心向所有對演化和基礎生物學感興趣的朋友(換句話說,任何對「為什麼我們會有線粒體?」「為什麼真核細胞有兩性繁殖?」「為什麼細菌和古菌都那麼小?」的朋友)推薦這本書。還是要再次感謝譯者嚴曦,如果沒有那麼高質量的翻譯,這本書的可讀性可能會大打折扣。
首先,這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書中涉及到的化學和生物學術語很多,但好在Lane在引入任何術語時都會加以嚴密的解釋,且嚴曦老師的翻譯嚴謹認真。在緒論中Lane說道:「我希望所有感興趣的讀者偶爾查閱相關詞彙後都能讀懂本書。」有些人會說這是「勸退」,但我認為這是Lane在像所有懷有興趣的讀者拋出一個挑戰:接受這個挑戰,宏大的生命史詩就大門敞開。
Lane在書中提到了許多讓我印象頗深的點,受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列出,就只舉2個例子。第一,為什麼所有的呼吸作用(包括古菌、細菌和真核細胞的線粒體和葉綠體)都要用到質子梯度(proton gradient)?Lane認為這與生命最初的演化有關。最初的演化發生在鹼性熱液噴口(而非海底黑煙囪)內,因為生命的本質是經過還原的碳,而還原則需要將電子從供體(在海底為氫氣)中傳遞到受體(在海底為二氧化碳)上。這一反應在同一pH值的環境內並非自發,但鹼性熱液噴口提供了一個部分由硫化鐵構成的薄膜,隔開了pH值相差3度以上的兩個環境,使得剝離氫氣電子並送給二氧化碳的反應能自發發生。如今,所有呼吸作用都使用與此完全相同的機制。
第二,原核細胞(細菌和古菌)無法長得如真核細胞那麼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真核細胞(由古菌吞噬細菌後,經過內共生形成)在演化的歷史中獲得了線粒體。細菌和古菌需要在自己唯一的細胞膜上進行質子梯度生成,從而製造ATP(儲存能量)。為了保證細胞膜的良好運行,它們需要將自己的基因組複製幾百次,分開放置於靠近細胞膜的各處(這樣,一旦出現問題,就可以迅速生成補救所需的蛋白)——複製幾百次的這個過程十分耗能,也就讓它們沒有能量去做別的事情,更不用說擴展基因組了。而擁有線粒體(專門的呼吸作用場所)的真核細胞不一樣,只需要一個基因組即可,這也就意味著它們可以極大地擴展自己的基因組,從而發展出巨大的形態多樣性。
這本書還有很多寶藏可供挖掘,我一言兩語實在無法說盡,只能盡己所能推薦這本書了。下面正打算繼續拜讀Lane的「能量、性、死亡:粒線體與我們的生命」,感謝這樣偉大的生物學家。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三):生命
关于这个 要如何追溯呢
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和生物化学学会奖得主全新力作 从生物能量学新探简单细菌一跃变成复杂真核细胞的内共生事件 追问40亿年间生命到底为何这样演化 ◎ 编辑推荐 ☆一次异乎寻常的偶然事件, 一段走向必然的演化路径 ☆地球生命是否是宇宙中绝对孤立的存在? 星际间是否还在默默推进其他演化试验? ☆从回顾式的历史描述,到可验证的科学预测, 一场不亚于又一次生物学革命的生命起源雄辩 ◎ 内容简介 地球生命在地球形成约5亿年后就已出现,然而在这之后的20亿年内,生命一直停滞在简单的细菌水平。在大约20亿~15亿年前,一种拥有精细内部结构和空前能量代谢水平的复杂细胞一跃而出。这份复杂性遗传给了大树和蜜蜂,也遗传给了人类中的你和我。我们与蘑菇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细胞又如此相似。从有性生殖到细胞衰老再到细胞凋亡,复杂生命共有的一套细胞特征在不同的物种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程度。生命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在4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从简单的细菌到令人敬畏的复杂生命,这样的演化飞跃事件为何只发生了一次?不得不承认,在生物学的核心地带,横亘着一个巨大的认知黑洞。 生命究竟为何沿着这么令人困惑的路径演化?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从生物能量角度,交给了我们一把有望解开生物起源之谜的钥匙。怪异的生物能量生产机制从各方面限制了细胞,而一次罕见的一个细菌入住到一个古菌体内的内共生事件,打破了这些限制,使得复杂细胞的演化成为可能。看似偶然发生的单次事件,却因为能量的约束而必经一种演化历程,许多最重要也最基础的生命特征,也由此可以通过基本的生物化学规律进行推断。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取舍权衡生殖力和年轻时的健康,换来衰老和罹患疾病的代价。生命的起源、人类的健康乃至生死,都可以从能量角度重新发问。 ◎ 媒体推荐 对生命起源令人叹为观止的追问。这本书让我折服。 ──比尔·盖茨 近年来出版过的最深度、最有启发性的生命史著作。 ──《经济学人》(Economist) 莱恩的理性推论如果是正确的,那将和哥白尼革命一样重要。 ──彼得‧福布斯(Peter Forbes),《卫报》(Guardian) 一本大胆、雄辩式的、充满自信的作品……莱恩是很稀有的物种,一个可以用明晰、清楚的文字解说生物学中令人困惑的复杂性的科学家。 ──亚当‧卢瑟福(Adam Rutherford),《观察者报》(Observer) 几乎快要成功地解开生命的演化之谜,这本书的深度可以对任何一个古老哲学家的大脑产生冲击。 ──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泰晤士报》(The Times) 关于生命新理论的绝顶高超的综合。 ──克莱夫‧库克森(Clive Cookso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创新科学的杰作。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展望》(Prospect)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四):《复杂生命的起源》
最终还是自己买了这本书,作为寒假的第一本读物。在豆瓣上的第一篇书评也献给这本书吧。
不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其实最初读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本书的受众。作为一个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尤其是自己学校是国内少有的在通论课中便以演化为主线,介绍到的研究前沿到white smoker的程度,我仍然感觉阅读这本科普书颇具挑战性。“如果你熟悉科学术语,它们就能承载更大的信息密度。这样的交流方式能把我们直接引到未知的边缘,让我们感受科学的乐趣。” 作者在书中大量使用的科学术语很可能会劝退那些没有专业背景的人,但是只要你具备一定的生物学基础,对这个学科提出并解释问题的逻辑有所了解,那就可以从中获得启发,感受到作者在热切地向你展示着自己的思考,并且期待从你那里得到同样兴奋而激动不已的回应。书后附录的术语表也很有价值,不是教科书上死板的释义,而是作者从有助于理解的角度对名词进行的简单解释,如果对个别概念感到困惑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简明的术语表。
本书主要就两个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探讨。第一是最原始最初细胞的形成(追寻到碱性热液喷口),第二是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的“跃升”。作者大胆地将目光投向这些科学认知的“黑洞”,基于缜密的逻辑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抓住每个穷幽极微的科学细节,并给出极为新颖的,颇具洞见的解答。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会迷失于反复的追问,假设的崩塌与重构,还有很多读完却仍难以理解的困境,但是作者有力的阐释给我带来豁然洞开的体验,虽然常常并不能完全理解或信服,但仍深受启发。
至少在国内的生物学教育中,演化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视角。初等教育中尽管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但也只是一个模板,往往还是以阶梯式上升而非系统发育的视角来解释问题。高考生物中的问题大多也只是为了设问而设问,对于演化观点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最表层。到了大学,在很多院校开设的相关专业,宏观生物学的教育往往是缺失的,即使有,教材也滞后了几十年,很少能涉及演化这个领域的新进展,忽视了这个百家争鸣、新见频出的活跃领域,导致相关专业的学生也往往缺乏演化的视角。这本书非常难得的一点就在于它为很多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演化视角的、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当我们重新从宏观的角度,从能量的观点,再次去看待那些我们已经熟习的生物学事实,得到的震撼和启发还是很多的。
这本译作是当下中文科普领域在演化生物学方向的一本极具前沿性的佳作。我甚至怀疑它有些太过独特,考虑其前沿性、创新性和思辨性,想必受众也不是很广,能回应作者炽烈热忱的读者也不会很多。作为一个对这一领域怀有兴趣,虽基础浅薄但仍有志于探索的年轻人,我期待未来能在更深地理解相关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这本书,同作者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和更进一步的讨论。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五):覆载天地,刻彫众形
(这篇本来是转发抽奖的文案,但不小心写太长了……)
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彫众形而不为巧。——《庄子 大宗师》
我虽是文科生,好歹也是读过《生机勃勃的尘埃》、《孟德尔妖》和一点点玛古丽斯(Lynn Margulis)的内共生理论的,就这样才能勉强阅读(好像无意中凡尔赛了)这本书。
简单地说吧,这本书里充满了微观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术语,剖析的大多是一些发生在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事件,作者虽然说“我会尽量写得简单”,但在满篇的“碳”和“呼吸作用”面前,我还是走神到了《鬼灭之刃》……
说这些,绝非要劝退读者,而是要说明,这是一本适合特定人群的书,门槛比较高。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译者严曦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翻译。
还是说说这本书讲了什么吧。作者莱恩(Nick Lane)企图解决两个问题:“生命是怎么来的?”和“复杂生命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问题非常哲学,哲学的意思不是说高深,而是说简单。它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朴素的问题,人人会问。记得几十年前研究生命起源的科学家米勒(Stanley Lloyd Miller)访华,有个中国作家非常自信地,跟米勒阐述了他对生命起源的答案——因为宇宙是男的,地球是女的,所以诞下了生命。当然这对找到答案并没有多少帮助。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硬核了。复杂生命,这里的意思是说,变形虫、树、蘑菇、蜜蜂、人类这样的生命,拥有非常复杂的细胞结构,跟细菌不同,细菌的细胞非常简单。而自然界似乎没有复杂细胞和简单细胞之间的中间阶段。复杂细胞不可能从天而降,所以它是怎么来的呢?
莱恩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涉及生命的一个基本属性:能量。他介绍了生命通过能量运转的基本原理,这是个非常繁杂的过程,为了不让你们走神,我在此不赘述细节。生命像发动机,需要能量才能运转。我们知晓了生命运转的方式,就大概可以猜想,在三十多亿年前的地球上,一泡化学物质汤里,怎样组装出最原始的“发动机”,从而形成最古的细胞。
而在大约十几亿年前,这台“发动机”效率的一次猛然提升——同样,细节就不赘述了——最终催生了复杂的细胞。这就像瓦特改良蒸汽机,催生了工业革命。
作为科学知识,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单单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心悦诚服地表示,这是一本好书。
给我震撼,在我心中久久回响的,其实是一个非科学的判断,一个书中并没有言出的概念:“生命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奇迹啊!”
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些强大、美丽或者聪明的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是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伟大的奇迹。在万古的洪荒中,三十多亿年的生命史里,每一粒细胞的运转,都是伟大的奇迹。我们得以了解这一奇迹,并身为这一奇迹的成员,仅仅是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旌摇荡,久久不能平静。
而这个奇迹是不需要言说的。它没有向宇宙打报告“因为所以,地球需要生命,请审批”,或者揪着人类的耳朵喊“看,我多伟大”。它只是碰巧出现了,然后遵循熵和演化论的原理,演变至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一切的伟大、美丽和复杂,都出现于此,生命不问为什么,它只是存在了,而我们是否为之鼓掌,是我们的事。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六):《复杂生命的起源》译后记
认识尼克·莱恩是从《能量、性、死亡:线粒体与我们的生命》开始的(台版译本,Power, Sex, Suicide : Mitochondri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被这本书彻底迷倒之后,我又找到了它的“前传”:《氧气:改变世界的分子》(Oxygen : The Molecule that made the World)。前两部书,加上拙译的这第三本,构成了莱恩以线粒体为中心的能量生物学三部曲。这是一座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的丰碑。
尼克·莱恩的第一个大陆简体译本是《生命的跃升》。在我看来,书是非常精彩的书,但在他迄今为止的四本重量级科普作品中,是最没有代表性的一本。
因为他的力量所在,并不是花团锦簇的诗集式作品(这方面的巅峰,请读马特·里德利的《基因组》);也不是宏大的全景视野以及科学人文的无缝连接(这种经典请读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他的语言“穿透”技巧(对非专业读者的思维而言)不是第一流的,比不上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那样娓娓道来的本事。他没有霍金神一般的光环,也没有阿西莫夫大祭司一般的庄严。
他虽然也变得越来越好斗,不断挑战伪科学、谬论乃至科学界的偏颇现象,但还赶不上道金斯的牙尖爪利。他的文笔起点相当高,但这些年来没有太大的进步。纯论科普作品的文字成就,我最欣赏的反而是系列第一本《氧气》。因为它在文笔、思想和科学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在我看来,《氧气》就是玉一样的文章,后面两部越来越水晶。这第三部,简直是水晶制成的投枪。
这才是莱恩的力量所在:极端锐利的思想,以穷幽极微的科学细节和深厚的思辨功底大力投出,冲击读者的头脑。翻译《复杂生命的起源》的艰苦过程,再次印证了我从初见以来对他的认识:二十一世纪以来最独特、最具冲击力的科普作家。
我最喜欢豆瓣网友毛樱桃对他的一句话简评(选自豆瓣Oxygen短评区):“这人是真不拿读者当外行啊,什么专业名词都往上招呼。头回被一本科普书折磨得死去活来!”
是的,这就是莱恩。在本书的绪论中他还记得你是个非专业读者,装模作样说:我会尽量少用行话,多打比方。术语很简单的,多看看就懂了。接下来开始讲历史,就不太对劲了。怎么看,怎么像一章生动活泼的文献综述。进入戏肉章节,名词们开始蜂拥而至。逻辑之复杂纠结,各方观点之此起彼伏,你会开始怀疑,这到底是论文还是科普?
这是一个精神动物,一个偏执狂。一个蝼蛄掘地求长生的探索者,掘一阵就要抬头看看天上的星辰;一位怀着赤子之心的熊状大汉,相信读者对生物化学反应原理和他有同样炽烈的好奇心。
相信很多读者是跟着比尔·盖茨的年度推荐找到了这本书。然而盖茨在此的意义不是他有钱或者视野高妙。意义在于,盖茨有世上罕见的条件和心境,可以客观真诚地道出:如果困在荒岛上过一年,只能带五本书,那么什么书才能和他的大脑party至高潮。大脑这个东西很贱,就需要受折磨,才会分泌让你欣快的物质。大脑喜欢两种毒品:新的信息;严整的逻辑与秩序。莱恩的作品从不缺乏这两者。在《复杂生命的起源》中,两者都呼啸而来。
这本书雄心勃勃。它讨论两个生物学中皇冠明珠般的课题:拥有线粒体的真核细胞(即“复杂生命”)是怎样起源的,以及生命本身是怎样起源的。莱恩给出的回答当然是一家之言。然而他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颠覆,逻辑之严整,证据之充分,对读者的期望之高,在我几十年的科普阅读中都是独一份。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差不多被他说服了。
于是我惶然提起译笔,再一次接受他的折磨。
——严曦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七):什么是生命——《复杂生命的起源》出版后记
从《氧气》到《能量、性、死亡:线粒体与我们的生命》再到《复杂生命的起源》,作为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方,能够出版尼克·莱恩这个以线粒体为中心的能量生物学三部曲中的任何一部,都是莫大的荣幸。“自达尔文以来最好的生物学书籍,本质上都是一场强力的辩论。”可以这么说,在现世的所有生命科学科普写作者中,尼克·莱恩是极有能力接过这一传统接力棒的一位。
和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时一样,尼克在论证如何可以通过能量探究生命起源的写作中也要面对修辞上的挑战:如何把一个新想法阐述得像每个人都听过的常识;如何把一条具有潜在颠覆性的理念剖析得像作者本人脑中构想的一样理性和直白。前者包括在生命起源研究发展到现在积累下的所有事实证据中厘出演化的基本规律(与达尔文背负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遗产)——这甚至本身听起来就像是生物学研究中的“异端”之见:难道生物学可以像物理学一样做出可验证的预测吗?而后者除了包含作者为自己定下的雄心勃勃的写作标准之外,还对读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诚挚邀请读者一同进入这场雄辩的尼克·莱恩恰恰不是站在知识和修辞的傲慢视角之上,而是作为信使站在生命起源最前沿研究和大众读者之间,发自内心地相信每个人只要稍加学习相关知识,就可以共同见证这场精彩至极的生命起源演化推理。这种体现在不强降阅读“门槛”的认知态度上的平等,是出版方理解的“科学普及”中“普及”的要义所在。
要跟上尼克的推理,关键之一要把握书中对环境与基因的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把新达尔文主义简单地概括为对环境和基因的二分——也就是说把环境视为自然选择的施予者,基因是被施予者——那么,尼克对环境和基因的认识,更接近于美国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陆温顿(Richard Lewinton)。他们都认为:没有环境就没有生物,没有生物就没有环境,不能简单地分离二者。所以,尼克能把“能量”注入薛定谔的“什么是生命”之问,把这个经典的提问转化成“什么是活着”。活着意味着生长与繁殖,这两种生命过程都受制于能量。而能量的实质在于环境,在于生命体结构与环境的关联,在于物理条件对细胞结构和演化的约束。
基于这个逻辑,尼克·莱恩不同意薛定谔“生命抵抗熵”的信条。在尼克看来,生命的组织和有序性,以增加环境的无序性为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的数值更高。而有序性的达成有赖于对能量的消耗,进而形成了一种不自然的状态。限制这一演化路径的,正是能量本身。如果该论证成立,那么宇宙中有类似环境条件的其他地方也应该上演着一幕幕能量限制演化的大戏。
如果我们解开了地球生命为何如此的谜题,也意味着可以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找到生命。这不仅能为“搜寻地外文明计划”助力,为证明“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增添更扎实的科学基础,也突破了“生物学研究无法做出预测”的学科桎梏。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是否存在创造地球生命的基本法则?尼克认为,如果我们把对生命的理解局限在 DNA 的信息视角之中,那我们永远在记载过去、记录环境对生命的影响;可是,结合能量理解演化,我们就能找出促使生命演化的环境。这是对生物学研究的重新导航!
尼克在《复杂生命的起源》中多次提及这种非二分的视角,也清晰地体现在本书的核心理论基石“化学渗透”中。提出这一理论的英国生物化学家彼得·米切尔正是因为把生命与环境结合起来思考,从而获得启发,构思出了化学渗透。尼克在多个地方反复引用米切尔那段著名的话:“我无法脱离环境来考虑生命……在思考方式上,必须认为两者是同一连续体中旗鼓相当的两相,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由膜来维持;膜既隔开生命和环境,又让它们紧密相连。”
“化学渗透”和彼得·米切尔,也是引导出版方找到本书译者的航标。2012年,有一位网友在豆瓣小组科学松鼠会读者花园中发布了一篇《二十世纪最“反直觉”的伟大生物学发现:化学渗透》的原创长文,写作风格、笔力和对化学渗透的理解都很像会写中文的尼克·莱恩。出版方后来真的联系到了这篇长文的作者严曦。能让系统熟悉尼克·莱恩作品的译者翻译本书,实在是书的幸运。同时,译者——也作为一个样本读者——基于尼克·莱恩作品的原创让人不禁想起美国作家H. L.门肯(H. L. Mencken)。门肯在讽刺自己那个年代纽约的绝大多数所谓的音乐爱好者时写过: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总会尝试创作音乐。希望本书也能遇到和收获这样的爱好者。
《复杂生命的起源》读后感(八):来自深海——40亿年间生命为何如此演化?
在日本伊豆小笠原群岛海域某处超过 1 200 米深的海底,有一座名为明神海丘(Myojin Knoll)的火山。十多年来,一组日本生物学家在这片水域拖网打捞,搜寻有趣的生命形态。据他们报告,一开始并没有找到什么让人意外的东西,直到 2010 年 5 月,他们捞起了一些附着在深海热液喷口附近的多毛纲蠕虫。有趣的并不是这些蠕虫本身,而是蠕虫身上的微生物—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细胞。它乍看起来很像真核生物,但是仔细观察之后,就成了最耐人寻味的谜团。
真核生物的字面意思就是“真正有细胞核”的生物。捞自明神海丘的细胞,其中有个结构粗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正常的细胞核。它还有层层叠叠的内膜系统,也有一些内共生体(可能是氢酶体,一种从线粒体演化而来的构造)。它与真菌和藻类等真核生物一样也有细胞壁,但是没有叶绿体。这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它来自漆黑的深海。细胞的尺寸较大,长约 10 微米,直径约为 3 微米,体积大约为大肠杆菌等典型细菌的 100 倍。它的细胞核也很大,占了细胞差不多一半的体积。表面上看,这个细胞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分类,但它显然是真核生物。你或许会想,只需要花点时间进行基因测序,就能在生命树上找到它合适的位置。
图为来自深海的独特微生物。
这是原核生物还是真核生物?它有细胞壁(CW)、细胞膜(PM),还有被核膜(NM)环绕的细胞核(N)。它还有几个内共生体(E),看起来有点像氢酶体。这个细胞非常大,长约 10 微米;细胞核也很大,占了细胞体积的40%。它显然是一个真核细胞吧?错。它的核膜是单层膜而非双层,也没有核孔复合体,只有一些不规则的间隙。细胞核中有核糖体(斑驳的灰色区域),外面也有。核膜和其他的内膜连续,甚至和细胞膜也连续。DNA 的形状与细菌一样,是直径 2 纳米的细纤维,而不是像真核生物那样的染色体。所以,它显然不是真核生物。我的猜测:这个神秘的细胞是一个获取了细菌内共生体的原核生物,正在重演真核生物的演化之路;它正在变得更大,基因组正在膨胀,正在累积高复杂度需要的原材料。但这是唯一的样本。由于没有进行基因组测序,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但是再仔细看看!确实,所有的真核生物都有细胞核,但是所有的例子中,细胞核的结构都基本相似。细胞核都有双层膜,和其他细胞内膜连续;都有核仁,核糖体 RNA 在此合成;核膜上都有精细的核孔复合体,以及弹性核纤层;DNA都被小心翼翼地包裹在蛋白质中,形成染色体;染色体是较粗的染色质纤维,直径有 30 纳米。真核生物的蛋白质由核糖体合成,而核糖体一定在细胞核之外,这是细胞核与细胞质最基本的区别。而明神海丘细胞呢?它只有单层核膜,上面有一些缺口,没有核孔。它的 DNA 是细菌式的极细纤维,不是真核生物式的粗大染色体,直径只有 2 纳米。它的细胞核中有核糖体。我再强调一遍:细胞核中有核糖体!当然,细胞核外也有。它的核膜在好几处与细胞膜连续。那些内共生体可能是氢酶体,但是其中一些的三维重建模型呈细菌式的螺旋状;它们看起来像是新近才被宿主获取的细菌。细胞虽然有内膜,但没有任何类似于内质网、高尔基体和细胞骨架的结构,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真核生物特征。也就是说,这个细胞实际上 与现代的真核生物差异很大,只是表面相似而已。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发现者也不清楚。他们把它命名为明神海丘准核细胞(Parakaryon myojinensis)。“准核细胞”(Parakaryon)这个新造的术语,表明了它实际的中间形态。他们发表在《电子显微学报》(Journal of Electron Microscopy)上的论文,标题是我见过的最吊人胃口的:原核生物还是真核生物?来自深海的独特微生物。他们立论的问题真是漂亮,但论文本身并没有很好地提供答案。如果他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甚至只需要测定核糖体 RNA 的特征,就能更深刻地揭示这个细胞的真实身份,也能让这篇被人忽视的科学文献,变成《自然》级别的高影响力论文。但是他们把唯一的样本做成了电子显微镜切片。作者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在 15 年的研究和 10 000 份电子显微镜切片中,他们从未见过类似的生物,在此之后也再没见过。其他任何人也都没见过。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不寻常的特征,有可能是研究者制备样本时人为造成的。考虑到电子显微学过去不太光彩的记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可能。但是反过来问,如果这些特征是人为造成的,那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份奇特的孤品?又为什么细胞的各种结构虽然古怪,看起来又自洽而合理?我认为,它不是人为错误的产物。这样只剩下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它是一个经过高度演变的真核细胞,为了适应不寻常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正常的构造,才能寄生在深海热液喷口的蠕虫身上。但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很多其他的细胞都在类似的环境中生存,但它们没有这样做。通常,高度演变的真核生物会失去许多原型特征,但残存下来的仍然是很容易辨识的真核生物特征。比如源真核生物一度被认为是中间型的活化石,但后来发现它们是由标准的真核生物演变的。如果“明神海丘准核细胞”是高度演变的真核生物,那么鉴于它的细胞基本布局都发生了剧变、完全不同于我们见过的任何例子了。我不认为是这种情况。
另一种可能,它真的是一个中间型活化石,“真正的源真核生物”,不知如何能幸存至今。在稳定的深海环境中,它无法演化出现代真核生物的特征。原论文的作者倾向于这种看法,但我还是无法赞同。它们并不是生活在从不改变的环境中,而是依附在多毛纲蠕虫的背上。这种蠕虫是复杂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在真核生物演化初期显然尚不存在于世。还有,这个样本的种群密度极低:搜寻了这么多年,只发现了一个细胞。这也让我不太相信,它们真能毫无变化地存活 20 亿年之久。小种群的生物极易灭绝。如果种群能够扩张,一切都好说;但如果不能扩张,随机出现的运气问题迟早会将寥寥无几的个体消灭殆尽。20亿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比深海中的腔棘鱼(公认的活化石)的存活时间长了 30 倍。如果真有从真核生物演化早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至少应该和现称的源真核生物一样兴盛且常见。
这样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如同福尔摩斯的名言:“一旦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情况,那么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定是事实的真相。”前面两个选项并非完全不可能,第三种可能却是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原核细胞,获取了一些内共生体,正在变成一个类似于真核生物的细胞,重演演化之路。我认为,这么解释合理得多,马上就能解释为什么种群密度如此之低。就像前文讨论过的,原核生物之间的内共生作用非常罕见,而且具体运作中充满困难。在原核生物初步探索内共生作用的阶段,自然选择对宿主和内共生体双方的压力都很严峻,绝不容易承受。这种细胞最有可能的命运就是灭绝。此外,原核生物内共生作用的假设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细胞的各种特征粗看貌似真核生物,实际上又不是。比如这个细胞很大,基因组看起来也比其他任何原核生物大得多,而且包裹在类似细胞核的结构中,核膜与其他内膜连续,诸如此类。这些特征都是我们之前根据基本原理做出的预测,理应在原核细胞内共生演化过程中出现。
我敢打赌,这些内共生体已经丢弃了基因组中的很大一部分。正如我之前论证的,只有内共生体丢弃基因,才能支持宿主的基因组扩充到真核生物的水平。只有内共生体和宿主两个基因组极度不对称,才能支持复杂形态的独立起源。看起来,这正是这个细胞中发生的情况。宿主的基因组显然很大,占了细胞超过 1/3 的体积,而本来体积就已经是大肠杆菌的 100 倍。基因组被包在一个表面上很像细胞核的结构之中。奇怪的是,只有一部分核糖体被隔在这个结构之外。这是否意味着内含子假说不正确呢?很难说,因为这个宿主细胞可能本来也是细菌,而非古菌,所以能较好地兼容细菌性的移动内含子。鉴于细胞核区室已经独立演化出现,我认为类似的演化力量已经在此发挥作用,而且同样会发生在其他有内共生体的大型细胞中。那么它有没有别的真核生物特征,比如有性生殖和不同的交配型呢?因为没有测得基因组序列,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真是最耐人寻味的谜团。我们只能静待新的发现,这正是科学中不可避免也永无止境的不确定性。
本书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试图预测生命为什么会是这样。大致看来,明神海丘准核细胞正在重走一条平行的演化之路,从细菌祖先通往复杂的生命形态。在宇宙中的其他地方,生命是否也会沿着同样的演化之路发展呢?这取决于出发点,也就是生命的起源。我认为,同样的起源也很可能一再重演。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使用化学渗透,都依靠跨膜质子梯度驱动碳代谢和能量代谢。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奇特机制可能的起源与后果。维持生命需要持续的动力,需要永不停止的化学反应制造出各种活性中间体,包括副产物ATP。这些分子才能驱动形成细胞所需的耗能反应。生命诞生之初,碳流和能量流必定更加充裕,因为那时还没有演化出生物催化剂,无法把代谢反应限制在狭窄的路径中。极少有自然环境能满足生命起源的诸多条件:连续、大量的碳和能量流入;流经矿物催化剂;反应集中在一个微区室化的系统中发生,既能浓缩产物,又能排出废物。也许还有其他环境能满足这些条件,但碱性热液喷口一定可以,而且类似的环境应该普遍存在于宇宙中有水的岩石行星上。碱性热液喷口环境支持生命起源的几个要素:仅仅是岩石(橄榄石)、水和二氧化碳,三种宇宙中最普遍的物质。光是在银河系的 400 亿颗行星之中,或许现在就有不少适合生命起源的环境。
碱性热液喷口既带来了麻烦,也提供了解决之道。它们富含氢气,但氢气并不容易与二氧化碳直接反应。我们讨论了半导性矿物薄壁两侧形成的天然质子梯度,理论上能够驱动有机分子合成,最终在热液喷口的微孔结构中形成细胞。如果是这样,那么生命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质子梯度(以及铁硫矿物质),才能突破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的活化能障壁。要依靠天然质子梯度生长,这些早期细胞就需要有渗漏的膜,才能截留住生命所需的各种分子,而不至于切断提供能量的质子流。这些条件又让细胞无法离开碱性热液喷口,除非经历一连串按照严格顺序发生的演化事件(比如必需反向转运蛋白),才能让主动离子泵与现代型的磷脂细胞膜一起协同演化。通过了这道狭窄的关口,细胞才能离开热液喷口,扩散到早期地球的海洋和岩石环境中。我们分析了这一系列具有严格顺序的演化事件,才能解释“露卡”(所有生命最后的共同祖先)那些矛盾的特征,才能解释细菌和古菌之间的深刻差异。也只有这些严格的条件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地球生命都使用化学渗透,以及为什么这种奇特的机制在生物中与遗传密码一样普遍。
适合生命起源的环境普遍存在于宇宙中,但又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控制着最终的走向。在这样的生命起源场景中,宇宙中其他地方的生命很可能也依赖化学渗透,所以也会面临相似的机遇和限制。化学渗透偶联赋予生命无限的代谢多样性,让细胞几乎可以利用任何物质“进食”和“呼吸”。细菌之所以能利用水平基因转移共享基因,是因为遗传密码为万物共有。同理,因为所有生物都使用化学渗透偶联的操作系统,那些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代谢套装,就可以在生物之间互相传递、即插即用。如果说,在宇宙其他地方(包扩我们的太阳系)找到的细菌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生存、不依靠氧化还原反应和跨膜质子梯度提供能量,那才真叫人吃惊。因为这些现象都可以根据基本原理预测到。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宇宙中其他的复杂生命也会面临与地球上真核生物同样的限制;外星人也应该有线粒体。所有的真核生物都来自同一个祖先,这个祖先的出现源于原核生物之间罕见的内共生作用,演化史中的单一事件。这种细菌之间的内共生,我们现在已知两个例子,算上明神海丘准核细胞,那就有三个。所以我们知道,不靠吞噬作用,一个细菌也能进入另一个细菌体内。在 40 亿年的演化历程中,这至少应该发生过数千次,甚至数百万次。这是一个瓶颈,但并不是最苛刻的。每一次内共生事件中,内共生体应该都会丢弃基因,宿主细胞倾向于变得更大,基因组变得更加复杂,这正是明神海丘准核细胞现在的样子。但是,宿主细胞和内共生体之间应该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才是瓶颈的第二部分,一道严酷的双重打击,让复杂生命的演化困难重重。最初的真核生物,很可能是在小种群中快速演化。因为真核生物的祖先已经有了许多我们从未在细菌身上见过的共同特征,这意味着前者的种群很小且不稳定,并且进行有性生殖。如果明神海丘准核细胞确实如我所想,是在重演真核生物的演化之路,那么它极小的种群规模(15年的搜寻只找到了一个样本)恰恰符合理论预测,而它最有可能的命运 就是灭绝。这也许是因为它没有把所有核糖体成功地排除在细胞核之外,也许是因为它还没有发明有性生殖。也许,它会抽中演化的头彩,播下真核生物第二次降临地球的种子。
我认为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宇宙中的复杂生命很罕见。自然选择中不存在固有的倾向去促使人类或是其他复杂生命出现。生命最有可能的状态,是停滞在细菌那种复杂度的水平,虽然我没法给出任何统计概率。明神海丘准核细胞的发现可能会鼓励很多研究者:如果地球上都多次出现了复杂生命的起源,那么在宇宙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比较常见吧?也许是这样。但是我可以更确定地说,基于能量的原因,复杂生命的演化需要两个原核生物之间的内共生;这是一个罕见的随机事件,罕见到怪异的程度,随后两个细胞之间的激烈冲突又使其难上加难。只有度过这个艰险的阶段之后,复杂生命才回到标准的自然选择演化道路上。我们论证了很多真核生物共有特征都可以根据基本原理预测,从细胞核到有性生殖。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两性的演化、生殖细胞与体细胞的区别、细胞程序性死亡、嵌合式线粒体、有氧代谢能力和生殖力之间的平衡、适应性与疾病、衰老与死亡,所有这些特征的出现,都源于“细胞中的细胞”这个出发点,也都可以预测。如果演化从头再来一次,它们还会重现吗?我认为大致都会。我们早就应该从能量角度研究演化了,这样的方法能为自然选择提供可预测的基础。
能量的要求远比基因严苛。看看你的周围,这个美妙的世界反映了基因突变和重组的伟力,它们是自然选择的基础。窗外的大树和你有一部分基因相同,但你和树在大约 15 亿年前的真核生物演化早期就已分道扬镳,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行。突变、重组和自然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基因,而不同的基因为你和树规划了不同的路径。你在树林中奔跑,偶尔还喜欢爬树;而树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用最神奇的生化魔术把空气转变成更多的树。你和大树之间这么多的差异,全都刻写在基因之中。这些基因都源自共同的祖先,但是现在却大多分化歧异,让人很难辨认出任何相似性。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漫长的演化旅程中被允许、被选择。基因几乎是无限宽容:任何可能发生的,都会发生。
但是那棵树也有线粒体。线粒体的运作方式与叶绿体差不多,无数电子在亿万条呼吸链中永不停息地流动,无数质子被泵出线粒体内膜。大树一直在做这些事,你也一直在做这些事。这些电子与质子的循环,从你还在母亲的子宫中开始,就支撑着你的生命:你每秒钟要泵出 1021 个质子,从不间断。你的线粒体来自母亲的卵子,这是她留给你最珍贵的礼物。这份生命之礼,可以一代一代、毫无间断地追溯到 40 亿年前深海热液喷口之处,生命最初的扰动。线粒体的功能性命攸关,不容干扰。比如氰化物进入细胞,就会遏制电子和质子的流动,让你的生命戛然终止。衰老有同样的效果,不过它的步调缓慢而温柔。死亡就是电子流和质子流的终止,是膜电位的停息,是从未间断的氧化还原火焰最终归于熄灭。如果说,生命不过就是一个电子寻找归宿的过程,那么死亡就是 电子终于可以安息之时。
能量流令人惊叹,却又冷峻无情。哪怕是几分钟、几秒钟的改变,都可能让生命的实验走向终点。孢子可以躲避能量流的严厉,沉入代谢的休眠,醒来时继续幸运的生存;但其余所有的生物,包括我们,仍然要随时依赖这样的能量机制,与最初的活细胞没有区别。这些机制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怎么可能改变呢?活着才有生命,而活着就需要永不停息的能量流。所以,能量流对演化路径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决定了什么可以,什么不行。细菌一直都是细菌,永远不能改动供给它们力量生长分裂、征服世界的火焰。一次偶然的意外:原核生物之间的内共生事件,终于突破了能量之障。但它也没有改动生命之火,而是在每个真核细胞中引燃星星点点的火种,最终演化出复杂生命。我们人类的生理与演化,完全依赖于火焰的继续燃烧,而火光也照亮了我们的过去与现在,种种不可索解之处。我们的头脑,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生物机器,被永恒的能量之流驱动,现在可以思考自身,追问生命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又是演化中何等的幸运!
愿质子动力与你同在!
尼克·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