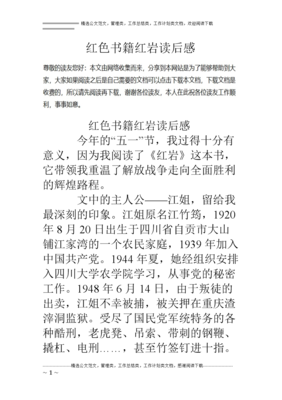
《金史(全八册)》是一本由脱脱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6.00元,页数:29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史(全八册)》精选点评:
●学习,经典,
●全八册。
●工具书
●20180715~0802,第一册。0815,第二册。第三四册略读。0830,第五册。0922,第六册。1019,第七册。1030,第八册。如果金源氏统一中国会怎样?
●da mafa...mini enduri
●二周目完成。大四、博四各一遍。《金史》的编纂是很不错的,阅读体验也要胜过《元史》之类。
●只看了《礼志》卷。
●金代国史免遭战火洗劫,因而《金史》较好地反映了国史的情况,对金国制度变迁细节有着详细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完颜亶之前是不重视人物传记的,以至于在皇后可以参政的金世代,除了女汉子徒单氏以及八面玲珑的唐括氏外鲜有与历代皇后相关的记载。从各种意义上考量,天眷新政都是女真汉化的里程碑。民主催生分权,儒治滋生腐败,中央政府在大乱世背景下集权能力不足已是硬伤,哪堪腐败加扰,这恐怕是金没于元的主要原因。
●
●: K246.440.42/7272
《金史(全八册)》读后感(一):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终!
一个加长版的寒假,闭关在家的日子,每天就是跑步,读书,终于有时间把这套八本的《金史》啃完了,与之前的史记,三国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阅读中最大的难题是人名,金史中充斥了大量女真语的汉化版,所以在全书的最后编修脱脱丞相还贴切地单列一张金国语解,不仅解释了汉语发音和意思,还解释了为什么金人的人名看起来那么粗不可耐,随便列举几个:完颜丑汉,完颜活女,郭蛤蟆,完颜陈和尚,完颜猪儿,纥石烈猪狗,还有一大堆的七斤,六斤,九斤。大金国的历史对一般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除了几个著名的人物:阿骨打,海陵王,就是金兀术,事实上这段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随便列举两个:金太宗吴乞买,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被大臣打屁股的皇帝,这个窝囊,面对打他的那群侄子他也无可奈何,还有金世宗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口直心快地皇帝了,有啥说啥,地图炮,鄙视契丹,疼骂到年龄坚决不退休的丞相,老而不死,颇有川普大统领的风格,还有比崇祯爷更没有像亡国之君的金哀宗,放个宠物跑到老百姓家里,还要三番五次地去索要,结果人家根本不睬他,他也无可奈何,还是有两个小疑问:首先这个赵思温被册封为天水郡王,天水郡王难道不是宋徽宗?还有这个李妃要置换的红币是啥,最后看完最感动的还是那句话:是时,河南已不能守,子孙不知所终!
《金史(全八册)》读后感(二):金史存照
如果说大辽印象最深官职的是南院大王,对金代的了解则是完颜洪烈和那个在原著里没什么好感,在此间里却让人印象很深的小王爷完颜康了。
闲话少提,辽代的官名人名就已经很难记了,金朝这些名字有过之而无不及。猛安谋克之前多少还听过一点,神马勃极烈这种官名,再加上更拗口的人名~~~~说起来,辽金都有好多“耶律八斤”“完颜六斤”之类的人名,看到后总是想起鲁迅小说里那个八斤老太~~~
开始就提到了”白山黑水“让我这个半个东北人很亲切。一直以为这个说法是明清后才叫起来的。早年一直是渔猎民族,农具,铠甲,部队都是在对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女真”万人则无人敌“没有几年就把显赫一时的辽朝灭掉,中间几乎没有休整积累实力的过程,又顺势灭亡了北宋,真是难以想象。
徽宗早死,钦宗正经在金朝活了好多年,还被封了个郡公。高宗杀岳飞的背景又更清楚点了。
对海陵王的贬低太多,但是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太强的戏剧色彩,其实是很让人着迷的。荒淫,滥杀,却又有时候很有人情味。
从有限的史料来看,金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比辽代要好的太多。特别是世宗朝以后。
不光宋朝,金朝自宣宗以后也有南渡,所以射雕英雄传的历史也颇可怀疑。
哀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末代君王。从蒙古崛起后,两任金主都格外宽仁,修城墙都怕耗费民力。尤其是哀宗这句”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或为俘献或辱之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印象里,只有王莽和崇祯能与之有一比。
金朝对黄河的重视,或许与汉化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关系,只是我很难区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毕竟,任何一个占据这个流域的王朝想要维持统治,都绕不开这条母亲河。
卢沟桥,金朝最有名的工程之一,也在近千年后作为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起点被人所熟知。在河渠志里,引人注意的则是关于两岸的闲廊,世宗期待由私人修建,而大臣则担心私人修建会只建利润高的一边。那个时代的私人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从这个小事里或许可以管窥一斑。
猛安谋克,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1猛安。说起来,清朝名字叫后金,在兵制上跟金朝模仿的也好多。牛录,固山就是猛安谋克的翻版吧。后来乱成一团的旗务也早在金朝就有端倪。
金史的列传顺序好乱,一般列传顺序是后妃,宗室,宰相,路人……但是金史后妃之后宗室和宰相或者路人交错,张邦昌写了“宋史有传”,一起列在“叛臣传”的刘豫却写了不少。
如同辽史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杨令公的最后岁月。金史对完颜宗翰,宗弼大加赞扬,好像两人都是以弱胜强的英雄。
某人跟宋兵打仗,元帅问他为什么山地战要用骑兵,他回答说宋兵腿上都画马做法,不用骑兵追不上”看来神行太保戴院长的纸马法术在两宋年间也是广为传播啊。
总而言之,其实对金代的皇帝比南宋的要有好感的多。特别是世宗。宋朝在金史里的地位就是个悲剧,如同一个很欠的孩子动不动挑衅一下,金朝皇帝如同长辈开始只是派个人去批评两句,每次一派正规军就能打的落花流水。另一方面,清朝和金代的相似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猛安谋克和八旗,汉化与官僚系统的膨胀腐败。军事力量的衰落,对传统文字和语言的保护,以及稳定的“后族”。
行省这个名字在元代被人所熟知,但是“行中书省”在金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和“元帅府”同时作为战时的军民政治机构。对其运作机制略微有些不解。可能和金代后期的中央军政机构混乱有关系。
另外,全书最后的简明金汉词典是亮点,比如粘罕是头,兀术是心~
《金史(全八册)》读后感(三):读《金史·海陵王本纪》心得手札三两摘
许多渴慕汉文化,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汉风文人雅士的游牧民族君主贵族,能真正读懂汉文化,且真心实意不带任何功利和政治目的去学习的君主贵族几乎没有。他们的亲汉,总是带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或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修身,或是为了满足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剥去罩在他们身上的汉文化的瑰丽外衣之后,人们会发现,底色终究是底色,再漂亮的颜色也不可能盖得住底色,因为底色即是这个人这个物件的根本天性。不同的民族文明可以相互交流融合,但不同的民族文化则很难达到统一和一致,因为它们各自的根基不同,它们传承自不同的土壤,有着不同的血脉维系形式,它们在集体道德和思想的认同性上注定无法调和,求同存异也许是它们和谐存在的最好方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在以完颜亮为代表的追崇汉文化的非汉族人群身上看到,端起书本说起话来与汉人分毫不差,但操起屠刀砍向汉人的时候半丝眉头都不会皱的,如此矛盾的结合体。因为从根本上,我们可以共享一个文明,但无法共同植根于一个文化传统。
————————————————————————
完颜亮是矛盾体,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他既是女真的一代雄主,又是荼毒天下的暴君。他对政敌冷酷无情杀戮残忍,但又会时不时表现出一张爱民如子的圣君面孔。他一壁限制女真贵族随意射猎,还农田耕地于百姓务农,一壁又在南下侵宋时屠戮射杀宋民百姓。这种鲜明的保护与摧毁的反差,让人恐惧于他风云瞬息而变的脸孔,他有着果断的不容置喙的强悍自信,任何阻挡他的力量阻挡他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障碍,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达成目的。
虽然他空有汉文化的表皮,没有实质内核,可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他在汉文学方面的诗词造诣令我们叹为观止。一阕《念奴娇·咏雪》道出了他豪迈雄壮的男儿本色,以及他锲而不舍的追逐人生更高峰的精神: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
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
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
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合旗角。
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
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
须臾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
他一直深切的希望自己能跳出苻坚的所遭遇的怪圈,能被汉家正统认可为天下正朔之主。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他为什么如此痴迷汉学,一心从兴趣爱好审美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尽力将自己打造成汉人的原因。一则是因为汉文化却是博大精深,令他不能自已,想要去感受了解,另一个原因则是想要通过自己亲近汉学,学习汉学,与汉人建立亲密的感情纽带,继而达到自己被奉为天下正朔,洗净自己是“胡儿”尴尬气味的目的。
————————————————
历史何其相似,当年二十七岁的他采用阴谋手段,串通唐括辩等人,买通了金熙宗身边的近侍,在夜晚潜入金熙宗的寝宫,将其杀死于御榻之上。而十三年后,他也在瓜州,被自己的将领和近身侍卫盗了护身兵刃,杀死于自己的大帐之中,就连情节也好像是老天安排好的重播电视剧一样。如果有因果轮回,这种起于阴谋杀戮,死于阴谋杀戮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不是算的上是现世报的因果轮回呢?
——————————————————
他曾经有过“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的诗句,更有过“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的豪情,其笔力的雄浑将他的鸿鹄之志挥洒的气象恢弘,也将他梦想的蓝图时时构筑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应该说,他一直为那个时点在努力奋斗,从来没有放弃过。
——————————————————
近来读书,较之之前不求甚解有所长进,也许是拜脑补先秦史的所赐,越发趋向于平衡状态。因偿还文债而翻看相关史稿,感觉有先秦史垫底,看其他的史料比以前更能入木三分。大好!
《金史(全八册)》读后感(四):女真貴族是如何因為學習先進文化而走向亡國
歷史上的金朝,似乎是漢化非常嚴重的少數民族政權,這種漢化的趨勢從金朝立國就開始了,不過有個分水嶺,我覺得這個分水嶺是海陵帝完顏亮,在完顏亮之前,女真的漢化速度較慢,在海陵帝之後,女真漢化速度加快,且不可逆轉。
完顏亮是個漢化程度很高的皇帝,非常羨慕南宋的文化、經濟,據說他是讀了柳永寫杭州的一首詞(《望海潮•東南形勝》)萌發了入侵南宋的軍事計畫,這自然是小說家對柳永詞的誇張之說。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完顏亮執政的金朝已經是漢化非常嚴重的時代了,他本身就是受漢化影響的產物,從他自己寫的詩詞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漢文化水平(如他言志詩“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等等)。完顏亮南伐宋朝似乎也並非單純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搞的好大喜功行為,他要征服南宋乃是為了獲得政治上的“正統”,而“正統”這個概念正是漢化到一定高度之後才能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說,完顏亮南伐的根本原因乃是他對漢文化,特別是宋文化的認同感。有史料為證:
《金史•耨碗溫敦思忠》(卷八十四列傳第二十二):“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讀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
耨碗溫敦思忠是跟隨完顏阿古打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女真族功臣,他反對完顏亮出兵的理由是從軍事角度進行思考的,而完顏亮則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決定南伐的,可知,耨碗溫敦思忠代表了女真族裏面漢化程度較低的貴族的觀點,他們對於軍事戰爭是持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的,而完顏亮受漢化的薰染較深,覺得要將逐漸漢化的金國帶進新的時代就必須拿下南宋得到“正統”,如此以來自己才能帶領國家徹底的名正言順的進行漢化。完顏亮批評思忠不讀書,正說明他以漢化的標準來要求思忠,而思忠則拿出了女真文化的傳統加以抵制。可以說,完顏亮代表了女真貴族的漢化派,思忠則代表了女真貴族內部的反漢化派。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完顏亮責備思忠不讀書不懂“正統”的價值,要他去問他兒子乙迭,說明了反漢化派的女真貴族後代漢化的程度也是不斷加深的。像思忠這樣反對漢化的保守派根本抵擋不住漢化的外在潮流。
海陵帝完顏亮南伐失敗,自己被部下叛變殺死,金世宗在北邊被推戴即位,這本應該是女真漢化的一個挫折,然而實際上金朝的漢化不僅沒有終止反而加速了。金世宗是個金朝歷史上有作為,思想卻較接近女真反漢化派的皇帝,他雖然幾次三番採用各種方式(包括要求女真族必須會使用女真文字,保存女真話,不允許女真人改漢族姓氏)保存女真文化,反對漢化,但是宋文化的高度還是深深吸引了女真人,光靠少數像金世宗這樣的皇帝也擋不住先進文化的“侵略”,正如今天反美的毛粉們也依然要依靠美國人發明互聯網來打口水戰一樣,女真貴族同樣阻止不了漢化。所以,在金世宗死後,金章宗即位就幾乎完全廢除了金世宗的保存女真自身文化的政策,不僅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主動漢化,甚至出現了命令要求女真族全部改漢字姓名(採用音譯)。漢化使金國的文明程度更高,但也使得金朝走上了南宋那樣的官僚主義道路,官僚主義使政府效率下降,辦事作風越來越像南宋一樣務虛不務實,繁冗的禮儀和官家排場,一點也不必南宋差(讀《金史•禮志、儀衛志》可知),女真貴族的軍隊更是因為漢化而過上奢侈的生活,變得腐敗不堪,女真開國的那種野性和務實的作風蕩然無存。就在女真族漢化的跟漢人生活習慣、文化差不多一樣的時候,蒙古鐵騎到來了。
官僚作風深重的女真政權一路敗退,當知道跟成吉思汗議和沒有希望以後,金朝知道已經守不住北方(上京)的領土了,金朝中樞於是與西夏開戰,想佔領西夏地盤苟安度日,可是他們現在連西夏也打不贏了,於是又想南伐宋朝,佔領江南富庶之地,而這時候的南宋也想跟蒙古夾攻金國,雖然南宋的軍隊幾次被金打退,但是金朝卻已經陷入了三線作戰裏面——北有蒙古,西有西夏,南有南宋。金國腐敗的內政、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官僚主義的中樞,終於蹣跚無能地把自己送上了徹底滅亡的道路。
《金史(全八册)》读后感(五):读元脱脱等《金史》
作者: 元脱脱 / 等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1975-07
页数: 2906
定价: 14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点校本二十四史
ISBN: 9787101003253
世祖与腊碚、麻产战于野鹊水,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发而抚之,曰:「此兒长大,吾复何忧?」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乌,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尝宴纥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识焉。
迁汴之后,北顾大元之朝日益隆盛,智识之士孰不先知?方且狃于余威,牵制群议,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
金朝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搞得很厉害,最终导致国力不济而崩溃。
凡县令,则省除、部除者通书而各疏之。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肃,捍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
阿鲁补,冶诃之子。为人魁伟多智略,勇于战。未冠从军,下咸州、东京。辽人来取海州,从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敌,力战,斩首千级。从斡鲁古攻豪、懿州,以十余骑破敌七百,进袭辽主。阿鲁补徇北地,招降营帐二十四,民户数千。时已下西京,阇母攻应州未下,退营于州北十余里,夜遣阿鲁补率兵四百伺敌,城中果出兵三千平袭,阿鲁补道与之遇,斩首百余,获马六十。后辽兵三万出马邑之境,以千兵击之,斩其将于阵。以十当百,女真骑兵锐利惊人。
及宗弼问琼以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余,又无良帅,何以御我。颇闻秦桧当国用事。桧,老儒,所谓亡国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颠覆是惧。吾以大军临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既而江南果称臣,宗弼喜琼为知言。评秦桧甚是。
上曰:「除授格法不伦。奉职皆阀阅子孙,朕所知识,有资考出身月日。亲军不以门第收补,无廕者不至武义不得出职。但以女直人有超迁官资,故出职反在奉职上。天下一家,独女直有超迁格,何也?」安礼对曰:「祖宗以来立此格,恐难辄改。」世宗似汉化较强,故反而无甚门户之见。当然若为试探亦未可知。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九年正月,三峰山之败,走钧州。城破,大兵入,即纵军巷战。陈和尚趋避隐处,杀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时欲其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酹以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
一日,上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其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然其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清臣曰:「兵书皆定法,难以应变。本朝行兵之术,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旧阵势以接敌,亦以疏矣。」
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未、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盖汴京被攻已尝得用,今复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