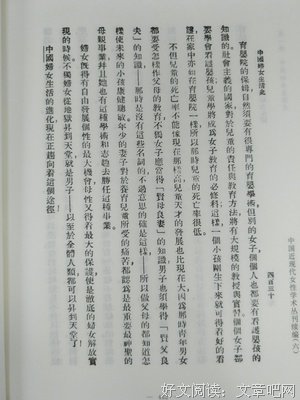
《固执已见》是一本由V·纳博科夫著作,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元,页数:2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固执已见》精选点评:
●喜欢捕蝴蝶 从以前到现在 以后也会继续喜欢
●Dialog Nabokov
●作家访谈,有启发。
●没找到原版,翻译一般,但是纳博科夫永垂不朽~
●拜论文所赐
●“没见过世面的大自然的热爱者,一个迷失在天堂里的偏执狂”
●可以了解纳博科夫的个性,非常有趣
●小聪明加毒舌,被纳博科夫烦死了。在纳博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果断站陀氏一边。
●你会发现,敢大放阙词臧否人物的人,不仅才华横溢,还得腰缠万贯,最起码也得是没落贵族。
●纳氏的见解相当特别,尤其是对作家的评价,对作品的解读,还有他独特的写作习惯。纳氏在科学艺术方面造诣皆非常人能比,因此见解非一时之感想,而是有其一贯之标准,固执己见,strong opinions. 译得不错,可惜漏译不少句子,都是相对难译的句子,译者态度上不够端正啊。
《固执已见》读后感(一):学会区别陈辞滥调
纳博科夫显然擅长武断地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粗暴地评价一些一流的作家同时,也肆意吹捧着一些有才华的二流作家、诗人,甚至达到了恶作剧的程度。对同时代的天才尤其蛮横无理,几乎次次信口雌黄,但是也偶有道理。
他研究普希金,与他业余捕蝴蝶一样,是洛丽塔的另外一部分。
2011.11.19
《固执已见》读后感(二):对比下原文和译文
“In fact I believe that one day a reappraiser will come and declare that, far from having been a frivolous firebird, I was a rigid moralist: kicking sin, cuffing stupidity, ridiculing the vulgar and cruel—and assigning sovereign power to tenderness, talent and pride.”
有一天,有人会对我的作品作重新评估并且会宣布——纳博科夫远不是轻浮的北美黄鹂鸟,而是鞭挞罪恶与愚蠢、嘲讽丑陋与残酷——极力主张温柔与敦厚的人,他把至高的权利分配给才能和自尊。
《固执已见》读后感(三):文学的美德——纳博科夫读后记
“你追求的文学的美德是什么——怎么追求?”
“用最佳的词汇尽可能表达所想表达的东西,文字要有韵味儿,让人产生联想。”
这是纳博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书评》记者1971年采访时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
和绝大多数读者一样,我读到纳博科夫第一部著作便是使他成为世界著名作家,也为他惹来不少麻烦的那本《洛丽塔》。在翻阅完这本小说之前,虽然在20C.欧美文学史课上接触过他的名字,但却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我对《洛丽塔》产生兴趣有些和纳博科夫自己的创作体会不谋而合——出自纯粹对美和艺术的追求。因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那个版本实在是太漂亮了,明亮的黄色封面,简洁的封面设计,厚实而柔软的印刷纸,行间距和字体大小都恰到好处的格式,让我从书店的柜台上拿起了这本书。纳博科夫在《固执己见》中说过,他有一种能从每个字母中看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颜色的天赋。而我想,可能明黄色就是《洛丽塔》这本书的代表色。它是一首轻盈灵动的长诗。
我在一次旅途中,坐在来回的火车上翻完这本《洛丽塔》。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去找些资料来了解纳博科夫其人其作——包括没有去读评论家们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洛丽塔》书中所引起的道德争议,我也是直到上一周翻阅《固执己见》的时候才比较清晰的体会到。然而我想,如果从纳博科夫自己的观点出发,这是阅读他的作品的一个良好开始:完全不受道德、社会、法律等各方面思想体系和社会价值评价的影响,只是把这部小说当作一个纯粹象牙塔式的艺术品,看它所表达的人心和人性,随后我反观自己第一次读完《洛丽塔》的体会:我没有感到后来引起争议的所谓老鳏夫猥亵小女孩有什么不妥,我只是为书中细腻的心理描写所折服。
后来,也就是大约两周之前,我读了纳博科夫的另一本小说《普宁》,有一点自传的色彩(当然,纳博科夫会反对我这样评价这本小说),书中的普宁教授和他本人一样是来自俄国的流亡学者,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教授着不太受人欢迎也不怎么得到同行尊重的俄国文学课。普宁有些怪癖,有些愚钝,有些固执,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其实他“很傻很天真”。他执着的钻研俄罗斯古文化和古典文学,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为的是记住失去了的祖国。在普宁很努力的融入美国社会,几乎要成功的时候,他所在的学院却要裁撤掉他任课的文学系,让他滚蛋——最后他宣布要离开那个地方,他的朋友们打电话去确认的时候,他抓着话筒大吼:他早就走了!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像是在默默忍受现实对他的嘲弄之后,终于鼓足勇气发出一声反抗的呐喊。
然而实际上,纳博科夫本人却与普宁不同,他很爱自己的第二祖国——美国。甚至在他后来因为私人原因再度移居欧洲之后,他也不断的想要回去。对他的生平和文学观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他和普宁所共有的品格仅仅是某种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信仰中的,不愿受外界干扰的执拗——也就是固执己见。纳博科夫对于评论界给他加上的各种帽子都不大理睬,他不主动参加任何集会,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群体,对于一浪又一浪的小说艺术革命更是嗤之以鼻——譬如他就曾反对过法国“反小说”这种说法。他常常喜欢直接写文章大肆反驳批评他文章和观点的评论家,甚至对于那些说他好话的人,他也毫不留情的指出他们文中对他的曲解。在《固执己见》一书中,读到后来会发现,纳博科夫这个可爱的老头花了好多篇幅去纠正一些翻译上、文法上的错误以及见解上的偏差。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经常不喜欢别人对他的评论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人们都在误读他。
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的一段情节。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其实是建立在误解之上。你自以为理解了我的话,于是发表了一通其实已经曲解我意思的看法,还自以为评价的恰到好处,而我又再次误解了你的误读,哪怕我明知道你是误解了,我也会拼命表示赞同,继续说下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指出你的误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继续沟通下去。(大意如此,具体的章节暂时没找出来)
误读是文学中的常态,文学批评更是误读的绝佳体现,或者毋宁说是文学批评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纳博科夫这个有个性的作家,怀着自己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坚决的想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一块神圣创作领地。可以这样说,他的这份捍卫,就源自于他对自己的真诚,对文学感受能力的绝对推崇。他曾这样说:“不过,我从未能对我文学课堂上的学生充分解释阅读技巧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你读艺术家写的书不该用心去读(心是极蠢的读者),也不该只用脑去读,而应该同时用脑和背脊。女士们先生们,背脊里的震颤真正告诉你作者的感受,希望你能感觉到。”(固执己见 P44)
纳博科夫曾经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国与俄罗斯文学,显然受过良好的文学理论成体系的教育。然而,他显然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无论从他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的看法,还是从他厚厚的两部《文学讲稿》看来,他更注重从经验上去体验写作的美和激情。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我不为群体、社会、群众等等劳什子写作。虽然我不太在意“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推动者如奥斯卡•王尔德和各类华而不实的诗人事实上都是道德说教者——但毫无疑问,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
事实上,纳博科夫并非对艺术创作持有完全自然主义的看法,他亦认为创作过程中的构思阶段是痛苦的,他无数次表明,写作对他来说是快乐与痛苦掺半。例如在《洛丽塔》的写作过程中,由于对亨伯特•亨伯特这样一个男子没有任何切身体会和观察,他只能完全凭借自己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去构造。在《洛丽塔》问世之前,他也没有读过(据他自己说)任何关于这种成年男子爱上小女孩的社会新闻,这部小说的成功,在我看来,正如他自己多次强调的那样,不是什么社会教育意义,不是为了揭露美国汽车旅馆肮脏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而是出于纳博科夫对于刻画这样扭曲的人性的渴望,一种表达人情的热情。他将对人、爱情、生命的思考当作至高无上的责任,这是艺术家和文学艺术应当承担的最终职责。无论我们的社会评论怎样变化,价值体系怎样变迁,无论现代主义怎样颠覆了现实主义,而后现代又怎样颠覆了现代,如果没有对艺术精神的自觉追求,那么文学艺术将只能流于庸俗和媚行者的境地。
纳博科夫非常厌恶许多出版商和评论家想要将他的《洛丽塔》和一般的“黄色文学”等同而言的行为。他甚至拒绝在这本书出版上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发行人请他一同抨击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的邀请。纳博科夫并不完全取消评论的价值和技巧的运用,事实上,他的小说有着精彩的架构,绝对不亚于博尔赫斯、乔伊斯或者卡尔维诺。例如他自己无比喜爱的《洛丽塔》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Lolita。他深知这样充满激情的开头,似乎突然凭空而来的抒情性议论会如何让读者眼前一亮。还有《普宁》中的叙述视角奇妙的转切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叙述者的出现:原来一直向我们讲述普宁其人的全知视角的画外音居然是普宁儿时相识的伙伴——如果稍微读一些他的作品便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他诙谐幽默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他细致的心理描写。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幽默欠缺锤炼,有些被广泛认可为精彩的片段甚至显得极其幼稚——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他在创作的技巧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而,这些令他乐在其中的努力并不是他推崇的最高境界,他懂得在把捉现实百态的时候坚持住艺术神圣的内核,即真和美。真,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说“艺术就其极而言是具有欺骗性和复杂性的,妙不可言”,而美,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不囿于俗套的表达,是认真的揣摩达到的境界,正如他所言,“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作品”。
真挚和热情、创造力和感受力是纳博科夫所认为的文学的美德。从他的采访来看,他不善言辞,回答问题会打结,于是他就要求采访者事先把提问给他,然后他认真的对每一个问题做出书面的回答,有的时候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过于较真。他不断的提醒出版者和发行者,为了保持自己谈话的原样而付出在一般被采访的对象看来实在有些多余的努力。在我们这个过于浮躁过于紧张的世界,尤其是作为一个学习文学评论的学生,我们很容易被套话、理论术语、思维定式、价值体系所淹没,而失去了最初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却是纳博科夫一贯强调的东西。虽然怎样对待评论,以及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因为他的否定而否定了对他作品的一些研究,但是我想,他的创作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示,用另一位文学家的话来说:他可能是一种异变,是一种暗胎怪生;是不那么赤裸裸的去对抗、控诉,不那么容易去定义。他可能犹犹疑疑,这样不情愿,那样不情愿,反复思虑,甚至带点邪气、不恭,但他却是愉快的。
中国古代文论之中有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说,称为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一位表演艺术者在做完一个大家都没察觉的动作之后说道:你以为我什么都没表演其实我已经表演过了,这才是至高无上的表演。他在翻译普希金长诗时候强调的直译,以及他对一些译作中字眼的研究,还有他对他不喜欢的评论者和讨厌的作家作品直面的抨击,使他那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中,每一步的轻盈畅快都让我看见他努力的痕迹。越是深入的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我越是为他作品之外的东西所感动——那种我们正在逐渐缺失的对艺术的真诚和热情。这让我想起上个周末听的聂振斌教授演讲之后,老师的总结:理论、生活和创作,这三样,如果用一种整体论的精神将他整合,是一个自觉的文学研究者,或者说任何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应当考虑的事。
本来我想将我这篇稿子命名为:创作与评论的艰难疆域——由纳博科夫想到的。最后还是改掉了题目。我想,虽然纳博科夫否定文学的美育作用,否定他是在为社会人群写作,否定枯燥的理论和程式化的批评,文学到底是不是无功利的,文学在当今的社会,在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中到底应该为了保持自己而做点什么,大众文化是不是真的如纳博科夫抨击的那些下流小说一样如此不堪,这些是需要再商榷的东西;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持的是:创作与评论可以不会那么截然对立,只要每一个为艺术而付出的心灵都从精神的高度去领会其真与美,那么,审美作为一种精神的活动,就可以发挥它引人向上的情操和净化的安宁。正如纳博科夫自己在论道《洛丽塔》时说的那样:它就在屋子里悄悄陪着我,仿佛一个夏日,你知道雾霭散去,它就是一派明媚。
《固执已见》读后感(四):纳博科夫:大师,三流作家?
纳博科夫:大师,三流作家?
1、关于《洛丽塔》:
众所周知,《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最知名的一部小说(纳也是因《洛》而著名),在现代西方物质主义社会背景下,这个事实本身无疑带有某种悲喜剧色彩。然而,针对BBC记者"变成以《洛丽塔》为标志的人你懊恼吗"的诘问,纳氏却老练地一口否认,并强调《洛》是他"特别钟爱的作品"。对纳一惯的虚饰、矫情与专横或许不值得较真,应该引起警觉/反省的倒是自己平日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闭了自身的感觉与判断力,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大众传媒及某些"专家"意见的盲目追随者?!
我一开始就隐隐觉得,《洛丽塔》不过是一部二流作品(我印象较好的纳氏小说是那册薄薄的《普宁》),可正是这本出生美国(尽管一度被拒绝出版)走红欧美的畅销读物改变了纳氏最后二十年的处境与命运("声誉和财富一夜间如蘑菇云般陡增"且成为传媒追逐的"明星")。可以说,没有臧否不一的畅销书《洛丽塔》,便没有后来财大气粗、睥睨一切的"文学大师"纳博科夫。
上述纳氏的"发迹"过程应该说并无特别之处,因为谁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多么善于制造"奇迹"的国度——不必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世纪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得力于市场经济时代"文化工业"这头怪兽几乎是操控一切、无所不能的威力。
2、谩骂与"俄罗斯性格":
纳氏自称"是个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喜欢的公开露面是有机会当众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是暴露叫人不快的个性",可翻读"访谈录",予人的印象却绝然相反。对诸多已逝的前辈作家或尚健在的同行,他都发表过大量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斥、贬抑乃至恶骂 —— 弗洛伊德:"维也纳江湖骗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庞德:"老骗子",其诗作是"做作的胡说八道";劳伦斯:"臭大粪","查泰莱夫人的性交"被说成"伟大的文学"是一桩"阴谋";博尔赫斯:"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法国"新小说":"臭烘烘的鸽子窝里的一堆垃圾"等等不一而足。对(非议其作品的)评论家,纳氏一概冠以"小丑"、"评痞"、"评棍"之名;至于跟他有过节的编辑,则是"几个不知深浅的混蛋"。
或曰:纳氏的狂妄自负不过是常见的文人"相轻"习气的流露而已,无须过分严重地看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尤其对那类自恃才高口无遮拦的文人,我们更不可能要求他言必有据、恪守世俗常规常理,放言、浪言、妄言,甚或兴之所至作一些非常可怪、不负责任的极端之论都是不足为奇、可以理解的。不过问题在于纳氏的某些言行已很难用文人"相轻"来解释,而是已经达到相恶/相谤/相仇/相诋毁乃至"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了。
何以如此?较直接的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纳博科夫的出身、生活及创作经历中寻出若干痕迹 :譬如他因俄国赤化而随全家流亡欧洲二十年,虽说在俄国移民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但毕竟收入菲薄、经济困窘;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他仍无法靠写作谋生,只能以做大学教书匠为主业,直到十五年后写出《洛丽塔》才彻底摆脱生存困境。大半生辗转不宁的侨居生活不可能不在纳氏内心深处留下浓重的阴影:那些诸如长期无人问津的失落、郁郁不得志的压抑、妒火中烧的熬煎一类的情绪或意识都会不经意地慢慢累积在一起,然后在某种特殊情势下以过度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更重要的原因还可能根于一种渊远流长的国民/种族性,对此我们一时虽碍难从学理角度作具体的分析阐释,但仍不妨驱遣感性来一番印象式扫描与联想类比——仅以文人艺术家为例,不少纳氏前辈或同侪身上流露的某些习气就跟他本人有着非同寻常的相近、相似、相通、相契抑或相反(从另一极显示其系"同一族类")之处: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与偏激、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唐与厌世、穆索尔斯基的固执孤独与悲观自弃、马雅可夫斯基的粗野热狂与傲慢自负、安德烈·别雷的怪僻乖戾与勃留索夫的趋势善变,乃至列夫·托尔斯泰的自我扩张与专制倾向等等, 所有这些都携有某些我们熟悉而又不易言传的"俄罗斯"性格的影子。
3、"戏仿"手法的后面:
纳氏曾多次谈起"记忆"并将其分为知识性/情感性两大类。他认为"知识性记忆"是靠不住的,一旦将其写进小说就失去了现实的味道;而"情感性记忆"是爱,"你越爱一段记忆,这段记忆便越牢固"。
从对记忆的分类看,纳氏似乎是一个尊崇感性的人(他也以此自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举例而论,纳小说常用戏仿(parody,或译揶揄模仿)的艺术手法(如《眼睛》模仿十九世纪爱情故事,《绝望》模仿侦探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模仿当时流行电影中常见的廉价三角恋爱故事,《洛丽塔》则效仿"忏悔录"文体等),反对文学"逼真"地记录现实,并声称"所有的艺术都是欺骗"—— 假如把"欺骗"理解为"以假(虚构想象)乱真(使读者不知不觉接受一个貌似真实的虚构世界)",那么,纳的说法还是不难被理解和接受的。可是如果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其着眼/着重点并不在这上面。请听他的解说:"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也即是说,讽刺的性质更倾向于教化,而戏仿则是一种娱乐性的、以智力编制建构操控的游戏(表现为颠覆文字的基本要素,消解词与修辞手段后面的意指性等)。又比如,当来访者问及纳氏是否有过被自己创造的人物纠缠,并对其性格发展失去控制的情形时,纳答:"我从未体验过这个,这是多么矛盾的体验啊? 有过这种体验的作家一定是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我的小说构思是固定在我的想象中的,每个人物按照我为他想象的过程行事。"让人感到乏味的是,自以为特立独行的纳氏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大多数"现代写家"毫无二致。事实的讽刺意味还在于,上述"矛盾体验"恰曾发生在连纳也不得不认可其"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及为数不少的一批公认的"大作家"身上,而并非他所贬抑的"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
quot;戏仿"手法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是作品的平面化、漫画化、布景化,并因之染上讽喻意味与滑稽色彩。在戏仿魔力的笼罩下,人物(角色)不再具有生命,而是沦为承载作者理念的符号/被随意支配的傀儡,表现为"性格"的基本定型无发展,常带有"痴念"或执迷、弱智、心理缺陷、类
型化等倾向(近似某些“新武侠”小说人物的言行特征)。如果不是将纳氏创作中的这类现象孤悬隔离开来看,而是将其置入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比较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前述现象并非特殊的“个例",而是一百年间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带有普遍/共通性意义的"共案"。主要根源于被一致视为"新异"、"前卫"、"小众"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麾下的创作 —— 亦即智性/技术性/游戏性/互文性写作。
由此可见,无论从作品还是从其相关自述看,纳氏小说都丝毫未脱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时尚写作潮流。
4、"拯救"抑或"逍遥":
纵观纳氏生平,定居美国是最关键的转折点(以1958年《洛丽塔》出版为标志),正因为此,其对美国的亲善态度与皈依情感时常难以抑止地流露出来。当BBC的记者问:"有一天你会回俄国吗?"纳氏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
纳绝非坦荡率直之辈,他的信口雌黄恶语伤人有时却可能予人坦率的误导。以上述纳氏的话为例:"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第一句话是真的,原因是"强权政治的原始禁锢心态,只能产生原始的禁锢文艺",纳氏自然不会再回到那个水深火热的所在去。第二句话则显得喜剧而夸张 —— 跟身处国内备受饥饿、监控、恐吓,集中营里的关押、殴打、流放甚至枪毙等迫害的同行们相比,远居西半球"自由世界"里的纳氏显然难免有"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之讥(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我读着曼德尔斯坦写的那些诗篇时,我感到一种无可遏制的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地写作、思想、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在此,我们无意(也无理由)去指责纳的"独善其身"或"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想指出他言行中明显的用心叵测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纳氏再三表示他对政治小说、有社会意图的文学的不屑,他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一类的作家称为"勇敢的俄国人",同时又极为巧妙地暗示自己不愿从"文学角度"去谈论对方的作品,其贬抑倾向也就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他又在早年作品《斩首的邀请》和《庶出的标志》里"对德国的极权统治表示了绝对的遣责",并指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歪曲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现实,是"狭隘的陈词滥调"和"遵循党的路线"的"劣作"。纳的指责虽不无道理,不过,我藉此想说明的是:A、任何生存着的人都是一个"现实"的人,不管他如何有意躲闪退让希图置身事外,都难以完全回避许多情势和处境中必须面对的"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问题,纳氏也不可能例外;B、俄罗斯文学有着"公民意识"的可贵传统,它始终承担着关注并守护普通人心灵与道德状态的使命,致力于同非人的集权制度相抗争,这样的写作是灵与肉彻底投入的写作。两相比较,纳基本上是一个全身远祸的逍遥者,一个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不过纳氏显然并未真正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这点(比如《洛丽塔》诸作的艺术成色到底怎样,其写作含有多少商业化动机等等,他自己想必也心知肚明——刀枪不入信誓旦旦更叫人生疑)。至于他以"专业评论"为借口对"勇敢的俄国人"所作的居高临下的贬损,则更加暴露出纳氏虚张声势的自负、偏见与无知 ——在我看来,以血肉之躯的生死体验和精神深渊中的良知搏杀为根基熬出的对人类真实处境的洞见、呈示与悲悯跟那类技术上圆熟完美的智性写作相比,其价值的孰高孰低,答案应该说是不难得出的。无庸讳言,纳氏的政治见解是肤浅幼稚的(仅止于本能性反应层次),但他又并非钱钟书式的从根底上看透了人类社会诸种把戏与人性本来面目的智者类人物 —— 大半生为生计辗转奔波的经历使其难免对迟来的世俗名利过分恋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他既郑重宣称不屑在小说中作政治、道德说教,并拎起一根笼而统之的"艺术"大棒八方挑衅,贬斥谩骂同行以示自己卓尔不群,同时又有意无意在各种场合率性发表一些浅陋蛮横不负责任的臧否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言论的怪现状。
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广大的,它需要"拯救者",也不排斥"逍遥者",只不过在这个痛苦残暴、精神与肉体的郁闷哀伤都已深切到史无前例程度的世纪,对前者的招唤似乎更为急迫,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丘吉尔语),能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