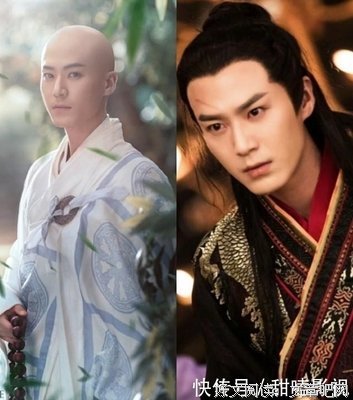
《欲望的旗帜》是一本由格非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欲望的旗帜》读后感(一):欲望的旗帜
格非的《敌人》、《边缘》对于周围环境的描绘所用的笔墨很多,着力渲染一种氛围,如描绘看不见的《敌人》诡异、紧张的氛围,描绘《边缘》人物的弱小、苍白无力。而这篇小说的对话在文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环境描写与对话描写有了种平衡感,就小说的写作顺序而言,这也算是格非写作手法逐渐成熟的表现之一吧。小说中掺杂了更多哲学化的成分,我觉得小说最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生活在真实之中。 正如小说所说:人们很难忍受实际生活中的空虚,乏味,无聊,他们的智力就被驱赶到了幻觉和想象的领域。通常,他们一旦觉得无路可走,想象力和虚构的愿望就会像野草一样生长。 所以,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不愿意面对生活,才会煞有其事的大谈哲学、欲望等,生活是无趣、枯燥的,要敢于面对这一事实,要在生活中加入有趣的哲学讨论,而不是用哲学来指导生活。
《欲望的旗帜》读后感(二):《欲望的旗帜》
“夜幕之下浮出多少张脸,这个城市就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本以为曾山是主角,后来发现每个人都是,大家都在各自欲望的深渊中沉沦。 人们仿佛一直在出俗和入俗之间摇摆不定,选择狠下心来放弃幻想接受现实,却又在不经意间闪过心底摇曳着的光。 张末似乎就是这样纠结地存在着。 她年少时对神圣爱情的向往,“她的爱情就犹如深秋时节被雨水洗刷后的一片山林,清新,爽净,简朴而悠远”。 然而她还是过上了她母亲所期待的生活,白天教书,下班后上街买菜,会与蓬头垢面的小贩讨价还价,被肥皂剧中粗俗的对白逗得哈哈大笑。 “过去的岁月在她眼前渐渐远去,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连她藏身其中的黑暗也一并失去了。” 故事不断展开,就在要真相大白的时候,一切却都悄然画上了句号。 没人告诉我们在故事开始时贾教授为何自杀,后记中也不见曾山的故事,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中,留读者自己去揭晓。 “当欲望的旗帜张开,有的人倒下,有的尚在挣扎,有的已经奔赴另一场狂欢。”
《欲望的旗帜》读后感(三):目的是击溃一切欲望
一两个小时以后我裹着沉重的羽绒服,刻意放慢步调去大门口取餐。手机被重重扔进口袋。如果烤串好吃我就原谅他,否则……情绪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又聚集皱巴起来,搅得人难受。走到一半,看着破裂斑秃的水泥路面我想,巨大的悲愤又攫住了我。无济于事的悲愤。我感到悲凉,巨大的虚无,荒诞,末日来临前的窒息。 不想看这样的东西了。我的日常生活中,类似的情绪已经过多,底色饱满,露出洞悉一切的疲惫笑容,无济于事的安慰。情绪。微波炉里的两个扇贝,替换掉的烤鱼,不能掌控的选择。 我对麻辣拌有着近乎挑剔的鉴赏力。因为我见过好的,这样我似乎感到满意——我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毫无要求无法批判,我也可以对别人说“我觉得这个不行”。 解释规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了解其中逻辑。生活在真实中。这也是竹山的经验。 也不必任何事都有答案。这是我学到的另一个经验。
“生活 真是易如反掌”。越是严肃的人越早溃败。
(睡前看到有趣的相册:我尚未明白那篇论文的意义。应景啊
《欲望的旗帜》读后感(四):午夜两点的电话|可以悦读《欲望的旗帜》
上世纪80年代,作家格非凭借《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等中短篇先锋小说,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坛,与余华、马原、苏童、洪峰并称为中国当代文坛“先锋五虎将”。此后陆续出版了《敌人》《边缘》等长篇小说,从《欲望的旗帜》起,格非开始书写当代题材,试图从先锋作家转型介入现实。
欲望的旗帜7.7格非 / 2020 / 浙江文艺出版社今天「可以悦读」和读者朋友分享的内容,是格非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第一章的节选: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一场重要的学术会议将在某高校举行,大会前夕午夜两点,哲学系副教授曾山突然被电话声惊醒……
第一章
预备会。代表们陆续抵达该市。在大会开幕前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
秋末的一天。曾山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
作为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早就养成了凡事追根寻底的习惯。他知道这一习惯并非为学术研究所必需,而仅仅是智力活动遇到阻碍的明显征兆。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他记得,从铃声响起到他拿起话筒这段时间的间隔并不太长,也就是说,对方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通过电话聊聊天,临时又变了卦,因为时间毕竟已经太晚了。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在他自己身上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能排除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的可能,但曾山显然不太愿意作这样的假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电话的突然中断预示着对方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屋外的狂风大雨使这样的联想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歹徒跳窗而入,女主人电话呼救……这样的情形原先较多出现于好莱坞式的凶杀片中,但在目前的中国,类似的案例倒也并不罕见。
在知道他电话号码的几个人中,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贾兰坡教授。身为这次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为了应付烦冗的会务琐事,贾教授嘱咐他的几位弟子随时听候差遣。一周之前,曾山与导师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曾山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大会筹备组,打算在会议上宣读。贾兰坡教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建议他“暂时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师生二人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曾山一怒之下便出言不逊,并声称他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他的导师一时语塞,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至此,师徒二人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微妙关系终于难以收拾。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如期举行。曾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得早早在床上躺下。虽然此前并无迹象表明那个顽固的斯宾诺莎的信徒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曾山依然在暗暗盼望着导师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寂之感。
接下来,他想起了他的师兄宋子衿博士。近些年来,他几乎已中断了他的哲学研究,将兴趣转向小说写作,并渐渐地拥有了一批读者。与曾山相比,宋子衿与导师贾兰坡之间的关系则要亲近得多。这种亲近之感并非源于学术上的一致见解,而是他们各自躯体中流淌的血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他的论文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之一,已被列入议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出席了昨晚的预备会。
如果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预备会议上一定出现了妙不可言的趣闻。一般来说,子衿不会放过任何冷嘲热讽的机会。那些迂腐不堪的学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除了成批地制造笑话与丑闻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子衿的电话或来访通常都与他身边的几个女人有关。对他来说,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他常常这样为他疯狂的追香逐艳的行径辩解,“再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本次大会会务组的临时召集人,老秦在深夜两点打来电话的可能性很小,何况,他们两人平时交往很少。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某位代表由于在发言时过于激动,突发心肌梗塞,急需送医院抢救(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这一玄想);或者,一位学者深夜驾到,被雨水困在了机场。再说,预备会结束后留下的数不清的烟蒂、果皮、茶杯总得有人清理……
几天前,老秦在校园里碰到曾山,曾悄悄地将他拉到一边,对他的论文被贾教授否决一事表示了慷慨的同情。接着,他向曾山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几个人已经酝酿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在大会期间付诸实施,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外传……”曾山不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谁,他对那个计划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只是稍稍敷衍了两句,便抽身走开了。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曾山知道自己已无法入睡了。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尽力使自己从这种无聊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明白,曾山对电话的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需要说明的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最应该首先想到的那个人恰好被他遗忘了。这种情形至多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们的大脑注定要将某一事件遗忘的话,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尚不知晓的奥妙。
2
站在寓所的阳台前,曾山不知所措地将视线投向窗外。他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槭树叶泛出红色,预示着初冬的降临。网球场上杳无人迹,表明泥地尚未晾干,煤气厂高高的圆塔耸立在远处,在它四周堆积的厚厚烟尘为一阵西风所吹散,天空再次呈露出它浅蓝色的质地,衬托出由树木、楼房、肮脏的街道编织而成的尘世图案。
多少次,曾山就这样看着张末从阳光下走来。她绕过网球场的一角,绕过那排漆成白色的护栏,出现在他的窗下。
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清晨,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轻轻地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替他打开窗帘。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双眼,亮晃晃的阳光就迅疾无比地照临到他的床头。
他一遍遍想象着这些残破的画面,吮吸着它的芬芳,徒劳地搜寻着它的踪迹,它所留下的嘈杂的回响。 张末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曾山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开始,他只是远远地注视着她,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但在暗中却突然加快了与妻子离婚的进程。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深深地打动了。那是一种消毒药棉的气息,它仿佛暗示了她的卓尔不群,却也证明了爱欲的存在。
可是,到了后来,他却不再喜欢这股气息,甚至感到了憎恶。实际上他是不太习惯张末对于洁净的苛刻要求。在张末被迫放弃了用药棉擦手的习惯之后,他觉得酒精的味道依然在她身上萦绕不去。 “这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张末曾这样提醒他,“你的判断力受到了记忆的愚弄。”
在他的记忆之中,张末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那是辛格写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可总也读不完。或者说,她舍不得将它一下子就读完。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国犹太作家,被称为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告诉他,这本书是她最喜欢的两部小说之一。
“那么,另一本呢?”
“《堂吉诃德》,非常可惜,我已经将它读完了。”
对于书籍,张末自有她的一套见解。似乎一本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够激起睡眠的欲望。她总也睡不够。
通常,她一旦坐于桌前,打开一本书,书页便不再翻动。她的呼吸越来越匀称,眼皮慢慢垂落,目光游移,让人难以捉摸。过不了多久,便会一头栽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
有一次,在她睡醒之后,曾山问她为什么如此喜欢辛格的那本不起眼的小书。她想了想,告诉他,她十分喜爱魔术师给他的两匹马所起的名字。
“它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
“那么,《堂吉诃德》呢?”
“驽骍难得。”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他知道她喜欢马,喜欢冰块和柠檬,喜欢幽蓝色的小花以及那些透亮的虚幻之物。
当然,还有用灯芯绒布缝制的背带裤。
她曾不止一次地央求曾山陪她上街去买一条背带裤。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能得到这样一条裤子,可他们每次上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起先,他还以为她的犹豫不决是因为她尚未找到合适的款式。时间一长,他才渐渐明白,她也许永远也不会真正买下一条背带裤,她只是看看它。用她的话来说:“我知道它在那里。挂在玻璃橱窗的木架上……”
对她而言,愿望的意义仅在于反复被提及,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延搁的快乐。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论哲学。在她看来,它过于严肃了,谈起来不免显得做作,“就好像我们真的能拿这个世界怎么样似的。”曾山反问她:“那么,在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上,你对于纯净和安宁的渴望难道就不做作吗?” “一点也不,”张末答道,“歌德就曾经说过,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奋斗、一切的呐喊,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永恒的安宁而已。”
在他们相识六个月之后,她第一次同意与他做爱,但随后就变了卦。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将她推向床边的火炉前,她依然感到畏惧。她的目光躲躲闪闪,再次向他发出央求,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鹿。而他则装着没有看见,未予理会。
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他能够感觉到她一夜没有睡好。
天快亮的时候,曾山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大雪在窗台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而炉火的灰烬早已熄灭。 借着拂晓的一缕熹微的寒光,他看见张末的枕下压着一册墨绿色的记事簿。他轻轻地将它抽出来,打开它。在第一页上,他读到了两行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下的诗句:
I’m yours
and my dreams are yours
他似乎隐约记得,这句话是从《卢布林的魔术师》上抄录下来的,但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他并未想到,这种喜悦的泪水同样是虚幻而不真实的,甚至是廉价的,仅仅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错觉。
当曾山终于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和张末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他像是从一场冗长的梦中醒来。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过的那样:一切都是静默的,暂时的,可替换的,树与石只是树与石。
但他还是牢牢地记下了这句话,并将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