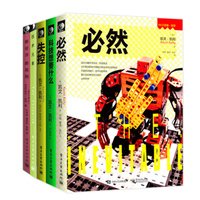
《互联网的误读》是一本由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 / 娜塔莉•芬顿(Na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互联网的误读》精选点评:
●现在目前时代的高点上去看待过去,当然能够看出许多错误。
●1 2019-5-1
●互联网就如同过去出现的报纸一样,新事物的出现一度被捧高,而事实上这些都不过是工具而已,关键是使用者与使用者的社会关系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
●对各种新媒体神话的去魅
●感觉需要再精读一遍(有时间的话
●从现在国内的情况看,有些观点已经落后于现实的状态了。
●挺一般,也都是常谈吧。缺乏理论,更像随笔集。
●大概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能读原版就读原版 没有能力读原版看繁体版 简体是最后的选择 删掉书中的一个部分难道不是阉割一本书吗??!
●挺好的书~另外,这个翻译看着实在是太舒服了,充分感受到了好翻译对的重要性
●得到听书听的,一般,做个记录,就不看书了。
《互联网的误读》读后感(一):审慎看待互联网
《互联网的误读》读后感(二):互联网的误读原因
互联网这一新兴技术逐渐发展,形成很多平台并逐渐延伸到各个领域,其影响力逐渐随之延伸。可以预想互联网未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力也会逐渐增大。
《互联网的误读》一书主要讲了技术对互联网的冲击和互联网的影响,探讨了互联网如何改变社会、互联网的历史、互联网中的政治经济学、互联网的规制、社交网络、互联网与激进政治的关系等。该书通过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总结,并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观点进行分析,提出对互联网的误读的分析,结合实例,让人对互联网的发展脉络与相关理论更加了解。互联网误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互联网与社会历史语境
关于互联网的误读,很多偏离了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
很多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很多事件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并非因为新技术而引发,社会问题尤其如此。比如2010年-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发的一系列政治抗议活动,并非是Twitter/Facebook引起的革命,而是有着更加深层的原因。抗议的预兆早先已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异见的积累。数十年异见的发酵、高失业率和低就业率,部落冲突、宗教仇恨是变革爆发的重要促发因素。
互联网作为历史中出现的一项新技术,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在历史中,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历史进程,并非单一因素会导致社会变革。
互联网在推翻维权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有效。但它却是妇女运动提供了工具;推动了妇女的进步。集体性强的群体文化可以产生互联网支持集体身份的结果。互联网与社会的互动是复杂的。而社会对互联网的影响超过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许多寓言没有实现正是因此。
二、互联网中心主义
互联网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气象。但是很多对互联网的误读潜藏着一个假设:互联网技术将使一切气象一新。这些寓言的核心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将互联网技术作为一切技术的终极版,是颠覆性力量。
互联网确实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将互联网看成是神一般的存在,太过夸张。戴明朝老师所说的互联网概念——灵魂无限泛在的技术实现。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细细想来却是将互联网升级到了终极技术力量的高度。但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我们无法预见的,互联网是否会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是否会出现新的超越互联网的技术,这些都不可知。若是出现新的技术力量超越互联网,那么这个定义也可以适用于那个新技术了。这个互联网的哲学概念便有点偏向互联网中心主义。
互联网发展迅猛,逐渐改造着整个世界。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变革性技术力量也都曾在各方面改造社会,影响历史进程。几世纪前的印刷术的发明到今天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技术不断发展,新的技术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互联网技术也会像蒸汽机、印刷术一样逐渐边缘化。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若是出现一个终极性技术力量,历史进程如何推进呢?终极性技术力量的预设与历史发展进程相悖。
三、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在考察技术时,经常把人作为考虑中心。
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为人类所用,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与社会。但技术并不是谁能掌控的。若将互联网技术单独看待,它是着自我生长性,是自主的。互联网技术一代代发展,从1991年万维网的建立,到全球互联网快速普及,再到互联网深入生活方方面面,可以看出互联网有着自身发展的路径。互联网技术发展没有人知道将走向何方,它有着自我生长性。互联网技术是超出人的发明,有着内在的进化逻辑。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将互联网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但忽略了互联网技术自己客观的发展逻辑。
《互联网的误读》读后感(三):译者序
一、相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怀
自2006年以来,我翻译出版了三本政治学、传媒政治经济学和新媒体演化的书,这些书均有创意,颇有锋芒。它们是《新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新新媒介》(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政治文化》断言阶级政治消解,党派政治式微,侍从政治淡出,认为阶级、党派、阶层、群体、集团的利益似在趋同。然而,它又承认,在乌托邦似的理想社会实现之前,任何社会都是分层分派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仍然适用。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质疑由资本家的利益和狭义的政府利益决定的文化议程。
《新新媒介》从媒介哲学和媒介演化的角度阐述了新新媒介的性质、定义、原理和特征,重点之一是深刻影响社会文化和个人的社交媒体。
2013年,我着手翻译的众多著作里有四本与当代政治和媒介有关。它们是:《互联网的误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群众与暴民》(复旦大学出版社)、《媒介、社会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新新媒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这几本书的政治经济文化关怀是相通的。
二、网络问政的及时雨
互联网革命、社交媒体革命、微博革命的呼号、呐喊、惊叹甚嚣尘上。媒介革命在什么意义上、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革命?
互联网对个人的表情达意、朋友的交流、同事的合作、同业的共事起什么作用?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球理解有何影响?对社会运动、对抗政治、反全球化运动、反独裁革命、反新自由主义有何推进?
无数的问题摆在政府、学者、网民的面前。如何解答?如何解决?
《互联网的误读》平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解说和主张,比较理性地审视互联网的性质、历史、功能等方方面面,不失为一本及时的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踏上了伟大的新长征,正在经历急剧的变革。我们的梦想是民富国强、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我们的理想是和谐社会、人民幸福。但在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在信息化、新媒体时代,一切矛盾均可放大。一只蝴蝶可以掀起翻天巨浪,一句谣言可以使万民不安。如何尊重民意、善待民意、引导民意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执政党应该是为民党,民有、民治、民享应该是政府的唯一本质和唯一宗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完善自我,完善执政能力。此间,倾听、沟通、引导、学习民意成了日常的要务。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执政经验都在学习之列。
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不可否认,网络问政也分上中下,左中右,消极和积极,温和、激进与极端,建设性与破坏性,理想局面与沮丧后果。“网络行动”的参与者既有“良民”,也有“恶棍”。英国人发现,2010年和2011年英国国内骚乱期间,“网络行动”的参与者就良莠不齐、分化明显,这是考察“网络行动”时不可不察的国内问题。2009年伊朗的“绿色革命”、2010年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就有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子,这是不可不察的国际问题。
新政治文化作为成熟的政治学课题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网络政治和网络问政则是比较新的课题。除了政界、政治学界之外,新闻传播学也要承担责任,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应该享有一席之地。
《互联网的误读》是一场及时雨,回答了互联网时代诸多的政治问题和传媒政治经济学问题。
三、全书概览
《互联网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从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简单介绍互联网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篇幅不长,简明扼要。
《误读》内容并不宏富,观点并不复杂,征引却极其丰富,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互联网的历史和影响;检视各种理论,批判各种实践,分析社会政治运动;肯定互联网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因素之一,但否定互联网决定论的思想;解析各种已有的和可能有的误读,现实针对性很强。
三位作者分头撰写,却配合默契,合作完美,因为他们是长期共事的一个团队。
柯兰牵头写第一部分“总论”(第一、二章)和第四部分(第七章)“展望”,画龙点睛,唱压轴戏。
弗里德曼承担第二部分(第三、四章)“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这部分讲互联网经济和规制。
芬顿负责第三部分(第五、六章)“互联网与权力”,这部分讲社交媒体和激进政治。此外,芬顿还负责第七章的部分内容。
《误读》大量征引,细察各家主张,防止片面;澄清差异,廓清谜团,纠正误解;做出解释,提出前瞻,非常详尽。
第一章“重新解释互联网”是导论,该章冷静地指出:互联网革命的四大预言(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和报业复兴)并未实现。
第二章“重新思考互联网的历史”对各界人士撰写的互联网的历史进行纠正或补充,纠正伊甸园式的讴歌,纠正只顾西方、不顾东方的历史叙述,纠正互联网商业化历史的弊端。
第三章“Web 2.0和‘大票房’经济之死”指出,互联网经济同样受制于阵发性的供求危机和投机活动周期,并不是与“旧经济”全然不同的“新经济”。
第四章“互联网规制的外包”讲互联网的管理、治理和“规制”,指出互联网服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性,勾勒了互联网从开放走向封闭的历史轨迹,断言它“发明——推广——采纳——规制”的历史逻辑,同时又旗帜鲜明地主张维护互联网活跃、创新、平等、中性的原理。主张互联网规制的多管齐下:国家的规制和企业的自我规制以及市场的调节。
第五章“互联网与社会化网络”或许是读者最感兴趣的一章,因为它论述人人感兴趣的社交媒体。该章分四节细说社交媒体的动力机制、多样性和多中心性、从自我传播走向大众受众的走势以及新的社会讲述形式。作者看到社交媒体功能的“无穷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并不是为社会谋利,也不是政治参与;其首要功能是表情达意,按照这一功能,理解社交媒体的最好办法是考察它们表达政治环境的动态(常常相互矛盾)的潜力,而不是去重组或更新支持它们的结构”。
第六章“互联网与激进政治”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章。互联网很适合激进政治,能催生、促进和放大激进政治。本章考察了多种多样的激进政治和抗议活动,剖析了近年英国的学生运动、“阿拉伯之春”、伊朗的“绿色革命”、反全球化运动。
第七章“结论”画龙点睛的意义不言自明,作者重申了各章的主要结论。互联网诞生时有关它神奇魅力的四大预言都失算了,我们仍在为互联网的“灵魂”而战。有关互联网抒情诗似的理论阐释都有偏颇,互联网的规制应政府、企业和市场多管齐下。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常常是在消费者或个人意义上的表达)的媒介,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娱乐和休闲的媒介,而不是政治传播的媒介(政治传播仍然由旧媒介主宰);是精英和大公司形塑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互联网是全球性、互动性的技术,与更国际化的、去中心的、参与性的政治形式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作者提出的一揽子建议旨在复活公共利益的规制,意在扭转市场与国家当前的关系。他们呼唤的是建设性的、可以践行的干预手段。
《误读》最后的结论是:“互联网的运行要使公众受益,它们不应该受到国家或市场的歧视。这个要求很紧迫,需要在一切层面上得到满足:国家和超国家的层次,离线和在线的层次;在社会运动和社交媒体中,在我们所属的一切网络中,这个要求应该都得到满足。”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3月8日初稿
2014年5月定稿
《互联网的误读》读后感(四):互联网能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吗? ———评介《互联网的误读》
《互联网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一书对互联网之媒介中心主义神话进行了祛魅。由于身在媒介中寻觅着数字足迹生活的人们将互联网当作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向,并以此给自己的日常仪式和习惯定向,因此人们迷信于互联网制造的神话中,绕过了社会政治生活深刻而关键的语境。
《误读》针对这种对互联网去语境式的认识和理解,特从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语境还原,在肯定互联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所重大影响之同时,也廓清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各种神话式谬见。互联网并非在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而受到其所在语境中的各种力量形成的合力的推助。
《误读》在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的历史的基础上,对互联网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了互联网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关系。这种分析路径是政治经济学式的,在分析之途上《误读》检视了各种理论,批判了各种实践,分析了一些社会政治运动。
具体来说,互联网究竟是从哪些方面或者说以怎样的进路来使人们对其产生迷思,而《误读》又是如何来祛魅的呢?
1.四大预言的破灭
2.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
《误读》对于媒介中心主义的神话从历史上做了简明扼要地探源。《误读》指出“和早期的互联网历史一样,那时的报刊研究也在技术的祭坛前顶礼膜拜,报刊(Newspaper Press)的首字母也是大写。那些著作也谄媚吹捧,把大众报纸的兴起与理性、自由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报纸的弊端凸显,报刊推进理性、自由和进步的作用受到了挑战。互联网的发展轨迹与报纸的发展轨迹似乎在初始阶段有部分重合,而这些重合部分都有妄自尊大之冒失。《误读》中关于互联网几大驱动力的分析,能有力地诠释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当代媒介秩序的领导者的角色。互联网是“军方-科学家复合体”,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和欧洲的反文化运动对互联网的广泛化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文化运动使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具有了人文意义。互联网成为了世人共享知识的媒介。
资本向互联网的渗透,让互联网逐步私有化。本来开源的代码被“专利化”为封闭代码。开源代码相比封闭代码具有更强的民主味。本来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被垄断了。商业化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大型商场,产品和服务在此兜售。付费网站的大量激增损害了互联网作为开放公共领域的性质。鉴于此状,有些科学家们开始反叛了,他们开发出免费开源代码抵制封闭代码。例如Linux操作系统就是反叛的代表作。在全民对免费开源代码全力热捧的情况下,像IBM公司放弃眼前利益,决定搭顺风车,参与到对封闭代码的抵制当中。开源代码支持用户生产的内容,有力地促进了互联网去中心化功能的增强,使其成为公共领域空间。
开源代码运动使互联网从技术上支持了阿拉伯人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突尼斯、摩洛哥、约旦、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暴。由于这些抗议活动时间短、又得到了技术的支持,有些人就将其称为Twitter革命或Facebook革命。但是《误读》认为这是一种忽略社会语境的“误读”。传播技术不是点燃阿拉伯地区抗议怒火的特别重要的因素。之所以革命爆发有着更深层的混合因素。在这些国家之所发生起义,混合因素中的公因子是经济因素,物价的高涨给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另外,政治、宗教等方面也是混合因素之组成部分。互联网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第二位的。《误读》承认新技术加强了起义的力量,但是它是否强大到能推翻政权,而且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还尚需观察。
互联网促进了妇女的进步。互联网为有组织的妇女运动提供了一种工具。但在阿拉伯地区由于妇女的识字率特别低,因此上网特别受到限制。而在伊朗因49%的网络用户是妇女,所以互联网成为中东妇女运动的左臂右膀。《误读》对这种认识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是很多互联网的内容受男性至上价值的影响,其二是只有很少的妇女阅读直接来自妇女运动的内容。《误读》让人们明白尽管互联网能使独立自主的妇女形象广泛流通,但是文化语境对于妇女借助互联网展开运动是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因素。
互联网正在消解集体主义的价值,个人主义越来越盛行。《误读》认为网络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到底如何,还要看语境,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在集体主义的东方有别于更加倾向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但是变革的动力正在走向个人主义,因为互联网加强了自我传播的能力,加强了个人主义的趋势。人们一般以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特征,但是《误读》用证据表明,互联网也强化了亚洲人走向个人主义的趋势。
3.互联网经济同样受制于阵发性的供求危机和投机活动周期
当前的时代精神建立于互联网的转换力量之上。无论在网络书店还是在实体书店,书架上摆满《群众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Crowdsourcing: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我们思考:大众创新而不是大众生产》(We-think:Mass Innovation Not Mass Production)、《人人参与:无组织的组织力量》(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ations without Organization),等等。这些书名有一个思想基础: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数字技术与合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进行社会交往、自娱自乐、了解世界、从事公务尤其经商的方式都为之一变。《误读》认为这些书是Web 2.0世界里的读物,他们和10年之前出现的一些书异曲同工。例如《距离的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知识经济大趋势》(Living on Thin Air)、《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这些书名共同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新千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新经济”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
进一步地看,媒介技术的换挡加速促成了媒介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将创新的工具交给了大众。摄像机、编辑软件、宽带费、手机话费降价,内容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掌握在群众手中。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Purcell,2010),美国的青少年中,有38%的人经常分享网络内容,21%的人对网络内容进行再加工,14%的人写博客。这说明互联网大大拓宽了用户的参与范围,大众可以在“众包生产”中贡献自己的思想。许多公司积极搜集“用户生产内容”,想借此降低成本,使自己与“用户生产内容”的“符号学民主”拉近关系。互联网技术引发的革命正在使市场变得扁平化,呈现出“大市场式微,小市场万岁”的景象。
4.互联网规制的多管齐下
人们也许对于互联网是自由话语空间的迷思如同互联网去规制的健将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一样痴迷。巴洛崇奉美国宪法的自由原则,崇奉网络空间的自由,号召人们抵制《传播风化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通过发布斗志十足的宣言支持互联网的独立,得到了许多网络斗士的附和。许多有影响力的热衷于新网络环境的人发表了看法。例如《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论述了模拟原子和数字比特在规制上的差异,法律是为原子世界而非比特世界所构想的,法律不应该存在于互联网的赛博空间中。《连线》的编辑凯文·凯利认为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转正常的无政府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主席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认为如何使公众的想象力聚焦于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政府的规制,甚至不是产业的自我规制,而是一个消费者能发挥作用、控制信息的环境。
这些声音反映了一个强烈的信念:终于有一个传播媒介可以绕开传统的守门人,可以篡夺其权力,尤其能规避“旧”媒介巨头和各种政府形式,并且能将权力还给普通用户。然而,《误读》与上述论调相反,回顾了过去10年里“互联网规制”过程中重要的关节点。这些回顾有助于形塑人们今天所理解的“互联网规制”。这些关节点分别是:互联网的非政府化规制,提出不需规制的保护,而是规制的节制;互联网的政府化规制,提出从微观上管理互联网的演化,确保网络空间对商务安全、对用户可靠、对政府可以接受;互联网规制的代码化,提出通过制定标准、制造硬件、编写代码来规制。
《误读》分析了各种互联网规制的局限性的基础上,认为互联网是一种矛盾统一体,互联网靠开放的协议运行,但它的中坚力量和入口是私人的,由私人运营的。对这种二分现象的唯一回应是接受一个既定的趋势:遵循一个既定的技术逻辑,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张力会充分展开。这一展开过程意味着从公众走向私人、从开放系统走向封闭系统。吴修铭、克里斯·安德森、黛博拉·斯帕尔(Deborah Spar)对此都有相似描述。但这是以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解读技术演化。这是危险的:认为规制不是以具体的观点或信念为依托去积极谋求形塑互联网的具体发展,或对互联网的发展做出回应;规制是耸耸肩、对既定事实表示无奈。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仿佛是上帝的意志,面对代码环境灾难只能泰然处之,对隐私的丧失、过滤软件的审查、公共思想领域的消失无可奈何。《误读》让人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会在互联网规制中消失是错误的,同时国家完全是规制互联网也是错误的。对互联网应该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多因素参与的相互制衡的规制策略。
5.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表情达意
显然,互联网有影响“普通”公民和弱势的社会群体和政治群体的潜能。Facebook和Twitter每天几亿活跃用户在进行着交往。有人声称社交网站捣毁了传统公共和私密传播领域的藩篱,把权力交给了用户,使私密关怀变得公开化,使官方政治和制度领域更容易受公民的监督。如此,互联网展现出一种“民享”、“民治”的特征。但有人也认为社交网站这种公开展示的传播形式和内容只不过是将“日常的我”(daily me)不断更新而已;而“日常的我”使公共问题拥有个人色彩,却失去了政治色彩。社交网站提供的在线营销和个人隐私的数据,只不过是进一步加重了不平等。这将导致公民个人主义。社交媒体存在于既有的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并未超越而是被深深的卷入,新自由主义语境被嵌入了技术发展的个性中,社交网站的技术延伸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并不是与其展开斗争。
《误读》认为围绕新技术,无论是广播、电视、互联网的辩论总是陷入毫无结果的二元对立框架,一边是乐观主义,另一边是悲观主义。这两条路径都误解了媒体的性质,误解了它们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形貌的影响,从而影响了社会政治的性质,误解了社会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这种还原主义式的各自一边倒,必然走向媒介中心主义,从而抵抗社会政治生活深刻而关键的语境化。似乎只要谁有权势掌握媒介,就能把信息传递给他人,因数以亿计的用户栖居于媒介的世界里。《误读》告诉人们这只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神话而已。经过《误读》把互联网和社会化网络置于这个神话中心的考察,认为社交媒体的首先功能是表情达意,并指导人们要理解社交媒体最好是考察它们表达政治环境的动态的潜力,而不是重组或更新支持它们的结构。它们表达政治环境的动态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说社交媒体更具表情达意功能而已。
6.互联网本身并不等于民主
互联网与激进政治的关系一再被神话般衍义。有些论者认为互联网能煽起激情和达成抗议。而另一些论者认为互联网并没有标示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对抗性政治文化,相反人们目睹的是一种变来变去的政治,距离下一场政治请愿永远都只有一次鼠标点击之遥。《误读》认为前一种认识路径忽略了占主导地位的环境。而后一种认识忽略了真实或潜在政治团结的体认,忽略了人民对于民主的渴望。这两条路径尽管不同,但是两者都把互联网放在了数字时代激进政治的中心。
互联网的确是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的工具,在广泛的共同主题下把多种话题融合起来,技术、青年和反传统政治相互促进。例如,在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埃及发生的“Twitter革命”。这样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正是由于社交媒体给他们打开了一个百宝箱,赋予它们大量表达抗议的手段,人们通过这些手段把多种话题聚合了起来的结果。与此相反的是,同样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的互联网,却被看成为导致社会精神分裂的元凶,互联网的多平台性,使得人人受制于人人。对新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成为平等和包容的传播的潜在源头,哈贝马斯也流露出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他指出,互联网非但不能保证政治动员与参与,反而可能会促成公民社会的碎片化。的确,社会行动被互联网“雾化了”,表现时而聚焦,时而模糊,反映了公民参与向新形式的转变,开辟了意见分歧而不是意见一致的公共领域。
对互联网实践与政治的认识路径颇具二元性,即使连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巨匠也拿捏不准。为此《误读》试图将互联网置于看似简单的社会语境里,力图求解人们对互联网传播与技术系统的关切。《误读》认为,当代互联网本身并不等于民主。在当代互联网与社会复杂的关系里,既有潜在的民主形成机制,也有潜在的反民主形成机制。具体是反民主呢?还是促进民主形成呢?战略的选择应该要适切“在什么语境下”的政治进步变革。
7.结语:被“过滤”的互联网
笔者认为《误读》的总体论证是沿着“正-反-合”逻辑进路展开。《误读》关于人们对互联网的“误读”是“正题”,其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在媒介中心主义神话中,互联网唯我独尊地脱离语境起作用;其二,互联网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是媒介中心主义的延伸。《误读》对这两种“误读”的纠正是“反题”,其使人们明白:第一,互联网脱离语境起作用是错觉;第二,互联网本身不是只靠技术建构,还有其他诸多嵌入性影响因素。“合题”是互联网只有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过滤才能起作用。撮要而言,《误读》旨在告诉人们,互联网能在“去语境化的状态”下搅动社会巨变仅是一种想象性的神话建构而已。
首发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