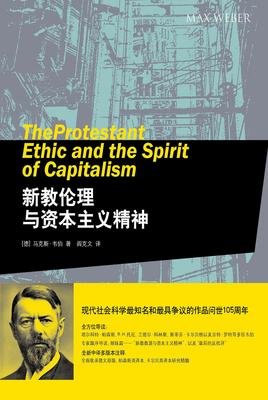
《基督教的兴起》是一本由罗德尼·斯塔克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3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基督教的兴起》精选点评:
●a must read book
●社会学写历史 是不太一样
●极为精彩而又清晰明了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具体观点上启发迭出,文章体例亦可资借鉴,结尾处由外在理路转回内在更增韵味。
●量化的历史。
●相当有意思。是持续的人口增长而非突然的集体归信、作为膜拜团体的早期基督教主要从社会上层吸收信徒而非底层、以亲缘关系为路径的传教网络、大瘟疫中因基督教教义而实行无差别救助……逐章深入由表及里,从最表面的归信人口增速到教义带来的美德。与受制于史料只能进行支离破碎史实建构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不同,Stark以社会学理论介入(如理性选择理论),用定量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当代新兴宗教兴起历史与之对比,来重构基督教兴起的历史。理论方法基础是对进化论的否定,对人类理性永恒性的预设,相当合我自己的观点。类似论文合集,体例可供借鉴,手把手教如何文献综述。局限在比较一神教的部分体现出来,Stark本人宗教背景的影响。
●力荐!!!!!!!!><
●思想资源是左翼的,即借用田野功能主义的方法,去还原基督教作为社会组织兴起的社会条件、机制。作者认为,罗马多神教徒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无法与基督教社团竞争,例如遭遇瘟疫,多神教徒会离弃“不洁净者”,而基督教社会会组织照顾病患。罗马后起大规模的瘟疫中,基督教徒更容易生存下来,其组织更容易壮大和吸引人,并显示神力的眷顾。此外,上层妇女大量信仰基督教,导致罗马上层男性贵族皈依,这也是走向上层社会的背景。这些思路,基本是功能主义的社会田野复原。如果西方右翼历史学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基督教的胜出不是一系列社会机制和偶然性叠加的产物,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展现了神意和恩典。
●比在十几个小时的航班上看这本书更蛋疼的事毕竟挺少的。作者对社会科学的迷恋令人心酸……或者虽然可能挺对,但他的表达方式太神经病了。
●有意创新的方法学,漏洞百出的论证,作者涉足史学实在是力有不逮。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基督教的兴起,作者也许不是基督徒,但他从别样的视角作出的分析,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启迪。
《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一):把学问做的雅俗共赏
读这本书时基本算是一气呵成,很喜欢,然后又自己琢磨为什么人家就能把学问做的这么生动有趣呢?想起以前硬着头皮读一些国内专著时的痛苦,真是不堪回首。
有没有想过剥掉宗教的神秘色彩,用社会学的方法去考量历史上的宗教发展?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打破那些隐藏的心底对宗教的敬畏和对神迹的盲从,真正把一个事件数量化。漂亮的紧啊
《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二):定量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做什么
可巧今天看到一篇关于最近披露的“全能神”教的新闻报道,提到了该“邪教”的人员构成,组织结构,发展模式等等。而刚读完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基督教发展之初,是通过何种方式传播开去的?如何理解“神迹”对归信的作用,社会网络扮演了什么角色,战争,瘟疫等灾难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凡此种种。
作为一个完全对宗教社会学一无所知,亦没有太大兴趣的人,读这本书全是因为一位喜爱的老师的推荐,而读书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于他具体论述的种种问题,提出的种种假设和结论(宗教社会学或者宗教历史的人会有兴趣),而是他论述的思路和方法,基本上是定量研究。
破题完毕。
我们只消来看看书里的一些论述,“把宗教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的商品”从而谈“宗教经济模式”,归信某一种宗教的“机会成本”,“殉道的理性”。基本上,斯塔克是一个具有十分科学主义精神的社会学家,我对于他用人口学的模型和数字去推论信教人口的绝对比例和相对比例,用测算城市之间距离的方式去推论宗教传播路线的方法表示非常感兴趣,且耳目一新(或者是我定量的东西看得太少,孤陋寡闻),总之,书里每一篇论文的模式都是如此,给出一个具体的假设(翻译成了“命题”),如“一个单一的宗教团体垄断一种宗教经济模式的能力取决于国家对于宗教经济模式管理的强制力程度。其次,一种宗教经济模式不受约束的时候,将会生发出非常多元化的倾向”,然后,用数字、模型、史料证实/证伪。
他显然是同意以下观点的,定性研究描述这个世界,而定量研究则负责解释这个世界,他的命题中,甲和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确定的,因果,正比,或者反比,所以可以检验。
遗憾的是,我仍旧没有办法觉得这样的研究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相”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所追求的,而且很明显,他力图证明,所得出的那些观点,是跨越某种宗教(一直将基督教和摩门教相比),跨越时间,跨越文化的,而人性是不变的。但是我还是认为,“真相”是什么不等于我们就更能理解这个世界。
《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三):基督教的真相:失传的圣经故事
在早年基督教还有使徒与圣人们在世的时代,那时的基督教是一个更加超自然的宗教,是一个强调体验天国或灵性境界的神秘宗教,后来才变成了一种标准的、有组织的信仰。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所持圣经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由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编辑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这个规范及审查圣经的过程大多发生在公元四世纪。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大多数经外书失去了它们的「经典」地位,只有少数经文被纳入「公元四世纪圣经」之中。而且很令人悲哀的是,很多重要的奥秘篇章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一千年来,希腊正教、叙利亚、苏俄、亚美尼亚、埃及以及其它古老教堂的旧版圣经一直包括这些经文。该是把这些数据公开的时候了,好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找到那些失传或被隐藏的圣经经文。
在考古发现的《死海手卷》中,我们可以找到「以诺书」。在书中,以诺先知描述了他在七重天云游的情形。如同埃及的郝米士和中世纪时代印度的伟大神秘人物卡比尔一样,犹太先知以诺描述了他在高境界之所见。
《多马福音》(也译为《多马斯福音》、《汤姆士福音》)记载了耶稣这位伟大的明师教导其弟子「我们来自于光,来自于光永恒存在的地方」,「光存在于由光化生的人之中,并且照耀全世界」以及「如果一个人完整,他将充满光」,还有「从我口中饮水之人将成为和我一样,而我也将成为此人,奥秘将会展现于此人面前。」
玛利亚被描述为一位与十二使徒完全同等的使徒,并为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玛利亚像是耶稣的灵性接班人,继承其教导其他门徒的地位。玛利亚因其超越的灵性了悟等级才成为其他门徒们的领袖。以复活后基督密传弟子的身分,玛利亚在她的福音书中教导其他门徒灵修之道,同时也很详细地描述她的师父(复活后的基督)以光之化身带她神游高等境界或天堂的体验。她将于这些奇遇中得到的基督有关灵修的指示传达给其他门徒们,而这些体验可能发生于她的深入祈祷或长时间静坐时。
诺斯替教派圣者的主要教理之一就是内在光的体验。事实上,看到内在圣光是一种普遍体验,全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天堂景象和内在圣光体验的记载。许多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经典中非常流利地描述与超越黑暗之上的光相逢的经历。许多圣者和神秘者,都将上帝或是无上存在描述为包含万物的、纯洁灿烂的光之神。观内在光的神秘体验是发生于深入祈祷或静坐时。
被排除在四世纪圣经之外的经典,多数提倡个人灵修体验以及打坐冥想。这个早期灵修传统从未完全被西方接受,而依我之浅见,这也就是它们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选自詹姆士.比恩所主持的广播节目的讲稿:失传的圣经故事。
宗教常有种现象,宣称信仰某个对象,可是信徒信的并不是这个对象的思想。而是这个宗教组织与组织的实质创立者的思想。例如道教宣称信仰的是老子,但其实大多数内容跟老子没什么关系。 佛教的某些教派的思想也不是释迦牟尼的思想。基督教也是,基督徒信的其实是保罗和教会,耶和华和耶稣只是挂名而已。
虽然基督徒都认为新约乃是旧约合理的延续,但犹太教并不认可。新约的构成比较简单,成书的时代也比较清晰可知,编纂的过程人为倾向很明显,篇章类型基本也就两大类为主——福音书和保罗等的教牧书信。四福音可以看成对同一事件或耶稣生平的不同描述和理解。而十几篇的保罗书信,更是强势的表现出作为教会成功组织者对后世教会和神学导向的巨大影响。保罗在文字数量上超过了耶稣的教导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保罗则肯定不是圣子身份,我们从两者可以看出巨大的思想差异,有人会把基督教称为保罗教。
耶稣和保罗对妇女的态度非常不同,作为女性,你应该对这个问题是敏感。耶稣对妇女非常尊重,哪怕是地位低下的妇女(被捉的妇女和妓女等),而保罗则不同,对妇女似乎无比仇视。至今基督教会不允许妇女讲道,还要蒙头就是这位保罗规定的。保罗从来没有见过活着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并什么可以代表耶稣的基本思想,取得以耶稣基督名义组织的教会绝对领导权,实际上没有耶稣的直接许可,甚至严重歪曲了耶稣的本意;有一些概念本来不出自耶稣基督,而被保罗独创出来,譬如“因信称义”;连基督徒也必须承认,作为圣子地位的耶稣基督对于宇宙终极真理的理解,应该是任何人不能超越的,而保罗提出的某些主张,则有明显与耶稣观点迥异。
最明显的例子是,基督徒受保罗书信影响,以为耶稣到来后的新约不用守律法了。这是错误的。耶稣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耶稣相信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预言都要应验,他跟信徒说的话都是拿希伯来圣经内容来替自己背书。
《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四):历史在发生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
历史在发生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没有人能够站在上帝的视角全知全能,不仅是时代的隔阂:现代的人与过去的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隔着时间的长河,现代的人想要了解过去是恰似拼图,用可以找的得到的零星碎片拼凑大概,但可能只是一角;还有个人视角的局限,即使是同一时代,甚至是事情的当事人,都只能从自身出发去揣度事情的全貌。
作者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结合大量考古资料、人口统计,结合近年兴起的摩门教试图重构基督教兴起的过程。这样的操作自然难免将许多东西简单化,但是真正地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不免会将一些旁支删去。故而全文的脉络十分清晰,问题也一个紧扣一个,比起一本学术书籍更像是一本侦探小说了,真挚地邀请读者一同解开这谜题——为什么基督教得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对于信徒这或许从来不构成一个问题,信徒或许坚信因为神带来的真理之光注定要照耀大地,神的力量如此伟大以至于让人生不出疑惑,仿佛它自创立以来必然就会繁荣昌盛。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则隐含着对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必然性的怀疑,至少不认为这个现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尽管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发现作者“西方中心”的苗头,发现作者其实是在力证基督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历史的必然并且最终回归到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上来。但是,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证过程是科学、理性的。
作者先基于数字分析将基督教的增长过程简化为量化曲线,在理论上说明基督教的增长不需要奇迹式的归信速度;再用摩门教的归信论证此点;接着,运用脱轨行为理论和社会网络命题,根据金荣恩的例子解释让人们归信宗教的原因是人们的情感依附关系。
紧接着,作者概述前人对早期基督教成员的阶级构成的研究,说明分歧,引出对早期基督徒的来源进行探讨;探讨宗教和社会阶层的关系,宗教的作用,是什么导致人们由旧的宗教转向新的宗教,论证缺乏传统信仰根基、对新文化感兴趣、容易接受新理念的人更容易投身宗教运动;通过摩门教的运动过程,对其中的成员的受教育状况分析论证这一点。在这一部分的论证中,作者打破了受宗教压迫的人更容易进行宗教革命这一观点。
诚然,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念影响的人,容易会想当然地认为进行宗教改革的是那些受宗教压迫狠的人。但是作者在这里点出,真正受压迫狠了的人是感受不到压迫本身的。须得那些知道不受压迫是什么光景的人才晓得什么是压迫,对压迫有着天然的敏感性。这样的人往往出现在施压者内部却又并非掌握绝对生杀大权之人,恰如历朝历代的造反背后站着的大多是在君主专制中获取好处或曾经从中获利现在失去渔利机会的群体。这样的人掌握着资源,有理论以及把理论付诸实践的能力,更可能摘得最后的胜利果实。
对于可能付诸宗教革命的对象进行描绘之后,作者开始着手解说现在关于犹太教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运用边缘人理论、介绍三个社会学命题并运用史料解释为何认定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一、新发起的宗教运动主要是从在宗教上不活跃和存在不满情绪的阶层和最世俗化的宗教团体阶层两个阶层吸收信徒。二、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与传统宗教在文化上有一脉相承关系的新宗教,因为他们对传统宗教已经十分熟悉。三、当社会运动在业已存在的社会网络中展开时,其速度更加迅猛。作者的这一点发现对于现在的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能有效地解释现在文化宣传中传统的回归。因为同宗教一样,人们更愿意接受与之前文化经验相似的文化。而据此也更能印证文化宣传依托于学校、社区等社交网络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这之后,作者将焦点放置于不基督教与异教和希腊哲学在面对瘟疫的时候的不同,以此说明基督教兴起的必然性:基督教能够解释灾难的发生,自圆其说并且发展人的潜力,在灾难来临之际看起来有效应,实际上也有效应。接着说明宗教的复兴是靠发动群众参与集体活动,而基督教能有效发动群众,爱人和普遍的爱的道德信仰使基督教徒的存活率大大增加。
然后作者将矛头指向基督教中的性别分布。论证基督教对女性的吸引力源于基督教对女性地位的提升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将女性地位提高和权利的提高与性别比例的重大改变联系起来。证明因为基督教禁止杀婴和堕胎使男女比例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又如何在后来随着女性教徒的增多而进一步扩大。论及女性基督徒与异教徒男性间相对较高的结婚比例如何导致基督教的“继发性”归信。说明基督教亚文化和异教亚文化之间出生率存在很大差别的原因,以及较高的出生率如何影响了早期教会的成功发展。
接着作者将目光投放在宗教补偿之上。作者认为宗教所提供的补偿是稀有的或者难以获得的报酬;探讨人类赋予这些补偿以价值以及交换这些补偿的理性选择过程;说明人们对特定报酬或收益的相对估价大不一样,论证个人会对宗教进行评估,衡量其收益和成本。解释投资于宗教补偿所要冒的风险,进一步阐释搭便车问题,引出污名化获得牺牲成为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法。殉教是基督徒能够做的最大牺牲,这种牺牲可以为其赢得生前身后名和实际的对于家人的照顾,所以殉教是一种理性选择。
接着以罗马作为例子,进行人口数量的分析,指出罗马对宗教的管制不严格,罗马宗教的多元化和过度多元化,宗教之间的竞争以及异教的孱弱使得基督教的兴起成为可能。说明社会的演化是向一神教迈进,指出宗教的排他性的产生和需要。
最终回归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认为是它激发并保持了有魅力的、解放性的、高效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基督的爱,脱离民族色彩和性别障碍使得基督教能够拥有吸引力。
本书巧妙地结合了文献资料和数据推演,为基督教如何从一个式微的群体发展壮大为世界性宗教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洞见。尽管真相不得而知,但或许人们追求的亦并非历史的真相,而是一点一点将真相揭露在众人之前的快乐。
《基督教的兴起》读后感(五):宗教社会学的侦探小说
相比《信仰的法则》中略显枯燥的理论演绎,罗德尼•斯塔克的这部《基督教的兴起》读起来十分有意思。作者在前言部分颇为严肃地讨论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但是通读全书之后我却希望以一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来描述本书的创造:罗德尼•斯塔克就好像是一个侦探(研究者),面对着一个“犯罪现场”(基督教业已兴起和发展的现状),希望从现场的种种蛛丝马迹(史料),加之自己多年办案经历积累的经验(社会学理论)和逻辑推理(逻辑推理),尝试重建“犯罪过程”(基督教兴起的历史)。
抛开斯塔克得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各种有关基督教兴起历程的结论不说,本书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史料的缺乏,因此,在考古或者考据有更进一步发现之前,很多历史事实只能是建立在扭曲而且支离破碎的史料基础上的。斯塔克的探索似乎指向了另一条捷径:将社会学所积累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推演至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之中。这就好像在对现存的物种的了解的基础上研究生物化石。
也正是因为如此,相比很多囿于史料限制的著作不同,《基督教的兴起》更好地展示了研究者自身理性研究的光芒。在对古代历史的推理中,斯塔克毫不吝啬地使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并不高深,但却恰到好处地填充了以往历史研究的不足。下文将列举斯塔克采用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而对斯塔克本书的创新特点进行归纳,此外还将就本书的一些局限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研究方法的案例分析
一、 跨时间维度参照样本比较
斯塔克在本书中多次使用了跨时间维度的参照样本比较,或者说以现代社会被充分观察和研究的群体或者组织来推测基督教兴起时相关群体或者组织可能所处的状态。应当可以说,斯塔克的基督教兴起的很多研究假设都来源于这些参照样本,当然斯塔克也不会忘了对这些假设在史料和社会学理论的支持下进行必要的论证。
案例一:统一教会和摩门教(第18页至第22页)
尽管统一教会和摩门教的例子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再次出现并被用来讨论其他现象。但是在第一章中,这两个样本被用来研究新兴宗教信徒增长的途径。通过对统一教会和摩门教的研究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即归信的核心因素是情感依附,因而这种归信行为通常容易在以人际关系为单元的整个社会网络载体上进行。
案例二:犹太改革派(第63页至第65页)
犹太改革派尝试将犹太教将神圣律法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相联系,继而对犹太教进行非民族化的努力被斯塔克用来和公元一世纪早期的某一位拉比对摩西五经的诠释进行了类比(第73页)。由于犹太改革派时期犹太人所处的状况和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的处境相似(这也是另一组跨越时间的类比),因此在斯塔克看来两者很有可能采取相似的行为,犹太改革派和一世纪早期拉比言论的相似性被斯塔克用来证明这一点。相比罗马时期,犹太改革派时期的材料和文献无疑更加丰富,由此归纳出的可能的行为选择也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也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斯塔克得以将边缘人理论引入对大流散犹太人中基督教兴起的解释之中。
二、 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引入
斯塔克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引入了或宏大获微妙的社会理论。以下将选择两个案例:边缘人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案例一:边缘人理论(第63页、第68页至第71页)
一个人在两个群体都拥有成员身份,而这两个身份彼此矛盾或彼此施压,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他在两个群体中的地位都被降低,这时,这个人就被边缘化了。由边缘人的概念出发,斯塔克得出了一个命题:人们总是会试图去逃避或改变自己边缘人的处境。历史上出现过犹太人在这种边缘化压力的作用下试图通过改宗基督教来改变自己边缘人的处境。因此,这个命题被斯塔克用来论述犹太基督教会出现的可能性。但是,斯塔克也没有忘记讨论这一理论对罗马时期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的适用性。在后文中,斯塔克指出“犹太人已经适应了大流散中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而言,已经被边缘化了……但他们也不能算作希腊人,因为犹太教无法预期源自犹太律法的民族性相分离”,并且给出了包括希伯来文的衰落在内的历史证据。
案例二:理性选择理论(第195页至第226页)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斯塔克提出的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在《信仰的法则》中有更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重复斯塔克理性选择理论的要点。阐述理性选择理论对研究基督教兴起适用性的第八章也可以被认为是全书的理论论述,如果说砍去这一章的《基督宗教的兴起》仍然可以被看作拥有一定社会学思维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专著,那么正是这一章宣告了斯塔克“社会学家而非历史学家”的身份。
三、 定性分析
作为一名接受了良好社会学训练的学者,斯塔克对定性分析的使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也正是这些恰到好处的分析使得本书的可信度有了更大的依据。
案例一:关于基督化进程的两种推测之比较(第3页至第15页)
尽管斯塔克在这一部分内容中已经通过对初始基督徒数量和最终发展规模的推断和与摩门教发展历程的比较得出了基督教徒可能的发展速率——每10年增加40%,但是作者仍然需要进行可靠的检验以进一步增加这一推测的可信度,并反驳“突然增长”论。于是,斯塔克将自己推测的基督教徒增长模型和埃及考古发现的埃及基督徒增长数字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条曲线的对比率达到了惊人的0.86。作者指出“通过不同途径和对于不同资源的调查所得出的如此吻合的结果,在我看来无疑对这两种数据都是强有力的印证。”
案例二:帝国城市的基督教化(第157页至第175页)
整个第六章都是作者对定量分析在这一研究中的适用性的演绎,任何一位读者都不应该错过这段令人拍手叫好的分析。作者为罗马帝国的17座城市设计了包括“基督教化程度”、“公元100年时的人口”、“从耶路撒冷的路程”、“犹太会堂”、“从罗马的路程”、“罗马化程度”等7个变量。在交互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基督教化”为因变量,“罗马化程度”和“犹太会堂”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在基督教化过程中惊人的67%的相关性。
在这一章中,作者还顺便用这一定量分析讨论了诺斯底派的问题,并由此得出的结果指出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应当将诺斯底视为基督教的支派而非与基督教平行的犹太教异端。
四、 严谨的逻辑推理
本书中是不是加入的用黑体标注的各种各样的命题便是作者逻辑推理的痕迹。作者从一些被现代社会学研究所证明的基本命题出发,推导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这种命题式的推理在形式上相比一般的叙述更加突出了本书的理性色彩。关于作者对逻辑和科学性的强调可以参见本书第25页至第32页,斯塔克对以往一些研究的批判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本书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分析
从大的方法论层次来说,斯塔克之所以能够将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无疑基于一种理性主义的预设,即当人类——无论身处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处于类似社会情境下时,他们都会从各自的理性判断出发作出相似的选择。因此阅读此书必须先否定各种形式的“理性进化论”,即认为人类的理性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或者更进一步将其视为现代化的产物。
由这个预设出发,可以进一步归纳斯塔克的研究思路,以期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有所启发。
步骤一
对现代社会的参照样本的研究,归纳出可能对历史案例具有适用性的相应社会现象和社会理论。
步骤二
分析已有的历史学研究结论。
步骤三
在对现代社会参照样本研究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具有社会学特色的研究假设。
步骤四
使用包括定量分析等在内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历史材料证明研究假设的可信度。
步骤五
在已经证实的研究假设的基础上以逻辑演绎重构历史。
本书的局限和不足
如前所述,斯塔克的分析基于一种对人类理性永恒性的预设,这可以被视为斯塔克包括《信仰的法则》在内的研究的基础和局限。因此就像前文所述的一样,如果坚持认为人类理性是不断发展而形成的话,那么本书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一种理论的局限并非一种理论的不足,因此这也不是这一部分主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我也倾向于接受这种理性主义永恒性的假设。
但是当我们着迷于斯塔克对基督教兴起的深刻研究之时,也不应当忽略宗教学研究的另一传统,即比较宗教学。如果说斯塔克本书的前95%都只是对基督教的较为客观而充分的研究的话,由第九章《机遇与组织》中的“走向一神教?”开始,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斯塔克某一种“基督宗教社会学”的价值取向,或者说由于论述不足而导致的某一种模糊的主观倾向性。在讨论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不同的宗教经济模式时,斯塔克令人遗憾地未能坚持一种社会学式的分析,而只是主观地从理性出发对两种模式进行了一种纯义理的讨论。不过不知道斯塔克在给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加上问号的时候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究,就可以发现斯塔克的理论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不妨将关注点从斯塔克的理论转移到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来,并用另一套学术话语去发掘斯塔克理论的局限,即:Institutional Religion(为避免可能的歧义,我暂时使用英语统一的命名方式,而非五花八门的翻译)究竟是不是为社会所必需?Diffused Religion难道无法承担人类的理性?如果这样,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文明又是凭借着什么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
在这篇简单的书评中我不会尝试展开对斯塔克的批判,应当指出的是斯塔克本书的瑕疵虽然仅仅体现在他似乎忽略了对东方宗教进行他一直坚持的社会学的思考和研究,但是追本溯源,斯塔克在本书中多次强调的“教义”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导致这一瑕疵出现的理论根源——或者说,斯塔克的瑕疵可能并非看起来那样仅仅是“瑕疵”而已,而是其关注宗教教义这一方法自身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毕竟相比Institutional Religion,东方的Diffused Regligion的教义和世界观并不容易被进行简单归纳,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于某一部宗教经典之中(甚至没有类似亚伯拉罕宗教的宗教经典),而是隐藏在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等等更加世俗化的社会现象之中。
因此,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斯塔克令人遗憾的展示了其作为社会学家和基督徒两者身份的矛盾,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作为社会学家的斯塔克倒了下去,站起来的是一个基督徒斯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