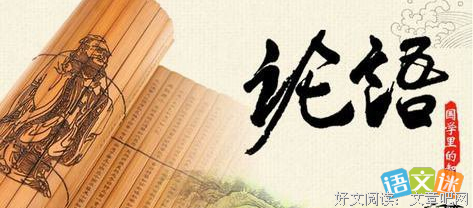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是一本由Carlo Ginzburg著作,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19.95,页数:1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精选点评:
●通过宗教审判所的档案深入分析一位十六世纪晚期意大利“普通”磨坊主的思想世界,指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互动,而非单方面的灌输。尤为精彩的是对该磨坊主阅读习惯的分析,指出其阅读精英或大众书籍时带有一双“批判的”眼睛,选择性阅读,自我组合所读材料,从而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世界观。
●读疯了。。。
●我們都是Menocchio。
●文化史通病:过度解读。
●微观史学典例,以小见大
●“I have said that, in my opinion, all was chaos, that is, earth, air, water and fire were mixed together; and out of that bulk a mass formed— just as cheese is made out of milk— and worms appeared in it, and these were the angels”.
●Argument is questionable, but very readable. I feel sad when I read the last several chapters stating that Menocchio was executed.
●金氏的史学论述可见于此书的序言。文中大部分内容是史料分析,而论述则夹杂其间及见于58-61章。此书内容概括可见豆瓣上唯一一篇评论。 这本微历史的最后点睛一笔点在了上流社会文化与低层大众文化的交互交流。
●好看><比论文好读很多很多(不过学姐也确实默默教导说短篇们才是Ginzburg的精华所在><)...the high & the low 似乎是Ginzburg的主题之一...马克:Preface[值得一读再读呐];59;60[threads!];61;
●popular culture里面的宗教真是迷人,要把巴赫金再拿出来看一下。题目取得太好了,里面顺便提到的印度宗教,虽然不能断定真有关联,但能这样想已经是突破。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读后感(一):依我看,上帝他媽……
怎樣探索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並進一步展開探討?個人信仰作爲既核心又社會同時又私密的命題,如湯用彤所說亦宗教亦哲學,未易言也。ginzburg的這本書探究十六世紀生活在意大利的一位磨坊主的宗教精神世界。
貧富對立的現實、宗教勢力與窮人以及富人之間的矛盾衝突、路德宗教改革精神的傳播、正統教義與民間信仰的相互滲透與絕緣、草根人民的定向思維、以及印刷技術的進步,主人公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現實之中。
設身處地,如果有人,而且是握有生殺大權的人劈頭問你怎樣看上帝、聖母、聖靈、靈魂……,並且加以長期監禁折磨,不老實交代不行,老實交代了不合宗教規矩更不行,你將怎樣作答?換作我,我肯定語焉不詳:上帝、來世這碼子事我怎麼講得清。於是我訝异於這位磨坊主的思維敏捷、唇齒流暢以及最後慷慨赴死的大義凜然了。可是ginzburg絕不肯就此停手,他抽絲剝繭,通過對磨坊主周遭世界以及磨坊主言語的凝神觀察,一步步把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揭開來給我們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者深入探討了主人公的閱讀體驗以及有意無意地誤讀,極見功力。
研究個體微觀世界的扛鼎之作,此書庶幾當之。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读后感(二):琐感
此书出版于1976年,一直被认为是微观史的代表作。正如周兵所言,与勒华拉杜里的那本书应该是微观史的两种面向。此书更倾向于心态史,或者说精神史。微观史最危险的一点在于史料,因其依赖史料往往具有单一性。与同样使用审判材料的《档案中的虚构》比,本书应该不存在史料能否真实反映叙述者思想的问题,原因在于主人公M叙述时带有传道与殉道的意味,且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事无巨细,甚至记载表情、动作。在序言中此书被认为是欧洲早期大众文化研究的杰作,作者亦认同此点。Ginzburg为自己建立的学术对话点在于检讨以往研究中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包括对巴赫金、福柯等的回应。作者首先依照审判顺序,试图重建M的信仰世界。值得一提的是M并非是16世纪的一般农民,他是磨坊主,但也从事其他工作,在当地社区有较高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他能读能写,能购书能旅行(包括拥有一本古兰经和一本意大利方言圣经)。显然,M 的信仰中有诸多复杂成分,对教会贪腐、无用的指斥,近乎因信称义的观念,唯物主义的奇特的宇宙观,对圣母玛利亚非童贞女的怀疑等。但M不是再洗礼派、路德宗信徒亦或是异教徒,他是彻底的基督徒。通过文本分析与阅读史的探讨,Ginzburg得出的结论是M信仰世界的形塑是印刷文本与口述传统碰撞的结果,以及M个人抱有的近乎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信仰。阅读史的探讨在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是亮点之一。M对文本的阅读显然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思想,而更像是选择性的使用文本作为其思想的正当性来源,或者说起“鼓舞”作用?印刷文本也为M提供了 概念与工具来表达自己。作者也对M信仰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概念作了分析,包括“new world”。另一个启发我的部分是此书在心态史之余仍不忘关注社会史方面的分析,对磨坊在16世纪村庄中处于信息交换地的分析及由此磨坊主往往思想新奇的解释颇有文化人类学的味道。M第一次入狱两年后,身心俱疲、妻子俱逝的惨况也令我唏嘘不已。总而言之,好书,胜过以前读的《王氏之死》很多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读后感(三):竟然还没有人写过一篇合格的书评
这么说吧,这是一本新文化史的代表作。
与后来很多新文化史的作品类似,这本书是从从一个案件入手的。16世纪下半叶,一个意大利乡村的磨坊主,因为经常向村里人散播他的宗教思想,被教会当做异端。经过几次审判以后,他被判处死刑。差不多同一时期,一样被处死的名人则是乔尔丹诺·布鲁诺。
这个叫做门诺乔的磨坊主,宣扬的异端思想包括:宇宙是从混沌形成的,就好像奶酪是由牛奶凝固而来的;天使最早出现,好像奶酪中生出的蛆虫;圣母玛利亚不可能是贞女,木匠约瑟夫是耶稣的亲爸爸;爱上帝不如爱邻人重要(这个论证比较麻烦:如果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儿子把爹的照片给烧了,或是把自己兄弟给打了,哪个罪过更大?)
作者金茨伯格之所以研究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可怜人,为的是印刷文化出现之初,欧洲存在的口头文化传统。金兹伯格分析了门诺乔的宗教思想,发现它们与路德派、再洗礼派只有表面相似,更多地却是一种“农民宗教信仰”。这种农民的宗教深深根植于几代人口耳相传的神话、幻想,但与印刷文字相结合后,终于在16世纪初显露痕迹(更明显的表现是拉伯雷式的小说)。门诺乔读过几年书,他自己也号称很多思想只是通过阅读而来。但金兹伯格对比了门诺乔读的书和他的思想,发现这位老兄断章取义、曲解原文、拼凑组合、将比喻当做字面意思理解。一位浸淫在口头文化传统中的半文盲,通过神话、传说的想象力,对阐述抽象概念的书写文字进行了有趣的误读,最后造成了所谓异端思想。
金茨伯格认为,门诺乔的案子间接说明,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底层人的口头文化不留印痕,却曾与上层文化频繁交换信息,为上层文化提供大众根基,拉伯雷的作品便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表现。但16世纪下半叶,德国农民战争、明斯特再洗礼派、价格革命等导致一次次危机,面对民众摆脱上层控制的危险,统治阶层开始重申阶级差异,并试图在思想上、肉体上重新征服大众。耶稣会审判巫婆、监管流浪汉和吉普赛人便是这股潮流的表现。门诺乔被处死正是上层文化镇压大众文化的证据。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读后感(四):《奶酪与蠕虫》英文版序言·个人翻译
《奶酪与蠕虫》样章,个人翻译
英译版序言:
正如寻常会发生的那样,这项研究也是出自偶然。1962年,我在乌迪内度过了大半个夏天。在这座城市的大主教管区档案馆里,我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宗教裁判所文献之中,搜寻着有关一个古怪的弗留利教派的审判记录。这个教派的成员被法官裁定为女巫和巫医。我之后写了一本有关这些人的专著(《善行者》,1966年)。在翻阅审判文件手稿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很长的判决,其中对被告的一项起诉是,被告坚持认为世界起源于腐败。这个表述立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只是我当时仍在寻找其他的东西:女巫、巫医以及善行者。我便写下了那个案子的编号。在此后的几年内,那个记号时不时地就会从我的文献及记忆中跳脱出来。在1970年,我终于下定决心想要理解那些言论对于这位说出这些话的人而言可能具有的意义。而在那时,我对他仅有的了解只有他的名字:多米尼哥·斯坎代拉,人称“梅诺乔”。
本书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多亏了丰富的文献记录,我们得以了解到他的阅读背景与论述,了解到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的恐惧、希冀、嘲讽、愤怒和绝望。材料的一手性不时地将他带到了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他就像是我们中的一位,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
然而他亦是一个与我们迥然有别的人。对此区别的分析性重构是必要的,以便能够重构他的文化以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语境的面貌(哪怕这个面貌很大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梅诺乔与书面文化的复杂关系是有迹可循的:他阅读过的书以及他读这些书的方式。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滤器,一个梅诺乔无意识间在他自己与那些到过他手上、不论有名与否的书之间架起来的格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滤器又是以一种口头文化作为前提的。这种口头文化不仅是梅诺乔个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而且也属于十六世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因此,一项起初是朝向个人的、同时显然也并非寻常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了有关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那既是印刷术传播与宗教改革的时代,也是天主教国家镇压宗教改革的时代——的一般性假说。这一假说可以与米哈伊尔·巴赫金用相近术语所提出的理论相联系,并且可以被概括为一个词:“循环性”——在前工业化的欧洲,统治阶级的文化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流通的循环性关系。(因而,这正好与一位批评家归给我的“农民文化的绝对独立性与延续性的概念”完全相悖。)
《奶酪与蠕虫》既要讲述一个故事,亦要成为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它的受众同时包括了普通读者以及专业人士。或许只有后者才会阅读那些注释——我刻意将注释放在了书的最后,没有使用数字标注,以免打断叙事。不过我希望,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都能从这本小书中辨识出一段几近湮灭、被人忽视却非同寻常的史实残片,以及意识到其所包含的有关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自身的一系列问题。
我向我的朋友约翰与安妮·泰德西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为翻译此书贡献了巨大的耐心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