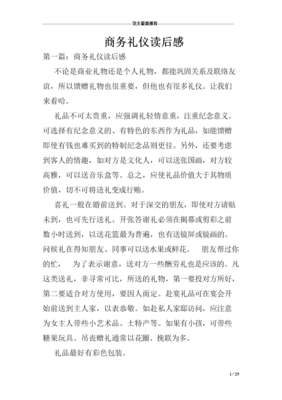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是一本由杨美惠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精选点评:
●里面关于毛崇拜的论述非常之精彩!
●就方法论来说,在90年代就用上了德勒兹的理论,可能存在硬套问题,但就当时来说,确实很时髦、很强大。
●罗嗦了点
●考察全面,指出了“在西方社会,人作为独立的主动者正式地具有同等活的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只受到个人金钱收入的限制”。值得一读的是第七章,对个人崇拜予以“现代心理医疗制度”层面上的关怀;第二部分勾勒出“国家权力”的逻辑运作,指出“‘国家权力’在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却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力量充分地加以论述和考察。对官员权力的经常关注模糊了国家权力的作用”,观点之一是“我想这种崇拜并不是传统中国人对于帝王崇拜喜好的延续……以二十世纪中其他不同的主管崇拜和法西斯运动为例来看毛主义是容易理解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在关系艺术中,通过从道德上降低对方这样一种策略运作,赠与者能够象征性地颠倒大范围的等级,这是一个有物质后果的颠倒”。不足之处在于转述书面化,多处语句不通,很多处错漏,如P266,只管——只要;P287
●关系学的论文
●后来想想,也许只有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理解了,本身就是不同的东西,如何用社会学角度进行比较呢
●人类学是温暖的。它同时做世界热情的体验者和冷静的旁观者,目的在于发人深省,既审视世界又反身自我。它安静,不争利。任何一种宏大理论,如果缺少细致末节的生活世界的支持,就会变成压迫思想的学问,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的学问。我依然热爱人类学,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略微有过度阐释的风声鹤唳之嫌,最棒的部分还是对国家权力渗透与个人日常生活之间互动的描述吧。所用资料自然是得来无比不易的,要是使用方法再精到些就更佳了。
●跪求英文版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读后感(一):一本读起来很费劲的中文书
作者是一个台湾的华裔,一个美国大学的博士,
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本人的问题,
每一句话都是汉字连起来的,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
希望啥时候作者能把此书从头到尾重修一遍,
学术书也要做到语句流畅啊。呼吁学者们不要
在谋杀中文了,谢谢了。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读后感(二):关于翻译问题说几句
中文版的翻译有几处问题或硬伤,不知道是何缘故造成。
比如著名的人类学家Mauss(代表作《礼物》,涂尔干的外甥),书中一会儿翻译成毛斯,一会儿翻译成莫斯。这也许是此书有两个译者之故?
又比如有一个翻译问题,中文版118页,“在出示礼物的时刻表现出的一定的规矩,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关系交往中所包含的化解其工具性的种种仪规。”“化解”一词,英文原词为dissemble(英文版137页),我觉得无论是英文愿意,还是文中情境,翻译成“掩饰”也许更恰如其分。
再如文中附录一篇杨美惠老师2002年在China Quarterly上面回应Guthrie的文章,谈关系近些年来的研究。然而译者把China Quarterly翻译成澳大利亚的刊物。我想这应该不是原作者的错误。澳洲的刊物是China Journal,而China Quarterly是英国剑桥出版的刊物。
还有诸多标题符号、错别字错误。有鉴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赵旭东老师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希望再版时能够更正书中诸多错误,对中文读者负责。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读后感(三):关系中国
说到“关系”,每个中国人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不论是喜欢还是痛恨,人人都意识到“关系”是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客观存在,有时甚至非常重要。人们凭借这种非正式的、不对外公开的网络获得一些机会和利益,而且常常伤害了其他潜在竞争者获得同等机会。由于它总是在隐秘状态之下运作,它令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人感到费解和头痛,自改革开放以来常有外国投资者抱怨他们因为关系不到位而莫名其妙遇到了一些挫败和麻烦。但中国人却也并不见得就能说清楚什么是“关系”——就像我们虽然都会说母语,却未必能阐明它的语法规则一样。
不论如何,“关系”是中国社会一个微妙而无法绕过的有趣话题。作为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学者,杨美惠的身份经历兼跨中西两种文化,因而使得她能够从“参与性观察”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她讨论“关系”并不是为了从道德上谴责(当然更不是赞扬)它,而是因为她意识到“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而她也的确做到了。
人情的社会网络
与强调独立和抽象人格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向来强调由社会关系定义的人——例如谈到一个人的责任和道德,首先要明确是对谁而言:作为儿子他应当如何,作为朋友他又应当如何。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应当符合这种社会角色的期望,如果他作为儿子却不像个儿子应有的样子,那就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每个人都像是生活在一张无边的网络之中,而其中每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也就是所谓“关系”)就变得极端重要了。
使这种社会性联系变得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习惯于和熟人互动,信任感也较强。因此在中国社会,陌生人之间接触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套近乎”、“拉关系”的现象,为了接近对方而采用某些“拟亲属关系”的语言,所谓“称兄道弟”,见面就叫人“大哥大姐”。这与西方形成鲜明的反差。西方文化是奠基于一个“陌生人社会”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以法律来界定,不要说是真正的陌生人,甚至连亲属之间有时都是如此:英语中“女婿”一词(son-in-law)直译是“法律意义上的儿子”,其他“媳妇”、“岳父母”、“公婆”等亲属称谓也都有同样的规则。
这造成了两种社会之间相当大的差别,中国人相当重视这种社会联系,且常常是从“情义”的角度来看待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律角度。一个重视并善于维持和巩固这种网络的人,易于受到中国社会的高度认可和表扬,反之人们就会觉得此人相当自私,也就是“没有人情味”。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力绝不可小觑,事实上它强大得惊人——看看中国传统清官故事中,这些清官排除各种关系的反复求情,我们就知道这有多么难,因为拒绝这些关系的说客,在中国社会里几乎意味着自我孤立,以及为了捍卫原则而与整个社会为敌,事实上他们常常被认为是“做人太绝”。
在任何社会,人际关系要维持一定程度的密切,总是需要当事人不断努力设法保持接触的。在中国,这种努力体现为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两种社会活动:“请客送礼”,而且中国人喜欢强调“礼尚往来”的互动。一个不懂得这么做的人会被人认为不能知情识趣,会冒被其他人疏远的风险。汉语中将赠送给亲友婚丧喜事的礼金称之为“人情”,就暗示着这些礼物本身的作用是沟通加强人际关系和感情的。虽然很多人私下里抱怨人情的支出所费不赀,但没有几个人敢将数额减少或压根不给。
当然礼物通常也不会白给。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早就指出,尽管从理论上讲送礼是自愿的,但它们源自对礼物接收者一方的期望——也就是说,礼物暗示了一套权利与义务的体系,收到礼物的一方不用说出来就知道:收取礼物在巩固双方关系的同时,意味着自己应当在将来某些时候作出回报。这是所有社会中礼品往来时人们都彼此心有灵犀的潜在规则。如果一个人只收取却没有等价回赠或相应回报,就会遭到别人公开和私下里的批评和疏远。
杨美惠对中国社会中“关系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深化和丰富了这些相关理论。她意识到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默认特点。礼品、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因为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当事人的社会声誉。
简单地说,这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压力:一个中国人要安身立命必须要处理好人际关系,礼尚往来、人情练达才能受社会认可;然而过分偏重这些,却又会使得他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下难以作出人格独立的判断。一个手中有权的官员很容易面对亲友的压力而遭遇两难:如果他屈从于关系和人情的压力为亲友谋私利,就会触犯法律;而如果他捍卫原则,则可能被亲友们斥为冷漠无情。这样,一个人要独立于他人作出判断,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欠任何人人情”,但我们都知道,这在中国社会谈何容易。这种困境正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
关系学的未来?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的基本规则实际上是从西方文化中衍生发展而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都要由法律来界定。不用说是人口一千多万的大都市,即便是几万人的小城市,人们也不可能认识所有人,因此这种界定在相当程度上能更好地确保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能受到公平对待,而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由于“关系”的存在,对不同的人都是区别对待的——作为重情胜于重法的文化产物,中国人的思维很难理解:你怎么能对待亲兄弟跟对待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两种逻辑就一直在不断的冲突、调和、相互妥协和遮盖之中。1981年后杨美惠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三年,亲见到那个剧烈变革的年代中因为快速变化而带来的一些“怪现象”。她敏感地意识到,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话语的扩展大幅度掩盖了传统文化中亲属制度的意识和话语,但后者仍顽强地存在着,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系学。它实际上了成为反抗正式组织的一系列非正式的组织方法。
在那些年代里,物资紧缺和机遇的难得使得许多人绞尽脑汁使用各种办法来通关系、走后门——这两个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就已经表示出“关系”是多么不容忽视。人们用个人关系来抵消国家机构的政治安排和社会控制,借以穿透和腐蚀公共政治网络。由于“关系”往往意味着机会的取得是凭借非正式渠道而非真才实学,导致许多真正具备资格的参与者反而落选,这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而“搞好关系”的礼物则被视为行贿受贿的赃物。这促使国家话语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将搞关系和走后门谴责为不正之风,理应为败坏正常的社会伦理而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
这种现象在前苏联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为指导、调节、分配物资资源和机会都集中在有关管理机构当中,在物资紧缺时甚至于一个国营商店卖猪肉的营业员都能利用自己手里小小的特权来谋取一些私利。因此私下的实物交换和好处就成了打开这些被各级人员把守的大门的钥匙,一时间出现大量个人关系发展、非正式协议、走私黑市。这其中关键的是特殊资源被管理机构的人视为个人财产,并用来搞关系的交换。
“关系”具有某些难以界定的暧昧特征,虽然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的蔓延,但却也是中国社会重视人情的文化特征。杨美惠拒绝将“关系学”完全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贪污,因为在“关系”中义务、恩惠、互惠的个人品质和物质利益的活动同等重要。她甚至援引另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考虑到美国社会繁琐的法律秩序、昂贵的法律和诉讼费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系”社会是无效的社会。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关系学”还是会逐渐淡出中国社会的公共政治和经济领域。这不仅因为它所造成的某些不公正和腐败遭到人民和国家的一致谴责,更主要的是因为随着立法和廉政监督的完善,搞关系所要面临的成本也在上升。此外,社会物资的丰富和机会的开放性,使得人们在许多领域根本不再需要走后门——如果任何时候在超市花钱就能买到猪肉,我又何必因此去费力搞关系呢?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人们更关注金钱得失及其收益,它不再顾及人情关系,“亲兄弟”也要“明算帐”,不能因为关系近就让自己遭受物质利益上的损失。
也许有一天,当“关系”在中国现代都市中逐渐衰落后,人们又会怀念起那种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许多人已经在抱怨和声讨大城市的人际淡漠。正如中国传统中的其他部分一样,“关系”既能被用来制造不公和腐败,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人也会一直记得“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老话,这提醒我们:如果改用“表达性礼物”而非“实用性礼物”(鹅毛无疑只是情义的表达和象征,而并不真正具有多大物质价值),那么我们可以在增强亲情、友情和其他人际关系的同时,又不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
校译:
129:19世纪,有个叫崔池的业师:按当是9世纪的崔群
250:杨庆坤:按当作杨庆堃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读后感(四):传统义理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制约
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
义理,礼之文也
——《礼记•礼器》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这本书研究的是文革结束后,关系学为何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以及其社会功能,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来,当今城市流行的关系学是一种情谊的延伸,其虽有消极的左右,比如扭曲了国家法制,是腐败的另一种表现。但作者认为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团体不发达的长时间阶段,“关系学”弥补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社会的真空,对向市民社会的过渡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个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这是一种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感情和伦理特性,在关系学中,伦理和手段紧张又和谐,共存于一体,这意味着官位必须落在个人关系、互惠和忠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其权力和权威。通过送礼可以颠倒主从关系,从而取得道德上的控制优势,可以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
相对欧陆有信仰法律之传统,中国之所以缺乏以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出现或再出现的肥沃土壤,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文化强调的不是抽象的普遍人格,而是由社会关系和角色定义的人,这一机理产生的基础则是中国传统上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使得“义理”成了华夏帝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集中表现,善恶是非之判断,言行之准则,皆由“义理”衡量规矩,认识清楚“义理”之内涵,对中国法制现代化有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原因就在于在西方历史上,“市民社会”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指个人权力、公民权和公民自由,另一方面指居中的社团和组织,因此西方的社会运动总是从基本的人权问题开始。市民社会的缺位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最基本法治资源。
关于“义理”最早出现的文献,有一说认为出于韩非。《韩非子•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又一说认为出自孟子,其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关于义理的含义解释,则显得尤为重要。
孟子在其作品里讲过作为政治思想的“义”,我们知道,孔子以德致位,强调的个人自身的修养,孟子以德抗位强调的是民本思想,有很强的革命色彩。如《滕文公上》说“君臣之义”,《尽心下》说“义之与君臣也”等。孟子的“君臣之义”内涵有三:一是君臣要相互尊重,否则关系就会关系紧张。如《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二是君行为不端,臣可易君或离去。如《万章下》说:“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三是“义”只适用于君臣,不扩大到社会其他领域。依传统的观点,一切政治经济上制度,皆完全为贵族设;可以看出,孟子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皆为民设,所谓君亦为民设。
孟子的“义”与理学的“义”有质的不同。如《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义”限定在政治领域,二理学的“义”,如朱熹所说:“义者,宜也。”“宜”,即“合当如此”,“合当如此”的君臣大义:一是“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是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是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
可以从孟子作品看出,孟子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皆为民设,所谓君亦为民设。依传统的观点,一切政治经济上制度,皆完全为贵族设。理学之“义”与孟子的“义”已经不是一个内涵的“义”了,理学已经强化了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思想了。
从孔孟学说来看,其追求的是一种德行,而德行有大有小,所谓《礼记•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孟子•离娄上》:“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孔孟学说主张的“内圣外王”,则隐喻着政治上至高之位,必须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有义务和责任为天地立法,以施行仁政。其人治思想昭然若揭。
对于礼,孟子认为不合时宜的,可以否认之改革之,衡量的标准则私人化很强的义理,这样不合时宜的“礼”怎么认定看来就属于一个个人很主观的判断了,那么西周确立的礼之真正目的乃在籍节欲之手段以图全体人民物质生活最大之满足,就会在无形中被遗弃,因“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由私人通过修养确立个人标准以“义理”评价“礼”之价值,就本身意味否定了“礼”在西周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义理之察是出于个人之心思与对时代环境补救方法应时发展的。
“义理”与现代法律“义务”最大的不同不仅在于“义理”是道德义务法则,并且还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义理是非常个人的关系;其次义理是基于主观判断,伸缩自如;第三,义理常和个人素好或者金钱有关系;第四义理与正义无关。在中国社会里没有纯粹意义上西方国家公共精神下的公的关系,都是私的关系交织而成。社会规范包括以法律为住的义务以及与此相背的义理两部分,但义理更发挥维持秩序的功能。
孔孟学说隐喻的人人可成圣成王以及德行大小之划分,以及其学说隐喻的革命精神;并在义理属于道德范畴,意味这义作为一种道德义务,履行的是人对人之间的义务,履行并不是现代法制下,对一种超然的价值施加在个人上的带有神或者信仰层面的义务,这样就必然导致诸侯思想,帮派和小利益集团的产生。
对事物的对错的评价和人际关系中的好恶,都依据“私情而定”,这种“难以言喻的私情”单从字面上理解,“私情”就是薄情的反义词,但从公共精神上来看,“私情”其实和公义是相反的,这必然导致“义理”不是一种对普遍的社会正义的追求,属于一种私人之间的伦理了。人际之间伦理产生的关系不是人格独立下的一种契约组合,相反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带有道德义务性质的彼此利益甚至无法言表的情感分享。
从中国与日本官僚制度的内涵来看,相对于日本国事由整个官僚制度决定来,政府领导人发会个人魅力是很小,甚至难以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决定的影响;但中国国家领导人个人能力魅力实在处于国家核心地位,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生活也会跟着领导人性格走,不利于培养民主制度下对国民公民素质的要求。
因此可以说,中国圣人本身就意味这一种环境产物,不是对一种永恒价值的追求者和守护者,时势造英雄,那圣人在社会其转型时其地位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待。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说明对一种客观价值的主观判断取舍,而这恰恰是内背于现代法治精神内涵的。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读后感(五):关系与人情
关系,无论在哪种社会、哪个国家,都是人们借以生存于世上的一种必要手段,有的人天资不足,反而更要采取这种弥补措施以求立足和发展。有的学说用关系来定义人。但是,对于中国语境,关系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变化展现出其意义的复杂性来:在官方话语中,关系被完完全全描述为“不正之风”,是自私的小团体忽略集体和公众利益牟取个人好处的行为,官方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表述,常常与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企业家把自己庞大的商业关系网作为资本,把四通八达的关系艺术作为情商和经营能力的体现。而对于我这个不善关系的人,关系经常是侵略性的,它不断压缩我的个体性和个人空间,使我陷入许多家庭、家族和感情的义务上:在要求下,学习繁重的我还不得不参加一些耗时费力的聚会。关系有时又和儒家伦理、礼法传统和人情世故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优秀传统”。 借着美籍华人杨美惠所写民族志《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我想弄清楚关系的一些要素,来解答自己的疑问。遇到外国人的作品我总是持谨慎态度的,它只给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不是新的立场,所以她的观点我时而怀疑,时而赞同。 关系,它的实质是利益的交换,不管这个利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情感的还是政治经济的。在利益交换的外层,关系围上了感情的面纱,任何不以人之间的交情为表现形式的利益交换是荒谬而卑贱的、更不可能达到目的,作者发现了中国关系中一些细微而生动的特点:一是交换价值的不稳定性,给予恩惠的一方和回报的一方无论是宴请还是礼品还是其他形式的关怀,他都要对他的行为和目的进行估价,这种估价主观性太强,与商品交换完全不同,取决于约定俗成和文化语义背景,故而是不稳定的;不稳定导致了时间延迟现象:在一方给予恩惠后另一方要等一段,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进行回报,以显示双方的深厚的个人感情,急于回报或以金钱报偿被看做是撇清关系而适得其反,让大家都下不了台,阻断了下次关系的可能。总之,感情不是关系的实质,尽管它再多修饰以动人的话语、热烈的仪式,都是用来淡化和转移人们对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注意力,避免尴尬的途径,它和中国人的面子观广泛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的感情特点,作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解释颇为独特:她说中国人意识里人的观念,从来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主客分离、抽象的独立的个体,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取得生存,中国人只能“抱团取暖”:一个人和他人以及他们的关系网融为一体,成为生存立足的整体。人的边界是模糊的,在送礼和搞关系的过程中,付出物质利益的一方从未真正的与利益割离过,也没有真正损失,他付出的实物,转化成为某种象征资本(人情投资?)积存在别人的记忆里,到关键时刻又会获得好处。这样,社会上的个体都隶属于各自的生存的圈子、生存的共同体之中,这个圈子是亲人、朋友的扩大化,圈子和圈子之间有交集借以联系交通,社会上没有圈子以外的领地。“中国人的观念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一种不是人。”这个观点并不新鲜:我在这里想强调两点:一是中国现代社会难以区分公私空间的原因就在于此,人们的边界感有时太差,具体到生活中你会发现有的人非常热情,但是在感情的裹挟下会使人感到很累、甚至感到被冒犯,这是边界没处理好,关系的侵略性部分产生于此,那么除了本体的考量,形式化的习俗、义务更令人难以忍受:“穷亲戚”到底帮还是不帮?繁冗的礼俗,和根本不认识的“七姑八姨”毕恭毕敬地套近乎是否合理?二是,中国人可能自古以来,就有把自己的个体性消解在某一共同主体中的心理倾向,作为个体的人他从未真正独立过,而是通过群体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2)使我有点不爽的是,作者以其美国人特有的狡黠把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性质描述为一种“对抗性伦理”。这个观点从关系的起源和发展角度来说是没有错,作者不主张把关系历史主义地仅仅看作“封建残余”、“旧社会的产物”,关系本身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有不同的实践语境的。她认为关系来自于分封时代,那时候,严格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封国之间实质是部族与部族之间松散的组织形式,就像周将夏人封到一个地区,将商人又封到另一个地区,将功臣和他的族人又封到另一个地区。每个部族是自成体系的由父系宗法制形成的统领制树状结构,但是,在部族与部族之间,与其说是树状结构,一种类似于关系网的弥散性的互惠互利的网状结构更为显著。人的行为、部族的关系,统一于礼法秩序下,这种“礼”不是通过制度层面,而是通过文化和信仰层面在人心中内在化,使人自发地完成生活和政治活动,联系天、人、部族之间的关系。很清楚,这种象征性和符号性的语言因其不确定性和弱约束力很难适应时代发展,一些封国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盛必须采取另一种外在化的高效、固定的国家制度,制定新的统治秩序。战国的强国如此,秦朝、汉朝以后也不是礼治,而是法治和帝制,所谓“内儒外法”,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中和法家学说君本位的强势,而运用儒家和阴阳家学说构造的一套意义解释体系,“天人感应”、“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只是对统治秩序的“正名”,是属于文化层面的,而礼法的政治制度再也不可能复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先秦儒家的政治学说其实挺粗浅的,不是想复辟奴隶制时代的统治秩序,就是理想化地将个人之间的人伦亲爱上升为统治者的关怀,寄希望于明君(“王道”),那么与其相反,中国帝制真正采纳的,其实是“荀子传统”,日本也是,因为外在化的国家管理体制更能适应君主专制。所以,一定要区分对待先秦儒学和国家儒教,我想所谓“封建帝制的产物”,这些词语批判的对象应该是后者。至于性理之学,又更具超脱意味。言归正传,国家“机器化”、“法制化”了,但是民间的宗法组织形式仍然以非正式的形态保存下来,统治秩序没有办法完全干涉,我们可以看到乡里的宗族之间、乡与乡之间,甚至在朝廷的组织之中,还是维持着某种弥散性的以熟人、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互利关系网,它与帝制形成了张力,“对抗性”初见端倪。我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见根据人情世故牟得上升地位的情形很多。建国以后,特别是60年代,社会主义普遍的国家伦理完全取代了关系的位置,关系网被国家的基层组织完全代替,人与人无私奉献、没有亲疏远近之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对新兴中国未来的无限憧憬,理想的狂热,能持续多久呢?接下来是文革,关系遭到进一步地打压,这种压力不再是来自于国家权力,而是另一方面,一种“革命的”与破坏的伦理和崇拜,后者也在不断地蚕食前者,故而,为关系的“死灰复燃”打下了基础。在80年代,“不正之风”和关系日盛,作者将其解释为文革对国家秩序的破坏带来的生存的不确定性,使人更想寻求关系作为保障,获得生存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分配经济下获取物资的一个重要的非正常辅助手段。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后,又出现了公私混合、金钱关系的新特征。但是,使我不爽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别有深意地引用福柯现代化管理和生物权力控制学说来形容我们的国家体制,然后竟然把关系美化为对抗国家控制、维护社会公平的一把武器。关系所构成的秘而不宣的群体组织甚至有希望组成正式的自治群体与国家控制进行对抗。弱势群体通过送礼和给予强势方好处,使接收的一方“丢了面子”,故而在情理上潜在地转化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以此来获取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的稀缺资源。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太西方中心了。仔细想来,我们图书馆学有些论断内在的逻辑结构与这种话语十分相似,是否是正确的呢?
不过对于经济领域,作者提出的“关系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倒是颇为中肯。“如果市场经济的金钱关系被人类之间的感情关系吸纳;个人社会地位通过个人财富的给予而不是积累获得;节俭美德和‘攫取’精神不再有效,或被高度的慷慨所制衡;感恩的体认围绕着每个获得物质利益的个体;消费不是通过个人行为——而是通过社会行为,像中国人的宴席一样,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又是什么样的呢?”关系虽然本质是利益互换而且是群体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可以以此寻求一条能够消解西方法理机制下的以独立的个体和金钱关系、契约、异化构成的冷冰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她反对把西方现代化理论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作者还举出了“亚洲四小龙”为例子,他们的商业组织形式,都和关系有关,也没有被证明比繁荣的法律体系和科层制绝对低效,甚至更灵活。那些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内地时也不得不维持好的关系......不过作者也没有过分理想化,她深知关系对正常政治秩序的破坏作用,而且,在关系与感情的裹挟下,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被解释为义务,性别问题仍然处理不当.....所以应该“阴阳交错”。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关系,她认为西方现代化政治体制理论是遵循着某种抽象的、普遍的、主客分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男性精神特征的方法;而女性则更注重周围人的情感需求,她们通过人际交流中的义务和行为定义自己,所以中国的文化形态先天的带有女性色彩,女性不仅是关系中的易于使用的媒介,而是关系本身就是女性化的。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是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就是关系和现代化二分法的产物。我的父亲是城市人,以他那种优越感认为自身奋斗、努力,遵守规则就能成功的理念教导我;而我的母亲,则是从乡下一步一步打拼上来的,她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天真的热情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以前我总把他们当成现代思想和传统观念的价值观的对立,当成农村和城市人的格格不入,我现在更能以多元的客观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也不会再去区分孰优孰劣,只是吸收经验,找到自己的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抛开关系的感情层面,在其底下藏着的毕竟还是惨厉的现实:一个父亲为了让自己女儿进单位当着领导的面把自己灌醉;趾高气昂的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放下了面子......在今天大谈传统的同时,也需要辨明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