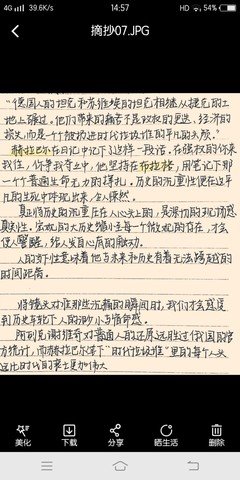
《扎齐坐地铁》是一部由路易·马勒执导,凯瑟琳·德蒙吉奥 / 菲利普·努瓦雷 / 于贝尔·德尚主演的一部喜剧 / 奇幻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電影非常出奇化,喺六十年代初期,路易馬勒就拍出一部令所有影評人啞口無言嘅電影!
電影風格好調皮、奇幻、可愛,zazie呢個女仔可愛得嚟鐘意講粗口,鐘意幻想,鐘意整蠱人,喺zazie身邊嘅人,都係啲冇嚟正經嘅人。
但電影搞笑還搞笑,反映成年人與細路之間嘅溝通問題,反而一針見血,比如話,zazie心目中嘅成年人世界,與現實世界好唔同,成年人好現實,好識做戲,與人溝通有代溝,無論zazie點扭計都好,zazie喺佢哋眼中,只係一個“未識世界嘅豆釘妹”兩日時間將zazie身心疲累...
(P.S)電影中演zazie嘅女仔演得非常有意思!有時我都搞唔清佢到底係女仔抑或男仔?哈哈
《扎齐坐地铁》观后感(二):地下铁的莎姬
路易马勒虽然在五十年代末斩露头角,但似乎与新浪潮走得不太近,他游离在群体之外,一方面他是超前的,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有点保守,毕竟他新浪潮的那些干将们大上几岁,而更成熟地遵循既有的体制。然而,即使他对传统偏见不深,却总是不时地让人惊诧于他的推陈出新,他少了点新浪潮生猛的原则性,但他的每次转变都会引起轰动。《地下铁的莎姬》就是这样一部一石击起千层浪的炫技作品。
这部电影里的技巧成分相当具有革命性,用马勒自己的话说,是一部“玩电影语言”的作品,纪实性的拍摄方式,镜头对准一个乡村小女孩眼中的巴黎,不胶着于城市的特质,而是在人物与事情的错乱关系上大费周章,制造出一个无逻辑无主旨的生活境地,片头在车站等人的先生一通牢骚嘲弄法国人不洗澡的习惯,紧接着一个老套的喜剧桥段,把影片的情绪打断,到处充斥着这样漫无目的的跳跃,玻璃橱窗外映照下的警察行动突然变成屏幕上的背景画面,突如其来的超现实主义,空间、时间的跳跃性连接,看似杂乱无章,却容纳了导演十分巧妙的精心构思。难怪戈达尔会对这部影片另眼相看,是因为太贴近戈达尔的影象风格了。
电影和原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原书中,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女朋友最后回家了,没有参加剧终的斗殴,而电影则完全不同。
所以先从这本书开始——这本书虽然题目是扎姬,但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角。我同意其他评论,说这本书从扎姬的眼中,道出了成人世界的颓废、混乱和荒诞。但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女朋友(酒店服务员)就是例外,抱歉上个月看的,记不起他俩的名字了。
在本书当中,结尾最后一幕的斗殴之前,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女朋友已经带着初婚的喜悦开车回家了,把其他一帮人留在了那个将要发生斗殴的酒店。在我眼中,出租车司机和他的女朋友,这两个人是作者展示的成人世界中不可多得的亮点,这两个人的小世界当中,没有其他人那种颓废和混乱(女服务员和司机的小幸福很温暖)。我觉得这正是作者最后刻意安排他俩远离那场斗殴闹剧的原因——但是很奇怪,在这本书改编的电影《扎齐坐地铁》当中,出租车司机和女朋友也留下来参与了斗殴。这是与原书很不相同的地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可能曲解了本书作者的原意;当然,也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对;第三种可能是,作者也想在电影中强化对成人世界的揭露和批判。
《扎齐坐地铁》观后感(四):无限的想象力
路易马勒调教小演员的确很有一套,三番四次让小演员出演充满禁忌的题材和充满争议的角色,从满嘴脏话的《扎齐在地铁里》到跟母亲乱伦的《好奇心》再到摘下威尼斯金狮大奖的《再见,孩子们》,他在法国电影史上堪称此类(描写孩童)作品的祖师爷。
回到《扎齐在地铁里》,这部改编自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幻想”作品,在今天看来,所有的虚构情节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的出处,就连剧中角色们谈论“未来”的事件,都已在当下得以实现,真可谓出人意料般的超前思维。
明眼人看得出,导演无非是借这个口没遮拦的小女孩,一针见血地揭露成年人的丑陋虚伪,以及现实世界的混乱秩序。然而,导演处理的手法却教人看得眼花缭乱,趣味盎然,幽默感十足。主要归功于色彩的调配和剪辑的技术。当中有许多段落都让我印象深刻:猫和鼠一般的追逐、巴黎铁塔观光,以及最后那场让人捧腹的“动乱”。我不知道是否原著小说里描写如此,但很多段落散发出惊异的想象力,开头车站等待的场面让我想起《天使爱美丽》,小孩和男人的追逐场面让我想到《祖与占》《断了气》等。剧中人物的行为怪诞,却展露出一种意外的轻盈感,让人联想到卓别林的默片经典。与其说这是一部“新浪潮”经典,倒不如说它给新浪潮乃至之后数不尽的电影,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空间。
最后不得不提,影片在巴黎很多著名景点实地拍摄,从车站、博物馆、铁塔、跳蚤市场等,活脱脱一本巴黎观光指南跃然眼前,美不胜收的风景配上荒诞不经的人物,简直让人心花怒放,立刻爱上巴黎这个浪漫之都。看来也只有法国人能拍出如此味道的作品!
《扎齐坐地铁》观后感(五):《扎齐坐地铁》:失序的巴黎永远是闹剧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378.html
扎齐来到巴黎要坐地铁,却因为正在罢工而被关闭;地铁罢工结束的时候,扎齐却要离开巴黎了——从关闭开始,到离开结束,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出逃和寻找,追逐和迷失,最后从未坐过地铁的扎齐回答妈妈在巴黎的最大收获时说:“我长大了一些。”
一个孩子,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一个自由自在的孩子,在巴黎这个城市会看见什么,会遭遇谁?一定是那个成人世界,但是当扎齐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她是该拒绝还是该融入?她是会逃避还是会参与?在从未出现另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扎齐其实是唯一的闯入者,她对巴黎陌生,她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干什么,于是,闯入而解构,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她以“我长大了一些”作为最后对巴黎的回答,这个成长是一种真实?还是一种讽刺?
孩子和成人世界之间,一开始总是错落,扎齐和母亲坐火车来到巴黎,这种错落就以喜剧的方式上演,高大的舅舅在火车站迎接他们母女,而镜头里下车的却只有母亲一个人,她欣喜地奔向自己的弟弟盖布瑞尔,并且伸出了双手做出拥抱的准备,但是即将上演亲人重逢一幕的时候,扎齐的母亲却报向了盖布瑞尔身后的男人——他是扎齐母亲的情人,他们拥抱在一起,他们在欢呼,他们在旋转,而没有抱住扎齐母亲的盖布瑞尔却从后面把矮小的扎齐抱在身上。
错位的拥抱制造了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而这种喜剧效果在拥抱之前就出现了,盖布瑞尔去车站接人,他对着那些等待朋友或亲人下车的巴黎人说:“这里真臭,怎么这么臭?巴黎是恶臭冠军。”可是当他走到一个女士面前的时候,反倒是那个女士闻了闻身边的盖布瑞尔,然后掩鼻:“你怎么这么臭?”发现别人的臭,发现巴黎的臭,却原来自己也是臭,自己也是巴黎的一员,于是这种关于臭的错位,在喜剧中变成了对于巴黎的定义。
巴黎为什么臭?是人的臭还是城市的臭?其实是秩序的臭,而秩序之臭以为着一种失序,当扎齐以闯入者来到巴黎的时候,这种臭和失序就变成了一个成人世界的虚伪。扎齐对于巴黎的向往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去坐地铁,但是当她从火车站下来,前往地铁站的时候,发现门紧锁着,盖布瑞尔告诉他,巴黎地铁正在举行罢工;当她从舅舅家出逃来到街上要去地铁站的时候,依然看到被关闭的进口,巴黎罢工的纸条还写在上面……地铁意味着出行,意味着四通八达,意味着自由,对于扎齐来说,地铁也是了解一个城市的开始,可是,罢工事件却抹杀了她的向往,阻挡了她的自由。而“罢工”对于巴黎来说,一方面在原因上,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钱——政治代表的是公民权利,钱却只代表生存,所以巴黎地铁大门被关闭,罢工者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这当然是一个世俗的巴黎,就像在埃菲尔铁塔观光的时候,丢了眼镜的盖布瑞尔失去了方向,他一步一步向着铁塔的高处行走,在充满危险的行动中,他自言自语:“整个巴黎像一场梦。”失去了看见的视力,行走在危险的边缘,这个巴黎梦是不是也像盖布瑞尔一样,走向了某种盲目。巴黎是世俗的,巴黎是虚幻的,巴黎当然是失序的,当地铁在罢工,整个街道上都是拥挤的车辆,拥堵限制了人们的出行,他们像被自己围困在那里,抵达不了自己想要的目的地。
一种城市的写照,也是一个城市里那些人的写照。扎齐渴望外出,她以出逃的方式离开了舅舅的那个地方,却被房东劝阻,扎齐溜了出去,房东紧追不舍,在街上被众人围住,扎齐对着他们说了一句悄悄话,于是大人们开始针对房东,开始议论房东,甚至开始围攻房东——因为扎齐说了一句:“他是个色鬼。”可怜的房东便在“众人”面前无处可逃,而失去了判断力的众人像对待一个坏人那样求追不舍,在这个过程中小偷便乘机而入,而麻木的人们连自己失窃了毫不知情。
扎齐在市场里遇见了佩卓,扎齐说想要一条牛仔裤,对面“清仓”的店铺正在销售美国牛仔裤,而促销之一是买牛仔裤免费送墨镜。佩卓大约需要的是一副墨镜,于是他有了某种贪婪之心,可是要得到墨镜的前提是买牛仔裤,又是一个错位的场景,扎齐拿了牛仔裤就跑了,佩卓于是追着她,在追逐过程中,扎齐似乎好好戏弄了他一番:扎齐在追逐游戏中,用鱼线刁住他,用巨大的磁铁吸住他,把即将爆炸的爆竹放在他手里,或者跑上了屋顶,或者一起跳房子——追逐最后变成了纯粹的追逐,只是一个在跑另一个也在跑的游戏,而关于牛仔裤关于墨镜都变成了一个背景。
累了就开始一起吃河蚌,扎齐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滔滔不绝中把河蚌的壳重重地扔下来,汁液溅到了佩卓的衣服上,佩卓小心翼翼擦去污渍,以使自己保持绅士的风度,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之后,佩卓似乎有些生气了,他甚至最后跟着扎齐来到了盖布瑞尔家里,在家里又看到了扎齐的舅妈埃尔贝蒂,对于她的美色无法自拔,以为自己发现了爱情,“爱情在见到第一眼的时候就开了花……”于是在爱情的名义下,佩卓甚至跟踪那次给盖布瑞尔送戏服的埃尔贝蒂,而埃尔贝蒂对他说的是:“你是一个假警察,是个傻瓜。”
的确,在错位的故事发生中,每个人的身份总是变得模糊,佩卓是扎齐在市场里碰到的,后来他说自己的警察,埃尔贝蒂却说他是假警察,一样的,房东在追逐扎齐的过程中,一句悄悄话改变了他的身份,他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色鬼。身份的模糊,也是一种失序的表现,和巴黎这个城市里所有人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于是佩卓在门口的鞋店里换了双鞋时说:“我迷失了自己。”迷失自己是不是应该寻找自己,而寻找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当盖布瑞尔在埃菲尔铁塔上丢掉眼镜而失去方向的时候,他说的竟然是:“生活让我成为自己。”一个是认识到迷失了自己,一个是失去了视力却说成为了自己:自己到底是谁?
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便是巴黎的群像,在拥堵的马路上,那个紫色衣服的妇人开着自己的车竟然被路边行走的盖布瑞尔迷住,而她竟然放弃了被堵在路上的车,和盖布瑞尔、扎齐一起走路,这种行为被扎齐说成是“勾引我舅舅”,而当路边又出现警察托斯卡隆的时候,妇人又被他所迷住,最后满大街寻找走散了的托斯卡隆,竟然对每一个警察都不放过。这是邂逅的爱情?和佩卓对埃尔贝蒂一样,总是以迷失自我的方式定义爱情,而扎齐的母亲和父亲呢?因为父亲喝醉了酒,那次据扎齐说,是母亲杀了父亲,“妈妈就这样送他到天堂。”而且,妈妈的杀人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赞赏,于是,在来到巴黎之后,她也从没有照顾扎齐,而是一头扎进了情人的怀抱。
房东变成了色鬼,佩卓模糊了身份,妇人不断勾引男人,舅舅失去了方向,而这一切扎齐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甚至变成了制造者,这一个看起来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却总是说着脏话,却总是制造劲爆的话题,她在埃菲尔铁塔上问查理:“舅舅是不是同性恋?你是不是同性恋?”当查理用否定回到了她之后,扎齐又说:“我听说出租车司机看过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她对勾引别人的妇人说:“你爱他?真心个屁,可怜的老丑女。”当扎齐在用这样的方式骂那些人的时候,她其实不是成为大人世界的一员,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抗拒这个不断逼近的现实,就像她被拒绝坐地铁一样,是成人世界的混乱导致了她唯一希望的破灭,而她又制造了混乱,用另一种方式让巴黎成为了真正的巴黎。
但是,在最后盖布瑞尔清大家喝洋葱汤的时候,冲突发生了,每个人都开始砸东西,每个人都在寻找敌人,每个人都在毁坏的故事里享受快感,醉醺醺的人,受伤流血的人,呼喊尖叫的人,组成了一副“动乱”的场景,甚至不像地铁罢工一样是为了钱,这一场动乱什么目的也没有,只是纯粹地毁坏,只是单一地狂欢,而在众人的喧闹中,扎齐却扑在桌子上睡着了,世界在另一边鸡飞狗跳,我却在这里享受宁静,这一种被隔离的世界,或者才是成人世界和孩子最本质的写照,而在摇晃的镜头里,在下降的舞台中,扎齐被埃尔贝蒂抱着离开而来现场,而一句“罢工结束”了似乎印证了这一场“动乱”才是罢工的真实写照。
不想结婚的查理和玛朵结婚了,妇人是个还是处女的寡妇,鹦鹉学舌比人还说得好,拿破仑是个傻瓜,如此种种,都在一种嬉戏中解构了爱情、身份、语言和历史。巴黎是一场梦却也是最真实的现实,巴黎人失去了自我,却在为了钱的生活中发现了自我,“灵车拖着他们下台,死亡在城市中腐烂”盖布瑞尔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说出的这句话似乎才是巴黎的写照,只是看不见而看见,看见的却是死亡,像一个悖论,就像扎齐的巴黎之行,只有等到离开了,地铁才运行,而这一切的意义似乎都被解构了。而最后当扎齐说“我长到了一些”,不是渴望长大,是因为自己从未脱离过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