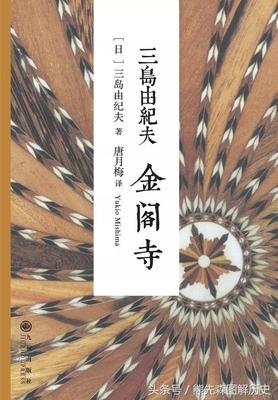
《金阁寺》是一本由[日]三岛由纪夫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阁寺》读后感(一):不是金阁寺,可以是其他,只不过在这个故事中,是金阁寺
美,之所以谓之美,是因为美承载了太多人们一厢情愿的存在,有了这种精神上的迷恋和寄托,人们才有勇气生存下来。对于“美”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人们简单、粗暴的隔绝了其他一切不利的东西,他们生活在自己编织出来的狭小世界中,卑微至极,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活的很好,而这才是最悲哀的人生。
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的小说《金阁寺》中塑造的青少年沟口的形象,是一个偏激、执拗同时又非常极端的人。也许是因为过往的经历,亦或者因为战争的影响,久而久之,他对金阁寺产生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浮夸和不真实的,但对于少年心性的他来说,金阁却是不可替换的。金阁的美,是唯一,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在金阁之下,哪怕是女人美丽的肉体和性,都无法与之相比。
三岛将口吃的缺点附加在了沟口身上,这进一步加重了少年的自卑和自闭,他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对比现实世界中残酷、凄凉的现状,沟口仿佛生活在社会的副本假象中。他对一切的态度都是消极、回避,提不起一丝热情,仅有的一点情感,也在童年时期看到母亲的背叛和在寺庙之外看到老师的行为之后,被击杀的消失殆尽,他的灵魂仿佛都已经不在身体之中,犹如一副行尸走肉的无意识的存在,堪堪的存在于介于现实和虚幻的世界夹缝之中。
不是金阁寺,可以是其他,只不过在这个故事中,是金阁寺。金阁寺就是最美的存在,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行。但是人在极端的情况下容易情绪化,并且这种认知是外力无法更改的,但心已入魔,却认为是善与美,这是一种对美的臆想性的魔化,这是自己的世界,因此心灵得到些许的安慰与平静。
《金阁寺》取材于1950年金阁寺僧徒林养贤放火烧掉金阁寺的真实事件,据林养贤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对金阁寺的美的嫉妒。三岛由纪夫抓住这种战后社会满目疮痍、动荡不安,民心溃散的现状,创作出了这本小说。挫折、痛苦让人麻木,深刻感受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无法理解,面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虚幻缥缈,让人无法“握住”,抓不住自己的人生方向,内心一片慌乱,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呢?
在毁掉心中认定的“美”之后,似乎一切得到了解脱,无关他人与世界,只管自己内心得到释放。
《金阁寺》读后感(二):《金阁寺》:虚妄与真实的边缘,悲剧与毁灭的极致
《金阁寺》是日本现代作家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作品以1950年发生于京都鹿苑寺的一起举世震惊的纵火案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个天生口吃、形容丑陋、与世隔绝的少年从崇拜金阁到焚烧金阁的故事。
书中融入了作家对美与存在、虚妄与真实、悲剧与毁灭的探讨,而使得金阁之火成为了某种饱含隐喻的哲学象征,在代表了永恒之美的金阁和代表了现实世界的人生中抉择不定,最终为了获得所谓的人生而将金阁焚毁的故事。
在创作《金阁寺》这部小说前,三岛曾就案件的详细经过和犯人的经历进行了详尽的调研,小说中多处情节皆与真实案件完美契合,然而《金阁寺》却绝非作者对案件的简单再现,贯穿小说始终的“金阁”也并非现实世界的建筑物金阁寺本身,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含义。
在三岛笔下, 《金阁寺》中人人都是罪恶的,有为子背叛了情人;柏木对他人施虐、亵渎;母亲遗弃了父亲;寺院的老师嫖妓。而沟口要步入这充满恶行的现实世界, 唯一可行的就是从内心对于“恶”的渴望到行动上施恶。
“恶”既可以使他摆脱孤独,步入现实人生,同时也可以使他彻底挣脱观念世界中绝对美的束缚。于是当他脚踏在陪美国大兵逛金阁寺的妓女肚子上时, 他感受到的是“喜悦”,是“满身上下充满的亢奋”。他的喜悦来自于在那一刻“美”没有降临在他的头上, 他感受到了“恶”是足以抵抗“美”的强大力量。在三岛看来, 这正是其从认知走向行动的实践。
三岛在《金阁寺》中似乎演绎了这一原理:沟口到金阁寺当了僧徒之后长住金阁寺。关于这一点还是要结合真实的日本历史来看,时值二战末期,日本本土遭到空袭,京都部分地区疏散了。面对眼前历尽沧桑的金阁寺, 此时他一方面不希望金阁遭遇空袭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觉得也许金阁将在空袭中化为灰烬。于是在他心中, 金阁又增加了一层悲剧性的美。
三岛将金阁置于与沟口同样的命运中,二者之间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平衡。在他看来(同样也是在读者看来),金阁虽然堪称一种坚固的美,与实际上却与自己脆弱的丑陋肉体一样脆弱,并且存在同样的危险。然而战争结束后,金阁没有毁灭于战火,此时的沟口心想:“我和金阁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战火也无法摧毁的金阁显示出了其顽强而强大的生命力,他将注定在金阁阴影的笼罩下卑微地生活,而不能踏入他所向往的现实生活一步。
纵观《金阁寺》全文,可以看出沟口纵火焚毁金阁有一个明显的动机思路,即:金阁是什么?——是“美”;为什么烧金阁?——出于对“美”的反感。在我看来,三岛就是从挖掘沟口焚烧金阁这一在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的内在必然出发,来构筑其审美观念世界的。
《金阁寺》读后感(三):我嫉妒金阁的美
近日,胡歌在一段采访中说,他已经40岁了,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如今看到了自己的演技天花板,再不想努力了。
对于40岁之前的胡歌来说,演技天花板,是梦想,是幻想,是遥不可及的美。而知晓自己的极限,再从追梦逐美的幻想中清醒,虽不知他经过了怎样的努力,但无疑是困难的。
明白一种美,在自己眼前,却无法真正拥有,这种痛苦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
01
1950年,日本的金阁寺焚毁事件轰动一时。在一片废墟中,人们寻到了金阁寺僧徒,以及他准备好的遗言:“我嫉妒金阁寺的美”。
三岛由纪夫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金阁寺》。有人说,这本小说是三岛由纪夫独特美学观成熟的标志,也有人称之为“暗黑美学的情书”。
三岛的独特美学,就是极致美的矛盾对立激化,因此,《金阁寺》出版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认为美无法得到就该被毁灭”的暗黑风,一种是“即使再狼狈也不该去破坏美”的气急败坏风。
因为嫉妒,便让美从人间消逝,只存在于幻想之中,这无疑是自私的。但因为无法拥有美,去责怪追寻至死的暗黑美学,又有些“白莲花”的味道。
02
有一个小和尚,他总是生活在自以为是的自卑中,直到他遇见了生命中绝美无二的金阁寺,他看到了自己的本心,不再畏惧。
但战火硝烟又带给了他一个难题:金阁寺很可能毁灭于火焰之中,那时自己又将如何战胜自己。通过不断地思考,他明白了一件事:我即金阁,金阁也必须即我。
在纵火的前一刻,他想:不被人理解是我唯一的骄傲。在金阁毁灭的那一刻,他又想:金阁还是金阁,即使成为灰烬,她依然不是我。
他秉持了自己唯一的骄傲,就如同三岛由纪夫“矛盾的美学坚持”,很难被人理解。追寻美的极致,然后再让其湮灭。只因这美到了极致,以至于自己无法接受极致的美,进而选择毁灭。他们都在仰慕美,想要得到,却又无法得到,从而开始嫉妒美,厌恶美,想要毁灭美。
当在极致美的面前,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欲望,唯一剩下的,便只有不被人理解的骄傲。
03
“生命这个好家伙,让他猛回头比让他一直走其实更需要勇气。”
接受总是困难的。她无法接受深爱七年的男朋友背叛我;周瑜无法接受蜀汉有个能借东风的诸葛孔明。于是,人性里出现了嫉妒,它是阻碍前进的挡路石,也是自甘堕落的致幻草。
无论是对美的极致追求,还是对美失去的惋惜与指责,都是无法接受“美不属于自己”的自私与嫉妒。
沟口很自卑,这不是他毁掉金阁寺的理由,只不过是无法接受比他更美的事物,也满足不了他近乎疯狂的占有欲。“不被人理解是我唯一的骄傲”,于是,他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让美湮灭。
从某种程度说,胡歌也是如此,他无法接受已然触摸到演技天花板的自己,在40岁之后重复追逐破灭了的幻想。他也选择了让40岁之前的自己湮灭,“不再努力了”。
但与沟口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他找寻到另一种美(公益、思考、生活),去替代曾经的美。
这种替代,是无奈的,却又是积极的。
04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美的事物,会产生极端的拥有欲,一旦无法拥有便会失落,一时间觉得无可替代。
进而嫉妒,愤恨,厌世,这都是正常的,毕竟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但是总有一天,会有另一种美进入我们的世界,或撞入心扉,或照亮前路。
别放弃自己,去慢慢接受。美丢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发现美的心。
《金阁寺》读后感(四):美从黑暗中来,也终将归于黑暗而去。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已经知道这部号称“暴烈美学”的《金阁寺》。它的作者三岛由纪夫更是因为这部作品登上了日本文学的神坛,成为一代文学传说。
然而可能是“暴烈”两个字阻挡了我阅读这本名著的脚步。一直到年近不惑,才有机会翻看这一本早就该阅读的书。
《金阁寺》讲述的是:患有结巴的少年僧侣沟口,进入了金阁寺做了学徒。他憧憬金阁的美,又在恶的边缘不断试探。终于在一个大雨的夜晚,烧毁了这座美丽的金阁。这本小说不算很长,不到400页的厚度。但是中间充斥的内容极其的丰富。三岛由纪夫的文笔非常的美,美到了一种极致。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作家的文笔能传达出如此美妙的景色与意境。和三岛相比,日本现在所有的作家文笔都太轻飘了,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三岛用了第一人称来写沟口。作为沟口的“我”,内心极度矛盾。因为结巴常常受到别人的嘲笑,又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同情。常常觉得与其接受同情,不如直接来嘲笑“我”。直到遇见了如阳光般透明无垢的好友鹤川,生平第一次受到了同等的待遇而感觉到了巨大的幸福。
鹤川如同“我”人生中唯一的阳光,是“我”与光明世界的唯一通道,是“我”人性中的“天使小人”。
柏木却是“我”身边的“恶魔小人”。柏木因为身有残疾几乎与我同病相怜。然而柏木却用一种奇异的狡辩征服了“我”的心,把我拉到了邪恶的那一边。“我”开始在堕落边缘越陷越深。但是每次一行到“恶事”,“我”一直憧憬的金阁就会忽然横在我的面前,阻碍行事。
金阁犹如夜空中的明月,也是作为黑暗时代的象征而建造的。金阁和鹤川是“我”对于美的全部想象。鹤川去世后,阻碍我堕落的只有金阁。如果我想要追逐自己的本能之恶,就要让金阁从“我”的世界中消失。
鹤川与主持代表的光明与善良,柏木与母亲代表的自私与邪恶,如同对立的两个力士,把“我”拉的支离破碎。在光明与善良的力量渐渐衰弱以及消失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火烧金阁寺。
—
《金阁寺》本是三岛由纪夫根据轰动一时的“金阁寺失火事件”改编而来。纵火犯是鹿苑寺的见习僧人林承贤。这场火灾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鹿苑寺720多年的历史几乎全被葬送在大火里。而林承贤纵火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嫉妒金阁寺的美。
小说中的沟口的行为几乎百分百复刻了林承贤的经历以及作案动机。加上三岛美到绚丽的文字。这一场作恶在三岛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行为美学。
每个阅读的人都对此有自己的解释。美到底滋生了善还是恶?憧憬热爱到极致是否就成了恨与嫉妒?
从沟口“我”的角度看,世界对于自己是充满了疏离的。唯一的光明连接鹤川死亡,认真关照自己的主持也对自己渐渐地不耐烦,“我”犹如一个茫然无措的弃儿,破罐破摔之下决定同归于尽。
从旁人眼中看,一个受到主持关照,家境破落的少年还能上大学,前途还是光明的,却结交坏朋友,自甘堕落。
三岛用一种诡异又无可辩驳的逻辑把旁人眼中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了。
三岛曾经说,仅仅靠 “美”这种浅薄愚昧的观念,就足以成为对国宝纵火的犯罪动机。 另一方面,要在现代生活下去,相信一个愚昧浅薄的观念并敷衍为生的根本动机,这完全可能。所有的行为都归结于“美”带来的“恶”。美从黑暗中来,也终将归于黑暗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