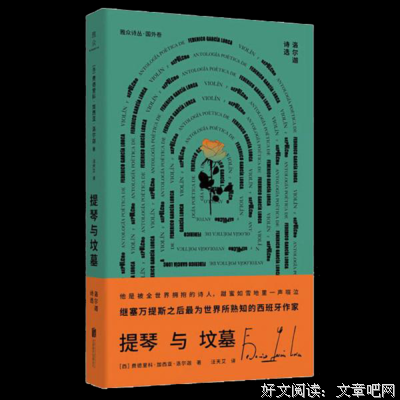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是一本由[西]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 (Federico Garcí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精选点评:
●喜欢那些简短直击人心的小瑶曲。去年八月去过Lorca故居,很小的庭院有绿色的橄榄树的风吹过 庭院里有一树石榴。洛尔加圆圆的脸像是男孩子,但是也有公牛的血性和 魔灵的灵气。爱~
●有甘美有苦涩,认准王家新翻译
●特别喜欢《深歌集》与《歌集》两部分。洛尔迦的诗就像西班牙民歌一样-原始质朴的吟唱,诗人写月亮、太阳,写橘子树,写西班牙的神话与传说,写故乡安达卢西亚的泉水,歌颂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绮丽诡谲的想象力,有如孩子一般的感受力去感知田野大地,诗人对故乡土地对西班牙那份赤诚真挚的感情太纯粹了,他只能属于艺术,他必然不会被政治所玷污。 另,诗人与达利与布努埃尔的的艺术气质太不同了,所以他们的决裂也是迟早的事,即使诗人是如此的爱达利。
●借塞尔努达来表达我有多爱你--「你曾是我们世上的盐」 A writer of elegy.
●王家新的洛尔迦 这次翻译我给十分
●比之前所读的洛尔迦的诗集译本要好。丰富的色泽和意象,充满卑微又浪荡不羁的跳跃感,如同从黄昏略过黑夜直接抵达黎明。
●你的幻觉 我的旋律 橄榄树在摇曳
●愉快地吐槽一下。这可以说是王老师这么多年遇到的第一部可以译也能够译好的诗歌。四星半
●少了几分戴望舒译作的轻盈和内在韵律,对比网上按原文翻译的作品和其他译作,错误太多,很多词语莫名其妙。名作《西班牙宪警谣》中皮革专利权是什么?手枪携带的风云是什么?其他译作是不测风云,王译不知所云,
●还没能寻到诗人的节奏。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读后感(一):Lorca
再次看到和第一次看到一样地,像背对着我们的一位赤着臂膀的歌者,在一些藍藍粉粉沉澱的帷幕裏。洛爾迦的好处不仅是优美,而且特别地脆弱,从不勉强自己要有什么态度。他的立场是没有中心的。
我愛他這一處的好。他自來就是那种历史和人民的诗人: 四海的人們與异乡,知识,创作,未能遮盖他的来源的那个群体中的粗糙与容易受惊。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读后感(二):匠气有余,诗意稍逊
少了几分戴望舒译作的轻盈和内在韵律,多了些匠气,及格作品,算不上优秀。以王家新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改译为例,“绿啊,我多么希望你绿”,戴译为“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明显戴译诗句的延展性和想象空间更大,韵律上也更适合,整句诗没有停顿,只在结尾以去声收尾,给人一种不尽之感。王译祈使的句型,显得很小器,而且绿之前的“你”字使韵律顿住了,“希望”所表达的多重意义和情感深度明显不如“爱”好。至于王先生所说诗句的多重含义,我读来反而戴译更胜一筹。成为绿,或者想要绿,都可以包含在某个句子中,应懂得取舍,求全并不能带来更准确和富有诗意的译作。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读后感(三):在诗神左边
这本书的魅力在于每一次我读它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新鲜的激情。从任何一页翻开,在任何时候翻开。而读过许多诗之后的这种认识会是更加深刻的,因为有些诗歌需要你自己找到入口进入那个描述的世界,但洛尔迦却是把你拉进了那个世界。
关于“西班牙性”
洛尔迦的西班牙毫无疑问是写得极好的,以至于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即使是西班牙自己写自己也不会写得更好。那么问题来了,洛尔迦是谁?
关于死亡
个人并不喜欢所谓“诗人的宿命”这一说法,因为有拿后来发生的事情对照前面发生的事情的嫌疑。我更倾向于将诗人的死亡看作一种积极的行为,即使是一种残酷的命运,作者也是一路走向它,带着某种预感走向它,而非是一路陷在了某种看不见的地图里。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读后感(四):献给安达鲁西亚的月亮和晚香玉
洛尔迦笔下的吉普赛修女被桃金娘和紫罗兰簇拥着,教堂是肚腹朝上的熊,吊灯是菱形飞鸟串成的,她的心是香草气味,在童谣当中有十二轮太阳,百叶窗下刺绣的修女虔诚地爱着受伤的耶稣,这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写的。我又想到他写的《西班牙宪警谣》中被割乳的圣女露莎,月亮,冬瓜,肉桂色塔楼,吉普赛人在水和影和绿光铺就的路上逃亡,而孩子般的诗人天然理解黑火药和玫瑰花背后的故事,却把这一切写得像睡前童话。《普丽西奥沙和风》更是如此,脱离民谣般的文字,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是个性侵未遂的故事。他并非不懂痛,而是正因为太懂,所以帮助读者在诗和梦的国与痛苦和解。孩子拥抱你,说,睡吧,我们用星星的口涎止痛,现实巨大的阴影就这样被化解了,读者既没有背负逃离现实的罪恶感,又在一个梦幻的维度找到了心理安慰。对死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诗人的创作思维,《献给伊格纳乔·桑切斯·梅希亚斯的哀歌》中,他歌唱斗牛士的冒险精神、风度、优雅、对死的渴望和英雄的喜悦,形而上的思辨化作橄榄林的悲风,从而令沉重的、经受苦难的躯体扬升。越是纯粹的灵魂越适合书写现代的堕落,《不眠之城》大段大段的排比正是极有穿透力的控诉,文字愤怒地啮咬眼前的污秽,因为书写者太真挚,所以尘埃中的人物本能性地羞惭了。马拉美也时常被冠以「纯净」的头衔,他用金光熠熠的笔欺骗你,直到你察觉出眼前看似是天国的景象不过是程式化的数码图案,而那没有生气的、拿竖琴的仙女就以僵硬的姿势被印在其上。
《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读后感(五):笔记
浪漫的狂想,情感的涌动。虽然诗歌提倡简洁和节制,但像他这样很多时候把简洁发挥到极致,甚至成为一种破碎和纯意象的喷射还是挺让人惊叹的。完全失去叙事,在意象的密集流动中带来一种浪漫的狂想,搅动人矜持的情感,不必问他的诗到了说了个啥,就感受那种时而魔幻,时而神秘,时而自然的意象的狂风暴雨。隐喻是艰深的,因为它藏在了一连串天马行空的冲击背后。自然说这种特点在他那些所谓的“谣歌”式作品中更加明显,因为谣歌的传统无论在哪个民族中,其内在的隐喻传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不像现代性隐喻,那些作品更侧重诗歌音乐和节奏对大众的情感的共鸣,而他纽约所做的那些诗我感觉似乎是将浪漫式狂想和对社弊病会的谴责隐喻放在了一起,就感觉像你在一首李白的天姥山浪漫狂想中感受到了隐藏其后的对社会弊端的深切呼喊。 “魔灵”理论可以说既是洛尔迦对传统歌谣神秘风格的青睐,也是他对超现实手法的非理性思潮的不自觉回应,跟达利还有布努埃尔一块混,如果不受影响,也说不过去。 毛雷尔说洛尔迦的全部作品“不论是顺着读还是逆着读,主题似乎都是关于”“不可能性”,其实从这里也能大概了解洛尔迦诗歌的难以进入,他的隐喻的指向从来就是不会停止的,是不断追寻的,意象指向意象,意象不断向前滑动,因为内心的渴望既难以确定,又无法被满足,如此导致所用的比喻也常让人觉得生硬怪异(不排除翻译的原因)。所以指向了一种不可能,我们阅读的自然也是一个不断追向“可能性”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