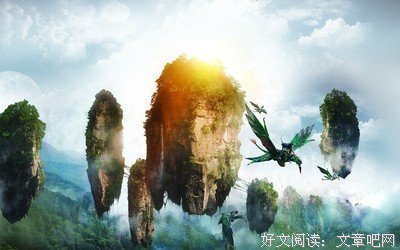
最近,电影《阿凡达》重映。
本来书单君觉得,特效大片重映不过是为了圈钱。
但书单君的一个小伙伴看完之后,却产生了深深的共情。
除了反战、环保和对殖民扩张的控诉之外,她还产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个人体验。
书单君听了之后感动莫名,于是想把这份独特的《阿凡达》观后感,也分享给你。
——书单君
以下,是青橙的自述
以及她看完电影后的感悟
真的看了个“寂寞”
阿凡达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用豆瓣最高赞的话来说,就是一封迟到500年的道歉信,一次伟大的反拆迁游行。
故事情节闭着眼都能猜到:
负伤瘫痪的退役战士杰克·萨利,被安排进了一个半外星人半人——阿凡达的身体里,目的是打入纳美部落,说服他们自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
而身为人类的杰克,在调解失败后,经历了一系列冲突和挣扎,最终选择为纳美人而战,并在剧终,以纳美人的身份永远的留在了潘多拉星球。
12年前,我只关注到那些绚丽的视听享受,沉浸于卡梅隆那天马行空的创世界里。
12年后,因为认知和心境的改变,我竟然在男主角杰克的人生轨迹上,看到了自己前半生的倒影。并从这近3个小时的沉浸体验中,感触到一种极致的孤独。
在降落到遥远的潘多拉星之前,杰克被一个漂浮在零重力下的服务员叫醒。
当他从长达一年的沉睡中苏醒,在明亮的飞船空间中“浮游“时,我觉得自己也被抛出了母舰,抛出了绕地的星轨,向黑暗无涯的外太空飘去。
明明坐在电影院里,身边人头攒动,可我却被一阵巨大的虚无和悲伤击中,感觉到灭顶的孤独。
孤独不是独自一个人,而是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就像杰克一样,是地球社会里的边缘人。没有人在意他的死活,大家对他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他成为哥哥那样的人,包括他自己。
他双腿残疾,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感;
被异样的眼光注视,被嘲笑,失去了自尊感。
后来离开了曾经认同和熟悉的环境,失去了归属感;
更可怕的是,不仅没有人在意你,你似乎也不在意这个世界。可每每又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不断质疑自身的价值感,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人生的前20年,我用了许多方法,试图应对这份孤独。
用的最顺手的,就是给自己一针麻醉剂,欺骗自己根本不需要关系,只要成为一个符合父母期待的工具,通过“优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顺便享受孤独就可以了。
就像男主抛弃了自己的人类躯壳,沉迷于跟阿凡达的精神链接一样。
我也远离了现实世界的束缚,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
方式就是看书,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像杰克在纳美人部落中放飞自我一样,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做无所不能的神,体验着极致的爱恨情仇。
然而,精神世界越美好,就会反衬得现实世界越残酷。
为了逃避现实,只好更深的沉溺于虚幻中。正如杰克链接阿凡达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迫不及待回到纳美人的世界里那样。
但除此之外,似乎一切进展得都还不错。
电影中的杰克收获了领导们的认可,现实中的我考上顶尖985,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以为自己做的很好。
可肥皂泡,终究是无法一直吹下去的。
记得是大三下学期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去食堂,被一个声音击中: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
像游戏里的NPC,正兢兢业业的走着剧情,突然间网络断了。
一瞬间,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不真实了起来,随后被灭顶的孤独吞噬。
为何会与世界“断联”
不是所有的孤独,都是令人不快的。更何况,很多天才般的创造就诞生于孤独。
但极致的孤独不同。
它让我们宛如被放逐,找不到归属之地,宛如虚空中漂泊无依的游魂。
这份与真实世界断联的孤独感,到底是怎么来的?
客体关系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概念“假我”,也叫“虚假自体”。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他的新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中也提到:
一个人如果不能做自己,而是必须顺遂父母的意志,那么就会形成“假我”。
点击上图,购买《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原价 55元,书单优惠价 42.5元
电影里并没有提及杰克的父母,但他所处的世界,一直在“强奸”他的意志。
所有人都期待他成为他哥哥,而不是他自己。
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清高自恋的人。她瞧不起我的父亲,瞧不起所有俗人,每天都沉浸在自怨自怜里,又无力改变,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于是,为了安慰妈妈的伤心和失意,我成了一个贴心贴意的小棉袄;
为了迎合她的虚荣,我从小就阅读艰深的名著,成绩从没掉过班里前三。
只有这样,妈妈才不会伤心。
我用了18年,去打造一个符合妈妈期待的人设。
在她眼中,我乐观开朗,博览群书,乖巧懂事,脱离了低级趣味,是她的骄傲。
可我深知自己不是这样的。
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连我也看不见,摸不着。
于是只好拼尽全力,去维系那个光鲜亮丽,却又摇摇欲坠的人设外壳。
正如杰克在努力成为“有用之人”一样,他死去的双胞胎哥哥,就是杰克理想自我的投射。
他执意打入纳美人内部,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的执念。
因为在杰克强悍不肯示弱的外表之下,同样隐藏着最深的恐惧:
如果我不能够有价值,不能够符合他人对我的期待,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这在心理学上,又叫做“被吞没创伤”,即被他人入侵自己的边界,活成了他人意志的延伸。
我和妈妈的关系里,当然也有爱,但爱是缺乏流动的,更多的是吸食与剥削。
而亲子关系的互动模式,会近乎原封不动的复制到其它人际关系里。
于是我潜意识里知道,一旦构建关系,就只能单方面被剥削。
正如心理咨询师卢悦所说:一开始我们恐惧孤独,随后我们认同孤独,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用一种表面的孤独来对抗另一种深层的孤独。
为了迎合妈妈的期待而捏成的小大人模样,让我无法融入同龄人,被同学排挤和排斥。
人际关系上一败涂地,于是干脆不去跟人链接,说服自己不需要情感和关系的滋养,用虚拟世界的喜怒哀乐当迷幻剂,来填充现实关系的残缺与空无。
没有归属的孤独患者,
如何找到此心安处世界
然而即使加再大的剂量,迷幻剂也有失效的一天。
活在三次元的我们,终究要面对现实。
那么,没有归属的孤独患者,该如何找到此心安处?
<图片来源:B站评论。同样体会到这份孤独和虚无的,远不止电影中的主角和我们>
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阿凡达》之旅后,我找到了答案。
电影闭幕,跟老公一起走出黑沉沉的影院,在北京那车水马龙的喧嚣夜色里,我与他分享了这份被世界放逐的孤独。
我说:亲爱的,我要把这份孤独写下来。
老公说:好啊,回家我去带娃,让咱家的小粘人精别来打扰你。
他含笑看着我,目光中是满满的欣赏和鼓励。
前3个小时,一直浸泡在灭顶孤独里的我没有哭。
可被他的目光触及,我突然无声地流下了眼泪,问:真的可以吗?
老公手足无措地抱住我:怎么啦?既然是你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能做呢?
是啊,为什么不能做呢?
我被狠狠地击中了,先是无声无息地流泪,情绪的阀门被泪水泡软浸透,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崩溃大哭。
结婚5年来,他曾经不断重复过的话,再次浮现于我的耳畔:
人生短短几十年,能做真正想做的,不容易。
再没有什么,是比做的事是想做的更珍贵的了。
有我给你兜底,放心。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
<纳美人的精神链接>
近30年来,一贯喜怒不形于色的我,哭得像个小孩。
我真实的渴望,被深深的看到了。
我真正想做的,被无条件的允许了。
我最脆弱的模样,被充满爱意和欣赏地接纳了。
这一刻,灵魂回到了肉身,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存在感。
正如阿凡达里,女主角对杰克说:“I SEE YOU.”
我看见你了。
你就是你,跟你的身份、职业无关,跟你是否优秀无关。
正如男主和女主,他们之间尽管横亘着种族乃至星球,这一刻,却在灵魂的层面彼此遇见。
原来,我们此前所有的努力、挣扎和蹒跚前进,都是为了这一刻深深的懂得。
被看到的那一刻,巨大的孤独就得以消解,在关系中得到了真正的滋养和力量,重新与这个世界建立了联系。
或许,这就是导演卡梅隆,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方法论:
与世隔绝的孤独患者,想要重新与这个世界链接的话,必须找回被看见的体验。
在正面反馈和抱持性的空间里,我们的人格才能够从破碎和虚无中重新出生。
一个懂你的爱侣,一个支持你的好友,一个互联网上的树洞,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甚至一篇共情的文字,一个陌生人善意的眼神……
在他们全然接纳的目光里,你可以自由的做自己,肆意地发泄攻击和表达活力,而不是做一个“应该”的假人。
死本能(黑色能量)被稳稳接住,死亡焦虑立刻被抚平,当下就会向生本能(白色能量)转化。
从此,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杰克在家园树下完成了重生。家园树也隐喻着:心之归处,即是家园>
"
书单君有话说:
看完了小伙伴的分享,书单君发现,原来《阿凡达》不仅是一份迟来的忏悔,也不止是对群体对立的预言,更是一部现代人的“心灵奇旅”。
毕竟,孤独在这个时代,已然成了一种流行病。
我们在钢筋水泥中独居,两点一线了无生趣;
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抱团取暖,反而迷失了自己。
半空中无依的风筝,该如何找回断掉的线?
只有与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联系,才能真正的“扎下根来”。
与物,或者与人。
我们可以在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时,获得无与伦比的心流体验;
也可以在深度的关系中,重新链接,找回失落的自己,如同一滴水融入了海洋。
我们不需要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潘多拉。
只要真正体验和内化了关系的美好,就能走出自设的囚笼。
四下环顾,原来天地宽阔,春光正暖。
原来脚下,就是充满人间烟火的,「家园」。
"
主笔 | 青橙 编辑 | 燕妮
图源 | 《阿凡达》
今日荐书 ➠《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原价 55元,书单优惠价 42.5元
戳此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