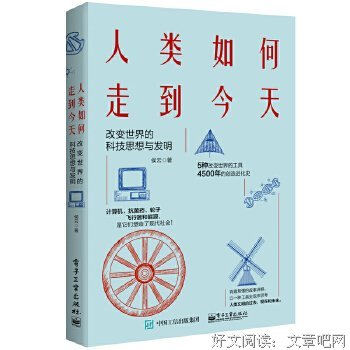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读后感(一):十分新颖!以一种工具史观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当谈到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历程时,大多数人会关注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认为是他们代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本书另辟蹊径,试图从工具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工具史观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中重点讨论了五种工具的发展历程:计算机、抗菌药、轮子、飞行器和能源。这些工具在迭代进化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们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与驱动力量。
十分推荐阅读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读后感(二):安利~
兼具故事性和趣味性,从工具的视角看人类文明的演变,蛮有意思的~特别微生物战争那一章,和最近的新型肺炎疫情很搭~
当谈到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历程时,大多数人会关注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认为是他们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这本书试图从工具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工具史观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推荐~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读后感(三):五星推荐,非常精彩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浅显易懂,很好的用故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大家的眼前,非常喜欢这本书,强烈推荐,买回家的第一时间,我就忍不住拆开来阅读,爱不释手,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买这本书已有一周时间,在现在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只好在家阅读书籍,这本书我已经通读3遍,书中的内容已了然于心,特别是第一章,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经过这几天的阅读,我发现我的历史成绩得到了飞跃提升,以前的我不怎么热爱历史文化,但是就是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历史这么有趣,我真的很感谢这本书的作者,是他让我在即将来临的高考之际,给了我注入一针强心剂,对于我这个文科生来说,真的是非常有帮助,我的家人也感到很欣慰,发现我有如此大的变化后,给我的亲戚朋友每人赠送一本作为新年礼物,我们每天心系武汉疫情,第四章很好的给予我们家关于病毒的知识普及。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在遇到这本书之前,我原本并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是这本书让我爱上了阅读,高尔基曾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以前的我并不是很明白阅读的重要,现在我有了这本书,我发现我拥有了这个世界,我的三观发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都是向着更高的层面。
我现在很期待作者下一本书,很喜欢,希望作者能看到我的评论,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我第一次买的三本书家人购置的一箱此书籍《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读后感(四):人类荒诞抗病简史:放血疗法、鞭笞者兄弟会和鸟嘴面具
从古至今,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中都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并时常以瘟疫的形式横扫整个人类世界,干预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与微生物的战争持续了数千年,并仍将持续下去,其中,人类与鼠疫的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战况也最惨烈。鼠疫,又叫做黑死病,它是人类同微生物斗争历史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鼠疫在历史上曾有过3次集中大爆发,席卷全球,夺去了数亿人的宝贵生命。第一次大爆发生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第二次在中世纪欧洲,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亚洲。鼠疫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在缺乏科学和医学的中世纪,面对疯狂肆虐的鼠疫,人们开始了漫长的自救之路,其中不乏十分荒诞、令人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
放血疗法、祖母绿宝石粉末和下水道
在中世纪,以宗教为统治武器的教廷禁锢思想,医学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的医学理论,盖伦(Galenus)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当这四种液体比例失调时,人就会生病。而血液是人体中最常见的液体,人们认为将患病处的血液放出,疾病就会痊愈,因此当时主要通过外科手术放血来治疗疾病。放血后,病人头脑清醒,倍感轻松,确实有种被治愈的感觉,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最初,放血手术一般由传教士完成,毕竟传教士是人们能找到的最有学识的人。直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ra III)在图尔会议(Council of Tours)上颁布敕令,禁止传教士放血,毕竟传教士的主要职责是传教,而不是帮人们割开血管。不过放血治病这事毕竟是老百姓的刚需,传教士放不了血,人们注意到了理发师手上的剃刀,于理发师代替传教士开始给人放血。直到今天,理发店门口都保留着代表放血服务的红蓝白标志,红色条纹是动脉,蓝色条纹是静脉,白色条纹是止血用的绷带。
图1 19世纪理发师的放血工具套装黑死病爆发后,人们争先恐后来到理发店进行放血治疗,然而由于黑死病能够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放血时并未有任何杀菌消毒措施,导致放血不仅没起到治愈疾病的效果,反而让黑死病加速传播开来,而理发室就是最大的传染源。放血起不到作用,人们又想到了一些奇怪的偏方,比如:吃祖母绿宝石粉末治病,这最早是由意大利医学家、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教授詹蒂莱·达·福利尼奥(Gentile da Foligno)提出的。福利尼奥一生著作等身,曾经为波斯大医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名著《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作注解,被欧洲医学界尊为经典。他还详细地研究尿液的形成,并首次探讨了血压和尿液量的关系,因此被后世认为是医学史上第一个心脏和肾脏学家。福利尼奥认为祖母绿宝石有强大的治愈力,能治愈一切疾病。不幸的是,福利尼奥在1348年6月因鼠疫而死,不知他有没有吃下能治愈一切疾病的祖母绿宝石粉末。
祖母绿当然是无效的,当时的医生还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既然地表的空气容易患病,那么地底的污秽的空气里肯定不会患病,于是鼓励人们去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居住,许多欧洲人就这样开始了下水道的奇妙生活。其实黑死病爆发时,拥有下水道的欧洲城市还很少。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直到1370年才开始建设,在此之前巴黎市民的排泄物都直接倒在街道上和塞纳河中,而塞纳河是巴黎重要的饮用水源,黑死病通过粪便和水源的交叉污染传播,几乎将巴黎变成一座空城。意大利部分城市保留了古罗马时期建设的下水道,因此当时住在下水道的主要是意大利人,这大概也是著名的美国动画系列《忍者神龟》中4只武士龟喜欢居住在下水道,拥有意大利名字,爱吃披萨的故事雏形吧。同样的逻辑,因为空气能传播黑死病,医生还告诫人们,千万别用热水洗澡,因为热水能够打开皮肤的毛孔,让黑死病乘虚而入。而通过不洗澡,能让皮肤上的污垢遮住毛孔,起到预防黑死病的作用。于是不洗澡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的流行风尚,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无论是贵族或是平民都不爱洗澡,并发明了香水来掩盖身上的体味。15世纪在位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只在出生和结婚的时候洗过两次澡。而法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Louis XIV)一生只洗过三次澡。访问过巴黎的俄国大使说路易十四国王浑身散发着恶臭,简直像一头野生动物。
鞭笞者兄弟会
这些方法当然都无法治疗黑死病,有些甚至会加速黑死病的传播。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治疗黑死病的人们陷入了空前的绝望,认为是因为自己的罪孽,神才会降下瘟疫,惟有通过肉体刑罚,鞭笞自己,才能祈求神的原谅,停止瘟疫。于是名为“鞭笞者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Flagellants)的宗教团体迅速壮大起来,鞭笞者通常赤身裸体,一边用钉了铁钉的鞭子抽打自己,一边痛哭流涕陈述自己的罪孽,祈求神的原谅,身体上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在现代人看来,鞭笞者是一群愚昧的自虐狂而已,但在14世纪教廷残酷通知下的中世纪,鞭笞者可是全欧洲的国民偶像,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完人,比教会中那些腐败无能的教士强太多了。每当鞭笞者兄弟会开始游行,都会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居民围观,希望他们的鲜血能飞溅到自己脸上,沾染上神的荣光。更有甚者,相信鞭笞者的血能够使死者复活。教会起初并位将鞭笞者兄弟会放在眼里,但终究还是无法坐视不管,因为鞭笞者兄弟会很快和千禧年主义者(Millenarians)勾搭在一起,宣扬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将要来临,人间将会变成天堂,耶稣会降临人间,结束黑死病,人类也将开启新纪元。1348年,欧洲同时爆发了黑死病,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这些言论威胁到了教会的统治地位,教会终于无法置身事外了。鞭笞者兄弟会出现一年之后,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 VI)下令取缔鞭笞者兄弟会,一场声势浩大的自虐运动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黑死病并未停止肆虐。
瘟疫医生和鸟嘴面具
和黑死病几百年的斗争历史中,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无疑站在战斗的最前线,在当时甚至出现了专门应对黑死病的医生群体--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瘟疫医生的职责除了治疗病人之外,还需记录因黑死病死亡的患者人数,检验患者遗体来弄清死亡原因。受宗教影响,解剖尸体这种在中世纪被禁止的行为在瘟疫医生这里也开了绿灯,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验尸、解剖和寻找治疗方法。黑死病主要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医生们每天得通过放血治疗大量被感染的病人和检查病人遗体,很容易被传染黑死病,医生群体的死亡率极高。为了降低医生感染黑死病的风险,在疫情相对缓和的16世纪,一位名叫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的法国医生发明了防感染套装,套装十分怪异:医师穿着打蜡的皮制或帆布套装,双手戴着巨大的手套,手肘处用绷带扎紧,戴着黑色礼帽,脸则藏在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的面具里 ,眼睛由透明的红色玻璃护着,鸟嘴里有棉花和海绵等填充物起过滤空气的作用,填充物包含有香料或香水,比如龙涎香、樟脑、古龙水、丁香、鸦片酊和玫瑰花瓣等,这些物质在当时被认为能够保护医师免受瘴气和黑死病的侵害。鸟嘴下方开小孔透气,手上拿着长棍,防止跟病人直接接触。当时人们相信,黑死病是一种长得像鸟的恶灵缠身,只有形象更为恐怖的鸟嘴面具能够驱赶走恶灵。自此,鸟嘴面具成为了医生的标配,只要有鸟嘴面具出现,就表示爆发了瘟疫,但医学的不发达终究还是硬伤,医生虽然能保护自己,但仍然无法救治黑死病人,鸟嘴医生的形象变得诡异起来,成为了死神的代言人。直到今天,医生有了更为科学的防护装备,但鸟嘴面具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比如威尼斯狂欢节的代表面具——瘟疫医生面具(Medico della Peste),热门游戏《刺客信条》中的鸟嘴医生和一些蒸汽朋克文学作品中,人们借此表达对禁忌、死亡和无常的理解。
图2 17世纪戴着鸟嘴面具的瘟疫医生其实,人们之所以会对黑死病产生恐惧情绪,并使用这些荒诞的抗病手段,是因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医疗手段。直到现在,黑死病也并未从地球上消失,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它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起来,但黑死病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让人类开始注意到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微生物战争。包括鼠疫病菌在内的有害微生物成为了文明的催化剂,促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催生了现代医学和抗菌药物。医学和抗菌药物不断迭代发展,又成为了人类抗击有害微生物最有效的工具,它们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为人类文明保驾护航,营造了今天健康、长寿的人类社会。
以节选自本书
【名人推荐】
著名作词家,代表作《鲁冰花》,《我愿意》和《最熟悉的陌生人》,华语乐坛金牌音乐制作人 姚谦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科普金奖得主 李淼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畅销科普著作《时间之问》作者、法国利摩日(Limoges)大学高频微电子博士 汪波
知乎27万粉丝、41万赞同,微信公众号20万粉丝的自媒体大V 高太爷
畅销书《桃李春风一杯酒》、《梦里不知身是客》作者 叶楚桥
联袂诚挚推荐!
【作者简介】
科学硕士,知乎盐选专栏主理人,简书优秀科普作者。现从事互联网行业工作,博学而好读书,是一名生活观察爱好者、科技史思考者和不安分的斜杠青年,致力于用故事表达科学与人文之美。
《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读后感(五):鼠疫卷土重来,这是你不了解的鼠疫简史!
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由内蒙古当地救护车转至北京市朝阳区医疗机构治疗。这两例鼠疫患者很可能是接触了野生土拨鼠而感染。
广大朝阳群众们开始议论纷纷,不少人反复追问,“鼠疫究竟是什么,很可怕吗?”“我们还安全吗?”。
鼠疫,又叫做黑死病,它是人类同微生物斗争历史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鼠疫在历史上曾有过 3 次集中大爆发,席卷全球,夺去了数亿人的宝贵生命。第一次大爆发生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第二次在中世纪欧洲,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亚洲。鼠疫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
从古至今,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中都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并时常以瘟疫的形式横扫整个人类世界,干预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与微生物的战争持续了数千年,并仍将持续下去。
其实,人们之所以会对鼠疫产生恐惧情绪,是因为对其不了解,不清楚鼠疫的致病原理和历史由来。只有真正了解我们的敌人,我们才能战胜它们,这本书,让我们穿越数千年的历史迷雾,揭开鼠疫的神秘面纱。
以下节选自本书《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和发明》第2章《瘟疫简史:微生物战争》:
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19世纪英国大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写过一首儿童故事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这首诗取材于民间传说,讲述了一个简短而又神秘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哈默林的德国小镇突然出现了很多老鼠。这些老鼠十分猖狂,偷吃粮食,咬坏家具,给小镇居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镇长于是贴出告示,承诺给能赶走老鼠的人一笔巨额奖金。不久之后,一个身着彩衣的吹笛人来到小镇。他吹起一首欢快的旋律,小镇中所有的老鼠竟然一股脑全出来了。花衣吹笛人一边吹奏笛子,一边朝城外走去,老鼠们排成长列跟在他后面,抵达河边后,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河里,全都溺水而亡。完成这一切后,花衣吹笛人回到小镇领赏。可镇长和居民们却反悔了,他们认为花衣吹笛人只不过是吹吹笛子,根本没花什么力气,拒绝支付赏金。吹笛人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当天夜里,他又开始吹奏起那奇妙的旋律。这一次,小镇每家每户的孩子,就和那些老鼠一样,全都从床上爬起来,跳着舞,向那个吹笛人走去,由于是深夜,孩子们的父母还在呼呼大睡,根本没有察觉到孩子已经离开家了。只有一个小男孩例外,由于腿脚不便,他无论怎么努力奔跑都跟不上其它孩子,没能跟上花衣吹笛人的步伐。他只能在月色中朝着吹笛人远去的方向大声哭泣。第二天,小镇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才发现,除了腿脚不便的小男孩外,小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和花衣吹笛人一起消失了。这个故事在小镇居民中代代相传,寓示着诚实守信的重要性。直到今天,哈默林人仍旧把“花衣吹笛人”奉为神明,市民们每年夏季都和游客欢度“花衣吹笛人节”,纪念花衣吹笛人的神迹。
图1 哈默林小镇上关于花衣吹笛人的彩窗图绘
当然这只是传说,但鼠患和孩子们被带走的事件确实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带走孩子们的不是花衣吹笛人,而是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鼠疫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瘟疫,是通过跳蚤叮咬,将老鼠携带的鼠疫杆菌传染给人类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因鼠疫患病的人,皮肤会出现黑斑,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一周内就会死去,因此人们把鼠疫又称为黑死病。由于黑死病病菌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均可传播,这让黑死病的传播成为了死亡的传递。黑死病曾一度让人类感受到严重的生存危机,它的每一次爆发都会夺取成千上万条生命。同时,黑死病传播范围和速度都十分惊人,跟随人群迁徙和流动,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次,它覆盖了四个大洲,累计受害者达到2亿人。历史上,黑死病有三次集中爆发:第一次大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541-542),几乎摧毁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大瘟疫”(1347 - 1351),以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直到现在,黑死病也并未从地球上消失,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它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起来,但黑死病给人类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让人类开始注意到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微生物战争。包括鼠疫病菌在内的有害微生物成为了文明的催化剂,促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催生了现代医学和抗菌药物。医学和抗菌药物不断迭代发展,又成为了人类抗击有害微生物最有效的工具,它们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为人类文明保驾护航,营造了今天健康、长寿的人类社会,这一切得从公元6世纪的的拜占庭帝国说起。
查士丁尼瘟疫和建安大瘟疫
公元395年1月17日,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346-395年)逝世。临终前,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并分别让两个儿子继承。其中东罗马帝国延续了近千年,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也被后世称为拜占庭帝国,帝国疆域初期包括叙利亚、巴尔干半岛、埃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到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在位时,又将北非西部、意大利和西班牙东南部纳入帝国版图,国力逐渐达到顶峰。当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是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最多的城市,许多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商队、船队在拜占庭帝国聚集,交易货物,这些旅客带来了黄金和财富,也带来了疾病。正当拜占庭帝国即将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打破了拜占庭帝国的中兴梦想。这场规模空前的鼠疫最早于公元541年在拜占庭帝国的属地埃及爆发。经小亚细亚由商路北上侵入君士坦丁堡,并进而散播到整个欧洲。
在鼠疫蔓延到拜占庭帝国的第一年,据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记载,仅君士坦丁堡一个城市的死亡人数就达到每天五千人,疾病肆虐最严重时,甚至达到每天一万人。他在著作中形容鼠疫肆虐的惨状时这样描述:“所有的居民都像葡萄一样被无情地碾碎、榨干”。当时,居民们在相互交谈或购买商品时,就会突然倒地不起,非常诡异,人们十分惊恐,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很快,官员们不得不向查士丁尼大帝汇报,帝国死亡人数超过了23万人,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和土地来埋葬尸体,病人们大多曝尸荒野,甚至连干涸的池塘也被填满了尸体,这加剧了鼠疫的传播。连查士丁尼大帝本人也被感染了,在御医殚精竭虑的医治下,查士丁尼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下令在城外挖万人坑,并花重金招募工人埋葬尸体,阻止瘟疫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病人的遗体堆积近百层埋葬在了一起。这次鼠疫使君士坦丁堡三分之二的居民死亡,在君士坦丁堡传播了4个月后,继续向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区扩散,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四分之一的拜占庭帝国人口因此丧生,帝国的疆土一时成为死神横行的人间地狱。因鼠疫而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复兴罗马帝国的雄心,也动摇了民众对帝国永久兴盛和皇权神圣性的信仰,让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
图2 查士丁尼大帝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鼠疫疫情随着军队和商队在欧洲大陆此起彼伏,在西班牙、高卢和北非地区数次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的沿海地区也未能幸免,总共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使欧洲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两个多世纪后人口才逐渐恢复。由于人口不足,欧洲文明对周边地区统治力被削弱了,阿拉伯帝国趁机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改变了欧亚大陆未来的历史进程,给千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灭亡拜占庭帝国埋下了伏笔。在接近两百年的肆虐后,幸存下来的人口大都具备了对鼠疫的抵抗,于是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查士丁尼瘟疫才真正偃旗息鼓,直到600年后才再次卷土重来。
而在遥远的东方,遭受鼠疫侵扰的时间要更早些。距今1800年前,中国东汉末年爆发了建安大瘟疫(195~220 年),当时的鼠疫和其他流行疾病被统称作“伤寒”。保守估计死亡人数为1000万,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大约只有5000多万,也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东汉时期的神医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神医家族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因伤寒而死,可见当时瘟疫之猖獗。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甚至无法理解瘟疫传染的病因,认为是战争带来的瘟疫。大才子曹植在文章《说疫气》中记载了这次大瘟疫,“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时建安大瘟疫的惨状,并认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导致的,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这是十分原始,朴素的因果观。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有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瘟疫肆虐后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记载,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统治的七十多年中,就爆发过17次瘟疫。连年瘟疫,民不聊生,即使是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更别说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老百姓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4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因这次瘟疫逝世,确实是古代文学的一大损失。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对瘟疫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查士丁尼大瘟疫和建安大瘟疫只是人类和瘟疫斗争的开端,而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中世纪大瘟疫才真正拉开了人类和鼠疫长达600年拉锯战的序幕。这场大瘟疫的流行,要追溯到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的爆发。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了黑海的港口城市克法(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由于围城的生活条件简陋,许多蒙古士兵染上了鼠疫,军队迅速土崩瓦解,绝望的士兵把鼠疫病死者的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内,希望尽快结束围城。城里的鼠疫也开始流行起来,原本兴旺发达的海滨城市在几天之内便成了一座鬼城。城里的幸存的居民四处逃窜,沿海路和丝绸之路逃到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地,鼠疫也随之而来。很快,鼠疫开始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持续时间长达六百多年,1629-1633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对欧洲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直到18世纪初才停止肆虐。这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欧洲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于此次瘟疫,鼠疫成了欧洲中世纪死神的象征,让欧洲人平均寿命从40岁减少到20岁,“黑死病”的称呼也是因此而来。
图3 14世纪黑死病的传播路线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放血疗法、鞭笞者兄弟会和鸟嘴面具
为了消灭黑死病,人们开始了漫长的自救之路,其中不乏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治疗方法。在中世纪,以宗教为统治武器的教廷禁锢思想,医学水平十分低下。人们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的医学理论,盖伦( Galenus)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当这四种液体比例失调时,人就会生病。而血液是人体中最常见的液体,人们认为将患病处的血液放出,疾病就会痊愈,因此当时主要通过外科手术放血来治疗疾病。放血后,病人头脑清醒,倍感轻松,确实有种被治愈的感觉,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最初,放血手术一般由传教士完成,毕竟传教士是人们能找到的最有学识的人。直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ra III)在图尔会议(Council of Tours)上颁布敕令,禁止传教士放血,毕竟传教士的主要职责是传教,而不是帮人们割开血管。不过放血治病这事毕竟是老百姓的刚需,传教士放不了血,人们注意到了理发师手上的剃刀,于理发师代替传教士开始给人放血。直到今天,理发店门口都保留着代表放血服务的红蓝白标志,红色条纹是动脉,蓝色条纹是静脉,白色条纹是止血用的绷带。
图4 19世纪理发师的放血工具套装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黑死病爆发后,人们争先恐后来到理发店进行放血治疗,然而由于黑死病能够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放血时并未有任何杀菌消毒措施,导致放血不仅没起到治愈疾病的效果,反而让黑死病加速传播开来,而理发室就是最大的传染源。放血起不到作用,人们又想到了一些奇怪的偏方,比如:吃祖母绿宝石粉末治病,这最早是由意大利医学家、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教授詹蒂莱·达·福利尼奥(Gentile da Foligno)提出的。福利尼奥一生著作等身,曾经为波斯大医学家伊本·西那(Ibn Sina)名著《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作注解,被欧洲医学界尊为经典。他还详细地研究尿液的形成,并首次探讨了血压和尿液量的关系,因此被后世认为是医学史上第一个心脏和肾脏学家。福利尼奥认为祖母绿宝石有强大的治愈力,能治愈一切疾病。不幸的是,福利尼奥在1348年6月因鼠疫而死,不知他有没有吃下能治愈一切疾病的祖母绿宝石粉末。
祖母绿当然是无效的,当时的医生还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既然地表的空气容易患病,那么地底的污秽的空气里肯定不会患病,于是鼓励人们去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居住,许多欧洲人就这样开始了下水道的奇妙生活。其实黑死病爆发时,拥有下水道的欧洲城市还很少。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直到1370年才开始建设,在此之前巴黎市民的排泄物都直接倒在街道上和塞纳河中,而塞纳河是巴黎重要的饮用水源,黑死病通过粪便和水源的交叉污染传播,几乎将巴黎变成一座空城。意大利部分城市保留了古罗马时期建设的下水道,因此当时住在下水道的主要是意大利人,这大概也是著名的美国动画系列《忍者神龟》中4只武士龟喜欢居住在下水道,拥有意大利名字,爱吃披萨的故事雏形吧。同样的逻辑,因为空气能传播黑死病,医生还告诫人们,千万别用热水洗澡,因为热水能够打开皮肤的毛孔,让黑死病乘虚而入。而通过不洗澡,能让皮肤上的污垢遮住毛孔,起到预防黑死病的作用。于是不洗澡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的流行风尚,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无论是贵族或是平民都不爱洗澡,并发明了香水来掩盖身上的体味。15世纪在位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只在出生和结婚的时候洗过两次澡。而法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Louis XIV)一生只洗过三次澡。访问过巴黎的俄国大使说路易十四国王浑身散发着恶臭,简直像一头野生动物。
这些方法当然都无法治疗黑死病,有些甚至会加速黑死病的传播。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法治疗黑死病的人们陷入了空前的绝望,认为是因为自己的罪孽,神才会降下瘟疫,惟有通过肉体刑罚,鞭笞自己,才能祈求神的原谅,停止瘟疫。于是名为“鞭笞者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Flagellants)的宗教团体迅速壮大起来,鞭笞者通常赤身裸体,一边用钉了铁钉的鞭子抽打自己,一边痛哭流涕陈述自己的罪孽,祈求神的原谅,身体上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在现代人看来,鞭笞者是一群愚昧的自虐狂而已,但在14世纪教廷残酷通知下的中世纪,鞭笞者可是全欧洲的国民偶像,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完人,比教会中那些腐败无能的教士强太多了。每当鞭笞者兄弟会开始游行,都会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居民围观,希望他们的鲜血能飞溅到自己脸上,沾染上神的荣光。更有甚者,相信鞭笞者的血能够使死者复活。教会起初并位将鞭笞者兄弟会放在眼里,但终究还是无法坐视不管,因为鞭笞者兄弟会很快和千禧年主义者(Millenarians)勾搭在一起,宣扬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将要来临,人间将会变成天堂,耶稣会降临人间,结束黑死病,人类也将开启新纪元。1348年,欧洲同时爆发了黑死病,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这些言论威胁到了教会的统治地位,教会终于无法置身事外了。鞭笞者兄弟会出现一年之后,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 VI)下令取缔鞭笞者兄弟会,一场声势浩大的自虐运动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黑死病并未停止肆虐。
黑死病的肆虐还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14世纪时,犹太人和基督徒由于信仰不同,聚居在不同的地区,犹太人的聚居地远离城市中心,比较偏远。黑死病爆发后,基督徒聚居区由于人口密度高,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而远离疫区的犹太人则大量幸存下来。基督徒们坐不住了,认为黑死病一定是犹太人的阴谋,他们一定在河流和井水中下毒了。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逐渐演变成了大屠杀,1348年4月,法国港口城市土伦(Toulon)的基督徒冲进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当天就残忍屠杀了40个犹太人。一年后,欧洲大地上从威尼斯到巴黎的犹太人都受到了基督徒的迫害,尤其是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当天,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基督徒将城中所有的犹太人抓起来,大概有二千多名,并逼迫他们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大约有一半的犹太人选择改信基督教,另一半誓死坚守自己的信仰。于是,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被全部活活烧死,史称情人节大屠杀(Valentine's Day Massacre)。等焚烧犹太人的火焰熄灭后,斯特拉斯堡的居民们纷纷寻找犹太人身上值钱的物品,十分贪婪。鞭笞者兄弟会也是屠杀犹太人狂热的倡导者,认为只有将犹太人消灭,才能平息神的愤怒,让黑死病停止肆虐。形势一度失去控制,有些城市的政府甚至承认并讨伐犹太人的罪行以平息众怒,在意大利北部,当地政府强制要求犹太人戴上黄色的大卫之星以示区分。与此同时,大批的犹太人聚居区被取缔,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屠杀。终于,教皇克雷芒六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取缔鞭笞者兄弟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同时,他颁布命令保护犹太人,命令文件中表达了对犹太人的接纳和同情:“鞭笞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披着虔诚信仰的外衣,却做着惨无人道的勾当。他们屠杀犹太人,却并不知道犹太人也是被基督教所接纳和保护的。”到了1350年,黑死病疫情有所缓解,欧洲各地屠杀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也逐渐减少了。大批幸存的犹太人逃亡到了波兰,向当时的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Casimir III)寻求庇护。卡齐米日国王最宠爱的妃子是个犹太人,卡齐米日又需要精明且善于理财的犹太人来协助治理国家,于是他便敞开国门接纳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犹太人在波兰建设剧院和大学,大力发展科学、艺术和商业,为皮亚斯特王朝(Piast Dynasty)注入了繁荣和辉煌。但波兰终究不是犹太人的归宿,犹太人也终究逃不过大屠杀的宿命,不过那是500多年后第二世界大战时的事了。
和黑死病几百年的斗争历史中,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无疑站在战斗的最前线,在当时甚至出现了专门应对黑死病的医生群体--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瘟疫医生的职责除了治疗病人之外,还需记录因黑死病死亡的患者人数,检验患者遗体来弄清死亡原因。受宗教影响,解剖尸体这种在中世纪被禁止的行为在瘟疫医生这里也开了绿灯,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验尸、解剖和寻找治疗方法。黑死病主要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医生们每天得通过放血治疗大量被感染的病人和检查病人遗体,很容易被传染黑死病,医生群体的死亡率极高。为了降低医生感染黑死病的风险,在疫情相对缓和的16世纪,一位名叫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的法国医生发明了防感染套装,套装十分怪异:医师穿着打蜡的皮制或帆布套装,双手戴着巨大的手套,手肘处用绷带扎紧,戴着黑色礼帽,脸则藏在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的面具里 ,眼睛由透明的红色玻璃护着,鸟嘴里有棉花和海绵等填充物起过滤空气的作用,填充物包含有香料或香水,比如龙涎香、樟脑、古龙水、丁香、鸦片酊和玫瑰花瓣等,这些物质在当时被认为能够保护医师免受瘴气和黑死病的侵害。鸟嘴下方开小孔透气,手上拿着长棍,防止跟病人直接接触。当时人们相信,黑死病是一种长得像鸟的恶灵缠身,只有形象更为恐怖的鸟嘴面具能够驱赶走恶灵。自此,鸟嘴面具成为了医生的标配,只要有鸟嘴面具出现,就表示爆发了瘟疫,但医学的不发达终究还是硬伤,医生虽然能保护自己,但仍然无法救治黑死病人,鸟嘴医生的形象变得诡异起来,成为了死神的代言人。直到今天,医生有了更为科学的防护装备,但鸟嘴面具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比如威尼斯狂欢节的代表面具——瘟疫医生面具(Medico della Peste),热门游戏《刺客信条》中的鸟嘴医生和一些蒸汽朋克文学作品中,人们借此表达对禁忌、死亡和无常的理解。
图5 17世纪戴着鸟嘴面具的瘟疫医生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黑死病的影响
肆虐600年的黑死病对欧洲的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结构和医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终结了中世纪,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并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黑死病给欧洲人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这从黑死病后欧洲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持续近百年的悲观主义思潮和末日忧虑可以看出。黑死病流行期间,大量神职人员因感染黑死病而殒命,对笃信上帝和教会的欧洲人造成了不小的震撼,而向上帝祈祷与忏悔也无法治愈黑死病,也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的权威性,很多不再相信空洞的天堂传说,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世俗生活上,他们放下手中的圣经,开始艺术创作和寻欢作乐,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一些文艺复兴先驱者站了出来,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就在黑死病爆发时期,以黑死病为背景写下了经典的《十日谈》,收录了10个青年相互讲故事度过10天的故事,它批判教会禁锢思想,主张“幸福在人间”,被后世视为文艺复兴的宣言,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可以这么说,黑死病相当于一剂猛药,让欧洲走向了现代化和文明的快车道。
伴随着宗教禁锢的崩塌,黑死病也促进新思潮--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诞生。在中世纪,教会广泛推行禁欲主义,随着黑死病的疯狂肆虐,人们体会到了生命的渺小和短暂,开始把目光从虚无缥缈的天堂移向尘世中的欢乐,追求自由和平等,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逐渐兴起,“文艺复兴之父”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曾在其著名的十四行诗中宣传人文主义:“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在永恒之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来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14世纪以前的欧洲,庄园经济和领主制让绝大部分欧洲人活动范围都不超过出生地方圆十公里,一生中去过最远的地方可能只是镇上的集市或河对岸的教堂。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茅屋组成的村落中,领主们则住在拥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大庄园或城堡中。农奴们为领主辛勤劳作,却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年还得给领主上交一定的税费,生活苦不堪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十分简单,且大部分来自于圣经故事,除了信仰上帝和偶尔爆发的战争外,生活中没有其他重要的事。如果让一个生活在13世纪的农民穿越回几百年前,他也并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熟悉的事物--反复无常的税赋和庄园中趾高气扬的领主,数百年来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中世纪是一个禁锢流动和变化的世纪。黑死病的爆发,导致了短时间的人口大迁移,让很多在故土生活了一辈子的欧洲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黑死病逐渐消失后,欧洲人口的剧减成为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庄园经济由于缺乏劳动力而无法持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的封建农奴制开始土崩瓦解。城市劳动力的极度短缺和在避难过程中产生的对世界的全新认识,让幸存者的中的一小部分放弃了祖辈们世代居住的村落,拖家带口向临近的城市移民,据记载,在1350年至1500年的150年间,仅在英格兰地区,就有1300个左右的村庄被废弃,由此可以看出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流动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在大规模人口流动过程中,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萌芽开始觉醒,这也引发领主专制统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壮大。和以庄园种植业为财富主要积累方式的贵族领主不同,城市中的商人由于资产更为轻便灵活,不受人口流动的限制,迅速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商人们开始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很多重大事物上他们取代贵族成为了主要决策人。城市经济的涅槃重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黑死病则让旧有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从技术生产到组织方式,从物质基础到各类新思潮的产生,黑死病的影响沉淀到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更为重要的是,黑死病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人们不再相信上帝和教会能够治愈黑死病,而是试图通过医学来抵制瘟疫,治愈疾病。政府也开始颁布卫生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的卫生准则,防止瘟疫传播。1377年,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拉古萨共和国最早规定了对商船中海员的管理办法。紧随其后,法国也在马赛建立港口检疫站。在意大利米兰,人们找到了阻止黑死病传播的有效方法:隔离。当米兰出现黑死病人时,政府下令对黑死病人居住的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立起围墙,禁止出入,很好地遏制了黑死病的传播。这是人类历史上对传染病首次建立隔离制度,至今仍在沿用。欧洲人也因为黑死病改善了卫生习惯,在此之前,欧洲主要城市,比如伦敦、巴黎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到处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黑死病爆发后,欧洲各国开始大力建设基础卫生设施,挖掘下水道,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和处理,广泛宣传和实行消毒措施,让黑死病疫得情到了有效控制。历史上因此吧把对黑死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与此同时,外科手术的兴起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开始衰落,医学界的研究重心开始迁移到新兴的传染病学和人体解剖学。医学领域逐渐开始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变革,这些变革都是为了对抗黑死病而产生的。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他表达了对传染病的看法:“有些疾病是能够传染的,传染的媒介是一种微粒,这种微粒能够在病人体内繁殖,能够通过接触从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甚至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疾病并不是由鬼神引起的。”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疾病微粒是微生物。弗兰卡斯特罗还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梅毒和斑疹做出详细诊断的医生,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想象和观察,并未通过实验证明,但在没有显微镜的16世纪,弗兰卡斯特罗能提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传染病理论,已经十分了不起了,因此被后世推崇为传染病学的鼻祖。但在当时,医学界并未重视他的理论,直到3个世纪后,传染病理论才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无论如何,黑死病终归还是一场灾难,但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动摇了教廷和领主们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人文主义的诞生,医学的进步和宗教改革,而这一切又成为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萌芽。黑死病是偶然现象,就算没有黑死病,黑暗的中世纪也终将会过去,不过,黑死病的爆发成为了文明大变革的契机,如果没有这次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人类不知何时才能终结封建专制的中世纪和生产工具落后的铁器时代,现代文明也无法诞生。黑死病这一外部威胁促进了人类文明自身的进化和完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本书气势恢宏,不仅展示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宏达历史,预测了未来抗菌药的研发趋势,还重点讨论了五种工具的发展历程:计算机、抗菌药、轮子、飞行器和能源。这些工具在迭代进化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们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与驱动力量。当谈到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历程时,大多数人会关注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认为是他们代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不过,《人类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科技思想与发明》另辟蹊径,试图从工具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工具史观来思考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因此,十分推荐阅读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