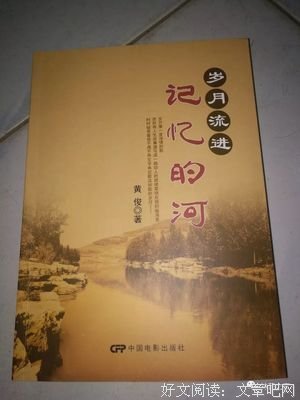
《争夺记忆(附送别册):单读25》是一本由吴琦著作,59出版的2020-12-12图书,本书定价:36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争夺记忆(附送别册):单读25》读后感(一):疫情
2020,最大的记忆,不过疫情。关于疫情,有太多的感慨,以下摘抄自最喜欢的一篇:
『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这些数字意味着一切,它们远非细枝末节,而是残酷现实本身,即使只是一串孤零零的数字,也清楚直白地说明了用文字难以表达的事情:瘟疫所造成的伤害。 但那些数据又被媒体一遍遍重复者,迟早会麻木我们的神经,哪怕全世界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早已达到天文数字,现在大家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接受了。 到头来,重读这本经典著作还是有好处的,新冠病毒一旦冒头,我几乎可以预测接下来的情节——笛福全写在他的书里了。起先大家会以为情况并不严重,然后会出现封锁隔离的措施,接着是民众对于来自疫区百姓的歧视与排斥。同时,谣言会四起,假偏方也会满天飞,最终死亡和感染人数会下降,但只是暂时,因为大家会马上放松警惕,过回先前的日子,所以没多久,疫情又会卷土重来。喜欢读历史的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警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忘记过去”,问题在于后头的那个字:人。是禀性难移的我们,一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有一篇大谈特谈疫情可以不上班不工作,可政府可以发救济金,他的生活更加从容,他更有时间去享受生活,当要复工时,发出了“革命”的声音。但现代生活的便利性,让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恰恰忽视了创造食物和衣服背后的工作岗位,他们以为面包就是在超市或者便利店里面的,所以即使不工作也会有面包,但是如果所有人不工作,你的面包从何而来?你批判压迫人的工作制度,但是人家自己种出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做出来的面包,凭什么就会给不劳而获拿着政府救济金的你?这难道不是对制造面包的人的工作的一种压迫?
2020,似乎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许多,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上的,思维上的——以后的史家会不会把这一年当做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不得而知,但确乎,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人生的转折点。
《争夺记忆(附送别册):单读25》读后感(二):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单读系列,看到书名与拼贴风格的封面便毫不犹豫的买下。2020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转瞬间所有人都在庆祝2021的到来。我在跨年夜写下“零点时前后相隔的一秒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但是人们喜欢给我们的生活以象征和纪念,给与新的动力、新的热情、新的勇气,还有,在那一刻拥抱所有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仍然想要在2020留住些什么,留住这宝贵的、只有一次而永远不会回来的珍贵记忆,也想在书中去寻找那个熟悉的自己,去阅读这一年世界每个角落的故事,去倾听每个人的声音。 世界,自我,附近,通过诗歌串联起了三个时空的章节,并与读者产生对话。因为文学素养和知识基础有限,我向来是无法读懂和快速理解诗歌的,特别是现代诗,即使我和诗人共享着2020年的部分记忆,依然难以将抽象的语言与真实的场景联系起来。由于疫情爆发时,我上半年也恰好在英国留学,期间一直在与家里的父母保持联系,大概6月底回国,所以对于国外和国内作者的书写并没有太多的距离感。独居的作家,大洋彼岸的朋友,抗议运动的参与者,大学讲师,基层公务员,所有人都在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方式述说着这一年的记忆。其中,《疫年双重记》和《不如去摆摊》两篇,是我最喜爱的文章,历史的重演与作者独特的叙事方式令我感受到个人的渺小与人类社会难以缝合的缺口,妙趣横生的摆摊经历和戏谑轻快的文风又将我拉回到疫情后最平实朴素的幸福中。 但是,序言的标题是如此的有力——与记忆搏斗,以至于让我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书中的回忆与故事有反思,有孤独,有快乐,也有希望,这都是国内媒体和主流意识下完全契合的产物,这不是在与记忆搏斗,这是在与记忆和解,缺少批判的和解。与记忆的搏斗,不应忽视在媒体掩盖下,2020年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罪行,不应忽视民粹主义横行时振聋发聩的质问与问责。我们总以为赞美足够优美且洪亮,就可以消除世间一切的丑恶和罪行。但是,正如标题所言,时间和记忆总是不同意的。
《争夺记忆(附送别册):单读25》读后感(三):与记忆搏斗
2020 年好像怎么过也过不完。我试过不同的度量时间的单位,试过直面或是背对它,进入灾难再往后退,试过消费和丢弃,暂停阅读又找回阅读,把注意力拆解分发给运动、三餐或者多余的一杯饮料,试过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消沉,试过在许多被截成碎片的短途旅行里甩掉它。它却还是像迟缓的噩梦一样久久不散。
要具体地回忆这一年却出奇得困难。所有事都向你奔涌,最终又穿过你呼啸地往前席卷。前所未有的经验摆在眼前,而任何单一、现成的处理路径都显得轻率,甚至愚蠢,因为问题的坐标和规模根本上都已被改变。举出一个例子很快就会被它的反例打倒。这时会想起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话,尽管历经文明的变迁,“没有经验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
一个难点在于,当人们被迫鼓起全部的勇气去应对病毒式的意外事件,情况仍然可以辨认,批判性的情绪和思考也都被刺激着,去寻找精确的指向。而当悲剧汹涌而过, 警报局部地解除,社会心理就迅速进入某种“事后状态, 甚至比意外发生之前更加保守和顽固。此前不同的阵营还会提出不同的设问,而现在,提出问题这个动作本身都变得稀奇。这里发生的还不是阿甘本所担忧的例外成为常态, 而是那种即刻复位的漠然——不仅一切仿佛没有发生,甚至拒绝承认、假装忘记,以日常为名,将问题再次简单化、特例化、自我合理化。
如果说历史太远,现实的血泪却如此近。不论是全球治理系统对于疫情的应对,还是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局部战争和个人的绝境,我们几乎亲眼所见,人们选择不记取那些痛苦,而更擅长绕过。比如,如果你下半年还在和人赘述疫情及其后果,无疑会成为所谓“后疫情时代”里的滥调,只会给已经足够辛苦的现代人徒增负累。急遽发生的教训——停留在应激反应的层面上,不出一年就都成了时间的肿瘤。
我们也目睹了,记忆是如何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姑娘。它远不止铭记或遗忘这两个层次,而是一个可以不断事后调整参数、临时排列组合的权力过程。偶然的意志,巨大的利益,趋利避害的本能,都在参与这种重塑和掩埋,而真实的人类经验、现实本身的难度,总是首先被放逐。2020 年已经展示得很清楚了,单向度的义愤不能带领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简单地调换种种二元对立,也只能缓解最浅层的无措,20 世纪所埋下的种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和价值,在新的世纪都难于推进了。而这一年作为转折,不是一个欢庆胜利的年份,也无法宣告任何终结或开始,相反,唯一真实的历史进程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失败、破裂、流散和谎言。也因为如此,记忆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大乱局之中试图看清什么,如同近视验光,会生出一种因为刻意追求清晰而产生的眩晕——我们不得不首先与之搏斗。
而另一个难点,是在什么意义上我可以去谈论“我”。在世界格局发生松动的时刻,个人竟成了唯一确凿的力量,这还是令人生疑。
如果说上半年告诫我们应该知无不言,沉默可耻,下半年急速收缩和倒退的状态却暴露出这条路径的另一面。“自我”已成为这个时代十足的幽灵,它一面扬起热忱的风帆,一面又扎进虚荣的汪洋大海,在内在的构造上它越发玲珑而幽微,在社会关系中却不断粗野、暴戾起来。愤懑、匮乏和扭曲的自我,常常乔装打扮,利用阶级、代际、知识与技术的结构性落差,盗用着冲击着普遍的共情。人们拯救自己,而不修补社会,不断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那些过时的对立之中,从而替换了更迫近的矛盾。弱者甚至是同盟者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在流行,除了进一步卸载批判本身的能量以外并无益处,共同的反抗对象反而在可控的硝烟中继续主宰一切。
在自我与社会角力这方面,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是一个决绝的例子。他主张接近社会而又拒绝加入其中,将自我作为分析对象而又充分引入历史化的视角,这种“分裂的习性”和“双重拒绝”实在是一面峭壁,让他成为极不讨好的人。但他在《自我分析纲要》中提出的问题,今天需要被重新回答。也可以说,这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和 2020 年残酷语境的遭遇。自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如何发言?
这种失语状态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顶峰。不愿袒露太多情绪,也耻于分析,所有原地踏步的观念都值得警惕。而悖论恰恰也在这里,不断拧干自我情绪的过程,也带走了挺过这一年所需要的最后那点情感和力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容易被人打动,也努力鼓舞别人。顾晓刚导演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希望电影能前进,也希望生活能前进”。这种乐观多么动人,几乎没有前提。而随着凛冬又至,悲剧远未终结,这轮回催人清醒,人这个物种本身是由前提构成的。
“无论如何,那个夏天,伴随我成长的所有恐惧,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控制着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像一座高墙横亘在世界与我之间……”几乎可以完全挪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近六十年前写的这段话来概括此刻的感受,它标记了一个起点——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沼泽中如何举步维艰而又始终往前。但实际上已经没那么无畏了。19 世纪的屠格涅夫所写,也许更接近此刻内心的感觉,“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这一年给我留下的印记,到最后可能仅剩那种无力面对而必须面对、试图抗争却难于着力的幻觉。这是人类奄奄一息的时刻,是我们急于忘记但不可绕过的一年。
(《单读25》卷首)
《争夺记忆(附送别册):单读25》读后感(四):这是人类奄奄一息的时刻,是我们急于忘记但不可绕过的一年
测温、扫码、戴口罩、做检测,冬季疫情再度紧张,如同一场轮回。最新一辑《单读》原本希望记录并反思即将过去的2020,对大行其道的闪烁其词和置若罔闻作出回应。未料到这一年没那么容易过去,不确定性依然在继续,年初的痛苦回忆再次上演,来到我们眼前。
今天,我们分享《单读 25 · 争夺记忆》的卷首语《与记忆搏斗》。那种无力面对而必须面对、试图抗争却难于着力的状况,并不会随着这一年的结束而终结。
与记忆搏斗
撰文:吴琦
2020 年好像怎么过也过不完。我试过不同的度量时间的单位,试过直面或是背对它,进入灾难再往后退,试过消费和丢弃,暂停阅读又找回阅读,把注意力拆解分发给运动、三餐或者多余的一杯饮料,试过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消沉,试过在许多被截成碎片的短途旅行里甩掉它。它却还是像迟缓的噩梦一样久久不散。
要具体地回忆这一年却出奇得困难。所有事都向你奔涌,最终又穿过你呼啸地往前席卷。前所未有的经验摆在眼前,而任何单一、现成的处理路径都显得轻率,甚至愚蠢,因为问题的坐标和规模根本上都已被改变。举出一个例子很快就会被它的反例打倒。这时会想起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话,尽管历经文明的变迁,“没有经验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
一个难点在于,当人们被迫鼓起全部的勇气去应对病毒式的意外事件,情况仍然可以辨认,批判性的情绪和思考也都被刺激着,去寻找精确的指向。而当悲剧汹涌而过, 警报局部地解除,社会心理就迅速进入某种“事后状态, 甚至比意外发生之前更加保守和顽固。此前不同的阵营还会提出不同的设问,而现在,提出问题这个动作本身都变得稀奇。这里发生的还不是阿甘本所担忧的例外成为常态, 而是那种即刻复位的漠然——不仅一切仿佛没有发生,甚至拒绝承认、假装忘记,以日常为名,将问题再次简单化、特例化、自我合理化。
如果说历史太远,现实的血泪却如此近。不论是全球治理系统对于疫情的应对,还是不同议题的社会运动,局部战争和个人的绝境,我们几乎亲眼所见,人们选择不记取那些痛苦,而更擅长绕过。比如,如果你下半年还在和人赘述疫情及其后果,无疑会成为所谓“后疫情时代”里的滥调,只会给已经足够辛苦的现代人徒增负累。急遽发生的教训——停留在应激反应的层面上,不出一年就都成了时间的肿瘤。
我们也目睹了,记忆是如何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姑娘。它远不止铭记或遗忘这两个层次,而是一个可以不断事后调整参数、临时排列组合的权力过程。偶然的意志,巨大的利益,趋利避害的本能,都在参与这种重塑和掩埋,而真实的人类经验、现实本身的难度,总是首先被放逐。2020 年已经展示得很清楚了,单向度的义愤不能带领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简单地调换种种二元对立,也只能缓解最浅层的无措,20 世纪所埋下的种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和价值,在新的世纪都难于推进了。而这一年作为转折,不是一个欢庆胜利的年份,也无法宣告任何终结或开始,相反,唯一真实的历史进程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失败、破裂、流散和谎言。也因为如此,记忆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大乱局之中试图看清什么,如同近视验光,会生出一种因为刻意追求清晰而产生的眩晕——我们不得不首先与之搏斗。
而另一个难点,是在什么意义上我可以去谈论“我”。在世界格局发生松动的时刻,个人竟成了唯一确凿的力量,这还是令人生疑。
如果说上半年告诫我们应该知无不言,沉默可耻,下半年急速收缩和倒退的状态却暴露出这条路径的另一面。“自我”已成为这个时代十足的幽灵,它一面扬起热忱的风帆,一面又扎进虚荣的汪洋大海,在内在的构造上它越发玲珑而幽微,在社会关系中却不断粗野、暴戾起来。愤懑、匮乏和扭曲的自我,常常乔装打扮,利用阶级、代际、知识与技术的结构性落差,盗用着冲击着普遍的共情。人们拯救自己,而不修补社会,不断把我们重新拉回到那些过时的对立之中,从而替换了更迫近的矛盾。弱者甚至是同盟者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在流行,除了进一步卸载批判本身的能量以外并无益处,共同的反抗对象反而在可控的硝烟中继续主宰一切。
在自我与社会角力这方面,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是一个决绝的例子。他主张接近社会而又拒绝加入其中,将自我作为分析对象而又充分引入历史化的视角,这种“分裂的习性”和“双重拒绝”实在是一面峭壁,让他成为极不讨好的人。但他在《自我分析纲要》中提出的问题,今天需要被重新回答。也可以说,这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和 2020 年残酷语境的遭遇。自我的位置到底在哪?“我”如何发言?
这种失语状态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顶峰。不愿袒露太多情绪,也耻于分析,所有原地踏步的观念都值得警惕。而悖论恰恰也在这里,不断拧干自我情绪的过程,也带走了挺过这一年所需要的最后那点情感和力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容易被人打动,也努力鼓舞别人。顾晓刚导演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希望电影能前进,也希望生活能前进”。这种乐观多么动人,几乎没有前提。而随着凛冬又至,悲剧远未终结,这轮回催人清醒,人这个物种本身是由前提构成的。
“无论如何,那个夏天,伴随我成长的所有恐惧,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控制着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像一座高墙横亘在世界与我之间……”几乎可以完全挪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近六十年前写的这段话来概括此刻的感受,它标记了一个起点—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沼泽 中如何举步维艰而又始终往前。但实际上已经没那么无畏了。19 世纪的屠格涅夫所写,也许更接近此刻内心的感觉,“生命的洪流在我们身外,同在我们内心,绵绵不息地泛滥”。这一年给我留下的印记,到最后可能仅剩那种无力面对而必须面对、试图抗争却难于着力的幻觉。这是人类奄奄一息的时刻,是我们急于忘记但不可绕过的一年。
(上文摘自《单读 25 · 争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