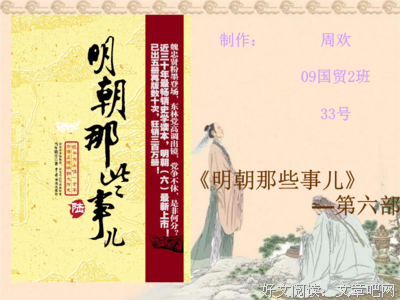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一本由阎步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50元,页数:5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精选点评:
●无需溢美之词
●当年影响非常大的著作
●阎步克
●有理想、有学养的学者:)
●总算啃完了,第一次读阎步克老师的书,没想到非常吃力。其实通观此书,特别之处在于论述策略和研究方法,而非具体观点。阎老师的旁征博引令我目不暇接,而其论述中又时不时冒出诸如马克思·韦伯这样的西方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话语或是研究成果,信息量之巨更增大了阅读的难度。现在恐怕还不是能臧否此书价值的时候,权当读了一遍留个印象,将来有机会时或可再度邂逅。
●@公民文化导论 读书报告一篇。阎步克从政治文化角度,运用社会分化视角分析士大夫政治下的礼治与法治文化。很有见地,史料丰富,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三统(亲统、政统、尊统)相异相维的古代中国社会。
●选课时看的,没看懂
●中史1 可作为先秦~汉代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来阅读
●研究官制的背景
●没读完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后感(一):极好,顿然释疑,唯觉文字漫长
真是极好的一本书,秦帝国因法图强,却二世而衰,两汉时代政权体制,儒法从排斥到融合,最终形成延续千年的士大夫官僚政治,本书就是书写如此恢弘的政治变革。
自己只是工科毕业,处于对历史的爱好,最开始热衷战史,兵法,到法家变法,层层深入。到一切变革的根本,当属思想之变革,政治之变革。对战国研究已久,这本书正是在最后一环,解释了我心中的疑惑,大赞。
如果要说什么意见,那就是,阎老写章节,不太会提炼关键字和标题,往往是大段数页也没有一个标题或者提纲挈领的总结,这算是美中不足的吧。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后感(二):《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中
原谅我自己理解能力太差,这本书实在看不下去。既然不是作者水平的问题,就一定是读者水平的问题了。我一直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从这本书里我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读这本书了,会不会把这本书看完了,反正最近我是不准备看完它了。我只能将其放在我的在读书单里。
本来以为这本书是从秦汉开始讲起,落脚点在东晋南朝。没想到从春秋战国开始讲,前面竟然主要讲周礼。讲周礼的那一部分我固然没有得到太多收获,以至于我后来的“儒法之争”我竟然没有心情看下去。我记得在武老师课堂上听说过类似的观点,但是他讲的比书上更加鞭辟入里。这本书就很难说服我。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后感(三):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 ——读阎步克先生《士大夫政治生涯演生史稿》
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以 “士大夫”为治国者。士大夫阶层的存在,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各领域学者对 “士大夫”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研究,硕果累累。阎步克先生于1996年出版的《士大夫政治生涯演生史稿》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全书论点鲜明,思路清晰,考证严谨,可信度高,启发性强,文字表达也很有技巧,为人称赞。
全书除第一章《问题与前提》和第十一章《结论与推论》外,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二至第五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秦以前士大夫政治的前身及其政治文化传统;第六至第十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秦至东汉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迁,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
该书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揭示出一些新的史实,还选定“政治文化”作为切入角度,并采用了“社会分化”即“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分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而对士大夫政治及其演生过程做了横向和纵向的系统说明。
作者在分析士大夫政治的演生与形成、士大夫政治模式的运转机制分析时,“借用了来自现代社会科学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概念与术语,并将尽力使这二者融会起来用于解说” 。 事实上,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如何使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是个普遍性问题。将社会科学的分析性概念运用于人文学科,最忌讳之处在于简单地套用,作外在化的图解。《士大夫》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并且被认为很有意义,其中许多操作方法值得借鉴 。
例如,作者在解析“士大夫政治”时使用了“社会分化”这一术语。借助这一核心概念,作者揭示了从周代到东汉,中国士大夫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演化过程。西周、春秋宗法时代,有一个封建贵族的士大夫阶级,他们集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于一身,是后来帝国时代士大夫的前身。到战国时期,从士大夫阶级中分化出学士和文吏两种社会阶层,他们分别承担了文化创造和行政管理两种不同的功能。随着大规模变法运动的展开和秦朝的建立,文吏最后压倒了儒生,成为帝国的统治基础。西汉皇朝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开始兼用学士和文吏。最后到东汉二者重新合流,形成了帝国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绵延了近两千年的中国士大夫政治遂由此定型。
在这个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较为成功地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方法的“内化”是很值得重视的经验。评论界说,“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分析框架与中国史学传统在本书中获得了某种内在的融合” ,这一成功多少预示着中国史学界某种令人鼓舞的发展方向。
(阅读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对于我来说,并不轻松。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其所用例证史料、史实考据等一时难以理解。看完这本书所花的时间不少,但感觉尚未把握其思想内涵,故该读书笔记中只谈其研究方法,不敢妄谈内容。)
参考文献
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 期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许纪霖,《跨越两个年代——评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总第五十一期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后感(四):爷爷阎步克
拼了小命写满了三张考题纸,失魂落魄地走了好多台阶到讲台前交了试卷。站在二教105的黑板前,背上包包,想起来什么似的往自己原本的座位看过去。却看到阎老师,穿褐色黑色的大方格条纹衬衣,和我一样塞着白耳机,远远地看不清却依然炯炯的双眼在教室的制高点往下看。似乎没有表情,似乎看见了我。我的耳边充盈的是某乐队亢奋的JERK IT OUT,我就这么有点呆呆地往上看着阎老师突然不好意思了因为眼眶湿润起来。
我一直觉得,阎老师特别特别像我爷爷。
第一次上阎老师的课,意料之中的满座。通选课供不应求在北大纯属正常现象,更何况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用的只是区区150人的中等大小教室。可是阎老师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课堂气氛就很不一样,当时的我说不出来。我就是觉得这个教室里的人都有点不一样,里面的气氛,有点沉。不敢大声说话,不敢乱张望。
阎老师来了,背一个黑色的三星双键书包,没有带助教。极瘦,用网上流传的历史系老师评价,就是“阎布克都瘦成一个杆子了。”双目炯炯有神,眸子黑亮清澈。说话的时候似乎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大幅度地运动嘴部附近的肌肉,每一个字都说得完整而饱满。声音偏小,但毫不含糊。上课前会轻轻说一句,“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吧”,然后整个教室就会在他没有丝毫强迫的嗓音发出后顷刻安静下来。
然后爷爷开始给我们讲历史。
阎老师54年生,比我爷爷小廿岁有余。可是我一直觉得阎老师特别特别像我爷爷,他的目光让人觉得很暖。
爷爷上课的时候大幅度运动嘴部附近肌肉,表情总是一本正经略显严肃。可他自己却总自嘲说自己总觉得自己怎么都不太像正经学者的样子,作为一个下过乡从过军做过工人的知识分子。笑。爷爷总是一本正经地说出一些让大家满堂善意大笑的话,然后有些满足地看着我们。笑。
北大电视台的同事特地来采访爷爷,等了他整整一节课。待爷爷从下课围攻他的学生里最终成功被解除软禁后,学生记者扛着摄像机走向爷爷。爷爷只是说,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包括央视。然后有些抱歉,但很坚决地背上双肩包迅速离开。
我总是想,经历过那样一段时期的人们,对舆论会有怎样的警惕和思考。这份坚持让人起敬。
看阎老师的书,《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后序里他提及自己如何忍不住给儿子讲历史故事的事情。因为自己是个喜欢听历史故事的人,不由得愈发觉得这个被很多人评价颇有杀手气质的先生,温情而温暖。
看阎老师做的课件说明,里面说,因为网上容量的关系课件图片都转换了压缩格式,因此,“这里的课件不代表我真实的作图水平。”典型的完美主义者。
爷爷上课很投入,挺爱拖堂。和别的课堂最不一样的是,这是我上过的所有课中唯一一个学生集体热烈欢迎老师拖堂的课程。爷爷讲士大夫政治,讲激动讲投入了,眼看超时20分钟了还剩下最后一讲。爷爷有点过意不去,说,这最后几页不如同学们自己回去看看PPT,我就不讲了吧?下面的学生集体回答:老师您讲吧讲吧!爷爷笑,于是继续。在下面赶着要去开会的我突然慌了神。爷爷的课堂突然让我对北大的学术充满了希望——这里不仅有严谨的学者,同时也有严谨的学生。热爱学术的严谨的师生。
最近我经常性地提及这句王小波转述的某北大数学系老师说过的话。原话是这样子的:
“我教给你们的数学,也许你们一辈子都用不到,可是我还是要把它们教给你们。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
我觉得爷爷真好。
爷爷继续运动嘴部附近肌肉,双眼清澈而炯炯有神。我有时候盯着爷爷看,出了神,总觉得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该手执麈尾,在魏晋清谈。他的目光清澈,是洞悉世事后留下的一尘不染。嗓音干净,冷静却不冷漠;相反爷爷总是让我感觉到有限但真实的温暖。爷爷的眸子很亮,深处,是智慧的光芒在闪耀。
我在二教105的教室抬头看爷爷,爷爷和我一样戴着白色耳机,眼神略显疲惫在教室最高处往下看。
我矫情地眼眶湿润,温情的敬意兀自增长。
对本民族保有温情的敬意者,必保有来自他人的温情的敬意。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读后感(五):不敢妄议,只求梳理出大概
读完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已经有些时日了,坦白地说,这是一本对我较有震动的著作,当然,由于知识的浅薄,读的过程并不是很轻松。读完之后,也有不少的感触,但真要整理起来,又感觉甚无头绪,所以只能将心中一些想法零碎地记录下来。
这本书的大致脉络在于考察了士大夫的身份和职责从合到分再到合的过程。在封建礼治的政治文化传统下,士大夫扮演的是兼具“三统”于一身的“君子”形象,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礼治已经无法执行相应的政治功能,所以,相对于“礼治”的混溶,“法治”作为更分化,更具官僚性质,更理性化的一种政治形态取而代之。由于它的相对理性化、工具化的行政方式,所以它需要剔除传统“礼治”遗留下来的某些非理性化因素,主要就是其中的亲缘秩序和文化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法治”力图将政治领域和其他的社会领域划开。而这种独立的政治领域需要的是大批的专门型人才,他们需要通晓吏事,精通法典,而对“德”的方面则不做要求,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文吏”。而在另一方面,“学士”团体也随着思想文化不断系统化的发展而形成了,他们承担着文化传播的职责。但随着依靠 “法治”而完成一统的专制帝国——秦帝国的二世而亡,继起的汉帝国相应地调整了政策。其初期的黄老政策无非是希望经历了巨大动荡的社会能够在一段时期的恢复后,能重新具备持续为其提供资源的能力。而秦帝国所建立的官僚体系,却基本被继承了下来。所以社会一旦恢复元气之后,黄老思想就无法和重新上路的官僚体制相契合了。而在此期间远离政治舞台的儒生们,却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为一方面他们是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普通民众心中具有一种神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礼治”思想与当时社会基本价值是相一致的,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单纯“法治”难以渗透到受传统影响的基层社会中的缺陷,所以儒生又重新被吸收进官僚体系。但此时文吏和儒生之间还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儒生在政治思想上的非理性化因素在暗中滋生,并以王莽“奉天法古”的变法为顶点。在这场“乌托邦”式的变法失败之后,儒家自身也回归了理性,所以东汉的儒生较少发高论,而关怀于世俗的事务,参政的儒生们更是要熟悉文吏们的事务。而由于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文吏们也多研习儒家义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儒生和文吏合流了,也就象征着“礼”和“法”的合流。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士大夫的角色又重新的多重化了,但这种多重化的确立是经过了实践尝试之后做出的一种理性化的选择。帝国的统治者需要的是在一个分化不够,保留了很多非理性化传统因素的基层社会之上构建一个分化的、理性化的政治体系,这就要求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缓冲层,以用来对它们进行调和。而儒生们就恰恰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分化的产物,因为作为团体来说,他们已经脱离了诸如血缘关系等原生性的束缚。但同时,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使他们轻易地就能联接起上下层。
正如书中所引美国学者赖文逊对中国士大夫的称呼——amateur,做为官僚体制内的人员,他们缺乏业务能力的培训;对于受过严格文化教育的他们来说,大多数人又担任了具体的行政职务。这终究还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分化不够所致,至于社会分化不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这一非常具有稳定性的社会便是衍生出“礼治”的沃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到:“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那么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已被默认和接受的社会经验。乡土社会由于它的变动性极小,所以对于生长在其中的个体来说,经验往往是很具有指导性且有效的,所以行事的时候只需遵照传统范式则可。换言之,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分化的,因为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很难从原生的、先赋的关系纽带中脱离。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们,尽管是一定社会分化的产物,但作为官僚主体,他们又反过来继续抑制了社会的分化。他们有了一定的政治表意能力,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以文化取向为主,他们注重的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只要执政者能够满足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就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政治和文化的混浊不分也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最大特色,而士大夫的官僚化正是这样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