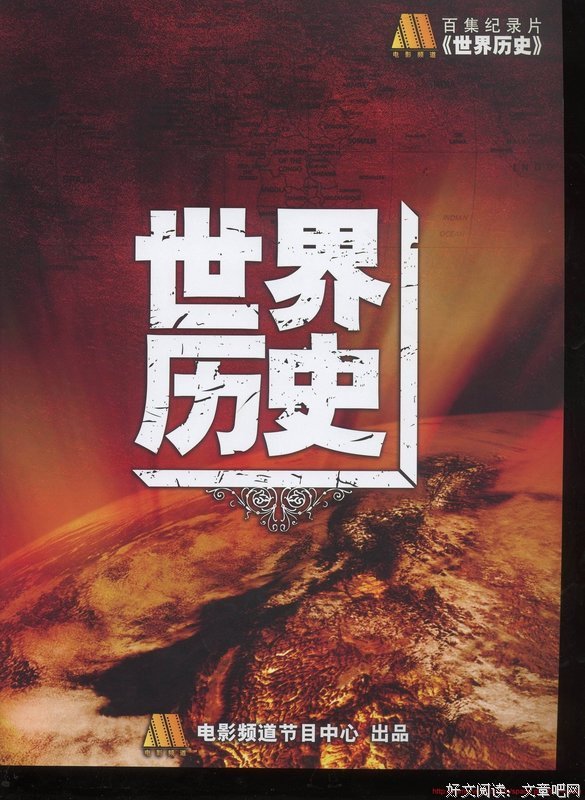
《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9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一):愿让我回到那个时候
每次读到这些历史书籍,总是免不了向往、叹息加痛恨,总希望能改变一些事情和人,重写历史,希望辉煌常在。最后却只能合上书。
自我也是有些鄙视自己这些心思,但是总免不了。
在我看来,这种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研究总是容易读些。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二):旧书新出,值得推荐。
余英时,钱穆弟子。相对目前思想家研究朱熹鼎盛之形势长久不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惜研究朱熹的精品聊聊可数。
大陆陈来老师为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但他是从哲学、思想史以及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朱熹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三):分打高了。
真不知这书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大概是一部部地拿理学家文集和经注认真研读下来的比较少吧。如果真正深入阅读理学家的著作其实会发现他们虽然对君权有限制,但任然个个都忠于君主、维护纲常名教。而余氏写这部书的用心,则是千方百计地论证理学是“虚君政治”,好像理学对接不上自由民主就在当今没有活路似地。不管理学对接得上虚君共和与否,它都不是余氏所编造出来的那个样子。
这本书只能说是:前见太多,专门挑取对自己有利的材料,作对自己有利的解读。如此而已。
余大师这些年的一些表现,程朱复生,也是不会同意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四):《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
作为一位并不专治宋史的学者,余先生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理学家与孝宗末年之政这一关键问题,并钩玄提要、明其待发之覆,其大历史学家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在洋洋洒洒将近千页的论述中,余先生着力营造的正是这一「历史学家」的形象,其演绎的立足点也在于这一形象背后的一系列现代西方学术逻辑。以此而言,本书大致能够实现自洽,又不失其可读性。仅看附论所引征的三位论者的批判及作者的反驳,似可知二者乃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之下进行,作者本就是探讨政治世界的事情,自不触及相关人物在价值世界的论说。即便洛闽嫡传看了此书,纵不感叹后世相知,大约也不会跳起来批判一番。然而,在本书之外,余先生实际上对这一价值世界持一至少是不予认同的态度,教人读着并不安心也是意料中事。
余可见拙作〈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一文。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五):读书杂感
在这样一个深夜,坐在自己的床上,突然想写这样一篇不算是书评的书评,因为它更像是我进入大学历史系两年来的一点感想。所以更多我要说的,是我阅读此书的过程。
如果在高中时候让我写一篇这样的书评,我肯定自信满满,夸夸其谈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但进入历史系两年来,我越发觉得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说一些话开始思前想后看有无错误,一些评论甚至自己都不敢下了。打个比方,在高中时,就像是那只在井里的青蛙,我的天空只是那井口大小,毫无疑问,我是我世界当然的主人,但当我终于爬出这口井时,才发现所谓沧海一粟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买到此书,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买,当然也只是冲着此书的名气,记得当时的我只是随手翻了两页,觉得无聊看不进去就扔在了一边,觉得上大学看也好,于是,在搁置一暑假后,我把它带回到了学校。
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是充满新奇的一年,有太多新鲜的东西需要接受,于是,这本书就在寝室的书架上,安安静静的待了一整年。
直到大一结束,在去军区军训之前,硬着头皮读了一百页绪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只是一页一页的看着,拿笔划一些我都不知为何要划的横线(这在我后来重新阅读时候深有体会),没多久,它便又回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
再次拿起,是这学期的期末,十天时间,读完此书。合上书本再想想从不在意去读,到发现根本读不懂,再到读完的这个两年的过程相对应的自己,态度可能正好相反。也许,这便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吧。
名为书评,还要再来说说这本书,大一读完陈苏镇《春秋与汉道》时候模模糊糊对政治文化有了个大致印象,陈书以《春秋》学作为贯穿两汉政治史的一把钥匙,从《春秋》学对两汉政治的影响入手。而余书则更多的针对士大夫“内圣外王”的“外王”层面。余先生敏锐的观察到了在理学或是朱熹研究层面上将时代与学术割裂的倾向。他要将朱熹还原到历史中去,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历史世界”。他从此入手,更加具体的分析了在种种分歧背后士大夫“得君行道”的一面。由此揭示出两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些面相。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庆元党禁的原因)也有了新的,更加完整的解释。
更可一提的是余先生对于心理史学的应用。他对孝宗光宗心理过程的揭示可以说分外精彩。在文献材料不足或没有直接证据时候,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借鉴。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六):礼乐崩坏,释之于仁。仁道不张,灾变有应。变乱频仍,兴诸道理。理灭人欲,礼孝复起。失之东隅,前车翻覆而生灵涂炭。收之桑榆,后圣继起以弥新道统。
绝壁:大义觉迷(节选)
巍巍中华,皇极经世。圣贤教化,彰春秋之大义。汤武革命,伐无道之昏君。强臣变法,去封建之荫庇。酷吏守义,挫豪族之盘根。周公创制,封土建国。夷吾相齐,九合诸侯。孔孟复仁,弥修礼乐。商君变法,利出一孔。封建之法,流弊积沉而式微。郡县之制,应然阙如而隐患。仲舒尊儒,天人感应。王莽改制,身首异处。佛法大乘,发愿渡世。拓跋兴魏,经纶中土。合久之分,贪弊厌世因大乱。分久之合,礼事双修有大治。程朱格物,内圣外王。洪武新朝,体国经野。陆王见性,此心光明。江陵改革,拯危救难。彼岸凋零,难逃此在涂炭。禅机无门,何有内外分殊?辟宋考经,道器一体。朝乾夕惕,摊丁入亩。公羊改制,变法图强。中体西用,师夷洋务。海权跃升,亘古未历之变局。神州瑰伟,代有雄奇之纾难。追慕宪政,思潮涌动。民有之国,五族共和。废黜孔儒,新尊德赛。效诸马列,共产革命。彷徨之时,非本以而忘源。呐喊之际,明义尔后笃行。嗟呼!大乘之邦,伦理长青。礼乐和谐,经史不坠。效哲人法圣王,修齐治平,野有国仕。省议论核名实,知行合一,朝有贤臣。
……
山水初蒙,万物实用而质朴。水天需制,密云不雨而小畜。火山贲饰,修德崇伦而文明。山地剥落,名实不符而大过。应然资产,实然负债。真空秒有,深意隽永。权益有盈,浮华以至虚饰无实。权益有亏,凋敝而至租值持世。道统应然,治统实然。治道一体,权益无存。左右分殊,无中生有之道显。弥合正负,寓有还无之意明。礼乐崩坏,释之于仁。仁道不张,灾变有应。变乱频仍,兴诸道理。理灭人欲,礼孝复起。失之东隅,前车翻覆而生灵涂炭。收之桑榆,后圣继起以弥新道统。混沌无制,封建化成。弭兵一统,郡县乍起。吏有封建,重彰宗族。夷夏大防,五族一体。时移世易,内外骤变而古制难循。改弦易辙,强干弱支以重整治统。士农工商,元会运世。物有大小,民有贤愚。一一之士当兆民,千千之商当一民。天地颠否,危如累卵。内据小人跋扈,外流君子蛰伏。狎昵利使,张狂乖戾。地天交泰,固若金汤。内有君子用事,外放小人效命。淡泊义聚,宁静致远。木体金用,东方之地尚义。金体木用,西方诸国求利。内重外轻,寻道之人。内轻外重,寻租之徒。行道抑租,其乃天下和谐化成之锁钥。轻利尚义,此诚华夏涅槃日新之福祉!
全文见此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44a34b0100zvvr.html
全文及后续见此处: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0646.shtml#adsp_content_replybox_frame_1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七):得君行道
余英时一书在《理学家与政治取向》这一章节中梳理了南宋四大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张栻和吕祖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个案,以此揭示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何内圣取向的理学家群反而特别活跃于“外王”领域之中?
余的一大发现就在于他认定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他称之为宋代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所谓后王安石时代,政治文化的特色在于“内圣”之学的介入,人们认定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如陆九渊云“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经世。” 理学的直接目的在于成就个人“内圣”,但“内圣”的最重要集体功用仍然为了实现“外王”理想——重建一个合理社会秩序,这也是宋代儒学贯穿始终的根本方向。
我们首先要厘清“得君行道”这一概念的四层含义。第一,这一概念包含着理学家群关于实现外王的终极理想不容质疑,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从他们的共同理想衍生出来的。第二,这个概念中“道”意义尤其突出,理学家们仍然尊奉前人“以道进退”,所谓“后王安石时代”的历史涵义即此。第三,理学家的得君行道代表了政治主体自待的群体意识。“得君”是必须通过某一个特殊的人,但“行道”则是属于群体。第四,行道之所以必须得君乃是由于传统的权力结构使然。当时的权源在皇帝手上,皇帝如不发动政治机器的引擎,则任何更改都不肯能开始。因而我们不能以现代政治眼光去看待得君。余在另一处也提出,宋代的得君行道的终极目的是重建理想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朱熹论“道统”、“道学”与“道体”,无一不与三代之治紧密相连。
余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家中最早表现出得君行道倾向的是北宋程颐,最重要的文本即他的《上仁宗皇帝书》,这对朱子本人得君行道的信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程颐所提“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作为他之后理学家们追寻得君行道的基本方式,他们都非常重视与皇帝直接面对谈话的机会。通过检视陆九渊和朱熹有关“轮对”的书信往来,即可发现在他们自身心目中,原始儒家得君行道观念是到宋代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这一观念的发展和实践直接跳过了孔孟之后汉唐诸儒。同时王安石也是第一个得到实验机会的,他与神宗的投契鼓舞了南宋理学家们的期待,尽管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收场,仍将这归因于王安石内圣之学不足,产生了舍本逐末。
若围绕朱子为中心的讨论,在余英时书的《理学家与政治取向》和《孝宗与理学家》两个章节中,详细考证了隆庆元年首次与孝宗“登对”前后,以及孝宗晚年改革中朱子的应召和立朝四十日过程。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是朱子本人政治实践的失败以及最终整个理学集团随着“庆元党禁”落幕。
而恰恰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之上,朱熹在绍熙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封书信中说:
……自此杜门,当日有趣,但恨虚辱招延,无所裨补,犹不能忘怀吾君进学之深浅也。……唯冀以时珍卫,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怀,缉熙光明,以扶庙社,区区至恳。
这是朱子正式结束政治生活的宣言书,但他的情怀仍念念不忘致君行道的。 理学家们虽然都是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面目出现,仍然无法逾越“君以制天命为职”。余英时在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个案的宋明政治文化比较中尤为突显宋代士大夫从未放弃过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宏愿,而阳明在继承此一思想脉络失败之后才开启了新的转向。 理学家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继承着北宋儒家政治文化。从个体的立场说,每一个都必须具备基本的“内圣”修养,但从群体观点看,他们共同的目标则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大学》一篇之所以在理学史上取得枢纽地位,其原因也在于解答了由“内圣”转出“外王”的可能。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八):宋代士大夫文化三阶段论
《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副标题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研究中以朱熹为中心展开的整个世界上溯起源到北宋,同时贯穿整个南宋时期。以余英时本人的话说即此书注意的焦距集中在儒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关联与交互作用。即将儒学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中以观其动态。
我们首先要明白余英时所用的“政治文化”一词内涵,以及他为整个宋代所划分的士大夫文化三阶段。书中此词有二义,第一,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另一层涵义是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再看士大夫政治文化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以称之为建立时期。仁宗朝的儒学领袖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获得普遍认可。第二阶段核心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想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至少在当时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完全交托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以称之为转型时期。所谓转型是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模式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以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但其依旧在南宋政治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着重探讨的其实是第三阶段的变异问题。
余英时认为朱熹向来被认定是道学的集大成者,而道学的完成恰好便是这一阶段中最大的变异。这里提出一个特殊而值得注目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和陆九渊两人而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在“外王”的实现。更重要的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作准备的,因此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南宋“内圣”之学的兴盛与熙宁变法失败也存在密切关系,这在理学家“得君行道”的实践中会更具体展开论述。
概而言之,从现代的观点说,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通贯宋代政治文化三大阶段的一条主要线索。
而有关宋代士人这种主体意识,在第三章节《“同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中有更详细讨论。“以天下为己任”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形态呈现“同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彦博曰: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值得注意的是:文彦博“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是神宗与王安石共同承认的前提。文彦博这句话脱口而出,视若当然,而皇帝也视为当然,这正是宋代的一大特色,也是宋代能获得“后三代”美称的一个主要根据。与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神宗正式接受“共顶国是”的观念,则象征着皇权方面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因而用现代的话说,这显示的是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大任放在自己身上。显然“共治天下”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治道”方面的体现。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九):原儒
对于这样的书,我写书评,就觉得有点惭愧。实际上很多书都是这样,抬高到评论实在太不好意思了,顶多是看过之后的一点小感想。
不过豆瓣只有笔记和评论两种,我想说的东西,说是笔记更加名实不符了。所以。
这篇东西并非只针对这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籍,也包括了我前段时间看完的《戴震和章学诚》以及别的一些书。总的来说,我是想澄清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纠葛于心已久,已经日渐清晰。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不管看起来像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儒家弟子。而且跟所谓的“新儒家”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太过刻意而生生将儒学送给了韩国。WHY?一言以蔽之,整容。
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认可人事在变化。或许我这么说对于我刚才说我是儒家弟子是个莫大的讽刺,而恰恰就是因为余英时老师这两本书才让我深刻认识到,儒学一样变动不居,没有脱离历史的学问,即使每个人都要找寻一两千年前圣人的话语,却无法不以自己的话语去诠释(包括一系列伪书)。
同时,我认为这种行为和思维模式是得不偿失而且阻碍着儒学的发展的。即儒学=某人。即使这个某人是大圣先师孔子也好。既然可以认为孔圣超越了周公,为什么后来人就不能超越孔圣?其实即使"超越”这一词也是危险的不准确的。每个时代的人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我们不可能和孔子互换时空去检验知行的高低,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反思历史时总是进行了一系列方便的假设。那么很多人都会显得自己非常高明了。
那么我为什么认可儒学呢?既然思想在变化,而且我汲取营养的来源亦绝不止儒家一派。即使与任何人都大为不同,我又为何不为自己的思想找一个新的名称?
我之所以认可孔子,是因为我认可他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当然并不是那种逐字逐句的认可,而是一种背后精神的认可。我认为良好的自发的社会秩序比法律更重要,并不妨碍我指出礼教的不可能;我认为人们的差距是教育而不是先天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什么人人生而平等;我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却也没有认为过谁是烂泥扶不上墙(这当然是因为孔子是老师而我不是,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
当然我对儒家其他人物也抱有相应的一些认可度,综合的来说,共同点在于这一些,而我认为(并且以为余英时老师也应该认可这一点)这些才是儒家真正的内涵所在,至于其他的,都是可以应时变化的。
这一些包括:热爱只有一次的人世,认为自己应该并可以对其负有责任,认识到人的软弱和卑鄙之处,用宽容的心去区别看待,抱有理想但认识现状,相信自己但懂得畏惧,学会尊敬和倾听。最重要的是,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可以沟通,并发掘出同质的真善美。
以上也并非我全部所得。我还想提出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是从反对一个过分到一个过分的反对,用矛盾的辩证发展模式来解释似乎可行。问题是我们总要沉溺于这样耗费精力的社会规律么?既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依然不能解决“当年爱之俞甚,今日毁之俞过”的问题,如果依然以为前人都是脑袋有病的怪物,我们又怎么能逃过求全之毁,又怎么能不成为后世的怪物。。。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十):从“共治天下”到“借君行道”
余英时的一系列著作,定义了中国思想史写作,人们想到思想史,国人不大理睬思想史的定义,而往往会将思想史的概念与具体的研究著作联系起来。余英时的许多作品,被视作思想史写作,特别是晚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更成为了其中的典范。
在这部书中,余英时先设定了宋代理学士大夫,与汉唐和明清士大夫有精神气质的差别,然后推论宋代的政治风气最为开放,士大夫地位最为高涨,这是由于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成果。这些假设,都是余英时在《朱熹》一书绪论设置的学术假设。可以说,本书的分论部分就是要用宋代的历史来证明上述的假设。
宋代分为两个阶段,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朱熹生活在南渡后的南宋,但是余英时的写作却开始于北宋,对于宋初的古文运动、政治改革与理学运动结合起来考察,这个判断大抵来自于钱穆的《国史大纲》的判断。余英时将这个判断,细化为具体的学术研究,将古文运动与北宋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考察,这大体是不错的。毕竟,北宋主要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是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与理学运动的关系,余英时深知二程与王安石并非盟友,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对手。如何将理学运动与王安石变法联系,就是余英时北宋研究的关键问题。余英时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二程是支持改革的,只是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认为王学不过是佛道思想,因此要将理学赋予政治改革新的学术精神。余英时非常擅长处理复杂学术问题,比如上述理学与王学的关系,被余英时轻松用体用关系给置换了。至于这是否是历史真相,自有读者来判断。
余英时花大力气处理王安石与二程的关系,就是为了朱熹做的铺垫工作。学术史上,自然避不开朱熹对于二程学术的继承,只有将二程与王安石的关系梳理清楚了,才能顺理成章地将朱熹说成继承王安石政治改革思想。那么,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的政治行为才有了学术上的依据。不过可惜的是,朱熹仅仅在中央政府总共就没有呆几天,更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那么,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论断岂不是要落空?
余英时则顺便就将朱熹的论敌陆象山、叶适等人归为理学士大夫,然后他们的政治行为也归入共治天下的范畴。不过,继续考察这些理学士大夫,发现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政治主张,那么,余英时只好修正自己的开篇论断,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变成了借君行道,从并列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因此,他就需要继续处理两个问题,第一皇帝是否是明君,第二官僚集团的反动性质。
所以,我们看到下篇中,理学士大夫反而成了配角,皇帝和官僚集团反而成了主角,这个转变恰恰跟余英时的假设转变有关。当没有办法论证理学士大夫的政治行为后,只能转而论证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各种原因,导致了理学士大夫政治改良行为的失败。
写到这里,我们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整本书的绪论与分论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裂,余英时设想的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上,在历史具体考证上,反而发现宋代政治历史的主体恰恰并非理学士大夫集团,反而是他们的敌人王安石、官僚士大夫们。那么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恰恰是王安石、官僚集团,与理学士大夫没有什么关系。无论理学家们如何设置了理想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们既没有能力实践理想,也没有真正的政治实践。理学士大夫作为政治势力,进入到历史舞台,要等到明代以四书取士,但是显然明代的政治生态,不符合余英时的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显然,余英时意识到了这个漏洞,因此他续写了明代政治生态问题,来解释为何虽然理学士大夫已经进入历史舞台,但是从明初朱元璋刻薄士子,因此就打断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选择了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不过,我们必须追问,历史上真的存在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