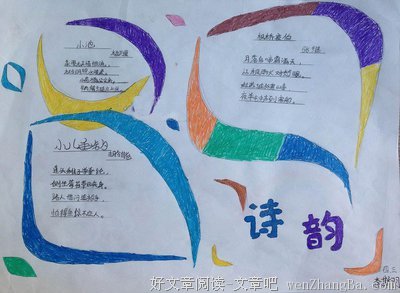《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92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一):《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
作为一位并不专治宋史的学者,余先生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理学家与孝宗末年之政这一关键问题,并钩玄提要、明其待发之覆,其大历史学家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在洋洋洒洒将近千页的论述中,余先生着力营造的正是这一「历史学家」的形象,其演绎的立足点也在于这一形象背后的一系列现代西方学术逻辑。以此而言,本书大致能够实现自洽,又不失其可读性。仅看附论所引征的三位论者的批判及作者的反驳,似可知二者乃在不同的问题意识之下进行,作者本就是探讨政治世界的事情,自不触及相关人物在价值世界的论说。即便洛闽嫡传看了此书,纵不感叹后世相知,大约也不会跳起来批判一番。然而,在本书之外,余先生实际上对这一价值世界持一至少是不予认同的态度,教人读着并不安心也是意料中事。余可见拙作〈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一文。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二):得君行道
余英时一书在《理学家与政治取向》这一章节中梳理了南宋四大理学家朱熹、陆九渊、张栻和吕祖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个案,以此揭示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何内圣取向的理学家群反而特别活跃于“外王”领域之中?余的一大发现就在于他认定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他称之为宋代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所谓后王安石时代,政治文化的特色在于“内圣”之学的介入,人们认定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之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如陆九渊云“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经世。” 理学的直接目的在于成就个人“内圣”,但“内圣”的最重要集体功用仍然为了实现“外王”理想——重建一个合理社会秩序,这也是宋代儒学贯穿始终的根本方向。
我们首先要厘清“得君行道”这一概念的四层含义。第一,这一概念包含着理学家群关于实现外王的终极理想不容质疑,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从他们的共同理想衍生出来的。第二,这个概念中“道”意义尤其突出,理学家们仍然尊奉前人“以道进退”,所谓“后王安石时代”的历史涵义即此。第三,理学家的得君行道代表了政治主体自待的群体意识。“得君”是必须通过某一个特殊的人,但“行道”则是属于群体。第四,行道之所以必须得君乃是由于传统的权力结构使然。当时的权源在皇帝手上,皇帝如不发动政治机器的引擎,则任何更改都不肯能开始。因而我们不能以现代政治眼光去看待得君。余在另一处也提出,宋代的得君行道的终极目的是重建理想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朱熹论“道统”、“道学”与“道体”,无一不与三代之治紧密相连。
余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家中最早表现出得君行道倾向的是北宋程颐,最重要的文本即他的《上仁宗皇帝书》,这对朱子本人得君行道的信念产生了巨大影响。程颐所提“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作为他之后理学家们追寻得君行道的基本方式,他们都非常重视与皇帝直接面对谈话的机会。通过检视陆九渊和朱熹有关“轮对”的书信往来,即可发现在他们自身心目中,原始儒家得君行道观念是到宋代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这一观念的发展和实践直接跳过了孔孟之后汉唐诸儒。同时王安石也是第一个得到实验机会的,他与神宗的投契鼓舞了南宋理学家们的期待,尽管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收场,仍将这归因于王安石内圣之学不足,产生了舍本逐末。
若围绕朱子为中心的讨论,在余英时书的《理学家与政治取向》和《孝宗与理学家》两个章节中,详细考证了隆庆元年首次与孝宗“登对”前后,以及孝宗晚年改革中朱子的应召和立朝四十日过程。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是朱子本人政治实践的失败以及最终整个理学集团随着“庆元党禁”落幕。
而恰恰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之上,朱熹在绍熙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封书信中说:
……自此杜门,当日有趣,但恨虚辱招延,无所裨补,犹不能忘怀吾君进学之深浅也。……唯冀以时珍卫,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怀,缉熙光明,以扶庙社,区区至恳。
这是朱子正式结束政治生活的宣言书,但他的情怀仍念念不忘致君行道的。 理学家们虽然都是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面目出现,仍然无法逾越“君以制天命为职”。余英时在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个案的宋明政治文化比较中尤为突显宋代士大夫从未放弃过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宏愿,而阳明在继承此一思想脉络失败之后才开启了新的转向。 理学家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继承着北宋儒家政治文化。从个体的立场说,每一个都必须具备基本的“内圣”修养,但从群体观点看,他们共同的目标则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大学》一篇之所以在理学史上取得枢纽地位,其原因也在于解答了由“内圣”转出“外王”的可能。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三):读书杂感
在这样一个深夜,坐在自己的床上,突然想写这样一篇不算是书评的书评,因为它更像是我进入大学历史系两年来的一点感想。所以更多我要说的,是我阅读此书的过程。如果在高中时候让我写一篇这样的书评,我肯定自信满满,夸夸其谈且面不改色心不跳。但进入历史系两年来,我越发觉得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说一些话开始思前想后看有无错误,一些评论甚至自己都不敢下了。打个比方,在高中时,就像是那只在井里的青蛙,我的天空只是那井口大小,毫无疑问,我是我世界当然的主人,但当我终于爬出这口井时,才发现所谓沧海一粟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买到此书,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买,当然也只是冲着此书的名气,记得当时的我只是随手翻了两页,觉得无聊看不进去就扔在了一边,觉得上大学看也好,于是,在搁置一暑假后,我把它带回到了学校。
进入大学的第一年,是充满新奇的一年,有太多新鲜的东西需要接受,于是,这本书就在寝室的书架上,安安静静的待了一整年。
直到大一结束,在去军区军训之前,硬着头皮读了一百页绪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只是一页一页的看着,拿笔划一些我都不知为何要划的横线(这在我后来重新阅读时候深有体会),没多久,它便又回到了它应该在的位置。
再次拿起,是这学期的期末,十天时间,读完此书。合上书本再想想从不在意去读,到发现根本读不懂,再到读完的这个两年的过程相对应的自己,态度可能正好相反。也许,这便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吧。
名为书评,还要再来说说这本书,大一读完陈苏镇《春秋与汉道》时候模模糊糊对政治文化有了个大致印象,陈书以《春秋》学作为贯穿两汉政治史的一把钥匙,从《春秋》学对两汉政治的影响入手。而余书则更多的针对士大夫“内圣外王”的“外王”层面。余先生敏锐的观察到了在理学或是朱熹研究层面上将时代与学术割裂的倾向。他要将朱熹还原到历史中去,构建出一个立体的“历史世界”。他从此入手,更加具体的分析了在种种分歧背后士大夫“得君行道”的一面。由此揭示出两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些面相。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庆元党禁的原因)也有了新的,更加完整的解释。
更可一提的是余先生对于心理史学的应用。他对孝宗光宗心理过程的揭示可以说分外精彩。在文献材料不足或没有直接证据时候,这样的方式或许也是一种借鉴。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四):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2013年,三联书店)虽以朱熹为主题,但副题“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更能概括本书主旨。以朱熹作为中心人物,既可以就典型人物做细密的材料分析与历史反思,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也可以借此考察宋代已经成熟的政治制度,描画终宋一代士大夫的思维模式与政治行动。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间的交织互动与士大夫在其中的运用,以正史、文集、笔记、官文书、日记、年谱等文献资料为主,辅之以今人的研究成果,“遍检群籍”,试图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正如自序所说,重构与还原近乎为不可能,故作者的史料证释与解读,未必为确诂,但确不失为达诂,其中的眼光和识见都让人佩服。
宋代独特的政治风格是全书所著力描绘之处,从宋初“回向三代”的理想对儒生整体的影响开始,展示宋儒的独特面貌,年轻的神宗皇帝也受到儒家理想激情感染而锐意变法。虽然变法不成,“新政”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士人努力争取的与皇帝“共定国是”、“同治天下”的权力最终得到了皇权的认可,并嵌入政治制度之中;君相与“国是”共进退,使皇帝再也不能以仲裁者的身份凌驾于士人党争之上,虽然后果是,执政派“引其君以为党”,对异己士大夫进行政治迫害。朱熹及其同辈人生活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王安石时代”。
本书在结构上分上下二篇,通论铺展在前,专论详说在后,各有侧重又互相牵涉。上篇通论宋代政治文化与士的政治主体地位,追溯北宋,展示朱熹生存其中的宋代政治文化环境的整体演变,探讨新的学术取向和政治风格的形成,论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的缘由。下篇专论朱熹时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以理学群体在南宋前五十年的际遇,凸显“君相共治”与“国是”在南宋的发展,展示理学群体的政治欲求,廓清“道学”与“庆元党禁”之间的微妙关系,与上篇所论道学因果相互交映,呈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和外缘情境。就布局来说,上篇是全文的全景俯瞰,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讨论的话题有过于精深而不得不点到为止的,下篇事件的发展则是上篇庞大铺垫的或然发展,故我拟就上篇做稍详细的讨论,而略去下篇。
新学术的产生,往往是对时代思潮的反应和回应,作者蒐集相关史料,将二程道学之定型放入与王氏新学竞争的大背景之下,以道学产生与外界之互动,在二程看来,新学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竞争对手。对道学来说,当时最强劲的思潮无疑是佛学。僧徒与士大夫密切的交游,塑造出一批士大夫化的名僧和好谈禅的士大夫,二者间纠缠不清,这无疑让严守界限的道学家感到紧张,集中火力于修禅的士大夫,新学也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批判。尽管如此,谈禅的风气所及,牵连心、性,已展开了一个探索“内圣”的谈辩境域(discourse),作者抉出当时极受各方关注的《中庸》,揭示儒家对佛门开创的“谈禅境域”的接收。佛学竟成为了道学的“助产士”,这是道学家所不自知或竭力否认的。
余英时在论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总体状态时借用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ideal-type”),将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他虽然塑造出“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这两个理想型,却又像韦伯一样不断提醒读者这仅仅是大体的理想划分,并非金科玉律且不涉价值判断,仅做一种简便的分析方法用。不过,与大众的印象里,“官僚”二字即带负面色彩,这种现代成见恐怕不能避免。作者虽然竭力澄清后世对理学群体的种种误读与偏见,但今人的偏见还是不断地影响着对本书的理解,单看书后附录就能知道这种成见之固。这些成见来源于在理解历史之前就已存在的对历史认知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日常文化环境塑造的历史景观覆盖在历史本相之上,成为今日的共识,重复共识固然方便也不会引得众楚齐咻,但是历史学家的所能做也在于此:揭露错误或粗糙的历史概括。通过回归原始材料,余英时选择对时代的历史共识的悬搁(epoche),“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挖掘隐匿的历史本相。人们固然质疑重现历史本相的可能,但这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需要靠着学术自觉努力接近的理想状态,当然,史学研究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只是远看漂亮的空中花园,在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分寸感尤其重要,这点尤见于余对心理史学的应用上。
往往以哲学史的取径来研究理学家,无非是借用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来重写中国思想史,即将理学从宋代的历史脉络里抽离出来,进行形上学或宇宙论上的研究,这自然也有它的价值,但却导致了思想史之中思想者的隐退,空余理论和概念的排列。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philosophy)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理学的传统在思考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inking)上,而不是思想的内容(substance of thought)上”,归根结底,理学家从未忘却“治道”,那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其他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 order”)的位置。将理学纳入哲学的系统理论之中,看似井井有条,实则是以“他者”目光重构自身,不免造成某种时间错置的“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这种对历史情境的“抽离”由来已久,我们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引用陈寅恪在近九十年前的一段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葛兆光以为“哲学就是西方来自希腊的知识,而且是有系统的探索原理公例的科学,那么,这种定义如何可以概括、解释和叙述既不同于希腊,又并不以发现原理或公例为目标的古代中国思想?”,若单单对理学家进行“哲学”维度的解读,恐怕是“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当然,这并非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以为双方“井水不犯河水”,没有比较的可能,而是在“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总体认同下,就迥然不同的历史和学术的发展脉络,区分细微的异同,做谨慎的比较研究。但种种词语和概念的表达已在我们讨论问题之前就限制好了思考范围,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怀疑或者放弃这些表达,将无法表达自我,朱熹曾疑古文《尚书》为伪,又曾疑及其余经书,但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被压了下去,他自己也承认,若疑到底,整个儒家信仰世界的基础就会崩塌,这是他所不愿也不敢的。戴震所说的“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今日恐怕很难实现,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小心谨慎的在概念的陷阱中行走,据此也可知余英时的谨慎态度建立在学通中西的基础上,正是因为了解,才不敢轻易做无谓的比较。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余英时师徒三代都曾以朱熹作为研究主题,但三者意义却大不相同。田浩(Hoyt Tillman)经历过完整的现代思想史专业训练,站在域外研究中国,虽然视角特别但又不能免于“隔”;对钱穆来说,朱熹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考察的对象,还是他自幼生长濡染其中的道统世界的圣人“朱子”,谈论朱熹的经历与学问都是他表达现实关怀的一种途径,在这层意义上,他回归了传统,余英时则刚好处于两者之中,他和自己几本专书的研究对象大概是同一类人,在学术新知之外,都有一套坚固的价值系统,不能简单地视作知识从业员(mental technician),而是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学术研究和价值世界交织在一起,尽管他们的一些政治意见恐怕不能让人信服,但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做出判断的背景,错误史料未必不能印证真实历史,其中还可能隐含着群体思维或时代风潮,对于思想史来说,这些材料的价值也是不能抹杀的。
本书篇幅九百多页,笔下所及以朱熹为中心,而目光所注则在宋代政治文化动态之整体,其中可以深论之处还有很多,但这已超出我知识和能力之外,以后生小子来评论学界耆硕的代表作品,妄谈而已。对本书,或说对余的总体学术写作事业的大致印象,我则还要斗胆引文献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一段话来表达:“历史的书写,很有可能如同任何人类活动,应当成为一种‘对立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努力回应两种相反的苛求,每一种都同样紧迫:为了感知和评估历史现实,一方面需要自我有意识的、完全的介入,另一方面需要完全超脱自我,要求有一种客观性、非片面性。在我眼中,这是科学的精确的修行,要做出客观的、不片面的判断要求这种自我的超脱,这可以为我们赋予嵌身历史之中的权利,也为判断赋予一种存在的意义。”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五):从“共治天下”到“借君行道”
余英时的一系列著作,定义了中国思想史写作,人们想到思想史,国人不大理睬思想史的定义,而往往会将思想史的概念与具体的研究著作联系起来。余英时的许多作品,被视作思想史写作,特别是晚年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更成为了其中的典范。在这部书中,余英时先设定了宋代理学士大夫,与汉唐和明清士大夫有精神气质的差别,然后推论宋代的政治风气最为开放,士大夫地位最为高涨,这是由于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成果。这些假设,都是余英时在《朱熹》一书绪论设置的学术假设。可以说,本书的分论部分就是要用宋代的历史来证明上述的假设。
宋代分为两个阶段,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朱熹生活在南渡后的南宋,但是余英时的写作却开始于北宋,对于宋初的古文运动、政治改革与理学运动结合起来考察,这个判断大抵来自于钱穆的《国史大纲》的判断。余英时将这个判断,细化为具体的学术研究,将古文运动与北宋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考察,这大体是不错的。毕竟,北宋主要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是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与理学运动的关系,余英时深知二程与王安石并非盟友,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对手。如何将理学运动与王安石变法联系,就是余英时北宋研究的关键问题。余英时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二程是支持改革的,只是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认为王学不过是佛道思想,因此要将理学赋予政治改革新的学术精神。余英时非常擅长处理复杂学术问题,比如上述理学与王学的关系,被余英时轻松用体用关系给置换了。至于这是否是历史真相,自有读者来判断。
余英时花大力气处理王安石与二程的关系,就是为了朱熹做的铺垫工作。学术史上,自然避不开朱熹对于二程学术的继承,只有将二程与王安石的关系梳理清楚了,才能顺理成章地将朱熹说成继承王安石政治改革思想。那么,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的政治行为才有了学术上的依据。不过可惜的是,朱熹仅仅在中央政府总共就没有呆几天,更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那么,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论断岂不是要落空?
余英时则顺便就将朱熹的论敌陆象山、叶适等人归为理学士大夫,然后他们的政治行为也归入共治天下的范畴。不过,继续考察这些理学士大夫,发现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政治主张,那么,余英时只好修正自己的开篇论断,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变成了借君行道,从并列结构变成了偏正结构。因此,他就需要继续处理两个问题,第一皇帝是否是明君,第二官僚集团的反动性质。
所以,我们看到下篇中,理学士大夫反而成了配角,皇帝和官僚集团反而成了主角,这个转变恰恰跟余英时的假设转变有关。当没有办法论证理学士大夫的政治行为后,只能转而论证皇帝和官僚集团的各种原因,导致了理学士大夫政治改良行为的失败。
写到这里,我们突然意识到,余英时整本书的绪论与分论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裂,余英时设想的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上,在历史具体考证上,反而发现宋代政治历史的主体恰恰并非理学士大夫集团,反而是他们的敌人王安石、官僚士大夫们。那么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恰恰是王安石、官僚集团,与理学士大夫没有什么关系。无论理学家们如何设置了理想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们既没有能力实践理想,也没有真正的政治实践。理学士大夫作为政治势力,进入到历史舞台,要等到明代以四书取士,但是显然明代的政治生态,不符合余英时的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显然,余英时意识到了这个漏洞,因此他续写了明代政治生态问题,来解释为何虽然理学士大夫已经进入历史舞台,但是从明初朱元璋刻薄士子,因此就打断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选择了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不过,我们必须追问,历史上真的存在理学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六):宋代士大夫文化三阶段论
《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副标题为“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研究中以朱熹为中心展开的整个世界上溯起源到北宋,同时贯穿整个南宋时期。以余英时本人的话说即此书注意的焦距集中在儒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关联与交互作用。即将儒学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中以观其动态。我们首先要明白余英时所用的“政治文化”一词内涵,以及他为整个宋代所划分的士大夫文化三阶段。书中此词有二义,第一,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以政治思维论,宋代士大夫从最初就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再以行动风格论,范仲淹处发轫的“以天下为己任”可以用来形容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另一层涵义是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在政治领域,赵宋王朝的特殊历史处境为士阶层提供了较大的政治空间。在文化领域中,民间对于文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开启了儒学复兴的契机。宋代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风格是和这两大领域中新动态相互关联的。
再看士大夫政治文化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以称之为建立时期。仁宗朝的儒学领袖都主张超越汉、唐,回到“三代”的理想。在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方面,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获得普遍认可。第二阶段核心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这是回想三代的运动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功能的时期。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则: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至少在当时理论上,治权的方向已由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决定,治权的行使完全交托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执政集团了。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以称之为转型时期。所谓转型是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模式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以一次彻底失败的政治实验但其依旧在南宋政治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着重探讨的其实是第三阶段的变异问题。
余英时认为朱熹向来被认定是道学的集大成者,而道学的完成恰好便是这一阶段中最大的变异。这里提出一个特殊而值得注目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如朱熹和陆九渊两人而言,他们对儒学的不朽贡献是在内圣方面,但是他们生前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在“外王”的实现。更重要的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作准备的,因此他们深信“外王”首先必须建立在“内圣”的基础上。南宋“内圣”之学的兴盛与熙宁变法失败也存在密切关系,这在理学家“得君行道”的实践中会更具体展开论述。
概而言之,从现代的观点说,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通贯宋代政治文化三大阶段的一条主要线索。
而有关宋代士人这种主体意识,在第三章节《“同治天下”——政治主体意识的显现》中有更详细讨论。“以天下为己任”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形态呈现“同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彦博曰: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值得注意的是:文彦博“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是神宗与王安石共同承认的前提。文彦博这句话脱口而出,视若当然,而皇帝也视为当然,这正是宋代的一大特色,也是宋代能获得“后三代”美称的一个主要根据。与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神宗正式接受“共顶国是”的观念,则象征着皇权方面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因而用现代的话说,这显示的是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大任放在自己身上。显然“共治天下”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治道”方面的体现。
《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七):原儒
对于这样的书,我写书评,就觉得有点惭愧。实际上很多书都是这样,抬高到评论实在太不好意思了,顶多是看过之后的一点小感想。不过豆瓣只有笔记和评论两种,我想说的东西,说是笔记更加名实不符了。所以。
这篇东西并非只针对这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籍,也包括了我前段时间看完的《戴震和章学诚》以及别的一些书。总的来说,我是想澄清一些事情。这些事情纠葛于心已久,已经日渐清晰。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不管看起来像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儒家弟子。而且跟所谓的“新儒家”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太过刻意而生生将儒学送给了韩国。WHY?一言以蔽之,整容。
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认可人事在变化。或许我这么说对于我刚才说我是儒家弟子是个莫大的讽刺,而恰恰就是因为余英时老师这两本书才让我深刻认识到,儒学一样变动不居,没有脱离历史的学问,即使每个人都要找寻一两千年前圣人的话语,却无法不以自己的话语去诠释(包括一系列伪书)。
同时,我认为这种行为和思维模式是得不偿失而且阻碍着儒学的发展的。即儒学=某人。即使这个某人是大圣先师孔子也好。既然可以认为孔圣超越了周公,为什么后来人就不能超越孔圣?其实即使"超越”这一词也是危险的不准确的。每个时代的人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我们不可能和孔子互换时空去检验知行的高低,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反思历史时总是进行了一系列方便的假设。那么很多人都会显得自己非常高明了。
那么我为什么认可儒学呢?既然思想在变化,而且我汲取营养的来源亦绝不止儒家一派。即使与任何人都大为不同,我又为何不为自己的思想找一个新的名称?
这是因为关心的重点没有变化。我记得豆瓣上某个人说过:细观《论语》,其实就不过是一些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会有的智者箴言罢了,老生常谈,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他来说这里面当然是看轻之意,但在我看来,这不外是最高的赞美,因为里面潜藏了四个字,即“普世价值”。
我之所以认可孔子,是因为我认可他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当然并不是那种逐字逐句的认可,而是一种背后精神的认可。我认为良好的自发的社会秩序比法律更重要,并不妨碍我指出礼教的不可能;我认为人们的差距是教育而不是先天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什么人人生而平等;我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却也没有认为过谁是烂泥扶不上墙(这当然是因为孔子是老师而我不是,别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
当然我对儒家其他人物也抱有相应的一些认可度,综合的来说,共同点在于这一些,而我认为(并且以为余英时老师也应该认可这一点)这些才是儒家真正的内涵所在,至于其他的,都是可以应时变化的。
这一些包括:热爱只有一次的人世,认为自己应该并可以对其负有责任,认识到人的软弱和卑鄙之处,用宽容的心去区别看待,抱有理想但认识现状,相信自己但懂得畏惧,学会尊敬和倾听。最重要的是,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可以沟通,并发掘出同质的真善美。
以上也并非我全部所得。我还想提出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是从反对一个过分到一个过分的反对,用矛盾的辩证发展模式来解释似乎可行。问题是我们总要沉溺于这样耗费精力的社会规律么?既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依然不能解决“当年爱之俞甚,今日毁之俞过”的问题,如果依然以为前人都是脑袋有病的怪物,我们又怎么能逃过求全之毁,又怎么能不成为后世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