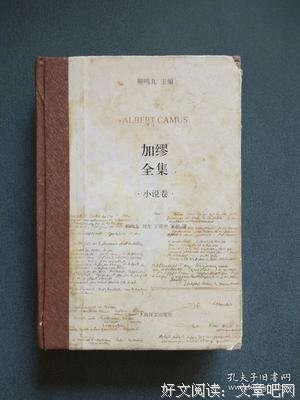
《加缪全集(全四册)》是一本由柳鸣九 / 沈志明 主编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200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加缪全集(全四册)》精选点评:
●19.永远的男神,精神领袖
●对加缪的爱源于生命气质的暗合,我爱这个贫民窟长大的百万富翁
●读到第四册,散文集《夏》的翻译简直令人发指,读不通且不论,怎么可以删改原作句子?
●人道主義精神,冷峻,外國文學在藝術上的追求與中國殊途。
●人性的困境与幸福,加缪探索的很好。
●大学图书馆看过前两卷~
●只看了局外人 那卷
●常看常新
●没有全部看完 承认有些难懂 毕竟达不到那阅历
●我在讀第二冊戲劇卷
《加缪全集(全四册)》读后感(一):对人生困境的哲学解读
《局外人》曾经影响20~22岁的我。
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荒谬世界中痛苦孤独的个人,在绝望、荒诞的环境中再现着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
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文学作品通常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哲学的结果,是这种哲学的具体图解和美化修饰。
《加缪全集(全四册)》读后感(二):新人道主义
其实没有谁是那种会为了自己而践踏别人的人,天晓得,有一天
这个世界会不会醒过来,开出一朵漂亮的达摩花。
可是,越挣扎就越痛苦,人是一种多徒劳的动物,越徒劳就越沉醉,弃去天赋异秉,甘愿沦为最诡异又最明白的一代。却依然不忍放弃,卑微的活着。
在漫长和萧条之间学会屏息。在顾盼和等待之间学会隐忍。这就够了。可是我偏却是乐观主义者。
《加缪全集(全四册)》读后感(三):献给永远无法阅读此书的你
多么感谢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当然,还有眼泪。我一点也不想隐瞒我的真实感受:读《第一个人》的时候,我哭了很多次,有时是眼泪自己就悄无声息地流下来,有时是发自胸腔的悲恸,那是一种窒息的痛——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头脑一时发热造成的软弱行为吧,不过还是加缪的女儿善解人意:“那些没有这类体验的人将很难理解这一点。”你可以说,这种爱好只是出于一种任性,缺乏辨证,缺乏说服力,但这正合我心意,因我并不想推荐你一定要去看这本书,尤其是当你迷恋于各种各样的表现技巧以及天花乱坠的自我时。
我想,我是一个影子,是天上那个人的影子。在宁静蓝色的梦幻当中,我们额头相碰,双手相牵。一种主观的、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情感在我头脑里产生,而且前所未有的强烈。我感觉,我曾经就生活在那里(阿尔及利亚),我了解书里的一切:山坡上的风,以及生活本来的样子。
《第一个人》是加缪未完成的作品,连1/3都不到,从雅克(或者直接说加缪)的出生到他上中学,并成为学校足球队正式的守门员(不到15岁)。在戏剧卷里有一张加缪十四岁时的照片,一个词:美艳不可方物。衣着体面,丝毫看不出潦倒的窘态,正如他的小学老师热尔曼先生说的那样:“这是对你妈妈最好的赞誉”——我的小加缪!我亲爱的小家伙!相貌多年保持不变,尤其是那双眼。
……看完雅克与热尔曼老师的两封通信后,我趴在床上痛哭起来,因为爱,因为《第一个人》没有下文,因为加缪,也因为自己——看不到了,圣奥迪尔修道院的寄宿女生们,雅克和皮埃尔经历的最深刻激情。看不到了,一如拼命离我远去的骄傲的青春……Never More,Never More,Never More,想起那只叫“Never More”的乌鸦,以及一个重复着问乌鸦叫什么的人。
:在小说卷总序部分,提到加缪在戏剧创创作与戏剧编导方面也野心勃勃,甚至对演电影也兴致颇高。杜拉斯的著名小说《琴声如声》(《琴声如诉》)由布鲁克执导搬上银幕之前,杜拉斯、让娜·莫罗都同意由加缪出演男主角,加缪也欣然同意,只是因为《第一个人》的写作进度与电影拍摄的档期有矛盾,男主角才由保罗·贝尔蒙多代替出演——禁不住地浮想联翩……唉,当时的法国!!
《加缪全集(全四册)》读后感(四):《局外人》默尔索,人类和上帝唯一的基督?
基督走向十字架,独自承担了人类沉重的罪。基督受苦殉难,用圣爱的温馨赋予了人类生活的意义,拯救了人类万千心灵。据说,加缪视《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为人类唯一的基督、上帝唯一的基督。据说,默尔索的死是对荒诞的反抗,是对人类命运的独自承担。据说,默尔索蔑视社会约定观念——荒诞,他的死是对非人生存境况的反抗,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先声。
果真如此?“局外人”默尔索果真是人类与上帝唯一的基督?用鲁迅的话,默尔索果真是那“肩住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地方去”的人?
为了追问的展开,首先对局外人默尔索进行一番正名。“局外”一词令人想起另一个文本中的另一个词——“槛外”。《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红楼梦》的世界遍被凄凉之雾,其中人物命运悲苦,却不失诗意。而《局外人》以惊人的冷静的理智阉割了现世诗性的温暖。
两个文本是诗与思的文本。一样抒写人的受难和爱之难,一样心怀乡愁去追寻家园。《局外人》却带有一种漠然的可怖的荒诞,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局无谓的游戏。莎瓮所言:“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 Signifying nothing.”( William Shakespeare, From Macbeth V, v )
我也相信,那种能够独自承担如此冷漠荒诞的人,是那“肩住黑暗闸门”、“放我们到光明地方去”的人,是人类和上帝唯一的基督。可是,在默尔索身上我们看不见这样的神性光辉。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加缪全集》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而荒诞感的存在,正在于对生命意义的无法确信。默尔索的冷漠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厌倦感。他因此以一种极端随意的态度对待生活,近乎蔑视。加缪称,西西弗是“荒诞的英雄”,“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加缪全集》3,p137)
可是,局外人默尔索并不具有西西弗反抗荒诞的精神气质,面对荒诞,他只是冷漠,只是无所谓。默尔索蔑视上帝,可是他无力充当新的神。抹杀上帝后,他无法使自己成为承担荒诞的英雄,而是冷漠地参与了荒诞,重新回到荒诞的世界。那个荒诞的世界没有爱,没有爱的心灵。
问题不是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已经预设了一个上帝的概念,我们的心中早已有了上帝,何须再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沉重的肉身、我们罪恶的心灵对上帝有多渴求——精神彼岸的饥渴。只有爱的温馨才能反抗心灵的黑夜,反抗这个冷漠世界的荒诞。
“希望不可能永远被回避。”(《加缪全集》3,p134)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旧约全书?诗篇 74 :16》,和合译本)
能给我们冰冷心灵以温暖慰藉的是十字架上的基督,不是默尔索。默尔索只会让我们冰冷的心灵更加冰冷,让我们荒诞的世界更加荒诞。默尔索并不是人类和上帝基督,更不是唯一的。
“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不可分开呀。”(《加缪全集》3,p139)荒诞是真的,对荒诞的抒写也是真的。但是走出荒诞才是拯救。荒诞的苦痛在于对爱的剥离。对荒诞的反抗也只有呼唤爱。正因为荒诞,所以要爱。正因为爱在苍凉的人间几乎不可能,所以要呼唤爱。
默尔索只是荒诞存在的一个符号,亲自参与了荒诞。“世界依旧,认识唯一的主人。约束他的,是对彼岸的幻想。”(《加缪全集》3,p136)一个对彼岸没有幻想的人,一个亲自参与了荒诞的人,怎么可能是人类和上帝唯一的基督?
我不相信!
《加缪全集(全四册)》读后感(五):在鼠疫的境遇里
在鼠疫的境遇里
鼠疫是人类一种灾难性的非常境遇,而加缪的《鼠疫》则是一个象征。
老鼠的大量死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看门人的死却使奥兰城的人们从震惊转为恐慌,使人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很快就将消失的噩梦,虽然有些恐慌和不知所措,但他们依然做自己的买卖、出门旅行和发表自己的议论见解,谁也没有想到,鼠疫会使他们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甚至生命终结。
在里厄医生被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下,省长召集会议讨论,却没有宣布是否究竟是鼠疫。当疫情迅速恶化,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的时候,当局才决定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并采取封城措施。省城奥兰与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
封城使人们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陷入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也不能通信的绝境。政府的禁令使任何特殊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列。
鼠疫导致了封城,封城造成了隔绝,隔绝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囚禁和流放之感。人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加缪写道,“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
精神、情感、心理的痛苦之外,当然还有鼠疫直接造成的人的身体的痛苦和生命的死亡。除了看门人外,加缪详细描述了三个人的痛苦死亡: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神父帕纳卢和与里厄医生一起并肩战斗的“外乡人”塔鲁。这其中,尤以对奥东先生的孩子死亡过程的惊心动魄的描述最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加缪并不仅仅在于描述鼠疫下的生存状态,而重要的是表现这种灾难性的境遇中,人们不同态度和命运。鼠疫是实验室,他要通过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及其人们不同的态度、选择和命运,来表现他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见解,来传达一种更为本质的信息。
里厄医生是《鼠疫》中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哲学理念的载体。他是奥兰城中的西西弗斯,是加缪反抗理念的诠释者。
书中另外的人物同样也是意外深长的。为求得内心宁静而到奥兰城定居的让•塔鲁,在鼠疫降临时,领头组织起了一支卫生防疫队伍,却在瘟疫败退、城门大开的前几天感染了鼠疫。尽管他与病魔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尽管里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塔鲁仍然在最终战胜鼠疫的黎明到来时,在寂静的寒夜里,离开了人间。死亡给了塔鲁安宁,但通过死亡带来的安宁对他却已毫无用处。
50多岁的格朗是一个瘦长驼背的市府小职员,准确地说是一个在市府默默无闻工作了几十年的临时小职员。妻子撇下他随他人而去,微薄的薪水维持着他拮据难堪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却积极参加到塔鲁的抗疫组织中。就是这个格朗,在他的生活中,有着一件神圣的事,那就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写一本关于“女骑士”的书或类似的东西,尽管只是开了个头,但无数次反复斟词酌句使他耗费了全部精力,使他不胜其苦,但他仍乐此不疲。现在,他却从“神圣不可侵犯”的晚上时间中贡献出两个小时来,不再去想的“女骑士”,而专心致志地做着抗疫组织中他应做的事情。
尽管如此,鼠疫仍没有放过这位无足轻重、简朴奉公的善良老公务员。圣诞节的前夜,里厄医生和塔鲁在大街的橱窗那儿找到了他。他泪流满面地贴在橱窗的玻璃上,瘦小的让娜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仿佛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里厄医生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当病情恶化的时候,格朗把那份神圣的手稿给了里厄医生。这份50多页的手稿上,都是写着同样一句话,只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词一再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的句子。对这充满着格朗一生心血的手稿,这位自觉不久于人世的老公务员,突然严厉而痛苦地要求里厄医生烧掉它。
然而奇迹出现了,可怜的格朗与死神擦肩而过,起死回生。
除塔鲁外的另一个异乡人是朗贝尔。据说,新闻记者朗贝尔这一人物与加缪本人相关。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时有过与朗贝尔相同的经历。《鼠疫》中隔离后人们的流放感恐怕是加缪的一种真实体验。当封城的禁令下达后,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爱情,他想尽办法以离开这座被封闭的城市。开始,他力图通过官方渠道离开奥兰。在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他转向那些走私分子,企图通过地下通道逃出城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出城的途径。就在他即将出城之时,他找到里厄医生,要求留下来为卫生防疫组织做事。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在朗贝尔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个人的幸福更重要。如果要谈到公众利益,那必须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然而在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下,纯粹的个人幸福是否还有其在正常状况下的那种合理性?里厄医生表示,朗贝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自己的爱,他可以选择离开奥兰。可是,当鼠疫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时候,他不能为朗贝尔的离开提供合理性的证明。而朗贝尔则指责里厄医生根本不为他这个与情人分离的人着想。后来塔鲁告诉朗贝尔,医生的妻子因病住在离奥兰几百公里的疗养院,与他的情况完全一样时,朗贝尔表示了极大的惊异。
这种惊异或许是朗贝尔最终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同战斗的重要原因。他后来对医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象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鼠疫这境遇下,要生存就必须抗争。任何主义、观念都必须服从鼠疫下的这一生存规律,不论作为合理个人主义的朗贝尔还是宗教的代表帕纳卢神父,在这种非常状态下,都必须改变既有的观念、态度、行为,做出新的选择。帕纳卢神父的前后两次布道,观念态度就大有差异。第一次布道,神父指出鼠疫是上帝对人们罪恶的处罚,得救之道是人们必须向上帝发出虔诚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但在第二次布道时,他就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对此,塔鲁评价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里厄医生则说,比较神父的布道来说,他更喜欢神父本人。
当信仰和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神父陷入了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中。但他仍然参加了第一线的抢救工作,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直到有一天他作为鼠疫疑似病人被送进医院治疗。第二天早上,神父便去世了。但病历卡上并未截明是鼠疫,而是“病情可疑”。
加缪对神父之死的原因语焉不详,因为里厄医生在对神父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鼠疫的主要症状,而且据女房东所述看来,神父生病的情况似乎很有些令人疑惑。我猜测,神父因无法再继续承受内心的矛盾痛苦而选择了某种方式的自杀。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所表达出来的明确的社会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意识,使它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其突出的地位。不过,从艺术的角度看,我想并非所有人都会对《鼠疫》给予最高评价。就我个人来说,初读《鼠疫》时,我也更多地认为《鼠疫》是载道之文,对其艺术性并未有何深刻的体认。然而再次阅读后,发现它确实不乏高度的艺术性,尤其是它对一些场景、状态和过程以及对人物的天才的状写和刻画上。我以为,对格朗这一人物的刻画和对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之死的描绘,具有经典意义,足以显示加缪天才的艺术创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