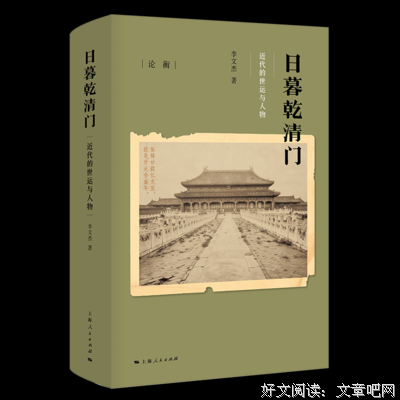
《日暮乾清门》是一本由李文杰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一):老大帝国陨落史
列强称呼大清,一称作老大帝国,再称还是老大帝国。这个老大帝国,在最后关头是怎样陨落的呢?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视角。
后人读中国近代史,总觉得在位者的昏招、损招一出接一出。如皇族内阁的设立、撤回留美幼童等,为何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后人带着“上帝视角”,知道事件的走向,从后果来返观过程,挑出那些将要导向历史进程改变的线索进行反复的仔细的检视。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就有超越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后人在套用线性的、简单的因果链条批判过往的时候,往往伴随着重要细节被有意或无意地修剪、遮蔽,因此并未掌握相对完整的真相;或者后人的思路脱离当时的语境,使得历史看起来像散落满地、一连串不可理喻的事件的集合。本书让你去掉“上帝视角”,回看近代史上影响中国的人物与事件。一件件细节、一件件轶事,换位思考,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读罢,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二):扎实的通俗之作
来新疆的途中及隔离期间读完李文杰的《日落乾清门》,特别好,说话实在,材料扎实,关怀宏大。从豆瓣上知道,是茅海建的高足,深感名师出高徒啊,陈旭麓教出几个好学生,然后徒子徒孙开花散叶,厉害得很啊!这学期阅读主要围绕晚清史,发现好书不少,但也是泥沙俱下。现在的学术体制,学者们功利心太重,能沉下心来写一点扎实的通识著作的,太罕见了。通识著作其实不好写,很容易写成鸡肋,语言要清通,理据要清晰,视野要开阔,比起学术专著,更有其难上加难的特点。李文杰的书,语言来说平实可爱,没有戏说体的戏谑庸俗,又重视理据,文章不空洞,说的都是小事,小中见大。这样的风格颇有乃师之风。想起读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当时颇觉惊艳,没想到这样的大学者也能写出这样生动清通的文字,读起来又是扎实可靠的感觉。最近读邱涛的书,也是有名气的学者,与李文杰一样,本科都是北大毕业的,可是书读起来总让人觉得不能信服。人是聪明人,很多分析解读,很有穿透力,不过,语言论证空疏的可以,去研究政治学也许是个材料,研究历史未免太不入流了。还是喜欢扎扎实实的书,就算艰涩一点,但是俗话说的好,贴骨的肉才香!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三):#搬运工#自序
人过三十五,在我的老师们看来,还是一个学历史的“小年轻”,勉强算是进入了历史学人的“黄铜时代”吧!我却开始有两个明显的感觉,第一是特别喜欢回放和总结过去。近期读过一部小说,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说远古时期人的寿命都不长,三十岁大概就是老年了,老年自然爱回忆,这习惯刻进了人类的基因延续至今;第二个与此相关,在回放和总结完过去之后,特别喜欢追问“意义”两个字,这意义是要从内心过得去的,而不是仰赖财富数量或者他人点头的东西:每天忙忙碌碌,眼瞎背驼面容老,做的事到底值不值?
实拍图既然谈到意义,就和每天做的事情脱不开干系了。我们这个学科的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跟文献打交道,在故纸堆中挣扎,对史料经过一番淘沥和加工,最后用论文的方式将所思所想展现出来,短则数千字,长则两三万;如果兴之所至、讲得痛快了,四五万字也未必刹得住。尴尬的是,我们花费数年功夫来生产,敝帚自珍、引以为宝的论文未必都能被业内接受(学术期刊);即便能顺利发表,阅读量也通常不会超过两位数,且数年之后,大概率就不再见光了(为了应付定期考核的急就章就更堪忧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曲高和寡”的道理来安慰自己,或者用“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大志向来自期(欺),记得在十多年前我这话还没说完,导师就斩钉截铁地正告我:“你写的东西今人都不爱看,后人还会看吗?”他说的果然没错,十多年前调置震动、放在一边待机七天的“老头机”诺基亚,早已被须臾不可离身的智能手机所取代,大学生用来读书的时间,也早已被两微知豆和B站彻底吞噬,当初想翻而没有翻开的书,今天就更不可能去翻了。以此类推,今天让人无法卒读的书,岂能指望后人来读?就算人家有心,也未必有力,毕竟太多的“今典”(就是大学生所说的“梗”)都是与当下息息相关。时过境迁,别人自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未必能懂,也未必想懂了。
当然,论文的价值并不能等同于眼下的下载量和阅读量,这就如同学问高低不能化为买书多少一样,但如果关于人和社会的学问,能拿出来与更多人一同分享,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记得当年在学位论文开题会上,我侃侃而谈,但又自觉不得要领,对面的几位老师貌似听得木然,如果不是碍于面子,我猜他们都有出去散心的冲动。下场之后,导师召集我们几个学生直截了当地问:“刚刚他讲的你们听懂了吗?”大家表情尴尬,不知做何回应,他却直说他没听懂,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替我讲了五分钟。这一次,我坐在听众的位置上,觉得他讲的不但凸显了我题目的意义,也讲明了研究的特点,还能让人满怀期待。这个面红耳赤的经历让我明白:对方没听懂,很可能是说话人没想明白,而不是表达高明;第二,在进行学术的表达之前,先对着自己讲两遍,站在听众的角度,假设只是一个略知题目大概的人,问问自己能不能听懂。后来在师范大学当了老师,我就更注意这一点。事实证明,越是想着听众,越是讲究表达,学生的参与和反应就会越热烈;反之,相同的内容只会让他们昏昏欲睡。
这本小书就是一个尝试,希望自己的思考不仅是一批程式完整、论述冗长、更多是照顾自己发挥的学术论文(它们放在期刊网上供人下载,偶尔被人征引,就足以让自己鼓舞万分),而是一些可以呈现给更多人读的短文章。其中的内容跨度约为百年,包括清末民初的制度、人物与世运,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章的底本是发表过的长篇论文,一方面可以说这些论文材料齐全、论述完整,另一方面未尝不是“面目可憎”:个别对该问题有兴趣的同行或许会下载征引,更多人则不会有阅读的途径或兴趣。不过,其中或有新材料、或有新发现,可能会对普通读者有所启发,我不忍看着它们湮没不闻,就试着略去冗长的论证,用课堂上平实的口吻将它们讲述出来,期待更多的人阅读(因为在师范大学的原因,我尤其希望这些内容能对中小学历史教师有所帮助)。第二类是以前在《文汇学人》《上海书评》等媒介发表过的通俗文字,感谢两处朋友们策划与我研究内容相近的主题,并鼓励我将它们写出来。还有一类是教学研究之余的杂感,是受到学生问题的启发,在试着回答的过程中进行的一些发掘。
让更多人看懂甚至爱看,绝不意味着牺牲质量、抛弃深度去迎合市场。选入本书的文字希望把握住两个原则:第一,能出一点“小新”,或有新材料,或有新想法;第二,通俗但又不失依据。除了个别文章之外,其他已发表的文章在收入时,都经过了大改。对于这种用简洁和通俗语言呈现学术论文的形式,希望翻过我学术论文的读者不要以“洗稿”目之。
彩插这本书取名“日暮乾清门”,是因为首篇所讲的御门听政是在乾清门外,书中提到的君主召见大臣(包括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乾清宫、养心殿,作为君主秘书机构和政务运转中心的军机处,都在乾清门半径一百五十米之内。参加“早朝”——御门听政的官员们所见证的,本应是日出东方的乾清门,只是这个朝会在1860年之后便宣告终结,不再举行。我们今天看到的1901年乾清门外小广场的照片,随处可见砖缝中一簇簇的荒草,地砖和台阶也久未打理,在暮色之下生出无穷的苍凉,让人感慨那个王朝远去的盛世。我们所处的时代,除去一些“年抛型”或者寿命更短的议题(或者叫“梗”),其实还有很多古今中西相通的问题要面对。本书中尝试去讲的国家事务的讨论方式、在上者对信息的获取、传统财政的困局、专业化外交思考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被家事影响的国事、人事纠纷引发政治恶果……诸如此类,大概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东方的事情。网络时代真是个资讯层出不穷且良莠不齐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剧情反转”,这更增强了我的一个信念:资讯不完整,则判断无意义;判断不依专业,则结论无价值。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资讯就是史料;史料搜集与解读不到位,好的想法或许就只是一个想法。在写作和修改本书期间,正值疫情持续燃烧,让我这个“纯文科生”深感无力,从头到尾似乎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只能加倍努力去做专业上的事。这本产生于疫情期间的小书,如能让非专业的读者增长见识我就很满足,如果能促成大家的一些思考,就更是我的荣幸了。感谢责编邵冲的督催,促成本书能及时完成。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了“论衡”系列,让我有机会去大胆尝试通俗写作,面对更多的读者,接受更多的批评。在书价动辄砍半、批量购买学术书的时代,人们更认的是作者品牌,热心地给未成名的年轻人(“论衡”系列中的其他长辈和同辈学人的作品除外)出书,成本已经付出,风险和销量却是未知的,用傅斯年的说法,这是一个“不生利”或至少不那么生利的事情。可是,理想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些不生利的心思养成的。
李文杰
庚子年初夏序于东川路
《日暮乾清门》读后感(四):“大清的希望”——留美幼童为何突然被撤回?
作者:李文杰1871年,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经商讨后向政府建议,从次年开始,分四次派幼童赴美国学习,期限十五年。希望这些未染习气的孩子在学成之后,帮助国家自强。这个大胆的储材方案,出自容闳的策划。容闳,原籍广东香山,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认为,学习西方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回国之后,他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并成功地付诸实施。曾国藩的幕僚、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与容闳一道,被任命为“出洋肄业委员”,陈为正、容为副,他们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市(Hartford)创设了“出洋肄业局”,办理幼童留美事宜。
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熟读儒家经典,逐级参加科考,通过成绩获得做官资格,这种路径才是多数读书人的追求,一如陈兰彬过去所经历的一样。相反,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跋涉,远渡重洋,去一个言语不通、风俗迥异的陌生国度,学习一些还不知道有何用途的知识,这些都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因此,前来应募的家庭并不多,北方人尤其少见。出洋学习的幼童,大半来自广东,且以香山人为主。
谁都没想到,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成材率惊人地高。他们中间走出了大量的工程师、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事人才,包括民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梁敦彦,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人。
容闳在说谎
1875年,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国公使,这是当时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代表,全称是“钦命/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这个职位旨在保护北美和拉美的华工。容闳也跟着被任命为“出使副大臣”,与陈兰彬同在华盛顿办理交涉。两位公使无法兼顾康涅狄格的留学生,出洋肄业局先后交给工部候补主事区谔良、驻美参赞容增祥、吴嘉善管理。
1880年,一位名叫李士彬的御史参劾出洋肄业局,说那里局务废弛,在美国学习的幼童们“习为游戏”、“流为异教”,不好好学习,还信了异国的宗教。第二年,在多次函商陈兰彬及李鸿章以后,总理衙门奏请裁撤出洋肄业局,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幼童们全都撤了回来。因为远隔重洋,当事人的记录有限,我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成为我们了解留美幼童的主要史料。他在书中强烈地指责吴嘉善,说吴的保守态度以及喋喋不休地向国内告状,让这个伟大的留学计划夭折。这也是我们对这段公案的一般认知。
然而,沉睡在政府档案里的文书,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幼童在赴美之后,寄居在美国家庭。他们与美国人一同生活,穿同样的衣服,一起学习、一起礼拜、玩游戏、做运动,行为举止美国化。根据容闳的叙述,这让陈兰彬非常反感。陈是翰林出身,当时已经担任公使,厌恶和鄙视留学事业,想方设法地加以破坏。他故意推荐吴嘉善担任监督,自己则退居幕后指使。而吴果然对留学生吹毛求疵,各种不满,故意将消息传回北京,进而被御史利用,最终酿成祸端。
对于容闳描述的事情,陈兰彬又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这样解释:
兰彬出使随员,大氐有人推举,惟子登系毛遂自荐,随使初志似甚坚也。到美后,未经派事,渠驻肄业局五月有余,即谋为总办,曾与副使密商。赴日后,又屡由沈县丞致函密订,彼时绝不令兰彬得知。迨前冬接奉钧函,局亟需人,并悉副使称誉极洽,因即奏换驻日参赞,便其遄行。在日都就道欣然,方谓督课或其所长,该局有赖。去夏旋美趋晤,则见其日弄机器化药,于各童神情隔膜,局事亦不肯谈,亦但疑其别有同心,不愿旁人参预耳。
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人,1852中恩科进士并入翰林院学习,后担任翰林院编修,曾在广州同文馆教习汉文。从履历上看,他与1853年中进士的陈兰彬,有过一段在翰林院共事的经历。作为陈兰彬的使团成员,他还出任过驻西班牙参赞。
根据陈兰彬的说法,吴嘉善是“毛遂自荐”跟他来美国的,并且意志十分坚定。来美国之后,他先被派到出洋肄业局做事,结果他想方设法谋总办之职。为了当上主管,还专门跟容闳密商。后来,吴嘉善被派到西班牙,他托身边的文案瞒着陈兰彬,屡次给容闳写密信。当肄业局缺人的时候,陈兰彬收到了李鸿章的指示,说容闳极力夸奖吴嘉善,应该让吴离开西班牙的职位,去美国管理出洋肄业局。从喜欢摆弄“机器化药”的细节可以看出,吴嘉善并不仇视西洋学问,只是对留学生的事情不太上心。
关于吴嘉善任职一事,陈兰彬的陈词和容闳的叙述完全不同。容闳说,陈兰彬推荐吴嘉善担任总办,暗中操纵他破坏留学事业;而陈兰彬则说,吴是自荐进入使团,至于他担任肄业局总办,则是容闳推荐的。
两相对照,陈的说法大概牢靠一些,因为陈兰彬给李鸿章的信中,复述李此前说过的话:容闳极力表扬吴嘉善。这等于当面跟李鸿章对质,自然不可能说谎。陈兰彬还对李鸿章说:“本年回美,力劝子登(吴嘉善)以整顿,虽子登系纯甫(容闳)所推荐,交谊比别人较好”,等于再次跟李确认,吴嘉善管理肄业局,是容闳举荐。陈、容二人谁在撒谎,一目了然。
既然容闳所说的陈吴关系并非实情,他所说的吴嘉善解散肄业局、遣回留学生的指控是否完全属实呢?
1881年初,吴嘉善曾给在华盛顿的陈兰彬发过一个咨文,咨文说:
兹体查现在情形,全撤终不如渐次抽撤之尤为善行无迹。现拟抽调愚鲁懒惰及花费不知节用者二三十名,先由敝编修管带回华,面陈事宜,亲承指示,或再奉派来局,或另委有贤员,以善其后。缘此,拟将现存经费并一切局务迫行移交贵大臣暂为收管,兼督饬各学生书馆功课支应,以免松懈。
李鸿章将撤销肄业局、撤回幼童的事情交给陈兰彬、吴嘉善商办,他二人一直没商量妥当。吴嘉善在审时度势之后,认为逐次撤回比一次全撤更合适。他想先把那些生性懒惰、学习不好,或者乱花钱的孩子带回去,再商量后续该怎么办。
陈兰彬收到这个咨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不是说要撤局吗,怎么又不撤了?撤回二三十人,剩下上百号人的吃、喝、用度、学业怎么办?他赶紧写信给总理衙门:吴嘉善屡次陈请要裁撤肄业局、撤回留美幼童,李鸿章为此专门写信给我;现在我让吴拟定具体方案,他却玩弄花样,撤局不撤人,想把学生交给我来管理。我屡次逼问他为何前后不一,他吐露说,是因为容闳不愿意撤。
由此可见,吴嘉善确实破坏留学事业,但他跟容闳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是容闳推荐了他,他也听从容闳的建议,软化了原来的立场。
不过,陈兰彬可没打算接手。他收到吴嘉善咨文,马上反驳说,接到贵编修的咨文,“阅之骇异”!上年既然屡次陈请北洋大臣要撤销出洋肄业局,不管是全撤还是半撤,都是贵编修的事,应该自行办理。想抽带二三十人先行回去,本来我也不应该多说什么,只是,肄业局的经费以及所有的局务,请您高抬贵手,“曲加体量,切勿移来”!明确告诉他:你吴嘉善想怎么折腾都行,但请不要坑我,让我接手。
陈兰彬的分析
早在吴嘉善的前任做肄业局总办的时候,容闳就坚持,学生入美国学堂,不要学习“中学”(中国学问),导致他们的“中学”抛荒。容闳将幼童留美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在积极地进行干预。李鸿章曾经交代陈兰彬,在合适的时候告知容闳,不要对肄业局管得太多,以便他人进行整顿。陈兰彬因此就明白了国内舆论以及李鸿章的态度,他给李写了一封长信报告原委。
在这封信中,陈兰彬提到,出洋肄业局近年的发展,和他在时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前就任公使之时,他曾到哈特福暂住,发现那里所藏的中国经史之书,早就被束之高阁;针对中国学问的考试,也都不再举办了。当时他就认为,肄业局“诸务废弛,久将不可救药”。这两年,留美幼童渐渐长大,已深染了美国习气,对监督他们学业和生活的总办也不再有忌惮心理。容闳推荐吴嘉善接手加以整顿,怕也难以收拾局面。因此,陈兰彬说,“不撤办理无效,兰彬已咎无可逃;长兹敷衍以终,兰彬益罪无可逭”,总体上,他主张撤局。但他又说,这些事情都要交给吴嘉善这个管局之人来主持,他陈兰彬不便有所行动。
不久,吴嘉善前往华盛顿,跟陈兰彬商量肄业局的事情。吴说,留美学生恐怕难以整饬,他提出了裁撤肄业局的建议。陈马上将之写成奏摺向朝廷报告。然而,吴嘉善返回之后,因容闳的干预,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即上文所述的“渐撤”的新方案,要带部分留学生回国,把剩下的交给使馆。陈兰彬以胆小畏事著称,本就不是有担当的人物,看到国内舆论对留美幼童不满已久,自然不想去接烫手的山芋。
另一方面,陈兰彬又不愿公开表态支持撤局,以免得罪容闳。他再次写信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强调撤局的建议是吴嘉善发起的,现在又出尔反尔。他要求李鸿章迅速阻止吴嘉善起程,命令吴把局务料理完结再走,千万不要把学生扔给使馆。
这时,陈兰彬已经改变了此前向李鸿章表露的撤局态度。撤与不撤、全撤或者半撤,他都无所谓。他极力撇清自己与肄业局的关系:既然主张撤局的是吴,主张半撤的也是吴,不管后事如何,希望此事不要再找上自己。
作为驻美公使、出洋肄业局的首任监督,陈兰彬为何如此消极,唯恐惹上麻烦?
原来,他怀疑吴嘉善不想得罪容闳,故意把火往他身上引。他还怀疑吴嘉善有意执行未经南北洋大臣核准的半撤方案,回国后好构陷他的“专擅之罪”。为了给曾国藩的继承者、留美事业的发起人李鸿章一个明确交代,陈兰彬在事后讲述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故事。
陈兰彬听有人说,吴嘉善从一开始就有意与他为难。吴明知副使容闳改服西装,娶了外国老婆,养有儿子,不愿意撤局回国,故意提出撤局的建议,并让李鸿章责成陈兰彬完成,这样,吴嘉善可静观陈容二人鹬蚌相争。后来,陈兰彬及时出示李鸿章的天津来信,容闳因此得知撤局的建议出自吴嘉善而非陈兰彬;吴担心彻底得罪容闳,所以改全撤为半撤,如果陈兰彬答应了,就一定会被吴利用,与二人纠缠不清。
好好的留学事业,先被御史攻击为忘本,后又被陈兰彬脑补为阴谋和权斗。连清政府的驻美代表都无心经营,避之唯恐不及,留学事业也就难以维持了。1881年夏,总理衙门上奏,概行停止留美肄业计划,撤回全部的留学生。
其实,在同一时期,清政府还派出了学生赴英法留学,学习西方科技。驻英公使曾纪泽说,这个留学事业其实“无大益处”。尽管如此,负面评价并没有让留英学生中止学业。如果陈、容、吴的关系没有那么僵,或者陈兰彬有一些担当,脑子里少一些“阴谋论”,留美事业也不至于半途而废。
正如李鸿章所说:“荔秋(陈兰彬)与莼甫(容闳)抵牾已久,且其素性拘谨畏事,恐管理幼童与莼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故坚持全裁之议。”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有理念之争,但更重要的还是权力纠纷所致。
本文选自《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李文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