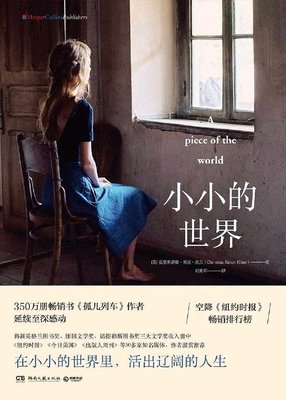
《Chronicles》是一本由Bob Dylan著作,Simon & Schuster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16.00,页数:3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Chronicles》精选点评:
●不同时间点的人生传记…时刻感受到他对folkmusic的深深热爱以及创造力
●清华图书馆有赠书,不知道是谁赠的
●补:BD很酷 把自己的起点写在了最后一章 回头看就很清楚他看到世界的眼光是在何种环境里成长起来 最后他写到菲茨杰拉德 与他同一故乡同一个起点的人 冥冥中似乎看到他们目光的重叠之处。bd也是那种很相信自我经验,不会轻易为环境影响的人,但如他所说“有时屈服一些个人趣味”。我喜欢他 也喜欢patti ,世界仿佛在我窗外带着呼吸声脉动 ,我很期待走入它。
●作为脑残粉怎样都得给五星……而且确实老爷子自己写的读起来感觉就是跟别人写他的传记不一样
●紧锁眉头冒青烟抓耳挠腮,卒。
●really not a good writer...
●It was a strange world ahead that would unfold...One thing for sure, not only was it not run by God, but it wasn’t run by the devil either.
●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读
●迪伦很会捧人
●花了好多年才读完了这本书。2011年买来时,还找不到中文版,也没想到老爷子会拿诺奖。虽然叫Volume One,但这本书写得太完整了,愿老爷子健康长寿,永远年轻。
《Chronicles》读后感(一):写得很真实,文笔流畅
作者身为音乐界活化石,年轻时摆够了架子,老了,写自传,还好没怎么摆架子。 国内有些人崇拜迪伦,把他过度神话了。他是牛逼,但他也是凡人,像凡夫俗子一样,懂得包装自己,懂得人情世故,而且,比普通人更懂。 这些他在这本书里写得很真切。
《Chronicles》读后感(二):完美的Bob Dylan
就如当年读《一个导演的自白》一样,我不得不对那些文学家们说一句Fuck,你们太不懂文字的魅力了。
就像我从来不相信所谓“偏才”之说,在一项一目里自慰有什么狗屁意义?读完这本书就知道,那些妄图把崔健高大到与Bob Dylan的人是多么的可笑无知!当然,比起那些大声质疑为什么要让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来说,他们还是稍微可爱一点儿了。
所以,那些以为音乐就是旋律的人,死了没啥好可惜的。
《Chronicles》读后感(三):像小孩在窗边凝视下雨
我非常痴迷世间万物联系起来的方式。我对Bob Dylan的好感除了那几首耳熟能详的歌,听了就不会忘记的独特嗓音,几乎全都来自Cate Blanchett演过他。多年后,我在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里,过着隔离的独居生活,偶然看到Cate在扣扣熊的zoom访谈里被问起了Bob Dylan,她说我无法说清楚我为什么喜欢那句you kind of wasted my precious time, it’s alright 那种漫不经心…于是我又开始听他的歌,翻开了这本读了一半的书。
他不久前接受了nytimes的采访,被问到即兴演奏,他说他从不即兴。有人评论说他真的太狡猾了!我们都知道正是他那些不可预料的即兴发明让我们着迷!而我碰巧读到他大段落讲他发现的一种演奏方法,通过音阶让旋律重组,近乎是数学上的严格,让他心潮澎湃,那是和即兴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创作。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乐理上的例子,让我感到了解一个人、从而又了解万事万物是多么难啊。可是人们又是多么轻易跳过万事万物去定义和评价一个人。我想他也许狡猾在他明明都把他怎么写歌怎么来的灵感怎么唱怎么找到听众怎么看待那些作品巨细无遗地袒露给你了,但却不多说他怎么和孩子相处、怎么爱一个姑娘。从只言片语瞥见他的个人生活,和儿媳的一句对话,吃的东西,他的一见钟情,都会让我感到很新奇。我跟着他听了很多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的歌,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旧时光的气氛,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想到他在最近的采访记者问他你会不会担心2020年人类已经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时代,他说虽然这个电子和高科技时代会比过去带来更多焦虑和紧张,但也只是让我们这些人,我们身上总有活在过去的倾向,而年轻人没有过去,他们就是出生在这里,他们知道的就是他们所见所闻的,他们是未来。我们最好能快速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的世界是被淘汰的。连我这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也被他的与时俱进和一点也不愤世嫉俗感染了。
这本书是流水账式想哪写哪,主要是创作上碎片化的心绪和际遇,不算是完整的自传,但着实相当坦诚。有些时间很遥远感知上却觉得很相近,有些情景缺少上下文却跃然纸上。而我再听他刚刚讲的话、从他到今天为止仍在更新的创作里,看到他身上的的一致性,一种纪律,一种让人感动的生命内核(我翻出两年前演唱会上我拍下的视频反复看了好多遍,77岁仍中气十足,听到Cate喜欢的那一首的“即兴”版本,太好听了)
他诚然是始终在学习,在不断变化(他的变化曾被指责你背叛了我们的时代精神 - 而他无意代表任何时代)他模仿他崇拜的歌手,他在他们面前曾感到大惊失色,他把他们的歌词抄下来分析,他想知道、也知道是什么在吸引他、他知道如何判断人和事情、如何不妄下判断。他又有很精准的洞察力、让他一眼就抓住那些生活中对他而言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为什么他总是能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也许他没有时间看别的)他不轻易就融入什么、也不轻易动摇。他有他心中的准则,他坚定不移地走过去。把任何虚假、虚荣的东西隔绝在自身之外,他的存在就是反媚俗的。你可能觉得他特立独行,难相处,他只是在走他的路。诚恳得简直老实,纯粹得几近忧郁。就是这样,而我看来他超越了他的偶像,他成为也始终都是他自己。我认为艺术和人格应当是一致的,我始终相信。
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里面写道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
“因为口琴比史蒂维·旺德吹得差?”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凝视下雨似的。”
我觉得他的声音比这个形容潇洒和从容(还有一点痞)。而他这个人,比起像一块滚石,的确给我一种小孩站在窗前凝视下雨的感觉。
最后一页他如数家珍地罗列了Minnesota他的家乡里走出来的艺术家,他也感到自己通过某种方式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而你很难不想到Minnesota刚刚发生的佛洛依德事件是如何震动了整个世界。有时候你不知道世界究竟向前走了还是只是换个方式栖息在另一个时空里。望着窗外川流不息,听着他的新歌,很荣幸(近乎是一种虚荣的)和他共存在同一个世界里。最迷人的也许是,我说了这么多,几乎仍对他一无所知。
《Chronicles》读后感(四):常青的音乐诗人鲍勃·迪伦
6月19日,鲍勃·迪伦发行了最新的创作专辑《崎岖吵闹的道路 (Rough and Rowdy Ways)》,当一位七十九岁的老头依旧在试图超越七十一岁的自己(按)时,放眼音乐史,能出其右者寥寥无几。(按:他的上一张创作专辑是发行于2012年的《暴风雨(Tempest)》)。
关于《崎岖吵闹的道路》的专辑反响在欧美几乎呈现出一面倒的好评:具有国家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评论道:“79岁的他有目光长远的资格。他的新歌翻过一页页历史、传记、神学、奇谈、神话和凶险……在《崎岖吵闹的道路》上,他拒绝安定下来,或像个元老一样。他看到死亡隐隐逼近,但他仍然不曾怯场。”老牌音乐杂志《滚石 (Rolling Stone)》称他从未原地停留——“当这个世界试图歌颂他为楷模,对他盖棺定论,铸进诺贝尔标准,把他的过去封存防腐,这位浪子总是试着再度逃离(按)。在《崎岖吵闹的道路》专辑,迪伦探索到了无人抵达的土地,然而他未来还将继续前进。”(按:《浪子的逃离(Drifter’s Escape)》是他1967年的歌曲,发行于《约翰卫斯理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专辑。)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该专辑亦受到了极高的赞誉。《卫报 (The Guardian)》给予了它满分好评:“……词曲创作全然统一,没有匆忙完成的充数歌曲,全部击中要害……《崎岖吵闹的道路》里的歌可能是迪伦数十年来,从头到尾最出色的:死忠粉可以花上数月去解那复杂的歌词,但你无需成为迪伦学博士即可欣赏它独有的品质与力量。”
借聆听这张专辑之际,也借这本迪伦的自传为线索,不妨由梳理迪伦艺术生涯中关键性的十张专辑而起,来窥探一下这位常青的艺术家一路走来艺术风格的缘起与变化。
鲍勃·迪伦1941年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 (Duluth),很小就迁居铁矿小镇希宾 (Hibbing) 。他的祖上从俄国迁移而来,是典型的犹太人家庭,中学时便和同学组过摇滚乐队。迪伦于1959年前往州府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接触到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 (Woody Guthrie) 关怀土地、人民的音乐,深受启蒙。1960年,大学生迪伦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前往纽约,和父母“签订对赌协议”——混不出名堂就回州里继续念大学。彼时的美国,一直扮演脱离主流音乐的角色,弘扬“以歌载道”理念的民歌复兴运动,并悄悄迎接着商业化的前夜,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正是运动的前沿。1961年,他在此像江湖卖艺人一样卖唱为生。他模仿偶像伍迪·格斯里 (Woody Guthrie),并试图挤入头牌的煤气灯 (Gaslight) 俱乐部进行演出。他认识了一批引他入门的民歌前辈、同好者,在他们那蹭屋住,蹭书看,如饥似渴地交流。不久,《纽约时报》的编辑罗伯特·谢尔顿 (Robert Shelton)撰文将其曝光后,哥伦比亚唱片的星探约翰·哈蒙德 (John Hammond)将迪伦纳入麾下。从此迪伦一举搭上民谣商业化洪流的快船,越开越远。
1.民谣三部曲之一:《放任自由的鲍勃·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1963)
踏上了世纪祥云的迪伦,于1962年发行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 (Bob Dylan)》,其中多数为传统民歌的翻唱,仅两首为原创作品。此时,他渐渐将模仿伍迪·格斯里的痕迹擦去(同名专辑里为数不多的原创尝试《给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可视为对他老师的告别),而老师伍迪·格斯心系时事的民谣精神却被提炼而出,持续陪伴。同时,他开始受到法国的兰波 (Arthur Rimbaud)、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Jack Kerouac)、艾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布鲁斯先驱罗伯特·约翰逊 (Robert Johnson)的剧烈影响,个人创作渐渐成为他艺术道路的主轴。这些在他的第二张专辑《放任自由的鲍勃迪伦》中有完整的体现——歌曲《战争之主 (Master of War)》里对战争机器的拷问咒骂、《大雨将至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里启示录般的末日炼狱,无一不呼应着彼时到达顶点的美苏冷战与核恐惧对普通百姓的支配,而困惑于战争、自由、平等问题的《答案在风中飘 (Blowin’ in the Wind)》则成了人人传唱的知名作品。
2.民谣三部曲之二:《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1964)
专辑《时代正在改变》延续了前作“时事”、“抗议”的主题。要说它最大的区别,莫过于将抗议具体化,在《海蒂·卡罗尔的孤独死亡(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 )》和《只是他们游戏的棋子 (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两曲中分别刻画了打死黑人女侍的白人顾客威廉·赞辛格 (William Zanzinger) 和枪杀黑人民权领袖梅德加·埃弗斯 (Medgar Evers) 的白人。二曲直接指名道姓,有着强烈的抗议目的。歌曲《上帝在我们这边 (With God on Our Side)》回顾了两百年来的美国史,批判了巧言令色的美国政府以上帝之名,屠杀无辜,只为了自己的政治企图。而专辑同名曲《时代正在改变》直斥老年政客、家长,把他们比作洪水猛兽,但仍然挡不了年轻人的路。时事歌曲成为这两张专辑的主轴,辅以少量非常规的,带有诀别情绪却强装无所谓的抒情歌,例如前作中的《别再想了,好吧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和这张里的《太多早晨 (One Too Many Mornings)》。
3.民谣三部曲之三:《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1964)
从这张专辑开始,迪伦逐渐淡出政治意味浓厚的民歌运动。虽然以爱尔兰古调入曲的 《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振聋发聩,《我会自由10号 (I Shall Be Free No.10)》中格斯里式回归的说唱依然紧扣民歌,但他在《我所想做的 (All I Really Want to Do)》、《那不是我,宝贝 (It Ain’t Me, Babe)》、《我不相信你 (I Don’t Believe You)》等情歌中,显然开始用比前两作更多的篇幅处理两性的议题。相比参加振臂一呼、口号煽动的运动场合,他更想静下来好好审视个人的状态。歌曲《我的底页 (My Back Pages)》里那“昔日我曾苍老,如今风华正茂”的言语,可视作他对自己一种蜕变的召唤。同期的《手鼓先生 (Mr. Tambourine Man)》还未发表,但凡是在现场听他演奏过的人,都可以从那梦境般的呓语中窥见,民歌现有的框架再也无法满足他的野心。而此时恰逢以披头士(The Beatles)为首的英伦乐队潮流席卷全美,民歌革命的日子到来了。
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传记书《鲍勃·迪伦:诗人之歌》对迪伦总结道:“短短四年时间——从1960年年初到1963年年底——他就完成了发现民谣、掌握民谣到超越民谣的历程,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民谣这种音乐形式的认识。”然而,他的公众形象比他前进的思维滞后得多。迪伦作为民谣歌手的声望在此时达到顶峰,受到年轻人争相崇拜,无数愤世嫉俗之人视其为时代良心,也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伏笔。
1965到66这两年鲍勃迪伦发行了艺术生涯为后世评价最高的三连作:《全部带回家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重访61号公路 (Highway 61 Revisited)》和《金发叠金发 (Blonde on Blonde)》,由于他首次在这三张专辑使用摇滚乐的标配:电吉他、电贝斯和架子鼓,在此可称之为“插电三部曲”。
4.插电三部曲之一:《全部带回家》(1965)
专辑一分为二,上半张摇滚阵容,下半张自弹自唱。这一时期他的歌曲开始与意识流连接,产生无数剧情混乱,解读多样的意象。摇滚“绕口令”《地下乡愁蓝调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为迪伦的插电时代拉开了序幕。 歌曲《没事的妈妈,我只是在流血 (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将抗议的格局上升到生命的挣扎。而《玛姬的农场 (Maggie’s Farm)》表面写反抗地主压迫,谁知道是不是也在说疲倦于民歌运动的自己?
总之,当1965年7月24日的纽约新港民谣音乐节,在民谣歌手的布道场,文艺青年的朝圣地,迪伦一向的主场,他率领新组的摇滚乐队电力四射地带来《玛姬的农场》。这一离经叛道之举把在场的民歌前辈和满怀期待的观众吓坏了,随之出现的倒喝彩与嘘声令迪伦始料未及。台下,左翼运动家 、民谣领袖皮特·西格(Pete Seeger)试图用斧子砍断电线的传闻成为了新旧摩擦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如今回溯,糟糕的音响表现或许亦是造成争议的原因。但不可否认,这是迪伦与民谣原教旨信徒正面交锋的开始。
5.插电三部曲之二:《重访61号公路》(1965)
一个月后,《重访61号公路》发行,收录了先前已作为单曲发行的,知名度足以与《答案在风中飘》比肩的名作《像一块滚石 (Like a Rolling Stone)》。时长六分五十秒,主歌洋洋四大段三十六句话,揶揄从前不可一世,现在落魄丧气之辈。这算不上他最长的那批歌曲,但作为单曲,这却是他个人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它刷新了打榜流行曲两三分钟的固有印象,使未来大量体裁多变、思想深邃的调子有机会在商业电台、在排行榜单抛头露面。此外,专辑中,钢琴、电风琴齐颤的《瘦子歌谣 (Ballad of a Thin Man)》讽刺了指手画脚的保守分子,《墓碑布鲁斯 (Tombstone Blues)》电力十足、同名歌曲《重访61号公路》中滑弦呼啸、深沉吟唱的《荒芜街 (Desolation Road)》更是古今虚实的角色乱入,行为各异,颇具末世荒诞色彩。
高强度的巡演计划也在这一阶段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此时,迪伦见缝插针地前往乡村之都纳什维尔(Nashville) 和一批老练的乐手们录下了《金发叠金发》。
6.插电三部曲之三:《金发叠金发》(1966)
专辑中大量歌曲都是现写现录,但在这套十四首七十三分钟的双唱片中,没有一首歌像是来凑数的。曲风同样延续了前作插电布鲁斯与插电民谣交替,但更为游荡、迷离,凸显出他受药物的影响与其睡眠的缺乏 。从标题“金发叠金发”可看出,专辑主题相比前作, 和女人的关系更多元、更复杂,像《就像个女人 (Just Like a Woman)》的诉说诀别,《我想要你 (I Want You)》的一片热诚、《绝对甜蜜的玛丽 (Absolutely Sweet Marie)》的苦苦等待和《豹纹筒状帽 (Leopard-Skin Pill-Box Hat) 》的揶揄拜金等。专辑的三首长篇杰作《乔安娜的幻想 (Visions of Johanna)》、《再次与孟菲斯布鲁斯一块被困莫比尔镇 (Stuck Inside of Mobile with the Memphis Blues Again)》和《低地的哀眼女士 (Sad-Eyed Lady of the Lowland) 》,私人情绪夹杂在意识流的飘絮中,漫天飞舞。
1966年的英国巡演,迪伦插电引发的矛盾愈演愈烈,蔓延至大西洋对岸。这场演出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木吉他弹唱部分还算安分,等到了下半场,摇滚乐队上台,来自观众席时不时的叫骂足以打断演出。5月17日在曼彻斯特现场,台下大叫的一声“犹大”(按),无疑将矛盾推向了高潮 。而这一阶段,由于创作、录音、演出的日程极其拥挤,迪伦大量嗑药以保持专注和兴奋,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损害。而此时命运覆雨翻云手,英国巡演结束后不久,一场死里逃生的摩托车车祸,使他的自我燃烧戛然而止。(按: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因贪图小利而出卖耶稣,这里表达迪伦背叛民谣。称对方为犹大在西方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要说迪伦艺术生涯最为轰轰烈烈的时期,当属这1962至1966年。他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挖掘发行了个人同名专辑,到因摩托车车祸暂时离开公众视线,短短五年,已完全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民谣歌手想方设法从迪伦处偷来他的写作妙方,摇滚乐团绞尽脑汁学迪伦怎么把自己的音乐写深刻,学不了的话,干脆翻唱好了。嬉皮士们从迪伦的意识流歌词取经,发展出万花筒般的迷幻音乐。
7. 《约翰·卫斯理·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
车祸之后,迪伦选择远离秀场,隐匿乡间。他和66年巡演给他伴奏的鹰乐队(The Hawks,此时已改名为“乐队”乐队 (The Band) )待在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乡下别墅的地下室,漫无目的地演奏、排练美国传统民歌,不闻窗外事,因而功力大增。《约翰·卫斯理·哈丁》是他隐居后发表的第一张专辑(1967年年底)。迪伦在编曲上大做减法,叙事则采用“一镜到底”,即不重复歌词,没有主歌副歌(除了收场曲《我会成为你的宝贝 (I’ll be Your Baby Tonight)》)。歌词中充满了侠盗、小丑、法官、信使、圣徒、魔鬼等民间传说、圣经故事中具备的角色,仿佛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穿上了卡夫卡的夹克。引发无数猜测的小品《沿着瞭望塔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也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此时随着嬉皮士运动愈演愈烈,曾以迪伦为精神力量的年轻人们开始寻找消失的迪伦,希求他重回聚光灯下,为时代发声。迪伦早已厌倦此等生活,1969年他一反常态地发行乡村专辑《纳什维尔天际线 (Nashville Skyline)》,毫无隐喻。1970年他干脆拼了一堆不走心的翻唱和实况录音取名《自画像 (Self Portrait)》,意在切割自己的过去。直到1974年的《行星波 (Planet Waves)》,迪伦才又复出舞台,举办了全美大规模巡演。他的创作高峰也于此刻再临。
8.《血色轨迹(Blood on The Tracks )》(1975)
《血色轨迹》毫无争议是他中期最耀眼的专辑。迪伦少了60年代中期那样的意识流拼贴,进一步探索了线性叙事的可能性,糅杂了他与妻子感情生活上不顺利的体会,诸如歌曲《纠缠进阴郁 (Tangled Up in Blue)》、《命运的小小转折 (Simple Twist of Fate)》,《你是个大姑娘了 (You’re a Big Girl Now)》。也是在同一年,他集合一批同道中人,开启了马戏团式的滚雷巡演。 《血色轨迹 (Blood on The Tracks)》中的歌词也在巡演中不断修改,完全契合了吟游诗人那种随意而来的特质。同一首歌,情节可以有成千上万种讲法。故事相同的发生过程,把 “他”替换成“她”,就像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水浒传》,一代代人讲话本,你修一点,我改一页的样子,愈发充实、精彩。
9.《欲望(Desire)》(1976)
巡演期间,迪伦与剧场导演贾奎斯莱维 (Jacques Levy) 合写的专辑《欲望》发行。录制阵容有太多从未合作过的音乐人,大家挤满了录音室,显得闹哄哄的,与前作大相径庭。据说,一次法国之旅他参加的“吉普赛”节日使他灵光一闪,为专辑的编曲定了“异域”的调子。不少歌曲夹杂了诸如古巴的康加鼓、西班牙舞曲的节奏,吉普赛音乐爱用的小提琴等等。他在这张专辑终于重拾时事歌曲,用《飓风(Hurricane)》声援了含冤入狱的黑人拳手卡特。其它歌曲诸如埃及探险歌谣《伊希斯(Isis)》、意裔匪首传奇《乔伊(Joey)》、墨西哥往事《杜兰戈的罗曼史(Romance in Durango)》,乃至同贾奎斯玩的尾韵游戏《莫桑比克(Mozambique)》,从名到曲无不吹着异域之风。但随着献给妻子萨拉(Sara)那首深情的同名歌曲一起落下帷幕的是,他的音乐生涯进入了滑坡。
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迪伦经历了十余年的沉浮,失去了音乐的方向。他和妻子离了婚,他皈依过基督(要知道他可是犹太人),创作了三张纯粹的宗教歌曲辑。中年危机也让他对自己失去信心。他感到新人不断把自己超越。他一度无法正视自己写过的,被新人们顶礼膜拜的老歌。89年的专辑《噢,仁慈(Oh, Mercy)》虽说回光返照,但之后再陷低潮。但92、93年开始,他翻唱起了老民歌,一如三十年前,星探约翰·哈蒙德带愣头青的自己进了录音室的门,录下第一张翻唱为主的个人专辑。就像情节里通常发展的那样,他想起了自己当初为何出发。
10.《久到遗忘之时(Time out of Mind)》(一译作“自古以来”)(1997)
过去有不少专辑被乐评人捧为自《欲望》以来的“回归”。但不可否认,1997年才是迪伦从彷徨摸索的中期至如臻化境的晚期的真正转折。制作人丹尼尔·拉诺伊斯 (Daniel Lanois) 的独特美学使得专辑显得质感潮湿混沌。一半歌曲使用了布鲁斯的音乐、节奏,例如《泥土路布鲁斯(Dirt Road Blues)》、《直到我爱上你 (’Til I Fell In Love With You)》、《百万英里 (Million Miles)》等等,像在下过雨的土里打滚。而剩下的慢歌《站在门口(Standing In the Doorway)》和《夜未临(Not Dark Yet)》等则像皮筏过水,轻轻摇摆。你能从发现他和乐队的合作轻松舒展;他熟练运用起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老民歌的文本,这里一词,那里一句,再赋予自己独特的模糊叙事——他不交代具体背景,你说不清“我”究竟在干什么,或为了什么,只能从上下文猜测。《相思病 (Love Sick)》说的是哪种爱让“我”无法忍受?《冷铁之缚 (Cold Iron Bound)》的“缚”,是真实的镣铐,还是爱的枷锁?乐迷们时隔多年,又乐此不疲地加入迪伦歌词的解谜游戏中 。
当晚期迪伦打通了任督二脉,剩下的就是,提笔写作,录制音乐,收拾行囊,出发巡演。像任何一位伟大的“江湖”艺术家,一直在路上,终身磨砺自己,没有退休一说,“唯手熟尔”。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的作品(《爱与窃(Love & Theft)》(2001)、《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2006)、《共度一生 (Together Through Life)》(2009)和《暴风雨 (Tempest)》(2012))一直保持着超高的水准。现如今,最新专辑《崎岖吵闹的道路》又一次刷新了他拒不定稿的编年史。
拓展阅读,此处仅列举中文著作/译著:
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诗歌集(1961—2012)》
霍华德·桑恩斯《沿着公路直行》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鲍勃·迪伦:诗人之歌》
格雷尔·马库斯《老美国志异》
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
张铁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
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
原文首发于2020年7月6日《文汇报》http://wenhui.whb.cn/zhuzhan/xinwen/20200706/359082.html,首发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