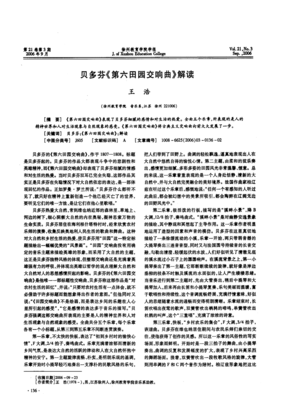
《田园交响乐》是一部由让·德拉努瓦执导,Pierre Blanchar / 米歇尔·摩根 / 丽内·诺罗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田园交响乐》精选点评: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你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
●电影的原样,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不畏惧情感的爆发,坦然面对远观或端详。让我想到夏布洛尔的Le Beau Serge。
●值得用心看的电影
●片名pastoral兼有“田园的”与“牧师的”的意思,够怪的。现在看来,这戏剧腔让人难受。尽管情节足够跌宕与讽刺。印象最深、最电影化的段落是雅克弹管风琴一段,从拍手的机位高度下降到拍脚,双脚在弹低音部分,感觉很美妙。
●古典静穆的美。根据纪德同名小说改编。从怜悯到爱,到爱的自私。是爱的原罪吗?
●这部片子我肯定连续看过四五次了。那是一个多情的时期……我认为人最好经历这么一个歇斯底里的时期,这么一个多情的时期。
●http://f.xunlei.com/88036372/file/d8cd9d20-0abb-45c5-b472-43176f0687e3
●啊......短评写的精彩的观众内心都好丰富. 你们的感受比电影本身精彩...
●摄影很美,配乐好听,故事很古典,爱情离不开善意的偏见,主角离不开可控的疾病。
●与名字大相径庭
《田园交响乐》观后感(一):在幻影的角落向隅而泣——记法国电影《田园交响曲》
在灵魂的抑郁中有多少青面獠牙暗谱心曲?从爱上美丽纯洁的盲女吉特吕德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牧师万劫不复的枯竭与沉沦。
用谎言和虚伪修饰自我的生活,牧师将心灵的暧昧性爱慕装点成人道式的关爱,而狭隘和扭曲注定了他无法自得从容,放过吉特吕德的自由而完成自我殉道的追觅。
更为惨烈可怖的事实在于牧师的儿子雅克也爱上了吉特吕德,燃烧着的炽烈让他顽强的追寻着事实的真相,并对这一切的压抑——人性的毁损有了独到式的孤岛体悟,并以性灵的冷傲孤高排斥了父亲的造作伪善,以执着于踯躅心路的方式达成了孤光的委婉。
面对热忱可爱的盲女,牧师具有师徒一般跨越了世途沟壑的相知相许之情,然而一切的掩饰在于对于激烈情绪的讶异,雅人深致的自我认知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克制情欲的翻腾反复做一场人格的自我回馈和作揖。
对于吉特吕德来说,她与牧师之间的心绪不过一场水中月镜中花的幻影。在她尚未复原之前,未能心明眼亮的察觉牧师内心的纠结爱恋,旨在无怨无悔的求取牧师的呵护偎依。在她重获光明之时,已将心曲附于瑶琴,知道了自己深爱着的乃是雅克,并幡然悔悟的意识到牧师的心胸偏狭龃龉而不具有正直可喜开阔清平的属性。
陷入生存挑战性囹圄的她宁可选择奔赴天国的灵域,在一场没有巧取豪夺也没有硝烟的心灵战争中放弃运命,选择了旷世的沉寂和自暴自弃。
溺水后的吉特吕德脸上带有冬雪的凄伤和水滴的纯净,如同烦恼中所生发的菩提。黄金打造、钻石琢磨的尘世对于她来说没有丝毫的创造性意义,她清楚的认知到牧师毁弃了她的幸福,是牧师的虚伪忸怩不肯认真对待灵魂,占据了她原本天赋应得的云天无限。
贪痴嗔是一种并不清幽洒脱的怨毒,世情的造作让人的灵魂弯曲颤抖,剜去了心目的清明而将原本素朴的情谜埋葬,让人于虚脱狭隘之中无法解脱终极的矛盾,如何使爱欲自由和教徒的责任兼顾并存?
吉特吕德秉持的只是一分基于心窗心曲缥缈怡然的灵气,然而伪道德却向她拉开了一张面孔斑驳的令旗,依旧带有童稚笑容的她无法为自己的凄然申辩,只能用宗教严苛的神鞭鞭笞贬抑自我,而以放逐涅槃的方式忏悔那一个凄寂风化的精神存在。
宗教存在的价值在于积极宽慰人的本质属性,在于慰藉受到世俗戕害而渐至冥顽漂移的性灵,然而却给牧师的人格风度带来伪的造化,让之无法从宦海深沉中舍筏登岸于生灭无度。人道的精髓在于宽慰五湖中杳然的孑孓,而吉特吕德的厌世正体现了现实消极打磨人类心曲的酷烈,真正的爱恋在于信任与放生,而非以一己愚情贪妄之执念给他人带来毁灭性崩溃。
《田园交响乐》观后感(二):米歇尔摩根的眼睛及其它
米歇尔摩根有一双使人迷惑的眼睛。
这双眼睛承载了太多的东西,诱惑,绝望,痛苦,梦幻,死一样的冰冷,火一样的狂热。
这是一一个具有中世纪气质的女人。
她那线条鲜明但却显得过于凌厉的面庞,似乎是艺术家用尖利的刻刀雕凿出来的,增减一分都会破坏这精确的美。
只有嘉宝的面孔才可以与之比美,所以我称她做法兰西的嘉宝。
她们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限于轮廓分明,带有强烈梦幻色彩的面孔,还有一种绝世的美与疏离感,这种美,不是现代的,而是属于精神世界的中世纪,精神从大理石一样冰冷的面孔上反射出来,和这个喧嚣的世界保持着距离。
有人说,这是古典气质,那也绝不是希腊的和谐与罗马的钢劲,而是宗教的禁欲与诱惑的混合气质。
梦幻,是中世纪的标志,也是米歇尔摩根气质的核心。
当我偶然在电影书籍里第一次看到她在这部电影中的剧照,就被深深的震撼了。
她穿着家常的毛衣和呢子裙,独自坐在雪地的栏杆上,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立刻就被这副画面吸引住了。
尤其是她那迷惑中带着困惑的沉浸在梦幻中的眼神,让我觉得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神秘的性感。
在整部影片中,她的表演都是沉静的,没有强烈的动作与语言,即使在表现复明之后的场景中,她的表演也是摄人心魄的冰冷。在最激动的情景中,她也保持着嘉宝式的无动于衷。她的全部感情,只在她的眼神里。
最奇妙的在于,她扮演的是一个盲人,而这个似乎并不重要,她的眼睛始终是迷离而梦幻的,在失明的时候,还点着些许天真,而在复明后,却更痛苦了。
她扮演的是一个孤女,但是却掩饰不住她那卓绝的风姿,象一个天生的王后,
这样的女人,这样的演员是不需要语言的。
而点睛之笔,正是影片结尾处,她投水而死,那个震撼人心的死不瞑目的特写镜头,那双眼睛在控诉责问世界,为什么,谁之罪?
这是一部具有天主教色彩的法国电影。
改编自纪德的作品,讲述了一个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个盲女,在抚养的过程中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从而影响了他的家庭关系。
牧师的儿子也爱上了她,于是和父亲发生了争执。
虽然盲女医治好了眼睛,却引发了更大矛盾,最后她无法解脱投水自尽。
影带有典型的原罪的色彩,这个女孩子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悲剧性的命运,她的美貌是罪恶的根源,在两个男人之间引起了纷争。
牧师形象是一个近似弗娄洛和《苔漪丝》男主角之间,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心理阴暗的教士,他声称自己是无私高尚的爱着盲女的人,是一种宗教的爱,他爱的是女人纯洁的灵魂。他不给女孩子医治眼睛,让她对自己产生了习惯性的依赖,就是为了占有她。在女孩与自己年轻的儿子之间产生了好感之后,又以各种堂皇的借口百般阻挠。
作为年轻的儿子,对父亲有一种宗教的恐惧和乱伦的厌恶,父亲象征的是宗教的权威,是精神的代表,而他本人是世俗与肉体的象征,他要带给女孩子光明,让她离开宗教的依赖。
在失明与复明中,是一个自我觉醒但是却又失去信仰的过程。
作者在暗示一种思想,一旦人的眼睛明亮了,心灵却失去了支点,被世俗的各种纷争所困扰,这是一种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和失望。当人的眼睛闭合,看不到世界的时候,虽然是黑暗的,可是灵魂是纯洁安宁的,然而一旦看到了外在世界,肉体,那么就会陷于混乱。
在影片的末尾,一本正经的教士终于承认他爱的也不过是女人的肉体,这才是女人最终绝望的根源,而原先她以为是存在一种圣的洁超凡的爱的。
她的自杀是对于人性和宗教的质疑与绝望。
因此这既是一部宣扬宗教原罪的作品,也是一部对宗教提出怀疑的作品。
整部电影的调子是悲观宿命的,与田园交响曲这个诗意的名字毫无关联。
《田园交响乐》观后感(三):《法国优质乐团演奏的<田园交响乐>》摘抄
在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德拉诺瓦让格特鲁德获得了视力。正如纪德所言,这么做和影片主要的叙事实践相吻合,但是却软化并抑制了小说中结局突然所带来的惊吓效果。然而,德拉诺瓦在影片中行使着自己的“权利”,将故事从牧师的手中解放出来,而将其伸展至整个角色领域,关于关于格特鲁德复明的决定性一幕需要反过来去影响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通过故事中最具激情的人物的思想和心理,纪德的小说描述了了这个转折。这种突变性的结局和整体的讽刺效果相一致,如此这般,掀翻了贯穿在小说中整个下半部分的牧师的想法和欲望。
除了删减、增加和剧情重组之外,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语言主要关系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充满戏剧张力和释放感的结构,关系到某种画面,这样的画面既不是通过一个镜头,也不是通过几个关系相近的镜头组成的,它们使影片的价值均衡地保持在合适的位置。例如,单个强大的镜头结束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由于双方都想要占有失明的格特鲁德而产生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要归因于视觉本身的占有欲。视觉使得双方关系疏远,也使得二者与格特鲁德的关系亦疏远起来。在她的触觉(双手的镜头)和听觉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时她才会幸福。德拉诺瓦在父子吵架接近尾声时对这种情况作了总结,这时二者都走到窗前,从黑暗的前景凝望坐在花园的格特鲁德[2]。这个镜头是影片前半段的神来之笔,通过模仿观众自身的处境而获得了吸引力:透过玻璃望着一个物体,可以看见这个物体,而这个物体却不能对这种凝视有所回应,即发光的电影本身以及处于电影中心、失明的性欲。
剧情的下一幕随着恢复格特鲁德视力的手术而拉开序幕。术后的她通过三个镜头出现在观众面前:她明亮的披肩和乌黑的头发使她明显有别于身边裹着黑袍、戴黑色面罩、搀扶着她的修女们,这些修女们以中景镜头出现在画面之中。此外,当她第一次在看得见的世界里呼吸时,画面转接至一个极长的镜头,将她以一种令人刺激的方式解放了出来[6]。这种“解放”的效果是由于镜头的距离,表现了她视野的突然拓宽;同时也是由于工作室中雪花的飞舞而产生的,这雪花既对她视力的恢复传递了来自天堂的祝福,也呼应了她最初被拍摄时白雪皑皑的景色。然而,同时她又被置于一个构图精美的镜头中,这个镜头几乎要将其从玻璃球镇纸中反射出来,她身后的教堂,她眼前的自然景象,以及身边一袭黑衣的修女们将其锁定在一个令人愉快的位置中。她在这种结构中大放异彩,但也被困于这个虚假的结构之中。德拉诺瓦可以靠近以给其一个脸部特写镜头,而此时她正为她眼前的生活而惊异。她由于视力恢复而产生的快乐成了我们的快乐,她对上帝的感激同时就是我们对这部影片的感谢。有一瞬间,她眼前的世界和这部影片是壮丽的视觉交响曲,是身体和道德特征的和谐结合。
当戏剧冲突不存在于单一的个人,而是被悬置在两个或更多的人物之间时,构图与灯光便几乎会以喜剧的风格对立。格特鲁德到了教堂,来到艾米丽身边,所有人都注视着她的眼睛。艾米丽告诉她,讲坛上的男人就是牧师。不出所料,我们注意到她和牧师之间眼神的交换;因为她现在能够看见他了,他们四目相对,眼神之间充满张力。从她的视角看去,我们看见牧师处于聚集的教民们之上,正从布道坛上往前倾,并几乎要掉下来。他看上去黯然而且严肃,威严但显得有点荒唐。一个反打将格特鲁德置于教民组成的各种构图线条网的包围中。她浅色的斗篷被一束光线照亮。当诵念感恩祈祷词的牧师伸开双臂,打破了教民们的震惊和寂静时,第二组相似的镜头变得十分戏剧化。从格特鲁德的视角看去,牧师的这一戏剧手势暗示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但剪辑突然跳到相反的角度,我们突然看见牧师像一只捕食的鸟正扑向处于画面中心的格特鲁德,而他那处于前景中的黑色身影几乎快将格特鲁德遮盖。
与小说迥异,电影故事的讲述没有局限,只受到“方便和清楚”原则的约束。电影多次做出微弱的努力,通过笔记本一张张的书页,一张化为一张,试图再现牧师的事后醒悟,这也标志着小盲女成长为米歇尔·摩根。但与此同时,摄影机自由而详细地拍摄了牧师不在的场景(特别是雅克与格特鲁德在医院沉默的相遇[3,5]),而且摄影机总体上观察了所有人物的反应。情节如此通过人物而交织在一起,而且简单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无疑使纪德的小说变得更受欢迎,但付出的代价是小说真正关心之所在,即行动与反思之间的相互作用。白雪、交响曲、镜子、手、光线和黑暗等象征都具有力量,但却很幼稚。纪德永远也不会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这些象征,但却乐于让牧师通过这些象征而思考生活。这类象征的不足是这个故事的主要讽刺。但是,通过将故事从牧师的手里带走,电影制作者让小说所质疑的非常简单的象征主义变为永恒。因此,通过它的自以为是的风格,一个坚持总体叙事需要和对其原材料的文雅再现的风格,优质电影被一部看上去对它来说似乎太过简单的小说所愚弄,由于意料中的表现力的局限,未能再现这部小说的精神。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说,电影制作者们的公众风格都很显然地表明:他们很自信地越过而且审判了牧师的道德盲区,但都无法理解牧师的复杂性。可是他们不能对此有所思索。通过这次改编,纪德的原著被放入了橱窗玻璃,人们凝视着它,但尚未阅读过它。咖啡桌上放着牛皮纸版本的一本书,德拉诺瓦改编电影的最成功之处在于让它的百万观众回到了牧师不整洁的笔记本,那就是,阅读纪德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