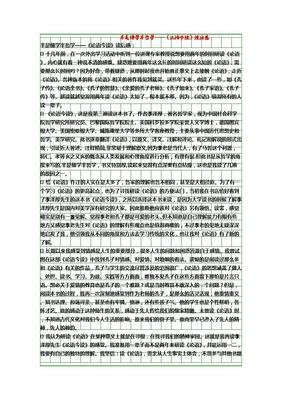
《论语今读》是一本由李泽厚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6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喜欢其中对于命的解释,认识命的本质,但是不认命,虽然大部分时间你不能改变命运,但是绝不随波逐流。
●不错
●跟李先生的思想史论、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等著作一脉相承,是个很好的睡前读物,而且读完先秦以降至现当代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后再返回去读孔子,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文明之早熟与早熟时蓬勃鲜活的生命力。后来的一切都不过是这一生命力枯萎过程的呈现罢了。
●李泽厚用他的理论来解释《论语》的一部著作
《论语今读》读后感(一):论语今读,让我们更多选择,更多理解。
李泽厚的美学三书,一直没机会读,但当你接触他的文字,他的文章,你会跟我一样想读完他所有的著作。论语今读更是给你一种全新的视角,多方面解读论语,结合当今的社会状况,国情发展,让常人能跟清晰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做人守则,育人标准。顿时让人对传统文化心生敬意!感谢李老先生给后人留下如此宝贵的财富。
《论语今读》读后感(二):从论语中找到中华民族的潜意识和本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贫而能乐富而有礼,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即便是当代没有经历过正规国学教育的大学生,对这些句子也是信口拈来,而在中国人灵魂的更深处,这些思想以通过代代的传承,铭刻至骨髓。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华夏五千年道德伦理行为规范指南,中华价值观原典。对于那些尚未自立的人而言,比如我,对为人处世的分寸拿捏\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相处原则,都可从论语中得到启发。国人必读。
李泽厚不愧一代大师,治学严谨,对中国儒文化中的乐天知命精神解读深刻,本人笔拙,三言两语难言其深,与南怀瑾著作相比,更严谨\更考究,南师之书多随性而作。李泽厚版本当为我所读过的论语中最佳版本。
《论语今读》读后感(三):个人读后感
就着李泽厚先生的译、注、记,每天读得两三页,终于把这本钱穆先生称为“每个识字的中国人必读的一本书”的《论语》完整读了一遍。读的过程中系越读越慢,深感传统所谓“学”与现在上学读书有很大不同。程颐讲得好,“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本书对于孔子的原典儒学做了一番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正本清源工作。相比董仲舒宇宙观图式的汉代儒学,朱熹天理人欲心性本体论的宋明理学等后儒加以改造的学说,今读全书都强调孔学之源于氏族社会的巫术礼仪,系一种以“情”为本体的,力求塑造自我个性得以“立命”的半宗教半哲学的学术。 除以上“我注六经”的工作外,本书也有“六经注我”的内容。对于“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的分辨,区别于康德纯粹理性的以“历史本体论”为基础的认识论等,都可以视为一个现代学人忠实地履行了继往开来的本职工作。
《论语今读》读后感(四):尽其在我,成其在天
李泽厚老师在全书中非常强调儒家的乐感文化中包含的“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的底子。我觉得可以将其总结为“尽其在我,成其在天”这8个字。
所谓“尽其在我”,即所谓要“学而时习之”,“一日三省吾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儒家与佛,道两家最大区分处。佛,道讲究出世隐逸,绝情寡欲,清静无为,而儒家强调君子有为。君子有为,是因为君子有欲,而君子有欲,是因为君子有情。君子有情于人,君子有情于世,君子有情于道,所以有苦苦追求,有艰苦奋斗。林觉民《与妻书》中说:“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此即孔子之精神。
所谓“成其在天”,即所谓“五十知天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儒家与基督教最大区分处。儒家没有人格神,没有一位真善美化身的全能上帝,儒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偶然性归之于苍天。然则苍天似乎是无情的,君子所求,无论如何高尚正确,皆未必可成。孔子不是耶稣基督,一生主张不得行,如丧家狗,死后三天也没有复活,应许在末日审判再来拯救信仰者。因此与相信可以依靠上帝的基督徒不同,儒者精神上没有依靠可供慰藉,不能希冀于来世和超越,必须从自己对内在道德追求,顺事宁人的修养,或者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在无常的人生,无情的命运中来获得慰藉。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是前者;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则是后者。
所以“尽其在我”是“仁”,“成其在天”是“命”。若只有“成其在天”,没有“尽其在我”,则变成一种逃避,消极的隐者文化。而若只是“尽其在我”,没有“成其在天”,则《论语》真如黑格尔所说沦为人生格言,心灵鸡汤而已。就是明知“成其在天”,也要“尽其在我”,甚至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知“尽其在我”之坚定执着,情深义重。就是因为“尽其在我”付出之多,所过之艰辛,才知“成其在天”之包含乐天知命,强颜欢笑,百倍悲情。此即体现孔子之学并非庸俗浅薄的廉价哲学糖果,而是“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种蕴含悲剧色彩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已经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美学境界,形成了一种不逊色于宗教的感召力,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其献身。所以中国两千年来能立国于世,与教义严整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分庭抗礼,太半在此。中国人经常被说成是没有“信仰”的,可是中国人一直有自己的“神”。每当境界危恶时,即有人挺身而出,不计成败得失,尽其一身,于荆棘中开出小径,于烈火中铺出道路。此即儒家之精神,也即中国之精神。
《论语今读》读后感(五):【好读书,求甚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最近在看四书,用孔子他老人家的话说,叫温故知新。读书时代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遗留了一大堆的历史问题。这次正好也可以挨个解决。
于是我 最近在想“语言环境”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说话背景。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论语》里面的一句话。
《论语.为政篇》里,孔子有这么一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从古到今,对这句话的解释一向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理解。就现代而言,主要是以杨伯峻先生的“攻”派,和李泽厚先生的“不攻”派两种比较主流的解释方式。而其解释的着重点,我估摸着,大约就是说话背景的问题了。
先说李先生的“不攻”主义。按李先生的理解,孔子这句话意思大约是:不要去攻击和你不同的异端学说,那样的话,反而是有害的啊! 假如这么解释,那么这个“害”字,就可以理解为有害,而最核心引起分歧的字义,基本上在于最后的那个“已”字。按李先生的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已”就是无实意的语气助词了。
李先生的解释,基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是“儒学”教义中的“宽容精神”。中国儒学,千百年来的延续,一直讲究一个“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这可以具体体现在孟子吸收墨家兼爱思想、荀子吸收法家法治思想,日后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天人感应”思想,而最最主要代表性的,那自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道释儒”三教合一的思想了。中国儒家传统,重视“道理”,讲究的是实用理性。因此中国人也很少为了和尚去和道士打架。于是一座山上,经常有道观也有寺院,说不定还有书院。典型代表就是岳麓山以及嵩山。这种异常宽容的人文环境,是欧洲从中世纪以来都不可能存在的。
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提倡“不攻”还有一个依据,就是《论语颜渊第十二》中说道,“攻己恶,无攻人之恶”,因此,李先生说“不攻”,是有其历史和学派的文化背景的,通。
再说杨先生的“攻”。杨先生的理论依据,我想,第一方面是西方式的思维方式,即非黑即白,和我不一样的,就是错的,就该消灭。直接表现为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号称让全世界都沐浴在主的光辉之下。但,正如上文所说,这和中国文化的整体背景特征不符合,所以这一条应该不成立。
那么杨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解释呢?我想应该和孔子自身的行为有关。《史记》和《智囊》曾经都记载过一个故事:孔子杀少正卯。
话说鲁国有个学者,叫少正卯,长的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口才非常好,而且知识相当丰富,于是很是吸引了一些学生去求学。虽然孔子也算是能说会道的,但和少正卯一比就没什么魅力了,他的学生除颜回外都多次翘课去听少正卯的讲座,甚至干脆转学了,孔子看着空荡荡的教室,曾经很不爽的问颜回:我K,人都死到哪里去了?
颜回是个很低调并且内敛的人,面对这种情况,就和老师说,天太热了,大家去游泳啦。虽然颜回给同学们做了掩护,但是孔子还是知道了少正卯在挖自己墙角。当时孔子没有权势,又说不过人家,也不好开什么无遮大会来PK。但少正卯严重影响了孔子的生意,虽然学费低,但好歹还是有些腊肉可以吃嘛。这下好了,连腊肉都没得了,孔子那个怨恨啊。于是估计心里在想,你个异端邪说,看老子以后怎么收拾你。因此孔子极度讨厌雄辩之人,故而时常说“巧言乱德”,提倡“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老先生于是还迁怒了。。。话说子路要子羔做一个县的县长,孔子就说了,你小子这是误人子弟啊!子路说了,有老百姓,有庄稼给他们种,难道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问么?孔子于是说,所以我才讨厌狡辩的人。
这话没多长时间,鲁国的君主就任命孔子担任大司寇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最高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检察院院长。孔子一看,机会来了,就逮捕了少正卯,给少正卯安了一个罪名:以异端邪说荼毒鲁国年轻人的思想。然后把少正卯给杀了。
而且,孔子还专门说了少正卯五大恶,简直就是把自己的敌人死死踩在脚底下,死了还不放过人家的名声。因此,我认为,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很可能是把少正卯杀了以后,在给自己的学生讲道理。很可能就是在回答问他为什么要杀少正卯的那个子贡的问题,顺带还下了总结性语言。假如杨先生是考虑这样的语言背景的话,那解释为“攻”,就相当准确了。
于是乎,语言环境何其重要,一句话,不过8个字,但假如考虑的语言背景不同,那意思可就完全反了啊。慎思,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