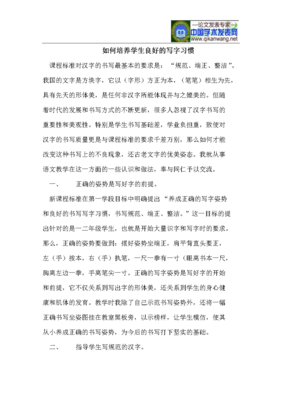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60年代,某剧团解散,一戏剧演员被派到某中学。适逢学校缺人手,校长找她谈话说:“经学校反复考虑,本着因材适用的原则,你去教高一语文吧。”她欣然受命,她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又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故她苦思冥想,忽然眼前一亮,“对,有了。”戏子凭着多年唱戏的切身体会,移花接木,把它运用于语文教学,她对课文基本不讲,让学生像她当年背台词一样,把课文都熟读成诵。三年后,高考成绩让人瞠目结舌,她教的班成绩优异,名列榜首。
读完这个故事,真有点让人可笑、可悲、可叹。可笑的是戏剧演员竟然成了语文老师,而且带出了优异的成绩,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荒唐透顶;可悲的是戏子教的学生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不禁使我这个语文老师汗颜,甚至无地自容,以至于长歌当哭了。可叹的是戏剧演员的以“背”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竟如昙花一现,没有被传承并发扬光大,使我们目前的整个语文教育陷入了低迷状态。
近几年来,语文教学备受非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声不绝于耳;高考题“气死鲁迅,难死巴金”的报道屡见报端;大学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甚至错别字连篇都不足为奇。于是人们不禁惊呼:我们的母语教育怎么了!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把批评的口水都唾到语文教育上,也有失公允。但我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每当看到类似的报道,看到学生那可怜的语文成绩单,看到那满眼错字,病句的作文时,一种莫名的困惑、茫然、无奈、悲凉涌上心头,紧接的是揪心的痛!我们何尝不每天努力地耕耘着,我们何尝不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而培养出二十一世纪的鲁迅、巴金……培养出我们中国的泰戈尔,川瑞康成……
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对母语教育的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敢于承认现实,勇敢地面对现实,查出病根用猛药,也许能有妙手回春之效。那么,语文教育的病根在哪里呢?十几年的语文教学经验告诉我:语文教育的积弊可以说由来以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真有点老病难除,积习难返了。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满堂灌,整篇讲,划段落,找中心,老师讲的神采飞扬,唾沫四溅,学生听的昏天黑地,不知所云。而我如今登上讲台,也是满口“之乎者也”,讲的天昏地暗,学生倒下一片。这与我上学时听老师讲课如出一辙,呜呼哀哉,“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其间虽屡刮教改之风,教学模式层出不穷,但常常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核。真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把语文教育之脉,我认为语文教育的病根在于老师讲得过多、过滥。老师备课也用尽苦心,翻教参,查教案,精心准备,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遗漏了知识点,愧对学生,真可谓用心良苦啊!但事实上教与学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老师教得多不一定学生就学得多,俗话说“过犹不及”,教得过多常会适得其反。正如我们吃东西一样,给的东西多,但我们吃不了,即使勉强吃到肚子里去,消化不了,也会难受的,这些食物不但成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也就是说学生的营养状况不是老师给多少东西吃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吃多少的问题。“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老俗话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
由此看来,语文教育非改不可,怎样改必须对症用药又不能走极端。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的那个戏剧演员的故事,从那个戏剧演员老师的经验里我们不难悟出:语文学习“背”为先。
纵观古今文学史,凡成大家者概莫如此。古代科举场上成功的士子们,都有一身过硬的“背”功,《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莫不烂熟于心,甚至倒背如流。正是他们这种过硬的背功,使他们“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考场上挥洒自如,如有神助,在众多士子中脱颖而出。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小时侯在“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内容是“之乎者也”,枯燥无味,艰深难懂,学生无非是读读、背背、写写、画画,先生那摇头晃脑读书入神的样子至今想来可笑,但正是这种以“背”为主的启蒙教育给了鲁迅以深刻的影响,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大家,世界级文豪。正如现代文学大师巴金老人所说:“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脑子里了,(指背诵了《故观止》书中的两百多篇古文),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这是巴金老人一生读书写作经验的心得,也道出了他之所以成为文学大家的真正原因。
因此,我们的语文学习必须正本清源,尊重语言学习的规律,还语文学习以本来面目。背诵—特别是背诵名家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作品中语言、形象、意境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磨洗不掉,并且会积淀为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