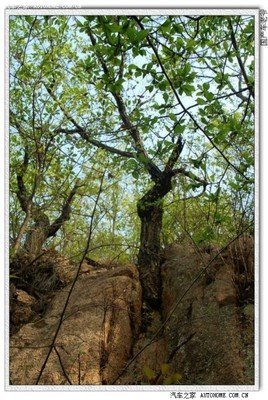
小村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两个小队,也就不到一千人。队长姓王,老头黑沉沉的脸叼个烟袋锅。
一条官道直通大海,两旁栽的都是大杨树,一搂搂不过来。后山有许多山洞,大炼钢那年人工挖的,恐惧又神秘,里面或许有逃犯或许有猛兽吧?反正家长们连撅带骂的不让靠近。山枣在沟渠旁,半红不绿。最好的美味就是黑天天,如若尝到一颗特甜那么整株都不会涩,好吃到齁,舌头祛紫。
偶尔来一辆大解放,悠悠开过去,后面跟一串小鼻涕虫,闻着尾气那么香甜,尘土里挥发着汽油味还有车上人的讥笑声:乡下崽子!那也挡不住跟在后面死追的脚步,踉跄的,绝尘。
生产队收工了,车锅赶着老牛车拉着犁铧,本就不大的车身上还得上去七七八八的野孩子,一个个黄毛跌些,破衣烂衫,还有上不去硬往上挤的。连滚带爬急了咕噜。
家长们就骂:怎不卡死你!也没看谁卡死,依然有一群群娃娃不是爬牛车就爬马车,更牛气的是坐在车锅旁边的副驾驶,有一天,暖洋洋的夕阳下那个傻丫头一蹦上了副驾驶,结果没坐稳掉了下来,我滴妈呀活祖宗啊,车从傻丫头腰上压过去,等车锅反应过来刹闸检查的时候,傻丫头已经一杆子跑了,全村哗然,挨揍是跑不掉的,里裆肉被掐的黑了半个月。
院子很长,再往前走走就是一条小河。夏天这里是崽子们的乐园,捉鱼摸虾都不在话下,最勇敢的事是经常在水坝上往河沟子里跳,河坝石头黄泥垒的,也就两米来高吧,连着自家院子的菜园子,大人们用瓢绑着一个长把做水舀子舀水浇菜,我们就把这个水坝当做跳台。冬天就是溜冰场,支爬犁,打尕,抽陀螺。一不小心掉冰窟窿里,因为棉裤棉鞋棉袄就一人一套,湿了就没得穿,躲奶奶炕头盖着破被,等晾干,等挨揍。
那时候的雪啊,真大。一开门,开不了啦,大雪封门。跳窗出去,先铲开门口的,再扫茅楼,孩子老人得去上厕所啊。猪圈里的猪冻的尿都尿窝里了。二大爷就骂:没几天好蹦蹬了!意思我们都明白,要过年了要杀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