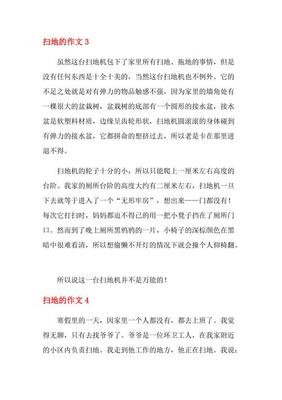
《我生于美洲》是一本由[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页数:75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生于美洲》读后感(一):卡尔维诺深度访谈录
《我生于美洲》这本书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本访谈录。
这本访谈录收集了101次访谈,跨越了四个十年。可以说是收集的最齐全的一本卡尔维诺访谈录集。
卡尔维诺本身并没有出自己的自传,所以读卡尔维诺作品的读者们也无从得知卡尔维诺在创作那些极具脑洞和魅力的作品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从这本访谈录中则可以窥探出一二。
这本访谈录中有一些问题我十分感兴趣。
-
比如说在1965年《意大利日报》上刊登的卡尔维诺、福尔蒂尼等著名作家的圆桌会议“文学转向,它将会变成什么的?” 活动上有人提问卡尔维诺:文学到底是什么?
卡尔维诺的回答就很有意思。
卡尔维诺说他自己从来不觉得文学是有权利和神圣性的。他觉得文学只是他选择的一个工作领域。
这个回答我觉得非常有趣。文学自然是有很多附诸其上的意义的。文学是一种形象活动,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虽然说并不显眼,但是又不可替代。
卡尔维诺本身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文学家,但他从来不以自己从事文学工作而自觉高人一等。对卡尔维诺来说,文学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份非常有用的工作。
而下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非常符合现在时代的氛围变化:出版业出现了廉价书的繁荣景象,是否认为这是件好事?
在这里我把廉价书可以理解为快消品书籍,甚至可以引申为现在流行的网文。环顾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快消品书籍其实占了很大一块市场。现在很多文学大家都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觉得快消品书籍其实会消耗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消磨人们在阅读中的深度思考。
问一个已故的伟大文学作家,对于快消品书籍和网文的看法是一件充满悬念的事情。而卡尔维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卡尔维诺对于这个问题是持赞同的态度。他觉得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广泛而各不相同的,所以把阅读文学化,其实是更狭隘的一种做法。
纵观历史上,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快消品书籍其实都有过流行、混乱和低谷的时期。也不能把快消品书籍一棍子打死,因为存在一些这样的书籍,其实是能够给读者提供普遍的文化纽带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快消品的阅读,其实是年轻人居多。年轻人的阅读其实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学校里面接受正统的,有文化沉淀的,由学校老师带领培养的对于阅读的兴趣,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课外生活中,由自己不同的兴趣去阅读的那一块。
那么同样的,阅读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经典著作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有时候正是这些作品恰逢于社会变革的时期,对于历史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才会成为经典著作。很多作品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文学性,而是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文化和其他一些因素息息相关的。
从卡尔维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完全可以勾勒出他对于世界、对于文化,对于书籍的主张和看法。他之所以在文学创作方面能够突破自己,创作出非常独特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其实与他个人对于文学的主张是息息相关的。
虽然我一直秉承着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非要了解作者本人的想法,但是这本卡尔维诺的访谈录《我生于美洲》确实是让我对卡尔维诺本人的想法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可以从另一些角度来重新看待他的作品,产生完全不同的思考。
《我生于美洲》读后感(二):童话与真实
我认为,作家描写的一切都是童话,甚至最现实主义的作家所写的一切也是童话。——《文学—向迷宫宣战》伊塔洛·卡尔维诺
2019年7月,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还是习惯了叫它《寒冬夜行人》)开始接触到卡尔维诺,在这本后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中,卡尔维诺采用多个故事嵌入的方式,摆脱了西方传统文学所要求的必须围绕某个中心构架全文的固有模式,令人耳目一新。借用书中女读者柳德米拉的话来说“最想看的小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的枝叶纵横交错……”,由此对卡尔维诺的初印象是狡黠、可爱。在这本作品之后紧接着又读了“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也是不由得产生相见恨晚之感。我们在书中读到的是童真与幻想,而书又是作者写下的自己,最深刻地延伸着他的个性,展示着他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存在。自此开始慢慢阅读卡尔维诺作品,刚好至今年5月,也陆续读完卡尔维诺已出的28本中译本。这时《我生于美洲》的简中版本出版上架无疑是个惊喜,书中收录了1951-1985年对卡尔维诺101次访谈录,刚好随着这些访谈内容再去理解、回顾作品,去探访更现实、客观存在的卡尔维诺。
写作之外,卡尔维诺并不愿过多讨论自己,也并没有传记作品留下,在此之前只有在《巴黎隐士》中通过其信札式日记、访谈、回忆性短文等内容能够略微感觉到靠近作者本人些许。而就性格特征而言,甚至可以说他内向、不善言辞,卡尔维诺自己也表示过,“如果人类没有一部分人性格内向,对世界的现状很不满意,如果没有一部分人盯着不会发声、不会活动的文字整天整天地苦思冥想,那么文学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文学上的一切虚构,写出来比讲出来更容易让人记住。”虽然接受了超过200次采访这点看起来与其性格多少相悖,却是难得可以与卡尔维诺透过小说纸页,直接对话的珍贵资料。访谈内容跨越近40年,恰好经历了其作品风格从新现实主义、童话和幻想小说、后现代主义的几次转型。
卡尔维诺喜欢尝试不同叙事方式。战后,新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文学主导地位,卡尔维诺成名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便脱胎于反法西斯战斗和参与游击队组织的真实经历,是一部叛逆又童真的现实题材小说,两年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最后来的是乌鸦》同样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但仍然难掩其轻逸和童话般的瑰丽想象。50年代,卡尔维诺陆续创作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并开始编写《意大利童话》,标志着其文学创作从现实主义向童话和幻想小说创作的一次转型,它们既是“寓言式的现实主义色彩”,又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寓言”。进入60年代,卡尔维诺作品风格再次转变为后现代主义,在这时期代表作品《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趣全集》《寒冬夜行人》中,对叙述节奏和形象的组织令卡尔维诺感到满足。他将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进行分类,再抽象至虚构的陌生空间,现实中的一切得以以童话、幻想的方式自由生长、天马行空。
卡尔维诺的自然倾向是幻想和虚构,当然,这与其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出生于美洲哈瓦那,认为自己是属于以世界为家的一类人,依然眷恋着故土利古里亚,名字“Italo”便是他流淌着意大利血液的最直接证明。旅居各地的经历让他看到更多元的人类社会,意大利方言和童话的质朴幽默、奔放欢腾又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同时,父亲是农学家、母亲是植物学家,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学习到诸多植物学、动物学的知识,对自然界的观察更加敏锐,这样与众不同的童年时光令卡尔维诺关注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创作更是添加了童话般的色彩与想象。
在《美国讲稿》,卡尔维诺说道,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童话与现实,抒情与哲理,便足够让我一直尊敬且热爱这位伟大的作家了。
当然,很难想象的是,这样以为擅长幻想的作家用词用句却是追求精准,访谈时有的地方甚至会思索许久方才做答。但也不无风趣、幽默之处,真是过分可爱了,比如,
问:您是否给出版社发过匿名手稿。
答:如果我发过,我也不会说!
问:可谁又能证明他刚刚读完的不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虚假采访呢?
答:这很简单,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虚假采访会更加光彩夺目……
《我生于美洲》读后感(三):世界上最大的成功,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相传,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临终前对其助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优秀的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欧洲近代戏剧创始人易卜生也曾有句名言:“人的第一天职是什么?答曰:做自己。”
两位先贤的智慧如果套用现今一句稍显矫情的文案,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不必仰望别人,自己亦是风景。”
这句颇为走心的文案如果拿来形容意大利当代文学巨匠伊塔洛·卡尔维诺创作的长篇小说《树上的男爵》最是恰当不过。
我们说,但凡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作家,都需要一个进阶的过程,循序渐进地去挖掘、去发现这位作家。而在这个挖掘发现的过程中,最好的方式无疑是阅读其作品。
《树上的男爵》被公认为是卡尔维诺毕生创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之一。65年后的今天,书中塑造的看似离经叛道,最终却成就了真正“自我”的主人公柯希莫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我生于美洲》一书收录1951—1985年间的卡尔维诺访谈录,跨度长达其黄金创作期的4个10年,在其毕生超过200场的采访中摘录101场访谈,内容主题包括文学、历史、文化、童话、电影、城市的未来等方方面面。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卡尔维诺最直观也是最清晰自我评价的文集,透过这些直面人心的访谈,我们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去深入了解这位不愿谈论自己的作家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构思。
在本书前言部分,卡尔维诺讲到,“我写作是因为我口头表达能力差。如果我谈话没有困难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写作了。”
也就是说,卡尔维诺不仅承认自己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同时将这个原因归功于写作的动力之一。
卡尔维诺
事实上,卡尔维诺笔下的柯希莫无疑是个人主义的绝对坚守者。出身于传统贵族家庭的他从小便显示出性格中性情坚毅、聪慧果敢的一面。
他不满旧式家庭对他的束缚,12岁时因无法忍受姐姐做的蜗牛大餐,愤而离家,住到了家门口的树上。
开始家人并没在意,都以为只是小孩子在闹脾气。谁都未曾想到,这种离群索居的树上生活柯希莫一住就是53年,时常都是弟弟爬到树上给他送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
后来,同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少女薇莪拉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出现在柯希莫的生命中,照亮了他封闭已久的心房,柯希莫对这个明媚的少女一见倾心。
尽管痛苦万分,但柯希莫还是拒绝了掌控欲极强的恋人让他下树的要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就如同曾经薇莪拉告诉他一旦他下树,双脚沾到她自以为的领土中,就会变成她的奴隶一样。这一次,他对于薇莪拉的拒绝分明暗示了二人之间不可逆转的悲剧结局。
卡尔维诺在访谈中曾隐晦地提及创作柯希莫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并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表示,“如果不充满力量地保持自我,就不可能拥有爱情。”
后来,柯希莫终于获得了父亲的谅解,当他的伯爵父亲去世后,身为长子的他继承了男爵的头衔。
此时的他虽然依旧生活在树上,但却始终不曾放弃自我。
年岁渐长,他长成了一位高贵优雅、风度翩翩且富有学识的青年贵族,这与他坚持不懈的学习和研究有关。在柯希莫看来,只有精神上达到崇高的境界,才是唯一塑造贵族的荆棘之路。
基于此,相对现实世界,我们有理由认为《树上的男爵》是童话大师卡尔维诺创作的一个乌托邦,一个远离俗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世外桃源。
此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柯希莫追求的“自我”不同,同样“自我”的恋人薇莪拉为了逃避家族联姻的命运而选择远嫁印度,嫁给了一个垂垂老矣的公爵,不久后如愿成为了贵族寡妇,她与柯希莫昔日的爱情也只是一场镜花水月,空余一声叹息。
然而,一声叹息过后,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个故事反映的是不是卡尔维诺本心的自我放逐?在柯希莫这个人物身上,卡尔维诺倾注了怎样的情感?
在卡尔维诺另一部后现代主义风格极其浓郁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超级驴友马可.波罗正在向他的东主,元世祖忽必烈绘声绘色地描述55个虚构的城市。
此时,这位庞大帝国的继承者、意气风发的帝王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想象着帝国的版图在自己手中一再扩大延伸。
讽刺的是,每每读到此处,这本只有一百多页、插上了无限想象力翅膀的小说总会让人生出一种类似“皇帝的新衣”之感。
在这55个以不同女人的名字命名的虚拟城市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代帝王对于帝国疆域的渴求和内心矛盾真实的挣扎与映射。
书中讲道,在卡尔维诺看来,“托尔斯泰是悲天悯人的;伏尔泰、布莱希特、毕加索是冷酷无情的。”
此处姑且不论后面三位是如何冷酷无情,单从长篇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托翁在老别祖霍夫伯爵私生子皮埃尔身上寄托的感情,便足以表达这份难得的“悲天悯人”情怀,同时这也是《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史诗级名著的魅力所在。
美国“最后一位真正的文人”厄普代克曾这样评价卡尔维诺,他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最温暖明亮。”这对于一个曾经距离诺奖最近,却最终遗憾擦身而过的作家而言是多么至高的褒奖。
行文至此,致敬卡尔维诺,致敬那个世外桃源般的童话世界……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