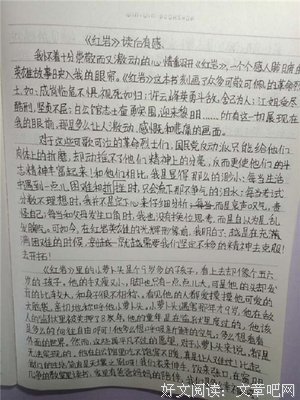
《先人祭》是一本由[波兰] 亚当·密茨凯维奇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先人祭》精选点评:
●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情绪侵人
●波兰和俄国上百年的战争中诞生了仇恨,爱国,破碎的人生,唏嘘的爱情,隐藏的受益者,剥削与被剥削者。 这无法评价,只能不断感慨
●大开大合!断续拖沓的阅读丝毫没有损减它的出色。一定要读第二遍。看到评论区有一句“我们不再敏感了”。这真是感伤的事实。
●强力。“显而易见的是,《先人祭》是关于一次失败的学生运动的戏剧体诗作”,为了逃避审查,四十年前译者挑了第三部译,现在看很有先见之明。
●“波兰就是在大地的阴影里生活和开花”
●只读长段,百鸟朝凤和赛德克巴莱,可作壁上观
●翻译非常有力道,不过这位浪漫派诗人写叙事长诗的功力好像还不是特别出众(也许因为没读原文)。注释实在太差,不该注的常识写了一大堆,该注的地方不注,以至于很多地方摸不着头脑。也可见出当前西方文学研究中波兰东欧方面的严重欠缺。
●8.5分(补)
●看哭了好几次……果然病态的时候就应该看病态的东西啊。
《先人祭》读后感(一):波兰先人诔
翻译的诗歌不好看,翻译的长诗就更不好看了。一首一首的诗歌还能字斟句酌,卷帙繁浩的长诗只能批量生产,一不小心就容易暴露译者的水平(如果作者本身没问题的话)。这本诗剧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贫瘠的词汇、比喻和修辞跟不上想象力。
(76)
这一段活像《红楼梦》里警幻仙子召集姑娘们唱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再比如:
(唱) 涅曼支流河水清 广袤原野草如茵 马林山哈飘落英 何人墓落无人境 萧疏荆棘绕孤坟 (停)(83)
读这一段脑补的都是昆曲唱腔了。当然,最糟糕的是,有的时候易先生为了押韵胶柱鼓瑟到不惜扭曲诗歌原意和逻辑了。
如今沙皇让它驾上那独轮车去挖掘煤矿, 与它同锁在一条铁链中的是波兰人的手掌。(441)
很明显铁链并不能锁住手掌。
也许正在用我的鲜血去染红我的祖国, 并在沙皇面前邀功似的夸耀罪过。不知道是否原诗如此,但不知道如何夸耀罪过,推测愿意应当是把自己的罪过当作功劳去在沙皇面前夸耀。
整本诗集最喜欢的是第四部第二场,真是激情澎湃震撼人心。
2020年03月29日20:26:18
《先人祭》读后感(二):克日什托夫·涅什科夫斯基:《先人祭》介绍
《先人祭》介绍
克日什托夫·涅什科夫斯基
何娟 译
《先人祭》由四部分构成,这部作品的创作跨越密茨凯维奇整个人生。其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部是在诗人二十三岁、二十五岁左右写成的;第三部则创作于诗人移居德累斯顿的十一年后(1832)。
当我们说到密茨凯维奇的时候,有必要先提一下波兰的戏剧以及它的艺术雏形。波兰的戏剧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创新性的架构,既带有实验的性质,又体现了现代的思想。因此,《先人祭》也是一部没有完结的、不按剧目顺序创作的、只有片段式的开放性的作品。它是波兰戏剧艺术形式的精华和典范,对构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想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无法将之简化,用一段陈述式的语言概括出来。密茨凯维奇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世界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达自己,它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多元且多层面,一直在不断变化着的。对于这些变化,人们也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克日什托夫·涅什科夫斯基②
2015年6月
———
①扎奥谢是诺沃格鲁德克附近的村庄,诗人出生时属立陶宛,现属白俄罗斯。历史上波兰与立陶宛的关系密切,曾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立陶宛人同时是波兰人。
②弗罗茨瓦夫波兰剧院的院长。2014年,该剧院上演了由波兰戏剧导演米哈尔·泽达拉导演的《先人祭》;2015年,该剧应邀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上演。
《先人祭》读后感(三):易丽君:《先人祭》译后记
《先人祭》译后记
易丽君
诗剧《先人祭》是世界文化名人、波兰的伟大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传世名作,这次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先人祭》是我国的第一个全译本。所谓全译,指的是既包括《先人祭》全部正文,即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三部的完整内容,还包括了序诗和附诗。而且这一次出版,适逢弗罗茨瓦夫波兰剧院来华演出该剧,这是第一次有来自诗人祖国的剧团来华演出这部名剧,剧院的院长克日什托夫·涅什科夫斯基先生应邀为本书撰写了介绍。两件盛事凑在一起,相互配合,相互呼应,成就了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想起四十年前第一次翻译这部作品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时光荏苒,转瞬过了近十年。1984年我们应波兰文化艺术部的邀请到波兰访问,期间,华沙大学提出想聘请我留在该大学任教一年,经国内有关部门同意,我便留了下来。由于教学效果较好,得到了广泛好评,华大提出续聘一年的邀请,又经国内同意,就继续留下来直到1986年夏天。在这两年中,我除了尽力完成教学任务外,便抽时间翻译《先人祭》第四部,跑图书馆查找、收集资料为回国后编写《波兰文学》和《波兰战后文学史》做准备,帮《世界文学》向波兰当代大作家塔·鲁热维奇和波兰作协主席哈·阿乌德尔斯卡约稿等等。
说到第四部的翻译,前面说过,《先人祭》第二部展示了立陶宛古老的民间祭祀仪式以及一切亡灵的痛苦,剧中出现失恋者的亡灵,他的痛苦超过一切亡灵所受的折磨。然而诗人指出,人民的苦难远远超过个人的痛苦;个人幸福之上还有更大的幸福——人民的幸福,为了它才值得献出生命。而第四部则是诗人那段镂心刻骨的初恋和失恋的印证。古斯塔夫是维系《先人祭》全剧的重要人物,也是第四部的主人公:一个因失恋而心理有些变态、如痴如狂的年轻人,他在先人祭之夜向昔日的老师袒露心中的悲苦。他的诉说是那样的悲凉凄婉,又不时迸发出对封建等级社会的血泪控诉和反抗的呼号;是黑暗的社会断送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人。通过这个人物,诗人倾诉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使整部作品成了一条最纯洁的感情长河,一首撕肝裂肺的忧愤抒情诗。
考虑到身在国外,身边的杂事较少,工作条件也比翻译第三部时好多了,有可能把较长较美的第四部译出来,我决定先译了第四部再说。果然,翻译还比较顺畅,没有碰到特殊的困难,即使有些小问题,找人问一声也方便。
回国之后,事情就多了。除教学和教研室的事外,得抽时间为《世界文学》译些东西,忙于编写《波兰文学》和《波兰战后文学史》等等。直到2000年左右,林洪亮先生要编《世界经典戏剧全集》的东欧卷,我才把《先人祭》第三部的书和第四部的译稿交给他,和他译的第二部合在一起,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至于这一次对第二、第四、第三部之外的内容的补充翻译,由于适逢弗罗茨瓦夫波兰剧院来华演出,本书的出版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所以不得不动员更多的人一起来干。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振辉先生勇挑重担,承担了附诗中两首最长的诗的翻译(另外五首我和林洪亮先生已经在此前陆续译出);何娟女士承担了涅什科夫斯基先生撰写的介绍的翻译;林洪亮先生承担了序诗的翻译;剩下的第一部的翻译和译后记就留在我的名下。由于我目前仍在病中,不能过于劳累,还得照常跑医院,老伴袁汉镕怕我完不成任务,着急蛮干,就主动请缨协助我写这篇译后记。
是为记。
2015年6月
《先人祭》读后感(四):王炜:在西安美术馆密茨凯维奇《先人祭》朗读活动中的发言
在西安美术馆密茨凯维奇《先人祭》朗读活动中的发言
王炜
新东西乃是对旧主题的更为深切的复活。
——米哈伊尔·巴赫金
关于重复,伏尔泰的命题是有效的:“他将经常重复,直到人们理解他为止。”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
时间不多,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先人祭》的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通过了解和思考它,也有助于理解这部诗剧与我们,与当代思想场域的内在关系。
在这里,我还想建议大家注意到,一个诗人并不仅仅因“持不同政见”而面临危险,而是——因其诗艺本身面临危险。这不仅是理解“何为诗艺”的前提,也是理解20世纪一些重要诗人的前提,这些诗人影响了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中文诗人,以及今天我们选择作为朗读配乐的斯大林苏联时代的音乐家乌斯托夫斯卡娅,在这些创作者身上揭示的命运,首先是他们的语言艺术的命运,因为诗艺来源于一种不同于社会发展领域的动力,这也是一个传统而未完成的问题:“诗与哲学之争”。因此,我想请大家注意《先人祭》开头的引文,这句引文没有在今天的朗读中呈现,源于《哈姆雷特》:“霍拉旭,天地间有许多事,是你们的哲学未曾梦见的”。
我们都注意到,《先人祭》中充斥着精灵的形象。这些精灵扮演了精神力量的催促者、决断的催促者的角色,他们的声音肯定而带有命令性。由此,我们可以认出密茨凯维奇在诗学上的真正先驱:弥尔顿,后者也是魔鬼力量的定义者。我们也不应忘记,密茨凯维奇最早出现在中文里,是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然后,又在以后长时间中被遗忘。在《先人祭》第三部第二场,康拉德的即兴独白中有一个重要的诗句,也是我们为今天这次朗读活动选定的标题——“这正是力量显示的时光”。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弥尔顿的对抗性的力量,作为反对者的自然力量,是被隔断的,被华兹华斯那样的国家诗人所隔断,后者,是被驯化了的自然界的国家发言人。我们从小就在学校中接触到培根的箴言,“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句箴言,实际上是对大不列颠国家扩张政策的一句核心表述。这是一句大不列颠咒语,它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现代亚洲的形成。
人不能独自完成历史,只要是,仅仅只有现代军政权势这一种世俗力量存在,影响并直接人为生产历史,对‘人之为人’的观念进行长期系统化的扭曲,各种矛盾就会加剧,导致冲突与灾难不断。地缘政治矛盾的程度,正是现代军政权势全面接手和生产历史的程度。只有一种制衡力量,一种传统、悠久而又微弱的力量:精神领域的能力——诗、戏剧和艺术创造的能力。只有各种不同的创作者对‘对权力的撄犯’这一行为的继续存在,而且是创造性的存在,才能干扰现代军政权势对历史的影响力、生产和独裁,使它对现实世界的组合方式、对人的解释不能成立。我接受的立场是:创造力对抗世俗。这不是新颖的,但是一个并未完成、需要被再次激活的立场,需要经由各就各位的创作实践所再次激活。”(2014年6月,《亚洲》访谈)
不仅弥尔顿、密茨凯维奇的“力量”被隔断,所有近代作者的力量,这种普罗米修斯知识(一如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前言中所述),被现代世界共同利益潮流下的“世界文学”所隔断。在今天,不论对于文学、艺术还是思想领域,在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已经构建形成的情况下,“世界文学”事实上也是“力量”的管理者和驯化者。
著名的往往就是生僻的,比如《先人祭》这样的文本。所以,在第三部第七场“华沙的沙龙”里阿朵尔夫的长篇独白中,关于遗忘的焦虑被不断的、有节奏的重复。很显然,我们这次不是在朗读一个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文本,这些文本也许更能刺激起认同感。但是,文学批评家克拉默德在《愉悦与变革》这本书中所说,一个历史中的文本与我们的关系,不是自动售货机那样的关系,我们对它砸钱就行了。不是的,这种关系应该是被我们勇敢揭示出来的,事实上,文学的和文化的传统正是通过这种变动中的关系才得以延续。
最后,我想“重复”提出一个我认为已经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呼之欲出的问题。
2012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一系列反核游行中发表公开演讲,其中提到:“当局和媒体都做出一副好像已经解决了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隐瞒事实,装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功了,很多人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即使我们想要忘记,或者即使真的忘记了,核电站的阴影仍旧会执拗地保留,永远地持续。这正是核电站的可怕之处。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顺从地听从政府与企业的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客观上,物质上的终结了。”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次关于“何为日本人”的讲演。与此同时,从泰戈尔一代以来,印度思想家也在试图重新认识现代印度和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可能性。他们也在问,何为印度人,何为变动中的亚洲人。
谢谢大家!
2015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