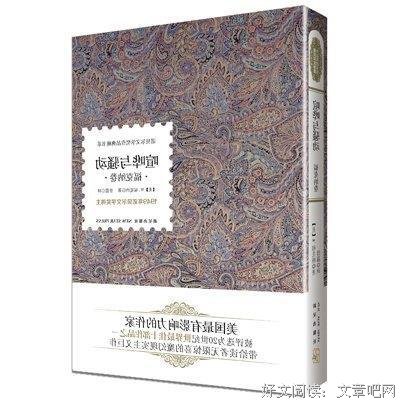
《公斯芬克斯》是一本由昆鸟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一):为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推荐而作
(书未上市,单向街未将《公斯芬克斯》列入候选名单。贴在这里。接下来还要写一篇正式的评论。)
7《公斯芬克斯》
作者:昆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5-12
推荐词:
在昆鸟诗中有一种鲜明的喜剧素质,用一把戏谑的锥子来钻开这个世界,充满激情,挖苦自我。放眼诗歌传统,很难找到一首诗能让人开怀大笑,这是他作品留给人最初也是最深刻的第一印象。不刻意文雅,不回避粗糙,而他这么做是有美学自觉的。昆鸟的诗能感人,句句落在实处。他从不屑于简单去写“生活流”,他也在诗中放入自我,但绝不是琐碎意义上的。他的诗气顺,尤其能诵读出声,势大沉雄,他的诗中没有同代写作中的大多数毛病:琐屑,谈玄,不入门等等。诗道幽微,昆鸟是那种一开始就写到正路上的人,这很不容易,从早期诗中他就有自己的声音,带有辨识度的修辞,这容易技穷和导致美学疲劳,但他一路过来,又突破了不甚成功的《肉联厂的云》和相当成功的《女性组诗》,这种美学雄心的确立对一个有内在考虑的诗人意味着成熟。
还可以印象式的列举。他最早印过一本《生活中的鸟》中有一首写乡村马戏团的诗,几乎以两页的篇幅重写了一篇河南百年孤独。“我们这些男人啊/ 一阵一阵地羞惭,一阵一阵地英勇/ 在一大丛女孩中间玩命地喝酒 / 头要裂开了,像个硕大的石榴”,我偏爱诗和生活中有如许的时刻,率真,欢乐而无所畏惧。“咔嚓一声/十二点/夜纹丝未动/今天和昨天/在我看表的脸上/交换了神色。”这是典型的昆鸟式伎俩,还挺“北岛”的。昆鸟诗中曾出现一个巨人,“是个悲伤的大个子,他不抽烟不喝酒,是人类的前夫,心地良善,是个没出息的男人。”这让人惊讶而无比亲切,动容。读其人,其诗,皆值得称道。我冒昧在这里推荐一本未及面市尚在印刷中的诗集,世人请谅解我举贤不避亲。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二):练习与作品
昆鸟在这本诗集的第一辑到第二辑之间有了进步,从《给黑大春》开始他找到了一首诗歌需要的语气和温度,而不是第一辑里面的混乱状态。所以这里我不理解第一辑放入诗集的意义,难道就是让人注意到《给黑大春》以后他的进步吗?在第一辑的诗里,我还看出了昆鸟是个爱听腰乐队的诗人,2008-2009年的诗里有显眼的《我们究竟要面对谁去歌唱》和《他们说忘了摇滚有问题》的痕迹。腰乐队是除了北岛以外昆鸟早期诗歌第二大痕迹,这种影响延伸到了诗集的第二辑诗作,他的诗保持了一种摇滚歌手式的自觉,但并非诗人的。这种自觉的偏差让他整本编年顺序的诗集显得太慢。
摇滚爱好者式的写作贯穿了整本诗集,他也访谈里自圆其说了,认为这是反文学化的实践,可我认为这是尚未在写作中理解自我的练习状态,相对于成为诗人写出作品。在这本诗集的第四辑以前都是缺乏意识的。我在前半本诗集的诗里读到了过多的宣告和梦想,“我要”、“我将”填充了不够饱满的诗歌空间,甚至好些短诗的全部内容就是“我要……我将……”。在第二辑、第三辑里面,昆鸟诗歌的篇幅逐渐拉长,并且引入了更多平克弗洛伊德歌词式的表达,一些诗完全是平克弗洛伊德歌词氛围的翻版,让人不由得有文字版《迷墙》的错乱感。这样的诗真的很是具有欺骗性的优美,因为当你忽略它是否真正独创时,你很容易因为它带给你的同质性的文艺青年享乐而感动,比如说记忆的模糊、梦境,这没什么难度。昆鸟的语言功底和想象力确实不错,有灵性,但他组织一首诗的方式常常过于随意(和他崇敬的北岛不同,北岛的组织是精心的,而昆鸟无疑粗糙)难听点说,是幼稚的。他避免自己的诗写得平白寡淡的方式很单一,就是跳脱出原来语境,插入新的一节:我想起一个人,我做了一个梦,除了加入新角色和加入梦境,他还会来一手“我将……我要……”。这其中没有注入情绪,也没有思想,只有溢出镜头的文字和不加自省的延展。这就是练习,还是懒惰的练习,对作品没有负足够的责任。我读昆鸟这些诗的不满和对读很多诗的不满一样,就是说这些诗它们几乎不能作为诗存在,它们不是完成的作品。这种写诗的练习应该只是初学写诗几年里的事,可是却几乎已经成了文青读者眼中诗歌作品的标准。诗歌作品它不应该是符合写诗练习的标准的东西,而是一种对写诗练习、对标准的反抗。这也是我对豆瓣文青乃至整个中国中产阶级诗歌读者的失望之处:欣赏的范围狭隘,关注的惊喜偏颇,喜欢华而不实,满足于审美表层的感动。
不过这本诗集的第四辑、第五辑开始变得好起来了,昆鸟或许是接受了王炜的影响而写出了《肉联厂的云》,以及后来的《给女性的诗》等作品。这些诗是够得上作品的,尤其是《肉联厂的云》称得上这本诗集独一无二的佳作。之前二、三辑里面每辑也有三到四首可称之为的作品的诗,但整体来看,从《肉联厂的云》开始,昆鸟才确实掌握了写出作品的方法。然而,这些作品依然不够耐读,不够经得起考验。即使昆鸟在访谈里很拽很动听也很有青春朝气的创作谈也不能掩盖他进步的缓慢,他宣称自己的反文学化实际只增加了他许多诗的文学腔调,他反对的裹着衣服也确实成为了限制他创新的衣服。谁都可以说出提倡这个反对那个的诗观,但是作品最后来呈现的它自身空间有多么开阔,是否朝向无限,北岛式的“英雄主义”也不是“一切”、“夜”和“光”这类的大词来在今天重申的。如果再严苛一点说,王炜只有一个,王炜式的诗歌也只有王炜能够自我复制,《肉联厂的云》有多少价值也很难言。在这本诗集中,昆鸟给我的印象是他和当今的许多诗人一样,有待从漫长的练习中脱离,去写只有他能写的作品。
2019.7.26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三):斯芬克斯在歌唱(一篇删掉的代序)
本来想写一个序言,但实在不知道能说什么。最后我想解释一下书名,结果写飞了,有成了个作品,如果把它当前言,不但什么都解释不了,还新添一层迷惑。放在这里,给大家读好玩吧。另,请允许我给自己一个三星,因为如果不评价,文章就发不出来;如果给四星、五星,有欺人之嫌;而一星二星,则纯属自欺,如果我觉得它差,就不会把它拿出来。
一、
斯芬克斯其实有一双翅膀。但她却跳崖自杀了。
人在自杀的时候,也会选择坠楼,因为人没有翅膀,所以无法对抗重力。斯芬克斯跳崖时,一定把翅膀抱得很紧。所以斯芬克斯的自杀,是时间之内最坚决的求死。
二、
斯芬克斯其实一直在等死,但死也是个很无聊的事情,所以她变成了一个赌徒,想把死变成一个筹码。于是,她设计了关于人的谜语。于是,死就成了某个赌局(自己与自己的赌局,一个是该死的斯芬克斯,一个是该活、活该的斯芬克斯)的结果,变成某种程度上的被迫,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这样,死就有意思了,至少似是而非地制造了价值上的某种紧张。斯芬克斯总得为死找个理由。
人的生命进程有什么玄秘可言呢?怎么配成为一个谜语?而即使这样简单的猜谜游戏,那个不该死的斯芬克斯还是一直在赢。
在吃掉那么多人之后,斯芬克斯还是蹲在那块石头上,既没有变老,也没有变年轻。她想为人类哭泣,但是她没有,而是将那种悲伤转化为残忍,因为与残忍相比,悲伤是一种过于人化的情感。
三、
也就是说,斯芬克斯是有情感的(据说,她是因羞愧而自杀的)。
但我无法想象她有情欲,甚至无法想象她的性别。因为,在象征意义上,秘密、真理,本质上都是厌世的、无性的。
作为独一无二的怪物,斯芬克斯打算消灭关于自己的一切。然而,她没能消灭人所赋予她的寓言。而对斯芬克斯来说,谜语和死亡都没有寓意,其中只有恶作剧。她的自杀似乎是某种启示,但人们却永远弄不清楚它启示了什么。
四、
最初,这并不是恶作剧。斯芬克斯自杀的最初情感动力来自羞愧。
传说,她是厄喀德那和自己的儿子俄尔托斯所生。这种身世在诸神世界并不稀奇,更算不上离经叛道,但斯芬克斯觉得这不正常。她太具人性了。她熟悉人的伦理世界,一生都在想善恶问题。
斯芬克斯开始反思知识问题。如果她不具备这些知识,那她就成了一个快乐的吃人怪物,心里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饥饿。只有饥饿是纯洁的。他完全可以因纯粹的饥饿而无罪,而摆脱所有寓言,摆脱对游戏的欲望和执着。
于是,她开始恨人类的知识,憎恨人类,憎恨自己掌握了这种知识。所以,斯芬克斯死于自我憎恨。她到死都没有理解的问题是:很多人,竟然有爱自己的能力,至少有过爱自己的瞬间。
五、
很多很多年后,神类学家考证出,俄狄浦斯是斯芬克斯的哥哥兼父亲俄尔托斯,而斯芬克斯真的是母的。
俄狄浦斯想请自我放逐的妹妹兼女儿回家,结果却害死了她。
他在一处断崖上找到了斯芬克斯。这个可怜的四不像正坐在最危险的石头上,朝一轮硕大的夕阳吐着唾沫,还不时用她脏兮兮的翅膀揩揩嘴角。但总体来说,她看起来还是娴静的。在她的周围,有一种高贵的、静谧的、不可凌犯的悲伤。怎么说呢?即使在这样的怪物之死中,也会不缺乏庄严。
俄狄浦斯已经预感到斯芬克斯不会跟他回家,因此远远地望了一会儿,就掉头准备走开。这时,他听见,斯芬克斯竟然开始歌唱。
“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下午三条腿,请问,加起来是几条腿?”
很明显,斯芬克斯在死前已经疯了。这种疯狂有时候看起来像是装的,短暂、突然,却致命。在一个无法容纳英雄的悲剧中,斯芬克斯无可挽回地成了怪物,成了一个多余的启示。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四):昆鸟的诗,或“新语”如何可能?
——对《干燥剂》的评论
《干燥剂》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不足五十页。然而较短篇幅的阅读已足以使读者在头脑中确认一种“风格”:就像诗集的标题一样,它关系到工业、卫生方面的暗示,关系到中文语言的“基地”——它的大陆性的深层结构。同时,就像“干燥剂”本身是一种“治疗”用品一样,诗本身也提供了清洁或“疗救”的功效——通过把病灶暴露在读者眼前的方式。 和之前的诗集《公斯芬克斯》一脉相承,昆鸟已经具有风格的稳定性和沉淀性。他的诗在相对温和的句法结构后面,蕴藏着地幔中被挤压的岩浆般的情绪和孤绝冷硬的质地,甚至暗示褶皱般的肌理——我们世界中的病患经由文字的消化不良呈现出来。 当代诗人频繁地使用反讽、巧智的修辞,昆鸟的诗在重新提示这类修辞的初衷。反讽始于一个诗人对于日常生活的不满——对生活不满很容易,而对生活的日常性因素的不满却是需要眼神的——它需要在陌异之间建立熟悉。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最庞大的部分(而不是经过加权之后“最重要”的部分)的关注,使昆鸟的诗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而这种激进性又是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实现的,巧智为文本内含的暴烈进行了脱敏手术。 比如,中国近四十年来低端工业化的事实,农业人口的庞大基数和凋敝的农村现状,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和其中的种种紊乱,全球化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冲击……昆鸟少有地把郊区的工厂、地下停车场、充满哥特气息的青旅写进了诗中,并且带有这些事物特有的“非诗的”气味。对于“我们跑到义乌,整吨批发手串和唐卡/在拉萨摆起了地摊”(《新神》)这类现象,“不纯粹的诗”和“诗的杂音”(见《原诗》)可谓对症要下的处方。昆鸟诗歌中捕捉到的许多词,公民、研讨会、老朋克、裹胸缠足、奴性、小农身份、融资、批发,都具有潜在的、充满张力的语义对话背景,这些词要么此前只有实用性和“使用价值”,要么被意识形态进行了强制的转基因处理,或者是被网络文化“格式化”了,此外还有古典的、翻译的、民间的、诗人根据语言的化合反应机制自造的语言,昆鸟逼使读者直面语言的截肢的、碎片化的现场。其作为“不纯诗”不在于其政治的倾向——在当代新诗中,对于前三十年的另类政治实践的满不在乎的戏谑,或者对当代“贫富分化”事实的掺杂着无能为力的调侃,成了一种规定动作,然而诗人如何激活自身的感受力,拓展感知边界,作出某种超出阈值的暗示,也许,偶尔发出一两个爆破音,把读者带入某种极端气候?昆鸟的诗有效地揭示了语言内部的层积性和断裂感,就像一个人需要同时通过犁铧、传送带、电脑键盘、青铜器工作,我们语言的同一平面的使用者是自耕农、福特制工人、赛博个体户和奴隶,在昆鸟的诗中,我们直接遭遇了语言的年代感。 在中文的当下语言中堆积着许多已经无用的事实、过时的情感、不同立意者穿凿附会的痕迹。昆鸟的诗就像是一个潜伏着内爆可能性的盒子,在一定的高压下实现了语言内部的次元破壁,于是伪造出一种“七拼八凑的合度感”(《原诗》)。他的诗是介入的、反介入的、反-反介入的。比如,如果说溢出在诗的表面的首先是政治,那么前现代的政治、革命的政治和后革命的政治是镶嵌在一起的,共同拥堵在诗歌的引文碎片之中,并在它们内部产生分子级别的对话和追问。 这也许就是昆鸟所提供的“新语”。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生活的现场生长出来的,背负着沉甸甸的负债,具有植物般的地理性和时间性,因而其根茎、枝叶的延展无法预测,时常欹侧。
可是,我们是那么想要说话,可是 我们没有语言了,因为我们的语言 也是一种被我们仇视的财产,在语言问题上 我们也成了代工厂,我们想要说出的语言 已经是国有语言:“无产者”(《寂静》) 这一“新语”直接受制于一九八四的事实,它感受到并内化了后者给言说带来的重重限制,因此,诗歌的反制措施本身就具有“新语”的审美特征:它直面挫折,不断碰触到语言的南墙,把残存的回音收集起来,作为婴儿咿呀学语的材料;诗歌不再致力于廓清定义,而是关注语言的不及物、真理的冷冻状态,它的清理工作不是拂除语言表面的淤泥,而是把被淤泥覆盖的现场展示清楚。引用昆鸟的诗,那是“厌恶那些不明不白的合理性”(《圆厅》),直面语言的滩涂写作,避免其返祖般的甜蜜。昆鸟实际上告诉我们,“新语”是一种迟暮的、斯多亚式的语言,它已经失去行动力和早年的朝气,只能进行游击式的、以毒攻毒的报复,如果用比喻来说,那是一只“语言跳蚤”(《圆厅》)。 昆鸟的写作现场呈现了半杆子工地的未完成性,它回避去预示未来完整建筑物的宏伟,看上去更像是废墟而非初生儿。通过文字的施工现场般的爆破性,诗人表明自己并非熟视无睹,而创作的艰苦,通过作品的生涩(汗水就像是一个个肉体之词)和——用作者的话说——“生冷拙怪”的风格,以及梦呓般的对沉思片断的截取,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写作“困难”的说明书。困难意味着生产的暂停、机器的失效、周转的不灵、货物的堆积、库存的不足…… 昆鸟对于人的身体的泥塑性的体悟是独创性的、也是深刻的,另外就是关于晚霞、病变、黄昏、大限将至、世界的可分解性……它蕴含了一个诗人持续的不安、刺动和思考。他把我们引向世界的有机状态背后的无机状态,有序状态背后的熵增状态。正是因为肉身的可被侵入,异己之物便作为无边无际的在场朝各方涌现,使诗人提出对感觉的不信任投票。 我们“这些有了权的人啊”(《新神》)需要“新语”,不仅如此,还需要新人、新神、新情人,总之,一整套对现有方案的替代计划。然而,“难道我们不是那终于被世界等到的人/既不是新人,也不是末人,只是永不靠岸的愚人/那既受供养又受驱逐的讽喻侏儒……”(《寂静》),这几行诗之后确实需要打一个问号。《干燥剂》可以说是对“讽喻侏儒”的发生学考察:它是如何地营养不良,它骨骼的钙质是如何被压缩,以至于无法长出均衡健美的身体;它是如何失去了直接命名的权力,而不得不调动讽喻。
2018.夏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五):好的虚构:浅谈昆鸟诗中的自传性
昆鸟是反对将自己的诗当成自传诗来读的。他曾经说过:“我从来不写只纠缠自己的主题,个人是不重要的。我永远没有我自己。”但我逆昆鸟自己的意志,专门要谈他的自传诗,并非有意与诗人对自己的看法相左。在我看来,自传诗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诗的形式写自传,姑且称其为“小自传诗”;另一种则是以通过对个人经验的书写,以追求更大层面上的价值与意义,姑且称其为“大自传诗”。
前一种自传诗当然并非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从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前一种自传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诗歌表现题材的拓展,即对日常生活的拓展。但是,倘若昆鸟的“自传诗”是前一种,那恰恰是他所反对的,我也就不需要在这里专门来谈了;但幸而我要谈的昆鸟的自传诗属于后一种。
对于后一种昆鸟不想以“自传诗”来称呼的自传诗,他是不反对的。他曾经说过:“即使在写个人的主题时,也把个人的尾巴砍掉。希望他的有效性是更大的。要想让私人的东西产生有效性,必须找到共同的。很特别、很角落的经验的呈现,使得诗歌的公共性完蛋(或终结),那么你所写的东西也就失效了。内在生活不重要,我们必须将这个东西看成更加有效的,更加对客观世界,跟他能发生关系的最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个时候诗的真正质量才出来。”
在这里面,昆鸟指出了“个人的主题”即所谓自传诗(的元素之一)真正所要呈现出来的面貌:一是从个人起,却不能以个人终(“砍掉个人的尾巴”),二是这种由个人而来的有效性应该是更大的,三是有效性的产生必须上升到公共性。这里举两个似乎不太恰当的例子:
一个是《姑妈的葡萄》。这首诗的副标题是“好的虚构”,因此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诗中的“姑妈”、诗中对“姑妈的葡萄”的描写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性。但这种“虚构性”恰恰是一种公共性的体现,它必须是综合了诸多农村女性(尤其是拥有姣好身体的女性)的不幸的生活的基础上才得以呈现出来的。当然,如果这首诗呈现出来的是真实的,那么其中所要面对的道德感、伦理感,也不再是个人的感性的经验所能囊括的。
另一首是《天要黑了》。我将它总结为“一次真实的体验”,因为诗中的许多描述也是很多人幼年时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坟上长出的植物/露给我们灰色的叶背/小子们,把书扔在荒野吧/采一颗即将变黄的蒺藜/开始为此刻的惊慌歌唱……”如果说这些都是对幼年经历的描写,那么这首诗接下来的诗句,则无疑更像是多年以后回忆这次经历时产生的情感:“我们,满腹尸骨化成的土/满头死人嚼过的雪/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连同脐带一起烧给大地……终于把世界赶到针尖上了”,这种情感无疑是在有了更多的人生体悟之后才能生发出来的,它绝对不是对那么一次小小经历的追忆,其中有着更多关于生命的体悟,而这种体悟有一种共同性在里面。
其实说到这种形式的自传诗,中国古代诗歌有着非常强烈的表现。古代诗歌在儒家诗教的熏陶下,讲求立功、立德、立言,立言无疑是在立功、立德不能之后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手段,而其表现对象也是关乎国家、关乎民生的,即便是在表现个人生平遭遇非常突出的诗人那里也是如此。从《离骚》以降至于唐代,无论屈原、曹植、阮籍、杜甫等,诗人在记述个人生平遭遇的时候,往往背后都有着非常大的时代背景,诗人们虽然呈现个人,但却是对整个时代来发声。但我想说的是,昆鸟是自传诗里尽管有着同样的对社会现实、对历史的关注,然而其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就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在昆鸟的诗里,这种大自传诗里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人比诗人更重要;其二,反思的精神。前者是昆鸟一切诗歌而不仅仅是自传诗的前提,后者则是昆鸟诗歌所呈现出的与众不同面貌的最重要手段。
说到人与诗人更重要,在昆鸟看来,“诗人的任务就是呈现他的独特感知、领悟”。当他在谈到诗人相较于众人的特殊性的时候,他又强调“诗人的特殊性只存在于自我要求的层面,首先,是作为合格的人的要求,其次,是作为合格的诗人的要求”,换言之,合格的诗人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人。昆鸟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合格的人”,这似乎也并非诗人的义务。指出什么是合格的人,这是属于启蒙的义务,而过度的启蒙造成的结果是,“已经将谜全部解完了,意义也没有了,启蒙的最后是虚无主义”,这也是他将这部诗集命名为“斯芬克斯”的原因所在,他想“重新组织谜面,让意义回来”。尽管可能拒绝对合格的人给出标准,但是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合格的诗人的标准:“诗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拥有现实,他要携带精神性”,“(诗人)需要另一种骄傲——纯粹言说的骄傲”;或者说,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诗人,然后把这些东西出色地讲出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诗人,其实应当先有内在之气,而后发而为诗;先成为一个人,再成为一个诗人。这在江汀的《自述》诗里也曾经提到过:“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又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人”与“诗人”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交缠往复、互相促进的关系。
如果说关于“人”与“诗人”还存在普遍性的话,即至少我们中间已经成为共识了的话,那么反思精神则成为昆鸟诗歌独特性的体现。面对现实世界,昆鸟说:“我必须接受它,哪怕是忍受。因为,我不能不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这就是人的悲剧。如果我完全抛却反思,认为这里的秩序是理所当然,或者,连这种‘认为’也没有,我也就没什么好忍受的。”后来,他又更明确地指出:“我需要对更普遍的问题发言,同时开始反思我们这一代人的处境。我对个人境遇、身份也开始有了一点自觉的认识。”在昆鸟的这段话里,恰恰可以看出来,“个人境遇、身份”这些自传属性的元素在昆鸟的诗中得到更多的呈现,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也是基于这一点,使得昆鸟的自传诗的讨论得以成立。这种自传诗,与诗人对普遍问题、对这一代人的处境的理解密不可分,诗人正是从个人的境遇、身份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而这一点,用昆鸟的话说,正是从《肉联厂的云》开始的,而《肉联厂的云》正可以且应当作为昆鸟自传诗的代表作。试分析第一部分。
诗的一开始:“我们出生时天还没有黑透/胞衣堆成的晚霞让天空也显得拥挤了/农业文明的最后一口气咽了很长时间”。一开篇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尽管诗人可能要说“我”,但“我们”无疑比“我”更具有普遍性,一个“我们”将同一时代的人全部囊括在内。“出生”意味着新的开始,但新的开始面临的却是黑夜,尽管“天还没有黑透”;面临的也还是一个“拥挤”的时代,不言而喻;更为悖谬以形成了张力的是,“我们出生”面临的却是“农业文明的最后一口气”,“农业文明”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或主体,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在苟延残喘,似乎要迎来了新的文明时代。
然而诗里并没有这么继续下去,而是写到“我们”的成长,由出生而长成童年,却是“仿古的童年”。原来,农业文明的最后一口气还在,只是已经不再是真正纯粹的了,而是“仿古的”,是赝品(这种赝品持续至今),农业文明成了一种虚假的象征,“村庄和田野仅仅留下了一种情绪”“一种记忆的炎症,时不时就来一次”,深刻的比喻。但紧接着,诗风陡转,“谁讲述田园,谁就该扇自己的耳光”,诗人深深地意识到农业文明早已逝去,不能再成为抒情的主题,让自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所有诗歌一连用五个“不要”来坚定自己的表达,至“不要杜撰自己的身世,不要修正自己的血统”而高涨,而做一个小结。接下来就是非常畅快的“反田园诗”“反农业文明诗”的叙述。
《公斯芬克斯》读后感(六):“但那光是黑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形象,而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从那个精神形象中分割出来的一份复本。在昆鸟的诗集《公斯芬克斯》中,那个形象十分鲜明。整本书的从头到尾都存在着尖锐的心理状态,第一辑中收录的短诗《复仇》是这样的:“我要重复地走向日落∕让皮包着的骨头嘎嘎作响∕让高窗里的人们∕都听到我骨头的叫声∕像一根忧伤的红刺∕闯进人类郊区的暮色”。在昆鸟的每一首诗中,那根“忧伤的红刺”都恒常地存在着,它可能生长在诗人的嗓子眼里,使诗人获得写作冲动。到了诗集的第三辑,《再没有少年》中又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再也没有少年,再也没有少年们∕面向薄暮时分的郊区呐喊了∕他们为生命找到了理由,咳嗽着∕他们推开屋门,日历上已经长出了蘑菇”。我们想到,昆鸟曾是一个如芒在背的少年。
我想向众人描述昆鸟的形象,但也许一开口就有错误。在他诗集的新书分享会上,昆鸟对读者和朋友们说,他的诗歌文本没有任何自传性。也就是说,虽然“少年”的形象在书上多次出现,但也许那只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文学场景?但作为他的友人,我知道郊区和暮色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北京最西边的一座小山边上,在那些时候他比别人更靠近落日。他的住处一度是几位青年诗人聚会的据点,我们在那儿做过大量的交谈。
昆鸟的第一批诗作写于2006年,现在主要收录在第一辑。两年前,诗人秦失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昆鸟写出的第一批诗歌,一上手就都很成熟,风格鲜明,这在诗人里是少见的。这说明诗人在开始写诗之前就已经修炼有成。大体上,这个过程就是感知、反思、领悟,最终形诸笔墨的过程。”秦失的判断十分准确,正是那个“感知、反思、领悟”的过程非常重要,它使得昆鸟的初试啼音之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早期写作”文本。
在2006年底,昆鸟的修辞已然十分紧张而微妙。《突然的理智》这首诗中有精彩的段落:“我猜他是白昼的平庸剪影∕是我在睡眠中孤独奋斗着的对手∕热情的灰家伙∕日历上流出的无名日子∕轻薄而活跃∕‘再见’,他说∕‘再见,丑角’∕我嚅嗫着∕同时学会了背光行走”。前五行的一连串比喻,让人仿佛听到北岛和多多的嗓音,而在后四行的简单对白中,寥寥数笔就呈现出复杂的心理状态,这让人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昆鸟一定是互相懂得的。
昆鸟是从八十年代的乡村成长起来的少年,我们想到三十年前,一个聪慧的心灵进入广阔、粗砺的成长历程,只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生活,才会锤炼出来敏感而又硬朗的诗人。当然,在这本诗集面前,谈论生活经验也许几无必要。昆鸟有广泛驳杂的阅读经验,在一群青年诗人朋友中间,大家交往、相知,在阅读上有相似之处,但各自的写作通往不同的方向。他的阅读经验并不构成他的写作资源,只是参与、渗入了他的精神重量。这一点使得他的诗句有时虽然短促,但从不单薄,它们足够沉重。
从2009年开始,昆鸟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时期,在一批精湛的短诗作品中,他完成了对自己风格的确认和强化,这些作品遍布在书中。例如在《天要黑了》这首诗的结尾,他“终于把世界赶到针尖上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在昆鸟这里自然地绽放,正如在海子那里曾经绽放过一样。可能在很久以后,人们会知道,把他们俩相提并论是恰当的。“大地的深处走着一个孩子∕大地将这个孩子当做灯笼”,“我常浑身冰凉地醒来∕嘴里塞满了泥土”,这几行诗来自昆鸟的《无题》,正如海子在《村庄》里吟唱的:“夜里风大 听风吹在村庄∕村庄静坐 像黑漆漆的财宝”。
不过,像上文那样比较他们俩的诗歌意象,也许是没有意义的;更值得比较的是,昆鸟和海子一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语法。这语法植根于自己的审美经验,从诗人的生命意志中生成。他将修辞和情绪统一起来,有时候修辞就是情绪,有时候情绪就是修辞。显见的是,昆鸟捕捉瞬间的能力非常强,仿佛能够原地起跳、一跃而起,如同某种运动天赋。他对待警句的态度不卑不亢,它们被看似随意地放置在诗歌结构的某一个部位。他的诗歌语序里没有简易的逻辑,每一首诗的写作肯定都是困难的。甚至,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奇迹,可能他自己都难以在另一个时刻写出类似的思索。西蒙娜·薇依曾说,体力劳动就是每天死一次,对于昆鸟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写诗当然是体力劳动。在他最好的几首诗中,真理浑然天成。要谈论他的语法,还需要大量地摘引他的文本,在这里我无法详述,只能提到这几首诗的名字:《我将再一次看到清晨》、《小姨》、《无题》、《子夜》、《傻爱情》、《月亮》、《佛陀之子》和《冬天与骨头》。
我所提到的真理,并非向上指的、玄幻的真理,而是关乎实际生活的真理。那是具体的、可被罗列的,同时绝对高尚的经验。昆鸟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结束了某种蓝色时期,进入了艾略特所说的二十五岁之后的岁月;更何况,昆鸟本人就是在二十五岁的年龄开始写作。昆鸟对当代诗歌的四十年流变明烛于心,他有自己清晰、老道的判断。例如,他屡次在聊天时说到,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应该重估朦胧诗的价值,而不是将它弃若敝履。而十几年前的“盘峰论争”对他的影响是,他的诗歌文本是口语化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昆鸟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总结了他的前驱者们。
在他最近撰写的一篇诗歌批评中,昆鸟谈论当代诗歌与同时代人。他指出我们的境遇三种:其一是“对大话语的全盘拒绝”,其二是“这一代的写作者往往很难辨清自己的亲缘关系”,其三是“趣味、审美主义统治了当今的文学”。通过文章和发言,昆鸟直截了当地抵达当代问题的核心。他明白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四围的地形,作为当代诗人他有着明确的诗学抱负。这抱负是他所认识到的历史强加给他的,而他的身躯必须承受它。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不紧张,不可能不焦躁不安,以至于连续几个夜晚无法入睡。想到这一点我再重新看他的作品,它们终究显得是自传性的,虽然经过了诗歌技巧的变形。而行文至此,我有必要把昆鸟一分为二了:短诗的昆鸟和长诗的昆鸟。清楚他的历史性视野,是恰当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阅读他的《肉联厂的云》。
《肉联厂的云》收录在第四辑中,它是诗集中的唯一一首长诗。事实上,在当代诗歌中,长诗与短诗并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我之所以确认这是一首长诗,是因为它的致密和沉重,昆鸟的长诗虽然只有一首,但却能够从他身上取走一半的重量。在《肉联厂的云》中,修辞的问题已经退隐了,也因为它在短诗中已经纯熟,足够他来锻造更庞大的物件,呈现自己对当代生活的认识,用诗歌语言来排列码放历史哲学。全诗共分七节,第一节开篇是“我们出生时天还没有黑透”,写到当代生活的背景和“我们”的身世,“谁讲述田园,谁就该扇自己耳光”,在这里“土地已经避孕,种子却照例被埋下”。第二节描述我们的现状,它就是“伪秩序,伪道德,伪文化”,“流氓的化学是无坚不摧的∕流氓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它历史性地嘲弄了我们的愤怒∕又把我们的失败摊派给辩证法”。第三节用抒情诗体进行反讽,我们“从许多层梦境里醒来”,进入了信仰和价值观的崩塌时期,“黑着脸的天空突然来到面前,怎么办”,但没有人引领我们,只能狂欢式地胡乱呼喊“全国人民大撒把万岁”。在第四节,“把先贤祠改造成宠物商店之后,我们获得了终生有效的道德免疫力”,我们又再度适应了这样的生存环境,“先是习惯了,接着就变得熟练了”。最后三节篇幅均稍短一些,也因为全诗的逻辑在第四节走到了尽头:第五节提到我们处在“第五时代”,这是塑料的时代,“我们已能塑造一切”已经成为世纪病;第六节哀叹我们丢掉了枷锁,如同丧失了坐标;第七节中的“我”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状,“这儿的天空让我早早地就瞎了”,而“我们的孩子还将在大地上迷路”。全诗以悲剧结尾。
早在1940年代,沈从文等人就试图通过长篇小说的写作,来寻找自我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而如本雅明所说,历史天使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肉联厂的云》并不是完美的作品,它在结构上并不均衡,最后三节诗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变得仓促(这压力来自中国的未来)。但虽然如此,在大部分写作者沉浸于自己的个人生活、私人情绪的时候,这首长诗的严肃关怀和高亢音调,使它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中闪耀着光芒。需要补充说的是,这里的严肃和高亢有别于海子式的长诗;昆鸟的诗歌建筑扎实地建立在地面上,他的现实感来源于“盘峰论争”之后中国诗歌的自我训练。
此外,《〈鹿苑〉及其阐释》也是昆鸟的一首重要作品。这首诗我曾听他公开朗诵过,当时的诗名叫《为自己建造〈鹿苑〉,并接受其中的屈辱》,昆鸟是一个反复修改、炼句的诗人,由此可见一斑,他在斟酌之后,还是将戏剧意味更浓的“建造”一词删去了。这是一首关于审美的诗,也可以看成是昆鸟虚构的一种个人简史,它的修辞和节奏中有吸引人的神秘气质。早期作品中的紧张感,到这时已经炉火纯青,像一张紧绷的弓,随时可能会被某个意外的东西触碰,它只能是昆鸟式的。在书中附录的作者访谈中,他也对这首诗做了详细的解读。
昆鸟是这一代青年诗人中特点鲜明的一位,我们的整体美学倾向,我们的哲思、超验性,都在他的作品中一览无余。出于某种反叛精神,他将诗集命名为《公斯芬克斯》,这来源于他的《灵魂目录》诗中一句无所用心的“斯芬克斯是母的”。这种即兴的、随意的态度,来源于他对正统话语采取的消解立场,但作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这种消解使他身上产生自我对立,这也是他紧张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主动地将自己抛掷进入当代诗歌的四十年场域,在谈论同时代人的文章中,他还说,“诗歌不是个人精神的后花园,而是前哨,祝我的写作早日成为诗歌总进程的炮灰”。这并不是言过其实,须知在漫长的潮流中,我们的有效期往往是由我们的历史境遇决定的,我们都将融入莱奥帕尔迪式的无限。这令我想起《灵魂目录》中的另一段诗句:“我在一种奇怪的光里看见东西∕那种光在我的屋子里住下了∕我能看见一切∕但那光是黑的”。
201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