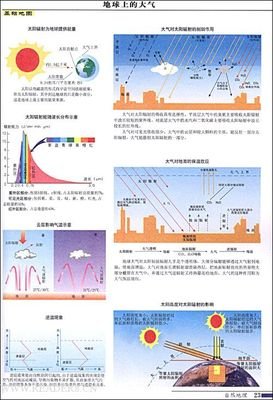
《地图册》是一本由[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图册》精选点评:
●原本是博尔赫斯与玛利亚·儿玉游历世界时的配图文字,但缺少了照片大打折扣;幸好保留了一贯的主题——世界处于上帝的大梦中,以及反复表达对圆形、老虎、黄昏的喜爱;拥有奇特激情的爱尔兰,适合幸福的日内瓦,美妙的威尼斯,克里特岛的迷宫,赋予这些地方以人文解读方式,“神话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博尔赫斯对王尔德真是感情复杂啊,一遍遍地提起他多蹇命运,也流露出对其作品的欣赏;书末儿玉的后记可真美:“如今我在这里铸造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
●“朋友圈旅行随想”没有带图实在令人憾缺,按道理只能给三颗星。但玛利亚.儿玉写的“后记”实在太美了,简直把这本书的光芒都压过了!美不胜收,感受一下:“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里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萨……博尔赫斯和玛利亚、普洛斯彼得和里埃尔,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
●“美是具体化的和谐,是把微微的海风永远凝固在衣裾飘拂的褶皱上” “如今我在这里锻造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
●组成我们的不是肉和骨,而是时间,是短暂性
●不旅行时,我们读万卷书,倚凭纸页、词句和想象力去认识历史;旅行时,我们行万里路,带着之前所有阅读的时日所贮存的学问、记忆与精神力量去见证历史,目击历史,感受历史。 P.S.后面的篇章不如前面的好;但仍旧不得不感叹博尔赫斯真牛,短短几行字便可营造出史诗感;旁征博引则引人浮想联翩,尽管后来对此有些疲劳;此外,这本小书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向我们证明了:每一个瞬间之所以珍贵,正在于它们都具有化身永恒的潜力。
●今天是博尔赫斯诞辰120周年,特地抽出时间来读这本诗歌随笔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对博尔赫斯而言,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镜子、老虎、老人的眼睛和时间。王尔德说,人一生中的每一瞬息既是他的全部过去,又是他的全部将来。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每天包含着许多瞬间,瞬间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每一瞬间有它独特的悲哀、喜悦、兴奋、腻烦或者激情。
●诗集11(44),1984。 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 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 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
●惊喜的是博尔赫斯夫人的后记写得真好,太令人羡慕和自卑了。
●定位为诗集有点说不过去,几乎都是散文杂记,好像还是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和诗歌之外的题材,觉得缓缓讲述很能安抚人心,读来是一种享受和趣味。
●读陀哥途中消遣一下。 之前看过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两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在于那本是纯虚构,这本是梦境➕现实组合。读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是熟悉的博尔赫斯。
《地图册》读后感(一):【2020/02/04】『文盲式读书:89页的博尔赫斯要看三个小时』
我特别喜欢《在拉丁区一家旅馆口授的笔记》中,博尔赫斯对于王尔德的分析——“王尔德说,人一生中的每一个瞬息既是他的全部过去,又是他的全部将来。果真如此的话,春风得意和文学创作旺盛时期的王尔德,又是监狱囚禁时期的王尔德;牛津大学和雅典时期的王尔德,又是一九〇〇年几乎默默无闻地死于巴黎去拉丁区阿尔萨斯旅馆的王尔德。”——那我是不是可以如此想象,此时双目失明却依然以口授形式进行创作的博尔赫斯,也是二十六岁写下了《面前的月亮》的博尔赫斯;和玛丽亚·儿玉愉快生活在世的博尔赫斯,又是年轻时不畏强权写信抗议的博尔赫斯。他们一摸一样,还是讨厌斑点但是不反感条纹,因为博尔赫斯喜欢老虎但是不喜欢豹。
我喜欢这样的孩子气式的假设。
读博尔赫斯的时候依然觉得自己是文盲,但是文盲式阅读已经进行了十几场,所以反而开始有了内心的笃定起来。
这样的心境变化似乎让我更好地沉浸在了他的文字里。舒缓的、悠悠的、睿智的、思考的、梦境的、奇诡的、醒悟的。“空间十分开阔,悠闲的风像缓缓的流水那样带着我们飘荡,抚摩着我们的额头、面颊和后颈。”“武器多如牛毛,整个世界濒临死亡。武器多如牛毛,死亡不是如如何选择。”——原来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看不到索性就放弃的文字里,还是隐藏着诗人的柔情似水,以及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忧虑思考。
难怪我一直看不懂博尔赫斯,也不能很好地去评价他的作品。可《地图册》却给了我一种继续读下去的信心。
也许就好像他最后口授王尔德的那一段话:“我无法对王尔德作出技术性的评价。我想起他时就像是想起一位好朋友,我们从未谋面,但熟悉他的声音,经常怀念他。”
我没那个水准胆敢也能够对博尔赫斯作出技术性的评价。我想起他时就像是想起了一位远方的师长,我们从未谋面,我亦从未知晓他的声音,可我感受过他的文字,并经常佩服并且怀念他。
《地图册》读后感(二):画外交响乐
打算读博尔赫斯,手头有他的整套丛书。从哪本开读,对一个文学门外汉来说,既不懂也是无所适从的事儿。《地图册》原本以为导读的意思,打开才知道原来是他和儿玉旅游照片所附的文字编辑而成。于是乎,简单的认为应该是可读性很强,类似于马可波罗等等的东东。可是,真读起来,并不如此。
博尔赫斯的《地图册》其实就是一部画外交响乐。
《地图册》一个又一个画面,由于缺少真正的画面,少了形象,但不乏生动。说句公道话,这本小册子,的确不好读,尤其是对一个既缺乏文学修养又不太常旅游的我来说。不只这些,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姿态。
这里所说的不好读,当然不是书不好,而是自己水平不够,我给了此书五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作为阿根廷的大文豪,在书中几次提及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不能不让一个中国读者感觉些许的亲切感,至少我如此。
《地图册》不只是一部画外交响乐,更是一次思想文化的旅行。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和他的《文化苦旅》。显然,《地图册》绝不同于《文化苦旅》,博尔赫斯也与余秋雨先生相异。大概余秋雨先生属于学院派,博尔赫斯则肯定不是,至于他是什么派,我其实因为孤陋寡闻而不知道。
书中通过一个个城市,或者场面,或者人物典故,或者其他什么,告诉我们相关的样貌,甚至样貌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不是在自说自话,他也没有什么煽情,他启迪的是思想,引起的是我们对那些地方、那些场景、那些典故、甚至那些梦魇的相望。人,果真有了相望,或许就有了意义。
作者说,“经过三天逗留之后,我对土耳其能有什么了解?我看到一个极其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入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文字的岩石。我听到一种悦耳的语言,和德语相似,但柔和得多。”接着的是“众多不同的民族的幽灵在这里游荡;我想象中拜占庭皇帝的卫队是由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黑斯廷斯战役后从英格兰逃亡的撒克逊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文中前后相贯又冲突,这冲突以及这冲突背后的惨烈和向往,留个我们的应该就是沉思。
书中说的“冥冥中某人或者某物具有刀剑、桌子、品达式颂诗、三段论法、沙漏、钟表、地图、望远镜、天平的标准型。斯宾诺莎指出,每一事物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头。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不就是我们活生生的现 实,石头希望做石头,我们需要做自己。爱和被爱谁又不需要呢?
《地图册》读后感(三):旅行:博尔赫斯的阅读与想像
今年夏天,我幸参加了几场“旅行”。与其说是“旅行”,不如说是想像。因为我的旅行不过是从家走到静安区文化馆,或是从家走到学校,或是健身房。我在心中揣摩着每一个遇见的陌生人的故事:他家在闸北,因为热爱辞了职,来做健身教练;她是个大学生,来兼职挣点零花钱;她是个小商贩,出于无聊和好奇踏上了瑜伽的道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无限神秘的故事,而我总是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充满好奇。
我的旅行仅限于脑海,而有的人的脚步却已踏至远方。那些同来参加《地图册》图片展开幕式的阿根廷人,那些来自拉美的男男女女,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魔都的土地,企图寻找一番奇遇。在他们看来,旅行最好的方式便是对该地文化的深入体认。为此,他们可以兼职教课,可以为公司打工,可以以各种零工的方式流动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更深刻的旅行却藏在文学里。想像会把你带到每一个遗迹,每一段辉煌,以及每一个和历史有关的故事。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文学有如织布,我们得以透过它穿梭进出。
地图册的想像,首先来自于作家对文学作品的熟稔于心。每到一处,他总能联想起无数作家、无数典故。柯尔律治、布莱克、王尔德等名字在他的笔下频现迭出,然而,更重要的则是这些作品中隐含的精神:《我最后的虎》中,布莱克的虎是“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王尔德是“像黎明和水一样美好清新”的美的代名词;斯宾诺莎让一切成为本色,让虎成为虎,让石头成为石头。这本地图册像是一部关于旅行地的索引,从一个地名发散开去。其中,《街角》便为一例: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个不知名的街角,让他联想到自己家附近的街角、九月十一日区一家咖啡馆的一角、阿尔玛格罗南街图书馆的一角、玛丽亚·儿玉和他进入的房屋的一角、书店的一角……然而最后他却说,正是因为有那么多街角,所以也可以说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他可以联想起无数个街角,然而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定型。
与其说是想像,不如说是某种真实。文字是一场巨大的隐喻,折射着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巨大世界。甚至就连物,我们所触摸到的每一物,都有其原型或“标准型”。“所有抽象的词类其实都是比喻”,“韵府也是一种思维器械”(P.67,《大艺术》)。这样看起来,思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看不见,并不是因为失明或者闭上眼睛;我们看见事物是凭记忆,正如我们思考问题也是凭记忆,把相同的形状或相同的概念在记忆中加以重复。”(P.38,《旷世杰作》)思维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致的绚烂,一方面却也可以把美变成丑,把善拧成恶。在《卢佳诺》中,他提到柯尔律治,后者在十八世纪末见到大海之前幻想中的格律和海洋,远比他去德国后见到的现实的海洋要更加盛大。现实是多么无聊而令人失望,想像却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这股力量鼓舞着他打破现实的百科全书,创造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语词意象。在《尘世巨蟒》中,他全文赞颂了蟒蛇的力大无穷,却在最后说:“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一切威武,一切雄壮,一切传说,有时甚至会掩盖自然本身的光芒。到底是假想带来了恶,还是假象出的形象带来了恶?
战争已成往昔,战争却也时刻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博利尼抄道》中,博尔赫斯从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联想起里瓦达维亚医院附近的小型斗殴。战争不分大小,不分内外,像一根线索,串联起我们对古代的回忆。高卢女神,凯撒大帝,古罗马斗兽场,阿提拉的骑兵和长矛……然而,却掩盖不了其野蛮的本质。“十字军东征是历史上最凶残、最少受到谴责的行动。”(P.13,《伊斯坦布尔》)“加拿大不在乎用那种野蛮的形象来代表国家。南美国家的政府却不敢冒险把一尊无名和粗陋的塑像送人。”(P.5,《图腾》)话语之中似乎略带反讽:野蛮的,究竟是谁?
还没来得及深究这一问题的答案,时代的沙土就已经把历史掩埋。在博尔赫斯笔下,似乎一切历史、一切辉煌、一切战绩,都不过是时间而已。时间转瞬即逝,任何一个“现在”都无法永久。在他说凯撒大帝曾经光荣一时,他的躯体死去,只留给世界“巨大的影子”。(《凯撒》)于是,一切都沦为一场又一场的梦,无论我们如何“有为”,如何破解,都无法改变“接近死亡”的结局。“我们的全部历史是上帝的一个大梦,最后我们仍归于上帝”,上帝“一旦醒来,天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P.9,《爱尔兰》)活着,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隐喻。
即便如此,生存依然有着它独特的意义。灵魂的世界远高于金钱和成就,唯有文化方能流传永恒。“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归功于剑,但靠笔证明。”(P.19,《威尼斯》)而《德国梦》给了我们最好的隐喻:字母和数字都不会消失,可心跳的次数满了以后,你就得死去。对和平与自然的人文主义关怀,贯穿了这部小小集子的始终。在《气球旅行》中,他热情歌颂气球旅行时那种贴面风拂过的真实感,是“封闭在一个玻璃和金属的整洁环境里的感觉”所不能比拟的。文明的现代科技,并不能取代自然的真实。
于是,我疑惑了。既然博尔赫斯极力赞颂王尔德式的美,那“自然”和“唯美”又如何达成共识?
或许没有什么是绝对真实。最美不过想像,不过隐喻,不过虚拟,不过创造。在《雅典》中,我们在梦境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之间往返进出。百科全书就是科学,可科学就是绝对的真实吗?梦境的虚幻,在某种程度上,和百科全书所胡乱编撰的条目并无二致。“动物可以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鳗螈;六、传说中的;七、自由行走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数不清的;十一、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十二、等等;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词与物》,福柯)想像使他快乐,却也使他落入某种不可知的宿命。而生命的丰富性,正见于那层层发散的想像。正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一样。
——胡安小七
2019.7.31
《地图册》读后感(四):《地图册》:人人都是发现者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310.html
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于是我醒了。 ——《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三年的一天,博尔赫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出门,转过几个街角,然后碰到了朋友海迪·兰格,他们便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谈话。当时的博尔赫斯拄着拐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坐着的桌子上摆放着餐具,还有一些面包,以及两个酒杯,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文学,还有和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当然,海迪·兰格也一定是面带微笑的,她时不是地问博尔赫斯一些问题,博尔赫斯则友好而礼貌地说起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是不是没有玛利亚·儿玉在身边?一九八三的一天,博尔赫斯是不是早就看不清事物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场景是清晰的?在他面前的朋友,桌子上的餐具、面包和酒杯,被谈及的文学和生活,都变成了看见和感受到的存在。但是一九八三年,海迪·兰格早就已经去世,“她是个幻影而不自知。”遇见和谈话只不过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梦,但是为什么这个幻影需要海迪·兰格自知?“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认为向她挑明说她是个幻影,一个美丽的幻影,是不可能、或许不礼貌的。”梦是博尔赫斯的梦,梦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清晰可触的,而不害怕的博尔赫斯没有提醒海迪·兰格这是幻影,是因为他自己不想从宛如真实发生的现实里出来,或者梦比现实更吸引人,更让人流连忘返。
一种梦或者幻影,似乎逃逸了现实的种种束缚,它可以让死去的人出现,可以让永不相遇的人相遇,可以漫无目的地谈论一些东西,它一定不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它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要博尔赫斯愿意——所以不提醒是一个幻影,就让美丽继续美丽着。但是,“于是我醒了。”醒来的博尔赫斯一定是怅然若失的,他返回了现实,他依然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这醒来的结果是博尔赫斯想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想让博尔赫斯醒来?因为“梦境衍化成了另一个梦境”,博尔赫斯永远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九八三年也永远是另一个一九八三年。
不说出幻影是一种沉浸的感觉,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境也是另一条通道,博尔赫斯做了一个“德国梦”,梦里有十九排黑板的仓库,黑板上用粉笔写满了单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那些单词和数字存在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博尔赫斯做过“雅典梦”,梦里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和父亲在下棋,父亲又是虚假的阿尔塔薛西斯,“我移动了一个棋子;对手没有动子,但施展了魔术,抹掉了我一个子。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了几次”;博尔赫斯还梦见了在公寓电梯门口遇见的一个鞑靼人,“他身材高得异乎寻常,照说我应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当然,博尔赫斯置身在卢塞恩、科罗拉多或开罗的时候,还梦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梦中的景象可能是绵亘的山峦,有栈桥的沼泽,通往地下室的螺旋楼梯,我必须清点沙数的沙丘,但是这些场景都在巴莫或者南城的一个确切的街口。”
梦里是变化不断的单词和数字,是捉摸不定图书和围棋,是陌生而奇怪的别人,当然,也有熟悉的城市。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当梦呈现为两个行走的方向时,博尔赫斯是不是在绘制两种地图册?陌生而变化,变化而富有意义,这大概是旅行的意义,虽然已经失明,但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玉一起游历和欣赏了许多地区,看不见那些景物、博物馆和存在的一切,但是玛利亚·儿玉却用她的眼镜看见,用她的语言描述,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看见,但是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游历,更在于体验和思考,甚至是发现,他说:“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发现光滑和粗糙,发现苦或咸,发现彩虹的颜色和字母表上的字母,这是最简单的“看见”,然后才是发现面庞,发现地图,发现动物,发现天体,而最后发现的是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玛丽亚·儿玉和我一起惊喜地发现了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实际上,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这一切都组成了博尔赫斯的“地图册”,它是一种穿透,用一道光发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有光便有了影子,而当影子出现,光是不是还必须穿透这个影子,找到真正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拒绝别人为他画像,他说,自己是纯精神原型的影子,如果被画成了肖像,那么便是影子的影子,而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普罗提诺的那些形象,那些被拍成照片的偶像摹本,便成为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纯精神是原型,肉体是影子,肖像是影子的影子,照片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一束光的意义就是穿透这诸多的影子,这影子的平方和立方,照见那个真正的精神原型——这一种发现,其实是需要用一种减法,在去除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努力中找到“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神话世界里走出来。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是一个图腾,图腾是影子,它被笼罩在神话中,“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当我们念及沙漠里的一个图腾,一个默默地需要神话、部落、祈求甚至牺牲的图腾,不禁浮想联翩。我们对它的礼拜仪式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在朦胧的晨昏梦想它。”高卢女神是影子,她被后来者的想象所改变:“她是件破损而神圣的东西,任我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不负责任地添枝加叶。我们永远不会听到膜拜她的人的祈求,也永远不知道仪式是什么模样。”波塞冬神殿只不过是荷马文本里的一个产物,它成了《伊利亚特》这部喜剧里的影子,“时间和历代的战争带走了神的外貌,但留下了海洋——他的另一个形象。”影子是埃皮扎夫罗斯大剧院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是但丁想象中的克里特岛有牛头盘踞的迷宫,是刺倒凯撒的匕首,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投入大海的“尘世巨蟒”——它们被书写,被神话,被演出,被传说,而那个纯精神原型在哪里?
那位英明的皇帝 曾经放弃桂冠, 指挥过战役和舰队, 遭到人们的礼赞和妒忌。 这里也是一个后来者, 他巨大的影子将整个世界笼罩。 ——《凯撒》巨大的影子笼罩着苍白的土地,“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破晓时我在梦中看见。”正如普罗提诺所说,这便成为了一种图腾,而在图腾里,人们忘记了仪式,听不到人们的话语,而梦中看见的无非也是一些污点。所以博尔赫斯认为,神话的意义是神秘,神秘能带来更多的精神体验,“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时,博尔赫斯沉迷的是语言和音乐,它们带来的是“古老的激情”,在著名的罗讷河和鲜为人知的阿尔沃河交汇处,他感受到了水的诗意,“神话不是词典里的一句空话;而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条汇合的河流是两种古老的灵感的交融。”所以在面对那些神话时,博尔赫斯宁可不对它们进行影子一样的命名,“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我们最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来,历史就更神秘,更平静了。”因为不命名才可以不受神话和比喻的束缚,才可以忘记祈祷和魔法,才可以“思考或者试图思考”,才可以从影子里穿过。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博尔赫斯就是要发现神秘、诗意和思想,它们是河流、音乐、语言,它们不被命名,它们像梦一样无形。在英格兰,他发现了狼的历史:“撒克逊狼,你枉活在世上。/你凭凶残不足以生存。你是最后一头。/再过一千年,一个老人/将在美洲梦见你/未来的那个梦帮不了你的忙。/今天人们在丛林里搜寻你的足迹,/将你围追堵截,/最后昏暗里的悄悄的灰狼。(《狼》)”在伊斯坦布尔,他听到了悦耳的语言,在三天的行程中他看见了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人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文字的岩石,“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在威尼斯,他发现了河流的规则,“威尼斯的运河则是忧郁的平底船行走的道路,平底船和忧郁的提琴相似,它们柔和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音乐。”发现了黄昏的意义,“在我看来,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一九一四年就生活在那里的日内瓦,博尔赫斯重新找回了回忆,“日内瓦也让我感受到爱情、友谊、屈辱和自杀的诱惑。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而在金字塔旁,他抓起一把沙子,然后松手,在撒落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正在改变撒哈拉,“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些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博尔赫斯在梦中为地图册打开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说用光线穿透影子发现纯精神的原型,是在去除一种图腾和神话,那么走进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种对现实的拥抱。他和玛利亚·儿玉乘坐气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在纳帕山谷起飞,在一个半小时的航行中,博尔赫斯“好像是重新浏览爱伦·坡、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篇章”,他想到了主宰月球内部的月球人,他完成了人类的渴望获得了升腾的真正经验;他喜欢老虎,认为一生和老虎有缘,“讨厌斑点而不讨厌条纹”的博尔赫斯曾经在父亲的百科全书上认识了虎,在蒙塔内尔-西蒙出版社的百科全书里看见了虎的图片,在布莱克著名的篝火诗“虎,虎,燃烧得多么明亮”中想象了虎,在切斯特顿为虎下的定义“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中定义了虎,但是只有那只用舌头舔着脸把爪子搁在头上的虎才是真切的虎,“和我以前感觉的虎不同的是,它有气味,有分量。”
真切可触,这是现实世界,博尔赫斯不是为了放弃想象返回现实,而是一样去除影子找回最真实的东西,气球旅行中的飞翔感觉,真正老虎上的气味和分量,让博尔赫斯建立了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一样抵达了普罗提诺所说的“纯精神的原型”。那张图片拍摄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一个街角,它可以是博尔赫斯家所在的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角,可以是以前是居民楼的对面街角,可以是让人流浪忘返的花园一角,可以是阿尔马格罗南街图书馆一角,“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街角,因此也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没见过的原型在图片里似乎变成了一种在场,而这种在场和气球的飞行、老虎的气味一样,提供了经验所建立的那个“标准”。
在雷克雅未克的埃斯亚旅馆里,博尔赫斯用手触到了柱子,然后用双臂抱住它,在那一刻,他感觉柱子是白色的,而且坚实稳固,“高大天花板”,就是经验建立了柱子的原型,使得博尔赫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触摸到了标准,而这种标准给予他的是“奇特的幸福感”——“当我领悟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纯形状——圆锥体、正方体、球体、金字塔体时的基本快感,在那一瞬间又回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一种观点:“人间的每一件新事物在天上都有其标准型的反映。”标准是纯精神原型建立的范式,它带来的是经验,也是事物独一无二的象征,“斯宾诺莎指出,每一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当玛利亚·儿玉在月亮面包房买了大奶油圆球蛋糕,博尔赫斯获得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幸福感觉,如一道光吗,照见了没有影子覆盖的现实:“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
以梦的方式逃逸神话的束缚,以经验重新发现原型,游历和旅行所建立的地图册便是博尔赫斯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的文本,所以人既是在场也是不在场,既在梦境中也在梦境外,关键是超越存在的存在,超越语言的语言,超越影子的影子,“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忘却也是永在,它是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它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逝世之后,玛利亚·儿玉在1992年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全集中,把博尔赫斯一生都看成了“地图册”,“是把我们的由精神世界组成的梦想织进时间经线的借口”,所以时间有限时间无限,所以生命不在生命永在: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我专注地重温那些日子、国家和人物,越来越接近你,直到完成我们再次携手所需的一切事情。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尔萨、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博尔赫斯和玛丽亚、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