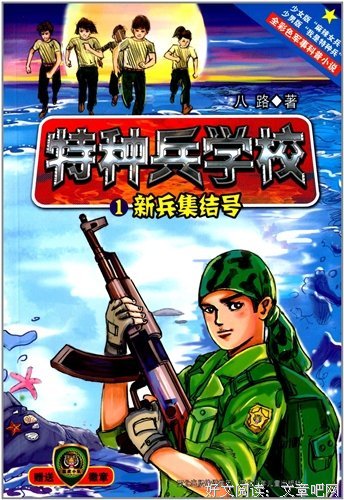
《六日战争》是一本由[以] 迈克尔·B. 奥伦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2.00元,页数:5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日战争》读后感(一):六日战争
小时候喜欢看打仗故事,那时觉得打仗输赢全靠谋略。有个好的指挥官,仗就基本赢定了。如果再有几个英勇无畏的士兵英雄,那就完美了。现在想想,那时看的书,情节与人物设定都是一边倒,好人既聪明又勇敢,坏人既愚蠢又胆小,这样两群人打仗,胜负还用说吗?
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象在这本《六日战争》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象小说里那样描写的英雄,即便象拉宾这样,被公认为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也有临战前顶不住压力,要辞职的举动。从可读性与戏剧性的角度来说,有个威风凛凛,所向披靡的主角英雄当然会吸人眼球。最近比较火的歌曲《踏山河》的MV里,项羽披着散乱的长发,穿着宽松飘逸的黑色长袍,独自挥舞长枪与围着他的敌人博斗。这个场景当然很man,但如果项羽真是这样打仗的,他恐怕等不到刘邦在乌江把他围住早就完蛋了。战争,毕竟不是给人看的电影和小说。
虽然又厚又重,价格也不菲,但这本《六日战争》真是值得一看。作者是以色列人,算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解读这场战争。但看完本书,你不会觉得作者美化了自己,抹黑了敌人。
全书500多页,其中一半以上篇幅写的是战争爆发前的事。如果换成小时候的我,估计会跳过前面部分直接从战争爆发开始看。对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来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比过程更难写,因为几乎每场战争的起因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象这场六日战争,如果真要深究其原因,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正是这种繁花渐乱中显出了作者深厚的笔力。
从发动空袭开始,六日之内,以色列干净利落地打赢了这场战争。无论从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以色列都比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要差得很多,为什么却会在这样一场看上去似乎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轻松获胜?这当然不能简单归因于以色列指挥官的英明或者士兵的勇敢。在我看来,以色列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军队战斗力要比阿拉伯军队高得多,或者说以色列军队运行效率要比阿拉伯军队高得多。
一部讲阿以战争的电视剧《泪之谷》里有一个情节,二辆以色列装甲旅的坦克奉命去阻击叙利亚坦克群的进攻。经过一场不算激烈的战斗,以色列的坦克指挥官说他击毁了40辆叙利亚的坦克。当时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指挥官在吹牛,他们2辆坦克怎么可能击毁40辆呢?而且自己还毫发无损。看了这书以后我明白,这是有可能的。因为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太差,有的坦克手甚至不会开炮。
军队效率就是国家社会效率的体现。以色列人团结高效是世界闻名的。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冷兵器时代靠人数或者少数人的英勇取胜。国家效率,才是战争胜负成败的关键。可惜的是,阿拉伯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几年后的赎罪日,不甘失败的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又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悲剧就又重演了。
《六日战争》读后感(二):不能換來和平的勝利
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以色列的建國肯定名列其中之一。猶太人在經歷了噩夢似的大屠殺之後,回到了「故土」打造自己的家園,卻是以剝奪當地現存居民為代價,從此中東就不得安寧。不過個人認為這是外人難以評論的事情,畢竟這之中牽涉的糾葛已經屬於生存權的層面,很難用什麼道德等形而上的標準去評判。儘管也不是沒有來自猶太人自身對於「以色列國族」的質疑。這些面向也不是我特別感興趣的部分,個人在意的是他在外交與軍事上的活動層面的歷史。華文圈對於這方面的書這幾年稍微有些增長,可選擇性還是不多,所以這本《六日戰爭》一出,翻翻覺得不錯就購入了。碰巧,HBO也撥出了以色列人自己拍的劇集〈眼淚谷之戰〉,雖說是不一樣的背景但可以湊在一起看也是有意思。
「六日戰爭」(這是以色列方取的名字)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這漫長的半個世紀多的衝突中的一個階段,本書作者邁克爾‧B. 奧倫(Michael B. Oren)在書的標題加入了一個「現代中東的創生」,但他自己在結尾也承認「這場戰爭改變了什麼?…答案依然模糊不清」。不過,歷史是延續性的,沒有這個事件,就沒有驕傲自大的以色列,然後也不會有贖罪日戰爭,按照蝴蝶效應的理論,中東史,乃至世界史都可能產生許多影響。按照此說法,作者這個標題倒也下的不算太過。
而這場戰爭,顧名思義,它前後不到一週,放在被霍布斯邦稱之為「極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紀裡面,非常非常短促,但又具有決定性。它非常符合發動方的企圖:迅速、一刀致命的擊敗敵人,迫使對方談判。四面受敵,資源短缺的以色列,經不起任何一場消耗戰。說來有趣的是,歷史上跟這個國家處境最相似的,恰恰是對其「促生有功」的德國。著名的美國戰史家羅伯特•M.奇蒂諾(Robert M. Citino)對自普魯士以來的德意志國防軍傳統給了一個「德式兵法」的名號,這支軍隊依照其國家的處境,替它們的戰爭方式做了一個量身打造的公式:以「任務型領導」來保持中底層官兵的活力,而將官採取高度進取與主動攻擊精神來面對戰爭,力求以高度機動性來尋求決勝機會,包圍殲滅對方主力消除抵抗意志,在有限資源情況下迅速致勝。奇蒂諾在他的《從閃電戰到沙漠風暴》中評論以色列國防軍時說到:在二戰之後,效法德軍最全面的莫過於這支軍隊。
但對以色列人來說,最不幸的地方在於,其處境並不能因為軍事的勝利而有所緩解,因為誠如克勞塞維茲所言,戰爭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手段罷了。面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敵意,猶太人過去十幾年裡,最多也只能爭取到「停戰」,始終無法得到對方的「承認」。這並不難想像,光是巴勒斯坦人的問題就非常棘手,更何況阿拉伯人把以色列的建國當作是西方帝國主義對其入侵的過往的一種遺緒,這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去殖民化浪潮中相呼應,產生了極大的話語力量,即便有些人對於此產生了懷疑,也很難發聲與立足。
而事實上,在冷戰期間的兩大強權也都為此問題增添了更多的麻煩。蘇聯利用了阿拉伯人的這種反帝情緒,把他們拉攏到了自己的旗下,儘管它並沒有企圖與西方打一場熱戰的意思,但做為一種無形的對抗,中東是主戰場。歐美各國也差不多處境,特別是因為石油,他們就算同情以色列,也不可能徹底敢開罪阿拉伯世界,別說英、法,就連美國也都是首鼠兩端。
以色列的困境也是非常明顯的。當然,猶太人首先自己得自立自強,全民皆兵,抱持著「馬薩達精神」(猶太民族大起義被羅馬帝國擊敗時的最後據點,所有人都寧願自殺也不願屈服),但他們也知道持續的對抗最終結果就只是共同毀滅,始終嘗試採取政治的方法解決。這次的六日戰爭前也是如此,埃及、敘利亞等國公然的陳兵邊境,動武企圖昭然若揭,但他們不願被國際指責是「開第一槍」的侵略者,又按兵不動;而以色列的處境就像是被一群武裝份子圍在家中,整天惶恐不安,但想主動驅逐卻反而會被指責是挑起戰爭的惡徒的住民。兩邊僵持不下,都沒法真正的和平,聯合國強權各自心懷鬼胎,大多時間口惠實不至。作者花了許多筆墨撰寫這段過程,讀來真的覺得無奈,此時討論罪責沒有意義,純粹就是國際政治的陰暗面。
戰爭在六日內結束,幾乎是以色列的全勝,埃及兵敗如山倒,外強中乾的一面被徹底戳破。說來好笑,這畫面看起來跟紅軍當初被納粹德國打的一敗塗地何其類似,原因也差不多:軍容表面強大,其實士兵訓練不足,軍官素質低落,將官各種不適任,上層明爭暗鬥,沒有任何具體作戰準備與計畫等。總之,最尷尬的莫過於蘇聯,他們的裝備顯得徹底完敗於歐美,儘管心知肚明是使用者的問題卻又有苦難言。而以色列也有陰險之處,一開始擔心多線作戰,對敘利亞採取守勢,表示不願擴大戰端;等到埃及完敗,發現戈蘭高地空虛時,又立刻主動出擊直逼大馬士革。要說沒有什麼領土野心,怕也是未必。不過,最後以色列也還是見好就收,很快接受美蘇的介入談判停戰,採取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畢竟國際政治也是很現實的,勝利者擁有最大的話語權,現在特拉維夫可以讓它的鄰居坐下好好談了。
聯合國做成了242號決議,要求以「不容許以戰爭取得領土」為原則,在保證以色列國家安全為前提情況下,無條件歸還所有佔領地並達成和平協議。但事實上以色列保留了西岸、耶路撒冷跟戈蘭高地(作者沒有提及),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沒有立即接受。這個決議還是跟之前一樣,它只是短暫的停戰,就像當年巴黎和會那樣,並沒有真正解決任何問題。作者坦言,至少這場戰爭讓雙方再次面對了實質:「以色列的存在」是雙方爭端的核心,阿拉伯人無力消滅,又不願意共生,那就最後只會陷入這無窮盡的爭端輪迴。只是,站在當下看來,似乎還要再經歷更多的磨難,人們才會真正的領悟。畢竟,這對以色列人來說,也是血與淚的故事,儘管他們是勝利者,並不代表沒有任何代價。前面提到的電視劇〈眼淚谷之戰〉,就拍出了許多一般軍民的犧牲與無奈。
坦白說,本書作者不算會講故事。他是很清晰的呈現了事情的經過,但其實更像是流水帳般的紀載。他把很多筆墨花在不必要的敘述上,反而沒有去著墨更多些關於主要參與者,阿拉伯與以色列的高層政治人物的心路歷程,或者是軍民的回憶或許更有意思的地方,這導致整本書的部分顯得有點沉悶。不過,至少他算是完整交代了〈六日戰爭〉的始末,而譯者的翻譯流暢,對此主題有興趣的讀者還是可以得到滿足。
《六日战争》读后感(三):现代中东的创世纪
Michael B Oren 在他的巨著《六日战争》的最后一个段落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六天的战争真的改变中东了吗?”。
也许是身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在目睹随后35年中相继发生的战争、冲突、暗杀后,作者显得没那么自信,答案仍然模糊。但是他在这里似乎忘了,在《创世纪》中,上帝也只用六天的时间便创造了世界,虽然随后同样有大洪水、大屠杀、建国、亡国,但这六天是与众不同的。1967年的6月5日到6月10日,同样是中东世界的一个创世纪,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篇章,从此故事的走向便与之前的1000年完全不同。
公元636年,阿拉伯军队与拜占庭军队在雅穆克河对阵,准备开始一场关系着阿拉伯穆斯林的大征服事业命运的起点性的决战。这支由哈立德·本·瓦利德指挥的彪悍之师,来自于阿拉伯腹地的麦加地区,受先知默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义鼓舞,英勇气概远胜于当时的两大帝国——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小战斗,最终阿拉伯人彻底击溃了拜占庭人。与领土和人员的得失相比,这更是一场帝国气运之战,从此之后拜占庭丢失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仅依靠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屏障偏居一隅;阿拉伯人在“天命”庇佑下轻松地席卷了伊拉克和波斯,北非直到西班牙。
回到战争的起点,雅穆克河是一条四季长流的河道,从戈兰高地流向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谷地。这条河周围有太多著名的地理名称,它们将在1300多年后见证或许惨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意义同样宏大的多场战斗。
随着阿拉伯人征服脚步的推进,无论是倭玛亚还是阿巴斯王朝,似乎都遗忘了它们的起点,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广袤的沙漠地区和零星分布的绿洲。在那里只有麦加和麦地那享有圣地的名号,波斯湾西岸的几个港口有船队进出,剩下的地区和贝都因人依然过着原始的生活。
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击溃了马穆鲁克第49任苏丹奥乌里,终结了阿拉伯血裔对伊斯兰世界的直接统治。不过奥斯曼苏丹聪明地接过了哈里发的名号,以伊斯兰世界共主的身份继续统治着阿拉伯帝国的疆域遗产,直到近代。
所以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阿拉伯世界逐渐产生了分化。我们更熟悉的是宗教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与冲突。而在国家治理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上,我个人将他们分为旧世界、新世界和边缘世界。
所谓旧世界,就是很早就成为阿拉伯帝国直接管理的疆域,有着高度发达的官僚组织和艺术文化的地区,主要包括两河流域、新月地带和非洲东北角,对应的国家地区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山地区、约旦、巴勒斯坦和埃及,其中不乏巴格达、巴士拉、大马士革、阿勒颇、耶路撒冷、加沙、亚历山大和开罗等世界级规模的都会和历史名城。
边缘世界概念中,狭义的边缘世界是指在地理上和种族上与阿拉伯人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现代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在地中海南岸沿海的地区。广义上的边缘世界的代表是两个非阿拉伯国家,但是它们都受到了阿拉伯宗教,也就是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和塑造,分别是伊朗和土耳其。
至于“新世界”的新,是站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而言的,因为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又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部分——阿拉伯沙漠。1913年,沙特家族重建了与瓦哈比后裔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个时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伊本·沙特。从此沙特人以瓦哈比主义为立国根基的宗教武器,通过先后与英美的合作,与占据旧世界的哈希姆人展开竞争,首先威胁到的就是侯赛因国王统治的约旦地区。而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阿拉伯沙漠中陆续发现多个油田,到了五十年代,随着石油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沙特、科威特、及其他海湾酋长部落都完成了一次“反现代”的现代化改革,与西方主要强国形成了一种地区性的共谋共享体系。
与沙特阿拉伯这个新世界相比,其他阿拉伯世界在奥斯曼崩溃后的近代-现代化进程中,都遇到了更加棘手的挑战和危机。而这个过程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因为中国和他们同样都是有着古老文明和艺术、成熟官僚政治和哲学宗教的“文明古国”,所以在转型过程中都非常痛苦:在欧美“帝国主义”时期,都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都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了“前现代”的民族主义斗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启了“现代主义”的民族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式上成为胜利方,而实际上更深地卷入了西方体系。唯一的区别是,战后四十年代末,旧阿拉伯世界的独立是“被安排”的结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通过赢得残酷内战的胜利而获得的。但是他们同样都受到了战后美苏冷战体系的影响,并努力在阵营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才会有“亚非拉”团结的不结盟运动,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不结盟国家”因为历史、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共性,基本上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尤其是他们普遍的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愤恨,使得这些国家都具有鲜明的“反美反帝”立场,并被苏联利用。
之所以要回顾整个阿拉伯历史,特别是旧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是因为这是我们理解阿以战争,特别是六日战争的钥匙所在。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或者Zionlist(锡安主义),本身也是近代的产物,同样是在二战后,在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地位的扭捏不决和美国的支持下,在现代世界成为了一个实体。1948的战争是这个实体的初生之战,对以色列来说固然是立国之本,但就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至少在当时而言并不是举足轻重的时刻。
但是1967年六日战争的世界政治背景完全不同。
大格局上看是美苏冷战此消彼长的转折期。在苏联依然是老大哥帝国,美国却深陷越战泥潭的表象下,苏联国家机器运转和财政发展的疲态已经开始暴露。在中东地区,旧世界诸国的“社会民族主义”似乎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都由少壮派军人和“复兴党”当政,甚至出现了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标志性事件。
这是一个以色列在国家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都四面楚歌的时代。
在本书的前四章中,详细描画了缅甸人吴丹领导的联合国轻易抛弃西奈半岛,把以色利暴露在狼群中的偏袒和懦弱,以及苏联人的强硬立场和美国人的患得患失。
关键点在于,对底线的认知。以色列领导层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都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东地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点,所以同时提高了战争条件的底线。对比之下,纳赛尔更擅长使用个人魅力和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地位来制造舆论并释放烟幕弹,以色列人的外交斡旋就显得直接诚恳地多。但美国人和苏联人对自己盟友的想法都显得比较迟钝,既没有创造和平局面的条件,也没有对盟友进行强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力上的支持。
随着以色利人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震荡中产生的新格局开始浮现上来。
首先,旧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民族主义潮流被证明是失败的尝试,各国更加转向于加强对本国的军政独裁统治。不到三十年后,这些政体的运转都出现了问题。伊拉克狂妄地发动了两伊战争和科威特战争,结果成了被美国画上记号的“世界公敌”;叙利亚在阿萨德二世统治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政变的抵抗,内战至今未停;埃及则先后经历了萨达特、穆巴拉克等强人政治后,在阿拉伯之春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夹击下,目前仍没有稳定的发展前景。约旦转投新世界阵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阿拉法特死后一落千丈。从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旧世界就开始走在动荡分裂和衰落毁灭的道路上,甚至波及了利比亚等边缘国家。
其次,苏联在六日战争中暴露出了外强中干的本质。其实如果当时苏联能以后来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决心,投入到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支持中,以色列即使不亡国灭种,也会被打击成中东的二流国家。但失去的时机不会再来,时间窗口一旦错过再多的工作也只是亡羊补牢。苏联在五年后支持了赎罪日战争,也只是赢了开局,却没能笑到最后。
最后,关于以色利的前景,至少在今天看,因为六日战争的速胜和赎罪日战争的顽强,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机遇期。因为包围他们的旧世界国家几乎尽数被破坏殆尽,目前只有两大边缘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特别是伊朗尚存有核武器的远方威胁。但伊朗同样是美国的大敌,所以以色列只要持续与盟友保持战略战术合作,削弱伊朗势力是大势所趋,虽然推翻其统治困难重重。至于同样是美国战略盟友的沙特和海湾国家,反犹主义只是走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宣言罢了。
六日战争之后,实质上围绕以色利的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实质变化。也许当时,乃至赎罪日战争时的以色列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帝国和敌人会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相继坍塌,是以这六日是以色列和现代中东的创世纪,绝不是夸张之语。
当然在《六日战争》中有很大篇幅介绍了战斗的全过程,本章不做赘评。关于战术只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倾巢而出的闪电战是以色列自古以来的战术风格;第二,普通阿拉伯士兵都坚韧善战,但是阿拉伯军队却保留着一个古老的弱点,一旦指挥官逃跑或阵亡,整支军队便会崩溃。所以叙利亚坦克指挥员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打开仓盖观察战场,而是躲在铁皮箱子里。
《六日战争》读后感(四):没有人想要的战争和没有人想到的结局
一、引言
中东对于世界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或许是石油,但是对于中东地区的人们,最重要的资源一定是水。对于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一书的作者Oren将其称之为“一滴水的蝴蝶效应”,自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以来,为了把这片荒漠变成圣经书中所写“流着奶与蜜之地”,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灌溉问题。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谷中的降雨量要比南部荒漠高出40倍,约旦河水发源自黎巴嫩、叙利亚,途径巴勒斯坦地区和约旦最终汇入死海。从1952年开始,以色列耗资1.5亿美元进行了历时11年的国家输水工程,将加利利的水引到内盖夫地区发展灌溉。
农业发展使得阿拉伯人担心这样将支持更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以色列加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于是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利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得到埃及等国支持,决定允许叙利亚将约旦河上游进行引流改造,这一举措遭致以色列反对和警告,同年11月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阿方的工程,于是持续不断的叙以边界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最终将区域内的国家引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沃尔兹说战争爆发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体系问题,水资源是一个导火索,但不是第三次中东战争背后的深层原因。1948和1956两次战场上的失败后,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认输,他们拒绝和以色列和解,甚至拒绝用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而是代之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从这一角度来看阿以固有的矛盾可以说必然会导致战争发生。
但是战争发生的时机仍是耐人寻味的,从1956到1966年,这一地区享有长达十年的总体和平。如果去看1964年这个时刻的中东体系,体系结构和体系过程都并不直接指向战争:从四国关系看,自叙利亚从阿联分离出去后,叙埃之间的矛盾极大,反而是埃以、约以都在沟通和接触;从各国视角看,埃及忙着与沙特在也门的竞争、并没有把矛头对准以色列,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始终面临着政权合法性和国内稳定的压力不敢有大动作,以色列则是由温和的艾希科尔取代了鹰派的本-古里安成为总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不能看出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是尖锐的两个固定和僵化的极的对抗。那么是是什么使得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再次变成了阿拉伯世界vs以色列,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战争?
二、体系结构的分化和重组:六日战争前的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
1.1961年后松散的体系结构
1961阿联出现裂痕后埃及和叙利亚走上了一条相互竞争的对苏友好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旨在巩固自身政权。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快了私有企业国有化进程,以及继续从1960年就开始的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并深化土地改革。1962埃及出台《民族宪章》——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与此同时,叙利亚内部则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纷争,在发生了1962年的三次未遂的军人政变后,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建立起来政党合一的军政体制,并排挤国内亲纳赛尔势力,造成埃以关系进一步恶化。复兴党掌权后,内部开始分化,右翼推崇阿拉伯主义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为代表的青年军官则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有化等经济问题矛盾的滚雪球效应下,1966年叙利亚再次发生政变,亲社会主义的新复兴党人夺权成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求,叙利亚加强了针对以色列的敌视态度。
作为君主国和亲英的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的约旦则在这场阿拉伯社会主义风暴中相对独立和温和,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就没有到关系严重恶化的仇人地位,反而不断有着接触和谈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约旦是高枕无忧的,侯赛因国王始终有着巩固自己政权不要被推翻的压力,也有着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压力。
相较于阿拉伯三国,以色列在国内上虽有纷争但并无大忧患,此时的以色列国内在争吵两个问题:一是工党的分裂,1963年艾希科尔接替本-古里安担任工党主席并被任命为总理,但两人关系很快破裂,本-古里安在1965年退出工党建立拉菲党,艾希科尔的工党则和劳工团结党合并为结盟党,随后大选中结盟党在选举中击败拉菲党,但本-古里安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破坏艾希科尔的权威。另一件问题则是历史遗留问题,伊休夫的犹太人长期以来有一种希望与欧洲羸弱的犹太人割席的想法,这在50年代是否接受德国赔款问题上已经引发过一次大的社会讨论,本-古里安看到德国赔款可以解决当时以色列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贝京代表的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人则从情感上无法接受,同样的事件在1961年的对艾希曼的审判上再次引发了争议。这次审判扭转了过去伊休夫的观点,让不了解大屠杀的以色列人直面现实,清晰的看到拥有自己国家的重要性,这是必要的,因为以色列在地缘问题上依然是麻烦不断:以色列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狭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仅12km,随时有被阿拉伯国家拦腰斩断的军事隐患;耶路撒冷圣地仍在约旦人控制下;叙利亚则控制着可以俯瞰加利利地区的戈兰高地;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力度,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正在削弱——总之,以色列需要建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确保生存并实现和平。
2.冷战在中东:僵化的意识形态让埃及外交选择受到限制
从世界视角去看,60年代是美苏冷战此消彼长的转折期,苏联占据上风,是第三世界各国的老大哥,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但与此同时苏联政治上的疲态和迟钝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在中东地区具体来看,美国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
既然作为老大哥,如果说听不清就是听不清,于是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后,纳赛尔将自身的命运与苏联绑定,埃及的政治宣传和行为变得更加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最大风险在于目的和手段太容易被混淆,纳赛尔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并将阿联的失败归结于将狭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保守君主国+受西方支持的自由主义共和国,这导致阿拉伯社会的分裂。站在进步革命价值观的角度,纳赛尔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当也门王室被推翻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最终埃及和沙特作为竞争对手卷入也门内战。
3.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如何将埃及和约旦绑架上战争的车轮
当冷战格局在中东地区固定下来时,这里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来自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阿拉伯人至今未能履行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1964年的那次讨论水资源的会议上其实确定了另一个计划,即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国家一致对外(以)的理由,却也是阿拉伯国家出现分裂的原因:1963年,叙利亚指责纳赛尔对以色列软弱,“为了几蒲式耳的美国小麦出卖巴勒斯坦”(肯尼迪政府对埃及的援助),纳赛尔则反击叙利亚试图在阿拉伯统一之前将其拖入战争。约旦首相也指责纳赛尔不与以色列作战而是躲在联合国部队的庇护下——埃及被孤立了,因为作为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它不愿采取行动。1965年埃及境内的作为巴解组织一员的法塔赫得到叙利亚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一行动让纳赛尔难堪,原因有二:叙利亚使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领导力大打折扣;并且有引发以色列报复的危险。作为回应,埃及采取行动逮捕了埃及和加沙的法塔赫成员 。约旦同样受到巴勒斯坦运动的威胁,侯赛因也担心巴解组织的运动招来以色列报复,所以逮捕了“颠覆分子”并关闭了巴解办事处。正如上面提到的,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三国中政局不稳定的那个,最需要的是转移国内注意力,于是成为最大力支持巴解的国家,这也导致了叙以冲突不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66年11月,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规定如果一方受到他国(以色列:你干脆写我身份证号得了)攻击时另一方应当参与回应。要知道在签订这一防御条约的同时埃以秘密外交仍在进行当中,所以不应当简单用意识形态/民族情感解释埃叙关系的恢复,纳赛尔的考虑是非常现实的:作为对叙以冲突的考虑,这一条约既是给以色列威慑(联盟的能力聚集和威慑),也是希望埃及能够限制叙利亚(联盟管控)。
同月由于巴解组织的活动,发生了另一件扰动时间线的事情:因为三名以色列士兵被法塔赫的一枚地雷炸死,13日以色列对约旦控制的西岸城镇萨穆进行报复,这次袭击给约旦造成了重大伤亡。历史地看,以色列的过度报复其实是误判了,因为后来在和侯赛因打交道的时候才发现国王恰恰是反对法塔赫的行动的。以色列的行为引起了约旦国内的不满和对国王的批评,侯赛因也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合作,这些促使他加入埃及和叙利亚的同盟,在1967年5月签署与埃及的共同防御协定时甚至直接表示“直接把你们跟叙利亚那份改个名字就可以”。
于是到了1967年,中东地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明朗,阿拉伯三国对以色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了,以色列再次回到了建国初的噩梦之中,地缘政治问题成了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4.最后一根稻草
1967年,在叙以边境上不断发生袭击和炮击事件,这种争端从今天你炸我一辆卡车明天我炸你一辆拖拉机的小打小闹最终升级到双方空军的交战,叙利亚的6架米格飞机被击落。5月15日,埃及部队进入西奈半岛,次日纳赛尔下令接管了位于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阵地,5月23日,纳赛尔又下令封闭了以色列的重要出海口蒂朗海峡,至此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的安排全部被修正,这使以色列下定决心与阿拉伯国家开战。交战一方为以色列,另一方为根据盟约被捆绑在一起的埃及、叙利亚、约旦。
三、六日战争的战果
以色列能够取得短时间重大战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先发制人和迅速夺取制空权的以色列战略,二是阿拉伯军队自身问题。
1.先发制人
在探讨先发制人战略为什么奏效之前其实值得讨论为什么以色列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首先是在蒂朗海峡问题上美国的担保,苏伊士运河战役后,联合国在西奈半岛驻扎了一支紧急部队。纳赛尔和本-古里安都抵制这一想法,纳赛尔认为这是对埃及主权的限制和以色列侵略的奖赏,本-古里安则认为纳赛尔随时会驱逐这支部队。于是作为对联合国部队驻扎的回应,埃以分别达成了自己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向纳赛尔承诺埃及有权撤走联合国紧急部队;杜勒斯则承诺美国将把埃及恢复封锁蒂朗海峡的行为的企图视作战争行为,以色列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那么当5月23日作为以色列海运生命线的蒂朗海峡再次被埃及封锁时,以色列已经将此视为埃及的宣战。到6月1日,虽然LBJ答应的帮助以色列恢复海上通道的计划失败了,但以色列也得到了国务卿腊斯克的保证“我不认为美国有职责约束任何人”,这是一个给以色列的可以进攻的信号。
其次是上文提及的艾希曼审判带来的民族大屠杀记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后来的巴解主席舒凯里也宣称“这场战争后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出现了反以示威游行,群众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甚至更过分的是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上出现了映射纳粹大屠杀的政治不正确的意向:一只手持刀插进画有代表犹太人的六芒星的心脏,配字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这些让以色列人感到恐怖,甚至做好了包括扩建急救站、防空洞和墓地在内的最坏的打算,那么与其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坐以待毙,倒不如殊死一搏。
第三在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危机以及联合政府的建立,虽然本-古里安天天给艾希科尔泼脏水说他缺钙,但也不是完全信口胡诌,5月27号艾希科尔发表了一个呼吁国内民众保持克制的演讲,这个演讲本身的效果是个大灾难,艾希科尔彻底失去了国内的支持,最后妥协同意组建以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让反对党进入内阁:达扬和贝京都进到了政府班子中。6月2号以色列政府决定先发动战争,4号则最终拍板计划首先进攻埃及。
2.在决定先发制人后以色列如何迅速获取制空权
5号战争正式爆发,以色列时间0710,以色列空军出动183架次飞机奔赴埃及10个空军基地,只留下12架战机负责守卫本土领空。从这一角度看,以色列这次先发制人也是在赌国运。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算准了,埃及时间比以色列晚一小时,埃及时间0745这批以色列空军抵达的时候,埃军还是早班交接,该写报告写报告、该加油加油、没事儿的人去吃早饭的时间,准备不足,损失惨重。总之,在一个上午的两次空袭中,埃及空军损失了322架飞机,多数机场遭到空袭,地对空导弹和雷达遭到破坏,地勤人员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在埃及空军遭袭时,阿拉伯三国配合糟糕的事实暴露出来,约旦和叙利亚并不知晓埃及空军的情况,很快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被消灭。两天内以色列完全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这为地面行动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3. 阿拉伯军队的自身问题
虽然说中东是一团乱局,但百年纷纷扰扰中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事情,就比如叙利亚发挥稳定地输掉了全部五场中东战争。但是我并不愿意过于有偏见地把以色列这次闪电战大胜利的原因简单粗暴地总结为“以色列武德充沛,阿拉伯费拉不堪”(毕竟不能认识水平总停留在p社是不是)。前面介绍背景时提及1962年9月地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埃及和沙特分别支持的一方的内战。1963年,埃及在也门部署3万人,到1965年巅峰时期达7万人,占埃及总兵力一半,但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埃及毫无胜算但是拒绝撤退,纳赛尔甚至把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而非一次军事行动”,结果这一羁绊严重制约了埃及为对抗以色列而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虽说如此,但三国联军仍比以色列强大是事实,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有一些传统迷思认为阿拉伯士兵贪生怕死、部队凝聚力差、将军愚蠢无能、武器装备落后,但美军对阿拉伯部队的研究指出事实上的情况和这相反:阿拉伯士兵战斗力依然强大;部队也并没有高于平均值的溃散次数;阿拉伯军队的将军们通常做出正确的判断;武器装备质量和质量都不落后于以色列。而阿拉伯军队的关键短板在基层部队的低素质上,旅、营、连的指挥员行事特别死板教条、缺乏随机应变、相互配合和信息情报意识。美方的研究提出的解释原因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长期把军队视为解决低教育水平青年就业问题的“国家职业”,士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使得要求基层指挥员在战斗中要特别机敏灵活的苏式作战体系并不能适合阿拉伯作战需求——更何况对手是基层指挥员能力极强的以色列。这一现象的背后不仅仅是军队战斗力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个体系的问题。
四、为什么同意停火
首要原因就是再打下去不行了:第三次中东战争打了六天,本来只是应对埃及的封锁,结果以色列在计划之外的拿下来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很久之前看过一个非常好笑的比喻称埃及带着俩小弟去抢iPhone,结果iPhone没抢到,又丢了四个Note,于是后续谈判就是“我错了你把Note还我吧”)。此外从战损上看,埃及85%的军事装备都被以军摧毁,以色列缴获了320辆坦克、480门大炮、2个SAM导弹阵地,以及1万辆车,约旦丢了179辆坦克、53辆装甲运兵车、1062门大炮、3166辆车、近2万件各式各样的武器,叙利亚也损失了470门大炮、118辆坦克和1200辆车。
其次,从前面的分析去看埃及和约旦是被同盟条约牵连入战争的,当以色列提出土地换和平的想法时,当联合国的242号决议出台要求以色列撤出六天战争后占领的它国领土,也要求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独立与安全时,当背后的美苏两大国参与到对地区格局和参战国的施压时,接受停火是意料之中的[1]。
五、影响和反思
1.对以色列:胜利了……吗?
很出人意料的事情是作为战争胜利者的以色列似乎没有胜利的喜悦,大卫战胜哥利亚的叙事光环和打鸡血效果仿佛不再起效了。战争胜利后,作为参谋长的拉宾获得了一项荣誉——为这场战争命名,在众多如拯救的战争、光明之子的战争之类的名字中他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六日战争”,不仅指这场战争为期六天,也暗指创世纪中的六天。很多以色列人表达出来对这次胜利的不适,在一本叫《第七天》[2]的书中,很多人表示“我并不因为杀死阿拉伯人而开心”、“我为什么要和阿拉伯人作对呢?就因为他有枪?可是他也有他的家庭”。
在这场战争后,以色列社会透露出一直厌战的情绪,这种情绪来自“占领土地的负担”——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10.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其原来国土面积的3.5倍。在战争爆发之前,以色列非常脆弱,其主要城市全都处于阿拉伯国家火炮的射程范围内。而如今,这个犹太国家正威胁着大马士革、开罗和安曼。该国首都耶路撒冷已实现统一,可是进入了耶路撒冷却让以色列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并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属于他们——生活在城市中的阿拉伯人是实体的存在。如何对待新占领的土地,一些人主张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进而保留大部分领土,但死去的人和无休止的争斗也让以色列人无法回避难民问题,也希望和平,而先发制人的做法带来的国际社会上的“挑起战争”的指控也束缚了以色列的策略——这些都成为了下一次战争中以色列行动迟缓的预兆。
六日战争中LBJ放弃了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在战败后认定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并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加强对中东控制的工具。1967年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美阿的地缘战略关切不再有交集:美国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阿拉伯也无法让美国认同他们关于以色列的看法)——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了。
2.对阿拉伯:失败了的现代化,更激进,也更保守。
比起胜利方,失败方反而可以静下心来沉思。战败暴露了阿拉伯人的不足,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为其所拥有的武器和英雄气概而感到自豪,1967年后,人们普遍认为团结不再是问题所在——只要阿拉伯社会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联合起来就毫无用处。强烈的幻灭感催生出更激进的情绪,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时代,
一些人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更加暴力的民族主义,或者回归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这场战争就像1948年一样,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
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里夫被复兴党领导的政变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被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尼迈里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阿塔西被阿萨德的军事政变推翻以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阿拉伯对以色列的立场趋于强硬,但是具体做法产生了分裂:受损最大的埃及和约旦都希望通过协商达成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领土,但是8月的喀土穆峰会却划定了对以色列“三不”原则(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成了一种阿拉伯世界的道义制高点。1967年联合国的第242号决议为“土地换和平”提供了法律框架,获得了埃及约旦支持,但是没赢得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最终由于对以色列的和解,埃及永远失去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拉宾总结这次战争时说“1967年的战争改变了阿以冲突的背景,不是使以色列不那么令阿拉伯人反感,而是使阿拉伯人相信,以色列永远不可能通过武力消除”,阿拉伯世界在喀土穆看似走向强硬,但是阿拉伯人的重点已经从巴勒斯坦转向解放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即从“消除以色列”转向“消除侵略的痕迹”。
3.巴勒斯坦问题:动乱的无休止
在提供和平机会的同时,六日战争为更致命的战争打开了大门:正如Oren所说的,“1967年被创造出来的现代中东是一种混合体:它既有初生的希望,又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新时代与旧时代的背景交织并存”。尽管以色列进行了所有的军事征服,但仍然无法实现它所渴望的和平;尽管遭到全面失败,但阿拉伯人仍然可以发动一场强大的军事行动。
长时间被忽略的、缺乏叙事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和建国要求从来存在。过去巴勒斯坦人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其他阿拉伯国家,1967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把握自己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巴解组织也在转型,战后法塔赫接管巴解组织,将其变成一个“伞状结构”,但人阵和法塔赫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前者脱离组织走向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战后纳赛尔不再像过去那样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进行,反而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从他们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的袭击,继而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也造成了后来黑九月的内战和黎巴嫩的内战。
参考文献
Ajami, Fouad. The Arab predicament: Arab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since 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Goldschmidt Jr, Arthur, and Aomar Boum.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Hachette UK, 2015.
Goldstein, Yossi. "The Six Day War: the war that no one wanted." Israel Affairs 24, no. 5 (2018): 767-784.
Gordis, Daniel, and Fred Sanders.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New York: Ecco, 2016.
Machairas, Dimitrios. "Th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June 1967 war." Cogent Social Sciences 3, no. 1 (2017): 1299555.
Oren, Michael B.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Presidio Press, 2017.
Pollack, Kenneth M.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U of Nebraska Press, 2004.
Rogan, Eugene. The Arabs: a history. Basic Books, 2012.
Shlaim, Avi.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Penguin UK, 2015.
彭树智, 王新刚.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M]. 商务印书馆, 2003.
[1] 6月7号纳赛尔下令撤退时其实是拒绝在停火协议上签字的,因为他要求协议上加入像1956年那样的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的保证,但是在完全明白没有这一希望后,8号纳赛尔接受了停火(大人时代变了)
[2] 接上面六日创世的梗,第七天是休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