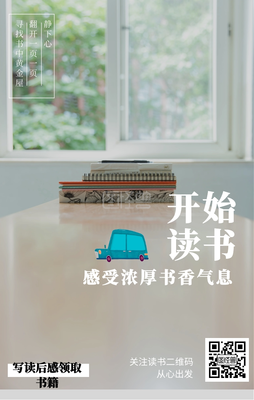
《回归,还是出发》是一本由高尔泰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2021-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回归,还是出发》读后感(一):史文化与巫文化 史文化与巫文化——从楚辞说起
文学研究要回归文本,我想这对于屈原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很多批评家一边主张“拿作品说话”,一方面又热衷于造星运动,对于久已邈远的历史人物极尽考古之能事,诚然,对于历史进行考古是无可厚非的,但与其让批评家来做这件事情,不如让文学的归于文学家,考古的归于考古学家吧,回到文本和审美虽然并不具备终极与绝对的价值,然而在当下浮躁的学风下,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适用于屈原批评,与其一再去考证屈原忠君与否,是不是同性恋,倒不如去分析他作品的审美与艺术价值,如高尔泰在此书中所说的“作品,这是思想与情感的化石,联系到它所出土的地层,即当时宏观的历史社会背景,我们也许有可能可以找到某种了解屈原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高尔泰进一步联系历史背景,引出了中国文化的两种形态——史文化与巫文化。华夏族的祖先炎黄族的文化是由史官来把控和拿捏,故华夏文化基本上属于史官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用理性的史学语言与思维来解释一切文学与文化现象,将属于诗与神话的内容也纳入史的范围,故而也将神秘与心灵的内容排斥在外,这也是华夏文明与文化长期缺少超验的一面的原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文章变成了经国之大业,文学为政治与伦理服务。而另一脉巫文化,此即楚文化则宏扬感性与性灵,这也是屈原的文章汪洋滋肆、神秘浪漫的原因所在。本人尤喜爱作者所说:“巫*以鬼神使者的身份掌管文化,文化就具有许多神秘和浪漫的色彩。纷红骇绿的神话传说,交织着仿佛来自史前时期深渊的各种原始意象,加上潇湘水国遥岑远波引起的凄婉渺茫的遐想和雨雾深锁的幽谷峻岭引起的惶惑与恐惧,便构成了一种斑斓万翠、闪烁明灭的文化心理现象:神话美丽,民歌多情、宗教仪式有声有色,民间风俗丰富多彩。哲学思想更是杳冥深远,汪洋恣肆而不受控捉。“
中国其实自屈原起,就不缺乏超验之思,比如屈原的《天问》,比如庄子的作品,都不囿于现实与可见的世界,正是未被理性所束缚,所以也就有了无限的感官所带来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但华夏理性文化仍然是伟大的,它是历史的丰硕成果,而楚文化则与生命息息相关,它是超越历史与现实的,而历史的运动归根结底是生命的运动。如果把对楚辞的研究回归到原始生命力上来,破除理性结构的束缚,想必对于诗歌写作与审美性想象是一种注定会带来收益的事情。如果把屈原看成是一个卓绝的孤独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忠于君王的臣相,也许对于理解他诗作对人心的震撼更为有利,如高尔泰所说:“《离骚》是矛盾的交响乐,它的整个结构,是力和阻力互相斗争所形成的动态结构。“
《回归,还是出发》读后感(二):文艺评论不能忽略社会学的角度
高尔泰最新版本的自编文集中,和《艺术的觉醒》以及《美是自由的象征》的哲学思考不同,《回归,还是出发》是一本文学评论集。这本文学评论集不仅涉及20世纪80年代爆发性的文学潮,也涵盖了当下的一些作品。从1984年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的《绿化树》到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作品。
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描写女主人公陶莹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 而男主人公范汉儒则认为,这是一种叛国行为,无法原谅。所以两个人的爱情也无疾而终。高尔泰说出了至今仍有很多人不明白的话:祖国和zhengquan不是同一个概念。祖国是土地、文化、人民和个人经验的总体,它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价值体系。
在《绿化树印象》中,高尔泰继续这个话题。祖国是母亲吗?还是zhengquan是母亲?那些“平反”后感激涕零,说母亲打儿子,是对儿子好,即使打错了,也还是要爱母亲。他毫不客气的指出,有些人在纳粹集中营关久了,会模仿纳粹言行。绿化树即塑料树,张贤亮所写并非真实,而是假的。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发表于1985年,颇耐人寻味的是,几年后,高尔泰也走上了陶莹莹的路,从此旅居美国。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诺言,高尔泰不吝赞美之词,称其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他也好不避讳对莫言的不喜爱,说其是“商用酷刑欣赏,加爱国主义”。故事好看,精彩纷呈,血腥暴力,但是高尔泰给出了最致命的评价——“没有人文精神素养”,批评莫言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真实魔幻视若无睹,三缄其口。
虽然高尔泰认为莫言的作品商业化气息太浓,也不够有独立的思想价值,但他并不反对文学作品也是一件商品。他对于文学作品的期待,不仅仅是消费品,而是能不断激发出新的精神的作品,如此才能不朽。从上个世纪过来的人,因为自身曾经的遭遇,见过太多假大空的话语,懂得这些看似真诚的文字的危害,对于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这当然不是说作家必须写真人真事,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也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而应该是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现实和中国作家的智慧、激情和灵感的共同产物。对于这一产物的文艺评论,不能忽略社会学的角度。
高尔泰的有句话很值得人思考:网络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是冲突。(当然这并不仅仅指中国,还包括了全球各国。)
共勉。
《回归,还是出发》读后感(三):人生的意义再追寻
人生的意义再追寻
评《回归,还是出发》
把高尔泰老师的书,当作新年阅读的第一本,不胜荣幸。记得2012年读过高尔泰老师的《寻找家园》,书中写的就是他对于过往回忆的阐述,没有太多主观的评价,而只是将事情重重地描述,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沉重的事情,“我们的很多故事,都是笨出来的”,诚如作者所言,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笨重的故事》。8年时间过去了,再次看到高老师将他之前发表的作品集结出版,并为3本书写了个前言《庚子春愁》,联想到当年的自己,以及现在身处异国他乡、疫情肆虐的情境之下,再次追问人生的意义。阅读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地追问自己,这些年来做了哪些事,还有哪些事没做,未来还需要做哪些事。
很早以前讲过许倬云和许医农的书信来往中提及的人生意义追寻,记得许倬云老师说:“人生意义的追寻,就是一个过程。每一次的追问,都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都会有新的认识。”从8年前阅读《寻找家园》,到现在看《回归,还是出发》,至少进行了两次的人生思考:出发了这么久,我的初心改变了么?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未来还会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在每次遭遇困境的时候,我除了困顿和苦恼,更多的时候也会思考这些人生的问题:我遭受的痛苦同时,是不是也得到了人生的启示?我在困顿过程中的思考,是不是能给我困顿之后的清醒?无论如何,阅读和思考伴随着我走过的这8年时间,感悟和体验是我最大的收获。
书中开篇就是关于屈原的故事,屈原跳河自尽的意义在于哪儿?是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忠诚,以及对楚王的不满?还是仅仅是对于自己处境的堪忧,不愿意继续苟活下去的自行了断?亦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1927年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的昆明湖畔纵身一跃,跳进湖中。王国维先生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从这两个故事来看,他们追寻的意义已经到了尽头,所以选择了自我毁灭,留给后人猜测其中的原因,留给后人纪念他们曾经的成就。
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于死生之间,而退一步之后,日常的意义更在于我们人自身所具有的“用处”,高尔泰老师用了很多笔墨去思考人生意义,包括文学的当代意义,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内省;诗词中的忧患意识,以及创作者在诗词中表达的人生意义,还有他们可以带给人类社会的一种启蒙;面对当今社会信息发展、科技进步,人文精神却日渐衰退,哲学思考难以为继,而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责任,等等。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新冠疫情之下的世界格局如何再调整,以及知识分子和思想者应该在哪些方面重新获得“人生的意义”,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2021-1-12
《回归,还是出发》读后感(四):《回归,还是出发》:青松折取当麈尾,与君试谈天地初
《回归,还是出发》是高尔泰先生的一本文艺评论集,书中集结的作品既有高尔泰先生的讲演稿,如《我怎么看文学——从敦煌经变说起》;也有高尔泰先生的访谈录,如《艺术与人文》;还有高尔泰先生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思考,如《话到沧桑句便工》,不一而足。
高尔泰先生在前言《庚子春愁》中写道:悬崖在前,我们必须后退。这一句乍看之下,是在劝世人倒退,实则不然。
回到过去,从传统的宗教文明和世俗文明,亦即人性中的神性吸取能源重新出发,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重建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和正义原则。高尔泰先有感于这次病毒大流行,有感于人类的自私、人性的复杂。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说:现在只有科幻文学在思考“灾难”。
刘慈欣在一次采访中说:“假如我是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让我提一个提案的话,我就会提这个提案。”
“什么样的提案?”
“就是人类应该做好面对‘超级灾难’准备的提案。”
刘慈欣说:“目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灾难,我们很难找到实际的例子。但是,人类应该考虑面临“超级灾难”时的情况,应该有所准备。”
这里所说的“超级灾难”指的是什么呢?
刘慈欣解释说:就是整个全人类同时处于灾难之中,外部根本没有救援的状态。
这次病毒大流行显然没有到达“超级灾难”的程度,高尔泰先生与刘慈欣先生所担忧的事情也并不相同。然而,我在读到这里时莫名想到了刘慈欣在另一次采访中坚定地说出“我对人类文明是很有信心的。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成长到现在是很伟大的(在宇宙中)”时的表情。
这种感觉在读高尔泰先生的《跨越代沟》时再次出现。
文中,高尔泰先生初时认为代沟两端的人犹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种生物,直到高尔泰先生接触了美国女孩克瑞斯蒂和朱平。
克瑞斯蒂画油画,以人们濒死时意识消失前刹那之间的表情为主题,高尔泰先生惊讶于克瑞斯蒂的想象力——在这个自由得失重的、后现代解构语境之中,能在一个孩子的艺术作品中,听到那古老而又新鲜的话语的回声。
朱平的画作随意,在高尔泰先生看来,朱平能够听到万物细微的语音。
“童心之童,无关年龄。”我很喜欢高尔泰先生写在文中的这句话。高尔泰先生“庚子春愁”、刘慈欣先生提议做好应对“超级灾难”的准备,在我看来都是基于一份童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正因为有童心,才有“家国天下的情怀,舍我其谁的担当。”
在《我怎么看文学——从敦煌经变说起》一文中,高尔泰先生讲到了对文学的担忧。高尔泰先生说,文学是精神产品,然而当今时代有些文学作品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人文精神。
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的表现力和独创性了。高尔泰先生的言外之意是当今有些文学作品失了初心。所谓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当文字不单单用来记录(史书、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而被赋予其他思想和情感,并具有了艺术之美,才可称为文学艺术。
高尔泰先生提议瑞典皇家学院取消文学奖项,多元世界文学需要自由的声音,诺贝尔文学奖“模式化”的甄选已经不能满足当今天时代的需要,甚至会带来价值的错乱,这是文学爱好者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文中提及莫言的《檀香刑》《酒国》恰巧前些日子刚刚读过。我震撼于《檀香刑》的残忍,惊讶于《酒国》的想象力。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快感”的确有,读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若论“没有人文精神的营养”倒也不尽然。单一句“执刑完毕,请大人验刑”虽残酷至极,却也道出了赵甲这位“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的职业自豪感。高尔泰先生说: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就是人文精神,一种个体心灵的素质。一方面,孤儿赵甲为生存沦为人性尽失的刽子手,另一方面,赵甲视职业为生命,精通历代酷刑 ,并予以再发明、再创造。赵甲这个人物形象变态扭曲,却也不能说没有人物精神的传递。
无论是阅读还是生活,愿我们都能够如高尔泰先生般有“不合时宜”的冲动——“青松折取当麈尾,与君试谈天地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