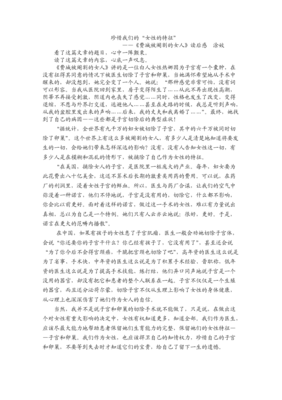
《恐惧与颤栗》是一本由[丹麦] 克尔凯郭尔著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页数:1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恐惧与颤栗》精选点评:
●因为是神学书籍,最终还是没能完全读完,也没理解。只是是讲伦理的
●克尔凯戈尔行文真得很罗嗦……
●显然,人们有可能理解亚伯拉罕,但只是以理解那个悖论的方式来理解亚伯拉罕。至于我,我也可能理解亚伯拉罕,但我意识到我没有勇气这样说,也几乎没有勇气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做;但这绝非是说,这种行为不重要,而是说,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那么,当代对悲剧英雄的裁决又是什么呢?他是伟大的,值得敬佩的。心灵高尚者的高尚是一致的,下一代总为上一代建立陪审团,而裁决总是同样的。但是,无人能理解亚伯拉罕。他获得了什么呢?他仍然忠实于他的爱。爱上帝者不需要眼泪,不需要敬佩;他完全忘记了爱的痛苦。他确实忘记得如此干净,以至于若是上帝都记不起的话,他的痛苦就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了,因为他暗暗观看,他承认烦恼,计数泪珠,而且什么也忘记不了。确实如此,要么存在着一个悖论,作为个体的个人处于与绝对的绝对关系之中;要么就是亚伯拉罕输掉
●前两个问题看的比较清楚。。第三个就糊了。。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从去年读到现在没读完也没读懂,为了读懂他,想说去看看存在主义的老祖宗,才发现,更没读懂,硬是把这本书每个字都看完。。整本书都以亚伯拉罕来辩证,存在主义是如何从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宗教信仰者发展到加缪这样激进无神论者的呃。。。
●而亚拉伯罕不作悲歌
●毛线啊毛线,我怎么会天真的以为你像卡夫卡
●偷懶過了一次中文,幾個關鍵詞都讓人困惑,比如recollection翻成回忆,意思马上变掉了。movement翻成運動也很讓人費解。還是去讀一遍英文版好了。
●印像中就只剩下这句话了,除了那个关于断奶期的描述,除了关于亚伯拉罕的种种美好,可是今天俺再认真审思,却发现这句话不对,克氏力图创造对立,不得不说其中惊心动魄,那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尤如一个油滑的摆渡者,一个内外动摇的导引者,一个极尽隐秘的窥运者,是的,他摆脱不了他叙...
●『唯拔出刀子者才得到以撒』 『人如不知恐怖,也就不知偉大』 為了更高的義務,信仰騎士必定要在無限愛意之中將最珍貴之物親手殺死。要相信,在無限棄絕的運動中,是平和和安寧。在深重的痛苦中,人與存在達到調和,也在此時,人才真正得到了永恆之物。亞伯拉罕的平靜無人可擾。他對以撒的愛不可言說,也絕不能說。所以從未擁有這種禀賦的人,也註定無法理解他感情與行為的絕對矛盾。他的偉大,同時來自於最高的自我主義以及絕對的獻身。它只存在於高於(外在於)普遍性同時又處於普遍性範疇下的個體性當中,也只存在於不可解的荒誕之中、在恐懼與戰慄之中。他不斷地經受著精神考驗。他背負著旁人一無所知的責任,孑然一身地走在曠世間,永不得安慰。他不是一個悲劇英雄,因而無法被定義,只能稱為奇蹟。只能相信,他沒有輸掉。只是悖論,不可解。
《恐惧与颤栗》读后感(一):一流的文本,一流的译者
这本恐惧与战栗,几乎可以说是克凯郭尔最通俗易懂的一本书了 如果连这本书都读不下去那么克尔凯郭尔的其他文本估计就是天书了 事实上,它们也正是天书不要跟我说你懂克尔凯郭这小子晦涩难懂跟黑格尔有得一拼其实他们背道而驰 然而同时这本书也是克尔凯郭尔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通过无限的弃绝而拥有的信仰和爱情在字里行间闪闪发光 怎么可以这样深刻这样绝望而坚定?其实像概念恐惧,致使的疾病,以及非此即彼等作品就算是哲学系专业出身的人,估计也懂不了30%而这本书几乎是我们能够到达克尔凯郭的唯一捷径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说这个译本不好的人,到底是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虽然这本书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就译者与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契合度上,绝对比京不特更高!这也是我阅读的所有关于克尔凯郭的文本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一个版本 为刘继老师疯狂打call 。
《恐惧与颤栗》读后感(二):他的信心就是他的痛苦
人们都会赞美亚伯拉罕的伟大,但人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都遗漏了——不安。
亚伯拉罕的所为,从世俗伦理看来,就是一场谋杀;
宗教表述为,他有意献出以撒。
——二者之间其实有一个荒谬的距离。
如果亚伯拉罕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弃以撒的性命,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得到世人的理解和眼泪;
如果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确信神不会让他真的动手杀了以撒,或者从一开始确信神会让以撒死后复活,那他的“确信”不是“信心”;
如果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坦然接受了神的试验,决心为了神放弃以撒的性命,那他就只是一个杀人犯。
正是因为到最后一刻亚伯拉罕都深爱着儿子以撒,所以,他愿意服从“献以撒为燔祭”这一打破伦理的试验时,其全程都是伴随着不安、恐惧与颤栗的,而所有的不安只是他个人(与神)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没有人可以理解,更没有借口可以慰藉自己。
甚至他没有办法说出口。
——这是孤独的精神考验。
信仰骑士在无人的旷野间,肩负着可怕的责任独自前行。
《恐惧与颤栗》读后感(三):对不起我的读书笔记略烦(。
花了一个晚上一个下午读完,只要把里头对于上帝的信仰换作自己的信仰的话,很多话简直不能同意更多。
——成为自己的骑士吧。
(亚伯拉罕颂)
3
向人示哀、与悲泣者同悲泣是人之常情,但更伟大的是拥有信念,更值得深思的是拥有信念的人。
(正文)
27
无限弃绝的运动是人人都能够做的,宣称无法去做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懦夫。然而,信仰却是另一码事。
34
当一个儿子忘记了他的职责,当国家把判断的权力托付给父亲,当法律要求以父亲的手进行惩罚,那么,父亲就必须英雄式地忘记那有罪之人正是他的儿子。他必须高高地隐藏起他的痛苦。
40
一个人可能会出生低下,但我仍然要求他不要不人道地对待自己,以至于只是远远地想象国王的城堡,模糊地憧憬它的伟大,并在抬高它的同时又毁灭它,因为他对它的抬高是如此地粗俗。我还要要求他充满信心地活着,充满尊严地活着。他决不能如此蛮横,以至于无理地闯入王宫破坏一切。他应该在轻松地、从容地观看每一种合适的标价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欢乐,这会使他早就一副自由的心灵。
43
当一个人走上了悲剧英雄那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里会有许多人可以给他忠告;可是对于走上了信仰的羊肠小道的人,却无人能够给予忠告,因为无人理解他。
49
任何要求一个人的爱的人,都相信这种爱是要靠不在乎与愿望相反的结果来证明的;但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任何以此种想象中的爱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人,在他要求这样一种爱的同时,也就签署了他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51
任何知道作为个体去存在是最为可怕的事情的人,都不惧坚持这是最为伟大的。
悲剧英雄将他自己让渡出去,以表现普遍性;信仰骑士将普通性让渡出去,以成为个体性的存在。
52
信仰的骑士很明白,为普遍性而放弃自己是令人钦佩的;它需要勇气;但正因是为普遍性而放弃自己,这里也就有一种安全感。
《恐惧与颤栗》读后感(四):悲剧英雄与信仰骑士
伦理具有普遍性,普遍性的事物是敞开的,而活生生的、具有感知和直觉的个人却是隐蔽的,但伦理要求人在普遍性中敞开自己。因此,在伦理的生活观中,个体的任务就是剥去自己的内在性,在外在的普遍性中表达自己,从一个具体的人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的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在普遍性的范畴中找到据点,遵守统一准则和信条,外在的言行近乎一致,可以到达彼此理解。但有一种不同于情感和直觉的内在性,就是信仰的内在性, 它不但高于普遍伦理,而且决定了普遍伦理。信仰的人其内在深深植根在绝对关系之中,因此这种内在性无论如何都无法调解到普遍的外在性之中,任何对信仰的第二解释都会落入某个普遍的范畴之中,因此处于信仰中的个体简直不能被人理解。在伦理中,外在决定内在,普遍高于个体;但信仰的悖论就是,内在性决定外在性,个体高于普遍性。 悲剧英雄和信仰骑士是克尔凯郭尔对两则古老故事的独特阐释 :悲剧英雄是希腊戏剧中阿伽门农献爱女伊芙琴尼亚的故事中,阿伽门农和他的海上舰队在讨伐特洛伊时得罪了一位女神,女神要求他献出自己的女儿才能平息愤怒,让舰队安全到达。阿伽门农在将士们的要挟下忍痛割爱,只得将女儿献祭,但他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和国民的爱戴。信仰骑士是一个基督教中经久传诵,也牧师在布道最热衷于挖掘其中深意的《圣经》故事——信仰之父亚伯拉罕献爱子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祖先,他直到九十九岁才有了一个儿子,但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自己的独生爱子献祭,亚伯拉罕听从了,将儿子带到祭坛前,但他向儿子举起刀的那一刻,上帝却及时阻止了他,因为上帝并非真的想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仅是对上帝之爱和信仰的一场精神考验。 在普遍伦理的范畴内理解信仰骑士,他和悲剧英雄并无区别,因为二者的传奇经历最后赢得了人们的百世敬仰。但克尔凯郭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令所有基督徒们惊骇的问题:凭什么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信仰之父,而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弑子凶犯?如果故事中的上帝没有及时阻止亚伯拉罕,他就真的杀害了自己的独生子,果真如此,亚伯拉罕不会赢得后世的称赞和成为信仰的榜样,而是《圣经》记载中的一个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但阿伽门农的女儿最后死了,是他亲手杀死的,但阿伽门农的这一行为却使他得到了荣誉和爱戴。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一旦改写,信仰骑士和悲剧英雄的不同之处就显而易见了:在悲剧英雄最后放弃了女儿,放弃了在伦理上父亲对女儿的责任,但换取了在伦理上更高尚的价值——国家和荣誉。但在信仰中的亚伯拉罕至始至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他从未放弃作为普遍伦理中父亲对儿子的责任,他在举刀的那一刻依然深爱着儿子,但与此同时,他在以最大的冒险代价进行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斗争,与至高上帝的斗争:他相信自己所认识和信仰的上帝不会真的要走他的儿子,但如果上帝真的想要,他也就真的给。这个信仰的悖论在于,他对儿子的爱越深,就越能体现他对上帝的信仰之深,一旦他放弃了对儿子珍爱和希望他存活下来的信念,他就非但不会是信仰之父,而且还是一个弑子犯。因此,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其关键就在于他从未放弃过任何,而是进行了一场关于争取最大可能性的信仰斗争,他在普遍伦理的边界上进行信仰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勇气源自于他处于与绝对者的绝对关系之中,因此有着内在精神的确定性而引发的巨大激情。 这个时代少有人真正理解信仰之父的伟大之处,也少人理解信仰的内在精神的确定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英雄论是以结果来判断英雄,因为结果证明,亚伯拉罕的儿子最后没有死。但这是对英雄的冒犯,这样的时代也就不会产生英雄,而只会产生小丑。黑格尔主义式的英雄将往往将自己看做是历史规律召唤出来的时代精神的合作者,但真正的英雄不是恰巧在他身上印证了必然性的规律而变得伟大,因为事实上没有人会认为中彩是一件伟大的事。如果因为一个人打算在开始行动时就推算好结局,那就不会有开端,更不会有英雄。尽管全世界都为英雄的成功结局而欢呼,但它却无助于英雄。英雄不是根据其结果成为英雄,而是在行动的开端。 信仰骑士和悲剧英雄的差异不单在于面对不可能性时是放弃抑或斗争,也在于信仰骑士是总是孤身一人,但悲剧英雄却是宗派主义的。悲剧英雄属于普遍性中,他知道属于普遍性的事物是光荣的,将自己转化为普遍性中存在的个人,其伟大之处人人可以辨认。他在普遍性中理解别人,别人也在普遍性中理解自己,他虽然放弃了某种普遍伦理的责任,但换取了更高的伦理价值,他在放弃的悲痛中获得了别人的安慰和理解,因此也获得了安全感;但信仰骑士在普遍性之外,在信仰的崎岖小路上,他处在恐惧中,却没有与他感同身受的人,他不能使人们理解自己,而且有可能被认为是疯子。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何为恐惧,也就不知道何为伟大。伦理只在乎外在的行为,而信仰在乎人的内在精神。一个人是有了内在信仰,才会表现得遵守普遍伦理,而不是遵守普遍伦理,才得出他有信仰。信仰是内容,伦理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因此内在决定外在 。 个体信仰高于普遍伦理。
《恐惧与颤栗》读后感(五):克尔凯郭尔的悖论——阿迦门侬、亚伯拉罕、信仰的骑士
三个故事——信仰、伦理(理性已经非常弱化了)
伦理学追寻的是普遍的价值,它的价值体现是悲剧英雄。
关于悲剧英雄——阿迦门侬的故事
古希腊关于特洛伊战争中,阿迦门侬因为在军事讨伐特洛伊的途中,无意间冒犯了女神阿尔忒弥斯。女神大怒,让阿迦门侬舰队所在的奥利斯港没有风使船前行,于是船支被困。占卜师卡尔卡斯预言只有阿迦门侬将自己美丽的小女儿伊芙琴尼亚献出去的时候,女神才会息怒。在众将士的要求和反叛威胁下,阿迦门侬这样做了,杀了他的女儿,成为了悲剧英雄。
(故事的其它部分:阿迦门侬的特洛伊之战胜利了,回来后,他却被她的妻子杀死了。很多年后,他的儿子为了报父亲的仇再次杀死了他的母亲和新的国王。最后诸神对之审判的时候由于雅典娜投给他的关键一票致使他免于受罪,于是整个故事结束了。)
当然当故事仅以梗概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整个故事的色彩,那悲剧性的声音就全部褪去了。因为你没有读到阿迦门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美丽的、充满生命的孩子,于是在你的脑海里出现的只是任何一个孩童的形象,一个缺少一张脸的孩子,而事实上,他所要献祭的是一个具体的、可爱的、他自己的孩子。于是两者之间的存在的挣扎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次又一次对道德和伦理的颠覆。
父亲杀了女儿,妻子杀了丈夫,儿子杀了母亲。倘若我只是将故事的第一部分说出来,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看不到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对整个故事的价值判断。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责怪阿迦门侬的做法,认为他不该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然而当我读到她的妻子杀了他的丈夫的时候,我却站在另一边,也是说我认为阿迦门侬是不该被杀的,不该为此负责的,他虽把女儿献祭,却不该被他妻子所杀。当他的儿子为他复仇的时候,我是赞成的。于是,整个故事,我始终偏向着阿迦门侬,于是他也就此成为了一个悲剧英雄。牺牲了自己女儿的性命为大家赢得战争的胜利,却最终被妻子背叛,被杀。
这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要谈的伦理的普遍性,阿迦门侬站在伦理的一边,用敞开可言说的方式告诉大家他是多么痛苦献祭他的女儿,他在这个故事完成了他的普遍性,也就是得到了理解,最终成为了悲剧英雄。悲剧英雄是伦理顶端的纯粹的凡人,是能被所有人理解的。为了普遍性而抛弃自己的意愿。
然而作为悲剧英雄的阿迦门侬,是否值得我们那样的尊敬。他的献祭在最初的我看来是值得指责,不过我却最终统一在他的那一边,也就是敞开的大众伦理一边。正是这一点,为了大家,献出女儿。克尔凯郭尔指出,这种悲剧英雄其实是容易做到的,他内心并没有那么多的挣扎。
作者在这里要展现的信仰与伦理之争。信仰是体现为绝对的个体性。信仰的骑士阿——
信仰的高度——亚伯拉罕的故事
亚伯拉罕是上帝中意的一个人,为了给他一个考验,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妻子在他很老的时候怀上了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于是他很爱很爱。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要求亚伯拉罕用他的儿子做献祭的羔羊。于是亚伯拉罕就做了。最后时刻,上帝用一只羔羊代替了以撒。
我用照做这个词是因为,我既不想表现亚伯拉罕行动上的毫不犹豫,然而同时也想说,他心里是比任何人都爱以撒的,世界上已经不可能有一个人更难执行这一行为。
在圣经里的大部分故事是不会为我们困扰的。因为上帝和道德同在,他总是伦理的典范,对他的信任也就是对我们共同道德尺度的信任。然而亚伯拉罕的故事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要告诉我们当伦理和信仰产生被悖论的时候,哪一样才是更高的。在这一点上,克尔凯郭尔说,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对一个人信仰的最高挑战。伦理站在普遍性一方,也是大部分的人的伦理价值——父亲不可以杀儿子,而信仰的那一方什么也没有,信仰是个人的,也是因为他是个人的,所以它是无法言说的,如此的个体要被别人理解几乎是难得。然而信仰却要求他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祭出去。这就是作者反反复复所谈的信仰的悖论:个体性高于普遍性。这种信仰和荒诞连接在一起,而荒诞的意义就在于缺少被其他理解的可能,却依旧呈现为事实了。亚伯拉罕的献祭是纯粹个人的,一旦他缺少一点信仰,他就会沦为一个杀人犯,把儿子献给普遍性是光荣的,而他却要在信仰中时时考验,并且没有原谅给他,他不接受任何人的理解。他是隐蔽的,是无法言说的。所以这是一个更难的选择,亚伯拉罕的境界要比阿迦门侬高很多很多,并且是作者试图理解,希望我们理解的,信仰的高度。
于是伦理学因为他的普遍性表现为外在性,信仰因为他的个体性表现为内在性。于是克尔凯郭尔追求的是要抛开暂时,追求永恒的纯粹,在荒诞和信仰中得到放弃所拥有的勇气,于是才能得到如同亚伯拉罕的永恒的以撒。诚然,这种放弃是痛苦并且孤独的,但是只有这般的坚持才能坚持上帝的爱,坚持信仰。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人最高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的信仰的骑士
最后,我要讲关于克尔凯郭尔关于信仰骑士的故事。
他是孤独的,是绝对的个体。是克尔凯郭尔所要称颂的所有。
信仰的骑士是如何行动的呢。
他刻板,他普通,他喜欢见到他见到的一切事物。这是世俗的人永恒的放弃了一切,却依靠荒诞赢回了一切。他并因为在有限性里的停留而感到害怕,而是是感到安全。……好吧,我也得承认关于这个信仰的骑士让我有点莫名(如果大家愿意对他有些了解的话,可以自行参阅《恐惧与颤栗》中的引)
于是他要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与认识这个骑士,这个令人失望的骑士。
“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公主,这种爱是他生活全部实质所在。然而种恋爱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从理想转变为现实。”
于是这个骑士该怎么做呢——他决不会为了任何原因放弃这种爱,因为爱就是他生命的所有意义所在,他要让他浸透他全身,让他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爱。忘记这种爱是最可笑的做法,忘记这种爱就是对他自己实质的爱,对他自己的遗忘。骑士做的不是遗忘对公主的爱,而是回忆这种爱,回忆是痛苦的,在对无限的弃绝中他与存在达成永恒,于是爱将成为永恒的表达。在另一方面,克认为骑士决不会像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追逐这一切,“因为精神中一切都有可能,但是对于现实,许多东西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不会可笑的去实现那些理想成真的可能,而是不在有限的意义上关注公主所做的一切,不再关心公主是否嫁给了王子,公主是否幸福,是否快乐的这类问题。他将永远沉浸在他的爱的永恒里。他在无限运动中保持着这种爱。
他甚至希望这位公主应该也有相似的禀赋,于是那所谓的“伯拉图的精神恋爱”实现了。他们变老,他们的爱情却永远不会变质,因为生命是有限的,而他们的爱是进行无限运动的。
可怜的克尔凯郭尔于是将这种精神运用到他的实践生活里。于是即使在那个没有现实阻碍的相爱里,他和她的热恋到最后却因为他对无限的爱的追求,放弃了与那个女子的婚约。他那与生俱来的罪恶(他是他父亲在他妻子过世几天后,与女仆通奸后所生下的),让他在信仰里苦苦挣扎。让如此忠实于此信仰的骑士,当他后来实在又在幻想这样的恋爱,重新与列琪娜取得联系时,却意外地得到她要结婚的消息。于是,我们的骑士终于实实在在的要一辈子进行这无可奈何的痛苦的无限运动了。是的,这是他要的,不,这也是他不要的。
于是这部作品的书名就是这样让人纠结的。
我并不是想在这里驳斥他的信仰,或者再次证明他荒诞的对信仰的坚持。因为这个信仰在这个世界里早已被科学的大厦所取代了。于是人人都可以对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不屑一顾。
同样是献祭,阿迦门侬是因为外在的世俗的普遍的(也就是伦理)的力量而放弃了自己对女儿的爱,牺牲了自己。亚伯拉罕是因为内在的超俗的个人的(也就是信仰)的力量而牺牲了以撒。前者成为了英雄,后者成为了荒诞。如果就这种放弃的精神而言,或许后者的确更为痛苦,也更值得人的尊敬。荒诞——因为缺乏理解就成了荒诞。
总结阐述了一下克尔凯郭尔在这本书里的观点。
在他绝对孤独的个体里,他一个人在信仰里完成了他痛苦、挣扎、矛盾,在他可怕的孤独里做着对“无限的弃绝”,努力达到信仰的高度。
唉,我既不能讨厌他,也不能喜欢他。他的言论让我觉得有点恐怖,即使撇开宗教的色彩,他的孤独,亚伯拉罕式的孤独意义何在呢。
我只是反复阅读也没有读到,那最高的所在。
也许只是因为我没有宗教的信仰,请不要那样在精神世界里保持着无限的爱。那信仰的骑士的爱,决不是尘世间的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