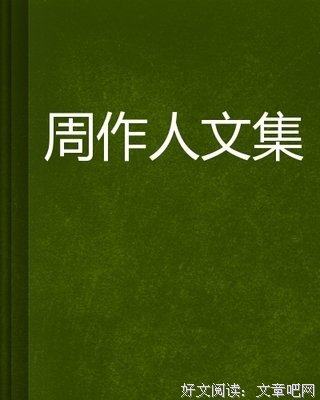
《周作人传》是一本由钱理群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6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传》精选点评:
●此传有很多精彩的点睛之笔,值得做深入研究。但如果想要了解周作人详尽生平,还是老老实实看年谱为好。作者有时情感太浓烈。
●购于绍兴鲁迅故居。高铁读完。
●个人在时代里面的渺小这命题太沉重
●在那样一个时代,如果不是斗士,那么只剩下悲哀的文人气了。
●有些評論不敢苟同。
●主观性较强,作者的情感融于其中,是特色。但于研究,需要去看客观史料才可,停于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已成网络里,便难得真相。
●思想传记,用力甚勤。钱理群的笔外一直有鲁迅在,周氏兄弟传里传外呼应。可与《周作人论》交互读。
●他比鲁迅在文学上的造诣低吗?难道只因为他做过汉奸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曾经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开拓者之一。
●周作人,是真正的文人,不向魯迅是戰士。真正的文人在亂世中,都是悲哀而寂寞的。
●本书写毕于1989年3月7日 喜欢童年章节还有二十年代巅峰时代的周作人文章 钱老师的分析心理,宗教还有一代知识分子都很受益 落水开始的章节就越来越压抑了。八十高龄的周作人还被红卫兵小将们抄家罚跪鞭子抽打,最黑暗的时代。顺便推荐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落水期间的周作人,这本书写的很有才。
《周作人传》读后感(一):七嘴八舌说知堂
钱理群写得很投入,有他自己的心灵的参与,所以读得慢,值得读。知堂老人该如何评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也是个难题,也许永远也是这样,没有定论,而反复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想,档案馆里的周作人与研究界的周作人,哪个更贴近真实?一个不轻的文人折射一个复杂时代。
《周作人传》读后感(二):读《周作人传》
一位爱读书的朋友对我说:“人文类传记中,我最爱《周作人传》。”于是,我对这本书肃然起敬,心往神驰,急索拜读。
人物传记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有其特殊性,是一个人写另外一个人,不是散文的以自己或其他真实为蓝本,也不是小说以绝对的虚构为支架,所以,上乘的人物传记也与两个因素牵连。一则涉及到作者本身的文采、思路、水平、格调;二则涉及到所写人物手是不是有书写的价值,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跌宕起伏的生命剧情,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交融。有些传记作者倒是文采斐然,笔杆子颇有力度,但选了个毫无价值的人物,读之也是味同嚼蜡。而好端端的人物,被作者肢解的面目全非、不堪入目的也有。二者都能达到一定水准的,方为大家之作。《周作人传》便是这么一个天作之合。
钱理群读鲁迅周作人是真正读进去的。比如对于周氏兄弟失和一事,列举了大量的材料,定性于家庭内部纠纷,但对于结论却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毕竟“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旺,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在《周作人传》里,没有资料的,作者也没有发挥穿越过的能力,用想象力来演绎一段曲折来。比如关于周作人的婚姻,由于周作人只字未提,所以也付诸阙如。钱理群把鲁迅周作人的很多治学理念都溶进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了。
《周作人传》梳理了周作人的一生。周作人童年浸润在江南水乡那“四时八节”的传统文化中,每一个节日,都给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生色香味之美的回忆。青少年时在南京、日本求学,与书结缘。回国后,周作人在寂寞中默默耕耘,渐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大时代的弄潮儿。20世纪40年代初又附逆伪汪政府,成了“老而为吏”的官僚。日本投降后,一千五百多日的老虎桥监狱,他满脸狼狈,晚年靠着回忆鲁迅赚钱糊口。1967年,这位”寿则多辱“,充满争议的老人,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后很快就“销声灭迹”了。
周作人是散文家,翻译家,民俗学的开拓人,在文学史上,思想史上,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我读完此书,有两个纠结之处。
一则,兄弟两人的失和。陈丹青《笑谈大先生》里提起周家人气质非凡,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的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鲁迅也“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如此模样的两兄弟,竟然“互为参商”,难免让人怅然。抛开政治因素,专就文学成就来说,他们没有谁在谁的阴影下,有的只是难以言说的兄弟情。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在南京上学的鲁迅鼓励在老家的周作人,“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在日本留学时期,兄弟二人亦是协同作战,共赴启蒙运动。对于兄弟失和,双方纵是决口不提,但留给文坛的总是一桩绕不过去的公案。更令人唏嘘的是,鲁迅缠绵病榻之际,都在读周作人的书,四十多年后,临近垂危的周作人,也在读鲁迅的文章。
二则,享受读书的人生。读罢《周作人传》,遂购置了周作人自编集《夜读抄》、《自己的园地》、《苦竹杂记》、《苦茶随笔》等,沉浸在五四年代的文化濡染。书籍是更有永恒意义的伴侣,且不论父母、儿孙、配偶,单说你喜欢的比如打球、或者嗑瓜子、嚼肉,有朝一日,因为年衰力竭,可能都会远离你。只有书籍,还能在孤寂时,给你以慰藉。欢快的日子总非是人之常态,周作人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省会或与我也适宜。”读《周作人传》后,我亦想追随读书人的脚步而去,在书籍里醉生梦死。
《周作人传》读后感(三):平庸的爱智者
有时实在不知道读什么好,那就读传记吧。读一本传记,就相当于用传主的身份活了一辈子,——阅读总是让我们活得更多。但是,每读完一本传记的最后一页,曲终人散,合上书,往往忍不住一声长叹。叹什么啊?说不出。很多事情真是不堪说、不想说的。
这篇短文在草稿箱里放了几个礼拜,好几次打开了写点什么,又一段段删去。顾虑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自己、甚至作者钱理群其实很难了解周作人,用个时髦的说法,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别的不说,周氏“不但精通本国语言文字,而且熟谙日本语(包括古日语)、希腊语、英语(包括古英语)、世界语”(268页),他看见的是山顶上的风景,我们这些住在地下室的房客要如何体会呢?
这么想下去,很多书都不必读了。最后还是自我鼓励:井底之蛙也有仰望的权利,再说了,我历来都是六经注我的野狐禅。那就随便做点记录吧。既然浅陋,又何必藏拙?
【日本】(99页)
周作人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
【“非宗教同盟”运动】(208-213页)
1922年3月,一个叫“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在《晨报》发表《宣言》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清华召开的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接着,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愤然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一时舆论大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卷入这场“非宗教同盟”运动中。此书记录:
周作人……从《宣言》的字里行间——“污蔑”、“宣战”、“走狗”之类——直觉地感到一种陈旧的似曾相识的气息,口气的“威严”有如专制时代的“诏檄露布”,这使人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
1922年3月31日,周作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在遭到批评后,周作人又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表明自己不仅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而是要进一步“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这即使只在纸上声讨的干涉信仰的事情,即为日后取缔思想——干涉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
这些话,今天来看,岂不正是一语成谶?
钱理群随后的议论也值得一记,他认为,被帝国主义侵略所激怒的中国青年不可能周作人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因为——
这里确实存在着可悲的认识误差。这是由于西方宗教思想的传入中国所具有的两重性引起的:一方面。它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成分,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在正常的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而是借助侵略的武力,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它的活动必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侵略性质,特别是宗教意识中的专断崇拜与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结合,更成为一种阻碍中国人民觉醒的麻醉药。正是这两重性,很容易形成认识与行为上的分歧:学者们着重于前者,就较多地肯定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积极意义;而群众(特别是急进的青年学生)则更具体地感受着后者,并激发起一种爱国主义激情,反对基督教的传入。而正如周作人及无私先驱者们所预计到的那样,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东西。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们一旦陷入这类非理性的宗教似的狂热中(尽管他们主观上是真诚地反宗教的),他们就越发容易趋于极端,并且对不同意见不能相容,表现出“群众专制”的倾向。于是,对于周作人等的谴责也就逐渐升级,直到暗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矛盾就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
近读《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后期,教授与学生之间也曾有类似的矛盾,只是远没有这样强烈。而接下来周作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很能表现他的个性:
对于这一切,周作人是坦然的:他从来没有如鲁迅那样对青年人寄予也许是过于急切的希望,他始终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信青年享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因此,他总是毫无顾忌地与青年据理力争。
随后,陈独秀与周作人展开论战。史料表明,“非宗教同盟”具有中国共产党的背景。
【《国语文学谈》】(268页)
1925年12月,周作人写了一篇《国语文学谈》,其中包含了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
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人民还说满清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
结论是:必须“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这是很难得、很清醒的看法。本想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只是一时间没能找到原文。
【文章】
周作人的文章我读过的极少,唯一喜欢的只是《故乡的野菜》开头那一段: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高中时我写过类似的意思,后来读到他这一段,既佩服又恼火,佩服的是他以平和的语调把这意思说得那么漂亮,恼火的是又一个想法被前人占用了。可惜他别的文字就不是这样,那种著名的文抄公风格我委实无福消受,缠夹不清的闲笔、吞吞吐吐的曲笔也多,又糯,又涩,又暧昧,让人敬而远之。这次读完钱理群先生为他所做的传记,对他晚年的文字如《木片集》又有了兴趣,得空会找来看看。另有买过而没读过的《知堂回忆录》,似乎也可以在秋日或冬夜翻一翻。
【平庸的爱智者】
论断人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不过我总是忍不住。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认为“平庸的爱智者”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周作人形象。先说“平庸”,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贬义,(如果以某些刻意“不走寻常路”的人士做背景,它反倒是个褒义词。)在我看来,除去肚子里的学问,他就是个平常之极的普通人,有些恍惚,有些懦弱,就像一个蔫蔫的邻居。至于“爱智者”,则是借用了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对于知识的好奇,对于清明理性的追求,这是周作人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地方。
看周作人的行事,常常忍不住想,读书阅世所得来的知识、经验对人的影响恐怕是很有限的,更关键的或许还是早年形成的人格与习惯。据此,我或许应当把上面那个偏正短语置换为“爱智的庸人”。当然,这个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贬义。要知道,如今要找他那样的庸人,可是难上加难。
《周作人传》读后感(四):与知堂的约定
读大学时常听到这样一段告白:不到XX岁,不读周作人。那年岁大概要大于而立,甚至不惑之年。但面对这样的告白,就如面对禁书一样,总有一种神秘的处境逼迫着自己不由自主地去验证,至于验证的结果,不管有无共鸣,都算是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了。
于是带着约定的心,我读起周作人。这算是有点游戏的心态,既然要找个年岁出来,我想,也应该要大些才是,否则便显得过于老成了。那么既然是公认的闲适温厚,总该是瞌睡碰枕头时拿起最为合宜。这样一睡着,我便可说“不行,不行,年纪还小,看不惯这样智者的散文”。
放下周作人大约一年,因朋友的推荐,又重新拿起。但此时的心情,已经变了许多,对文学对人事,不再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天真浪漫。但偶尔也能找出类似心情的话,看见前辈也是这样成长的:“这一年里我的唯一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以前我也自以为是有所知的,在古今的圣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以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这倒是很简易的办法。但是这样的一位师傅后来觉得逐渐有点难找……”于是还有些感动,有点宽慰。
想起早期的“绅士鬼”“流氓鬼”之说,我想,这是所有人永恒的对立统一的生命状态。钱老师说:
原来周作人其人其文都有不平和的一面。他早期有充满“浮躁凌厉之气”之作,可以为证;他后期时时标榜闲适,其潜在动因之一就是内心深处并不平静,即所谓“有闲而(心)无暇”,并且有时也会冒出“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的“神来之笔”。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喜欢弄一点过激的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只是到‘要被火烤了为止’”——仍然是“游戏态度”,不过换了花样而已。
只不过换了花样而已,这是战略的不同。但心境呢,我想也早已大相径庭了吧。人,最荒凉的时候,是决绝而无力的,所以才沉默转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至于文字呢?大先生曾说“长歌当哭”,周作人却说“就是平常谈话,也常觉得自己有些话是虚空的,不与心情切实相应,说出时便即知道,感到一种恶心的寂寞,好像是嘴里尝到了什么肥皂。”我想大先生的长歌并未能当哭,他心里还有太多的远方,他也只是远方之一。但当他成为独立宇宙时,一并也有如此感觉,作文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不过,前人早已说过“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即乎篇成,半折心始。”情与言之难合,人之互相理解至难,也不可勉强。周作人只说“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个人读,想结点缘罢了”。然而,总归是寂寞的。
这样想来,我倒于文字有些悲观了。不但不相信那“心灵的对话”,也一并否认了那“心灵的独白”。但文字终归是有功用的,论理、审美、慰藉,甚至休闲。周作人说“我们的天性欲有所取,但同时也欲有所与。能使我们最完全地满足这个欲求的,第一便是文学”。而我现在对于文字的要求,也即周作人的自我评价。“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但反过来说,此道德也只是我以为的“道德”,那么,也就自作主张了。
但庆幸至少目前,我还相信读书,能成全较为健全的思想和独立的判断。记得胡兰成对周作人有段评价“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无论这评语是否到位,这样的境界,我想是吾辈凡人心向往之的。
忘记在哪本书里看见周作人被带上法庭的一张照片,那本书的作者似乎给了这样的形容词——从容。姑且不论政治罪,但在这样的情形,走出这样的步伐,无疑是一种修养。记得大学上某门课程,某师义愤填膺地讲述周作人的叛国。我趴在桌上想,如果现在有颗子弹恰中我胸,又正好被钢笔反弹出去,那么也就那一瞬的惊吓,我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将被颠覆至尽吧。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倒不是为周作人翻案,只是于他个人的遭遇,我有点同情甚至心疼。想起周作人曾对一时事进行点评,事情是吴稚晖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说什么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周说“本来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应哀矜勿喜,决不能当作嘲弄的资料”。周在五四时期极爱安特来夫的一段话:
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治文学的,总是夸张浪漫的。我不信这“拭去一切”,但我相信总能让心灵变得宽大、包容,并且这也是自我派遣孤独的一种方式。那么在心理学上,读书这件事,也算是助人自助了。
重新回到那个约定。都说中年再读周作人,连周作人自己也承认“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是智者的散文。钱师说“周作人在根本气质上,就是排斥诗的”。于此,我倒不以为然。没有诗情的人,是无法接近自然的,同时,正如陶渊明不仅仅只是静穆,周作人也不只是平和,更何况年少时爱嬉笑怒骂,周作人也曾经年少时。不过,有这样的约定又让我想起一事,便是什么年龄读什么书。
周作人曾说“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周作人是推崇人的自然发展的,而他对儿童学及对传统的反思的贡献也是极大的。周作人以为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是“还自然之债”,债务既了而情谊长存。关键词“情谊”并非“名分”,而保存这份“情谊”,在于尊重与引导。马克思有段著名论断: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儿童年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吗?
近来常觉得每一个年龄段都有每一个年龄段该经历的故事,过早过迟都使心智受到损害。身为成人,自有一些智慧始,便能体悟成人的责任与痛苦。而身为过来人,也明白孩子总会长大,长大后也自会体悟生活的痛苦。那么,为了保存那份真实与天真快乐,何以不让他们在最简单的年龄,没心没肺的幸福,何以不去保护那段岁月,让孩子迟些长大?
零零碎碎胡言乱语,只能说这是我以为的道德的文字。关乎心情吗?或许心情更为灰暗。但悲观的认识与乐观的行为也并非截然对立,正如周作人,也不正是努力协调着闲适、诙谐与忧患吗?没有忧患,何来感情力度,没有闲适诙谐,何来从容气度。
我提早赴了周作人的约,或者,我赴的是知堂的约。有多么喜欢“知堂”这个名,这是源于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及荀子“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我以“智”为常识,而我的“常识”暂为周作人的定义“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曰智慧”。人是仙子和魔鬼。魔鬼是仙子的影子。我愿意宽容,自己及他人的仙子和魔鬼,正如没有不可原谅的个人,只有不可原谅的行为。正如我在《论张爱玲》那里看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