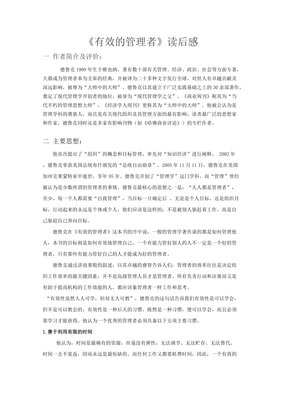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本由黄宗智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37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精选点评:
●经济内卷的中国,与赵冈的中国近代经济可以一并读
●扫盲第一步...
●农业内卷化—增长而不发展
●方法论
●一星给how to say
●继续试……短评它到底会不会出现啊
●师姐毕业时留给我的书,经济学背景有点弱,难啃。不过关照书中的观点,现在正在全国铺开的城镇化,让农民上楼这件事,可见又要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以及经济形势造成多么深刻的影响。
●在至少三门课上读过这本书。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赞叹在层层数据中黄宗智先生的抽丝剥茧
●: F329.2/4838
●分析透彻,考虑周全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一):黄宗智的基础,杜赞奇的再分析
主要学习黄的方法论,从个案33个村庄的调查,提升为7个类型化的存在,以概况相对普遍的结论,确实值得学习,同时,看过黄对《惯调》的分析,也可以理解为何杜赞奇选取了2省2县6村的原因,资料的详实,以及黄的分析,同时,也相对概括了当时华北村落的一般类型(按照黄的理解)。经历战祸型(良乡吴店),出外佣工工人型(昌黎侯家营),手工业发达型(历城玲水沟),高度商业化型(栾城寺北柴),中度商业化型(恩县后夏寨、顺义沙井)。当然,对于所谓高度、中度、以及不发达的商业化村庄定义来自那里?作者似乎没有交代。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二):黄宗智的基础,杜赞奇的再分析
主要学习黄的方法论,从个案33个村庄的调查,提升为7个类型化的存在,以概况相对普遍的结论,确实值得学习,同时,看过黄对《惯调》的分析,也可以理解为何杜赞奇选取了2省2县6村的原因,资料的详实,以及黄的分析,同时,也相对概括了当时华北村落的一般类型(按照黄的理解)。经历战祸型(良乡吴店),出外佣工工人型(昌黎侯家营),手工业发达型(历城玲水沟),高度商业化型(栾城寺北柴),中度商业化型(恩县后夏寨、顺义沙井)。当然,对于所谓高度、中度、以及不发达的商业化村庄定义来自那里?作者似乎没有交代。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三):试着写评论 加 黄宗智与杜赞奇文的比较
本书是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所写。作者利用满铁惯调的经济人类学资料、部分清代刑部档案等政府文件,分析了华北(冀-鲁西北)的小农经济状况及出现的社会变迁。文中论及的该区域“农业内卷化(过密化)”,封闭式村庄共同体等观点,与格尔茨、弗里德曼、施坚雅、杜赞奇的相关研究形成有力对话。无可否认,该书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农村经济、农村政权建设所无法忽视的重要文献。
读者不免会将黄宗智与杜赞奇进行比较,而且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先看杜文再看的黄文)。对于有清一代至民国、日据时期的华北描述,他们关注的是不同的侧面。
黄是从经济角度入手,且主要描述华北的小农经济的状况,分析如何可能及在二十世纪的变迁,并借生产关系和阶级分化的概念,由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分析。杜并没有谈及经济的状况,在分析其主要研究对象——政权时,也没有分析世界市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商品化对乡村社会及政权带来的影响。杜是从一个内生的传统的政治的角度,归因乡村社会政治的变迁,分析框架是文化-权力,文化网络-经纪制-国家,基层控制者是国家经纪;黄是一个从经济到社会/政治的分析模式,即小农经济-地主制-集权国家,基层控制者是地主。杜强调的是跨村际、甚至县域的非实体的文化共同体/集体意识/文化网络的作用;而黄关注于村内的实体的内聚、自我封闭的村庄共同体。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四):读书札记
1) 乡村研究的范式
关于这一点,作者在本书开头就有提及,即农学中的三个传统,分别为:a)形式主义,这一派主张把小农当作理性的经纪人来研究;b)实体主义,这一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这一派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c)马克思主义,这一派大家已经很清楚,强调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如果把这些学说放入中国乡村的具体环境,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范式是能够套进去的。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加强调方法,而非范式,如果非要硬套范式,这样的苦果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尝到过,没必要赘述。
此外,前近代社会的中国乡村,南北方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例如长三角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宗族组织高度发展,这一带佃农居多;而华北地区以旱作为主,缺乏河道运输,因此农村商品化程度元低于长江下游和四川盆地,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造成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由此可见,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区分不同地区的特点是多么重要,想要用一个通吃的范式来涵盖是没多少可行性的。这一部分的研究,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有更加深入的阐述。
2) 高水平均衡的陷阱
艾尔温最早提出这一学说,他认为人口压力通过两条主要途径迫使中国经济的落后: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累计“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这对于中国的农业为何一直陷于停滞,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3) 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中国明末在长三角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黄宗智持反对观点。商品化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是“萌芽”派认坚持其主张的一大证据,黄的不同意见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生产关系。在人口过剩、有数以百万记的从农村流离出来的游民的中国,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存在,并不足以证明生产力开始有本质的突破。关键问题是:雇佣劳动是否伴随资本的积累及生产力的执行突破而兴起?事实并非如此。
4) 关于乡村自治
前近代的中国乡村,国家权力无法过多渗透进入,在国家和农村之间,地方士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定意义上的“自治”,当然,这不能混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治。20世纪之后,随着战乱频繁,国家和地方权力触角一点一点渗透进村庄,导致二者的矛盾逐步升级,这个时候,地方豪强趁势而起,造成欺压一方的局面。中共革命时期提出的“打到土豪劣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的。但是,要说中国的农村历来就存在“土豪劣绅”,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建国之后,中央政权不但没有试图恢复和促进乡村自治,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干涉,用国家意志强加于乡村的后果,我们可以从今天千疮百孔乡村看得出来。农村问题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大难题,未来的发展,乡村自治将是一条不能逃避的的路。
5) 何为“地主”
根据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地主”是主要靠地租生活的,“富农”雇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长工,“中农”自己从事大部分田间工作,“贫农”除了耕种自己的或租来的小片土地外,还受雇为短工,“雇农”则主要以受雇维持生活。土改时期对“地主”一词使用不十分严谨,1950年施行土地改革法时,把“经营地主”和“地主”同等对待,实际上,经营地主就是经营式农场主,他们都是亲自参加劳动的,与脱产的地主完全是两码事。
6) 一点感想
姑且不论其的观点,因为我对乡村研究也仅仅是一知半解而已,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三百多页正文里,到处都是干货,没有一个观点不是依靠扎实的数据得出来的。黄宗智对研究议题的深入更是让人佩服,一般人只能看个大概的问题,他能刨根究底,从中发现出一大堆有价值的信息。
其实我还是很想看到更多作者观点性的东西,这也是平时阅读积累下来的一个陋习,但作者的研究一直收得很紧,从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给出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学术研究态度,确实值得我这种浮躁的人学习。
虽然作者扎实的方法和强大的研究能力我学不来,但也至少应该抱着“虽未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
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 著,中华书局,1986年,定价:4元。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读后感(五):华北农村日益失去的生活(二)
作者在分析华北农村时,借助了农民社会学的三大分析传统:第一个是“形式主义经济学”,其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是有进取精神的,并且对资源进行了最适利用,小农虽然贫乏但是效率高,追求利润并进行创新;第二个是“实体主义经济学”,他们认为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小农家庭农场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活和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即:地主和小生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而作者采用的则是一个综合的分析,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小农,其关键是要把小农的三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是一个利润追求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其次,作者还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小农,并对这些小农作了分析。
作者根据满铁调查资料、档案史馆的档案与地方档案和社会史的资料,对华北农村地区的小农经济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研究。
解放前,中国农村社会可以从两种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一是租佃关系,这主要着眼于土地关系,区别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二是雇佣关系,这主要着眼于劳动关系,区别为雇佣他人的地主、富农和与人佣工的雇农。
富农多是进行经营式农作。他们的农场大小一般在100-200亩,因单人可以一人耕种15亩左右,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农场里做工外还雇佣一部分的工人,工人可能是长工也可能是短工。华北平原以旱作农业为主,地少人多。土地产量并不高。部分地区因为历史、市场以及现代交通发展的原因,开始种植商品类经济作物,比如棉花、烟草。经营式农场主因为土地较多的原因,他们可以将土地分为几块,种植几种粮食作物,一则是为了均衡劳动力,二是为了规避风险。土地由他们自己来经营要比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利润高得多。社会政治体系中,经营农场主是底层农民在乡村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层级,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体系中,他们若还想上升,便只能从农业之外获得上升途径,比如进行商业活动或者参加仕途。一部分经营式农场主有了足够资本后,若还想获得更大利润或者更高的社会身份,便无暇再顾及农业经营,所以他们会放弃经营农产,转而成为地主,地主制成为了吮吸最成功经营式农场主的制度;还有一部分经营式农场主会想着依靠考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官远比经营农场赚钱和地位高。上升通道吸引人们进入商业和仕途,而不是进一步的扩大农场生产、增加农场利润,从而使他们无心技术变革;而人口过多的低廉的劳动力的存在,也使他们无需进行技术变革以减少劳动力的雇佣。他们也就无法转变成为资本而积累资本的资本家。经营式农场主除了‘上升’通道之外,亦有‘下降’通道。分家制度是造成经营式农场主‘下降’的主要原因。几代之后,可能就会从原来的富农阶层变成后来的贫农阶层。
在华北小农经济体系中,由于人口压力和商品化,造成了本区的社会分化。种植高商品化的农作物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高利润、高风险则可能使原先分化不大的农民之间形成不同的农民阶层——富农、中农、贫农。人口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使部分农民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但即使如此,小农经济依旧维持着它的生命力。小农经济除了本身农业这个支柱以外,还另有两根‘拐杖’,一是商品化的家庭式手工业,这部分收入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当国内或者国际行情发生变化时,农户的这部分收入也随之浮动;另一则是雇工,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长工几乎完全失地,拿着仅能维持个人生活的工资,难以成家,所以往往会成为他们家支的最后一人,长工地位比较低,当地人往往不愿意成为长工,除非生活实在难以维持;短工则多是在农忙时出现,价格相对较高,所以那些本身家庭地比较少的农户往往会在农忙时寻做短工,为家庭赚取生活资本,但是也因为他们在农忙时为他人劳动,自己的土地没得到恰当的照料,从而使他们自己土地产量低。有的农户尽管土地较少,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出去做工,情愿在自家的土地上增加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这样带来的是增加劳动力时的边际效益的递减,农业内卷化出现,即使单位产量较高,但是劳动力多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同比例的单位产量的增加。
华北平原的村庄之前在政治上存在闭塞性,“皇权不下乡”和乡绅有限地参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活。但是在近代,政治力量开始试图“下乡”,以及各种因素导致的农村内部的转变,使华北平原的村庄政治也出现了不同。有的村庄因其内部分化不大,所以还能保留着村庄内生的权力结构,形成更加紧密的组织,保护着村庄,与外界的种种压力相抗衡;而有的村庄的权力结构则因为小农内部分化而瓦解,造成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的崩溃和权力的真空,从而使某些“赢利型经纪人”有了可乘之机,村庄变得如一盘散沙。
有机会继续补个人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