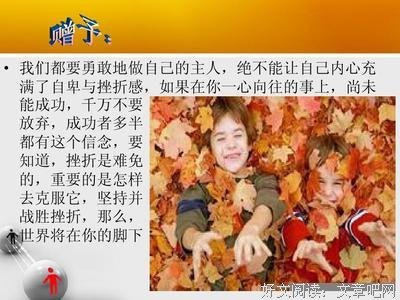
《政治中的人性》是一本由〔英〕格雷厄姆·沃拉斯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元,页数: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中的人性》精选点评:
●克服政治中的唯理智论 发现情感的力量 感情附丽于色彩比附着于一个词更容易 大多数见解是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推理结果
●作者说在政治中是个人理性是不可靠的,所以现代的看法是公共理性在充分的言论商谈中产生。
●2001年买于兰州。2009-2010通读完。虽然是一个教授所写的书,但总体不错。
●西方的民主选举可能是广告和金钱的胜利,热心和了解政治的人并不多,大多受到传媒的影响。
●你不能使一位新国王(他可能是个小孩)在各方面都像他的前任(他可能是个老人)。但是你可以在他们两人身上刺同样的花纹。
●太琐碎
●嗯,挺有意思的~
●经典读物都这样...太他喵的啰啰嗦嗦和自我感觉良好了...
●政治冲动,政治人不是理性人。 政治推理的方法过于简单化,政治的争辩成了语词的争辩。
●政治心理学
《政治中的人性》读后感(一):政治的另一面
本人读的是1988年郑永年翻译的版本,译文十分流畅。Wallas看待政治的视角的确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多层面的政治的一扇窗,我们现在所信任的政治系统、政府决策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是理性的”,延展到政治领域中,那么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们共同设计的政治形式大致也是理性的,通过设计精致的政治共同体的手段,来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目的,那么这个逻辑推理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却大大忽视了,其实在很多时候,即便那些看起来十分中肯的政治决策是非理性的,“拍脑袋”决定的政府决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虽然作者的分析是建立在西方选举政治基础上,但是所涉及的政治中的“人性”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这里就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东方社会主义的问题了。或许是暂时读了内容的一半左右的缘故,对有些问题还是有些疑惑:“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假设还是让我们有一条路可走,即便是认识到政治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那又怎么样?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一项城市规划是科学的、有目的的,即便知道这项规划中有人为的因素,非理性的因素,难道我们就此打住不再规划城市的下一步了吗?
《政治中的人性》读后感(二):西方选举制度的前提
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智的,但是一个人的认知形成、了解候选人产生的沟通成本决定了人的投票未必是理智的。
理智和情绪是人不可分割的两面,情绪是一种强烈的判断,不可能轻易改变,这种判断的形成往往是碎片化的、武断的,受很多因素制约,不可能如选举制度设计下的那么理智,经常可能被人操纵。作者可能是把心理学引入政治学的开创者。
这本书有两点描述让我感到震惊:
一个稳定的政府首先是必须得民心的,不管是曼德拉的政府还是萨达姆的,不管是用良政赢得多数人的心还是用欺骗、蒙蔽的手段愚昧化人们取得民心,不得人心的政权是难以为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就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第二个描述:在英国早期的陪审员制度中,证人的发言规则:“我说”、“我想”、“他说”等平常推理材料在法庭上是被排除的,因为它们“不是证据”,证人必须把他们记忆中的所见所闻简单地陈述出来。法律规定不许对审讯中的案件加以评论,违者以藐视法庭罪论处。
证人如果评论案件会被以“藐视法庭罪”论处,这个规则令人震惊。
《政治中的人性》读后感(三):政治生活有人性吗?
政治生活,有人性吗?有!格拉厄姆•沃拉斯作出了肯定地回答。
从“那些读历史的人已为我们在1859年洗劫圆明园,毁灭了我们永远休想望其项背的千年艺术瑰宝而感到奇耻大辱”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可能暗示给那些把自觉生活的火炬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迷惑的人以更仁慈的怜悯”。书读到最后,这些句“醒世恒言”让我从略微困惑的状态中猛然觉醒。你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白人作者之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人性中普世博爱的那种体现。这本书跳出了马志尼的“单一民族论”与俾斯麦的“强权即是真理”,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经典的力量,超越国界,直抵人心。
从《万历十五年》跳出来看《政治中的人性》,本来它应该是最直白的,但反而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让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主题。虽然在我们东方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以人为本”“人性论”似乎是潜意识中的常见观念,但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看待这门学问,沃拉斯确系首创。彼时,政治的研究方法多囿于分析体制,将时下的各类体制作比较,或者是空泛地奢谈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与贵族主义对人的合适性,而人的天性则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大大抹杀了政治心理学之于政治分析的重要意义。《政治中的人性》开辟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领域,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想起前些日子我们政治主体小组的讨论发言,我做了关于麦凯恩败选演说的人性分析。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我对他的支持者对这样一位“失败者”的狂热惊诧不已。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他被挖掘的负面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不论是贿选丑闻,抑或是在电视辩论上的拙劣表现,乃至他搭档年轻时的裸照,都被长枪短炮掀了个底朝天。可依旧有那么多志愿者甘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挨家挨户为他筹票,依旧有位老妇人在隆冬季节声泪俱下地对奥巴马当选后的“苦难”生活的凄苦描述。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主传统下的“理性人”的推论显然无法给这个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在此时,也许其他某些因素发挥了作用,可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跳出“唯理智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经验检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推理结果。功利主义政治学大师边沁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则》中强调“大自然把人类置于痛苦和快乐两位主宰的统治之下,人人都想以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句话有它的适用范围。单就选举来看,它的局限是很明显的。譬如人的认识往往依附象征而存在(譬如党派的象征歌曲、旗帜等)。前文中的老妇人如此憎恨奥巴马,正与她日积月累的反民主党情绪相关。除了特定类型的人与他们在遗传变异过程中所发生的微量变化之外,他所在的环境与所观察到的环境对他的政治行为与冲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奥巴马也应该意识到,尽管他的竞选方针可以改变得极其迅速,但他的声望、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名声以及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往往会产生道德上的麻烦。也许这才是老妇人动情捍卫麦凯恩的原因所在吧。对于奥巴马,记住林德赫斯特的那句话“千万不要在群众大会上为你自己辩护,除非是对批评进行反击;听众沉浸在攻击带给他们的乐趣中,会忘掉以前的指责”。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人们对于与自己相似(包括政见相似)的领袖的心底的支持。喜爱和自己一样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基础,这是由先理性特征条件所决定的。譬如在感情上,恋爱中的男人不会煞费苦心地解释他的完全正常的感情,并把它称之为这是从他心上人的出类拔萃的优点中得出的理智结论。麦凯恩看到了这点,并作出了亲民的表现。政治就是像踢足球,流行的战术不是制定规则的人期望的那样,而是球员发现能使之取胜的那种种。一些白人,可能从心底缺少对奥巴马的肤色的认同感。基于此,麦凯恩的志愿者为其辛勤拉票也就不辞辛苦了。
最后麦凯恩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白人政治精英的形象。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论来制造舆论。他凭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国绅士、越战老兵的形象来吸引自己的支持者。这正是利用了“联想”这一因素并抓住了人性中的基本内涵。一个刻有使“一切人都弯腰”的神像名字的圣像,或甚至声之于口但未出之于口,在感情最强烈时,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义大得多。我们还会认同这样一个观念――“词”本身是非常硬性的,但通过联想,它的意义则会丰富许多。这种联想需要时间产生,譬如民族主义者用歌曲或过去的业绩来恢复和加强他们与较大的国土发生相关的感情联系。麦凯恩深知这一点,他不停地给他的选民以他光辉过去的回忆。尽管他没有达到成功的结果,但单就选举本身而言,抓住了政治生活中的人性因素无疑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性因素大大地影响了选举生活,但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它是否依旧会发生作用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譬如二十世纪初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代议政体,大多数英国人隐隐地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然而,当一个中国人问他们自己是否应该投身于一个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他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这也许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吧。一些政治老手也会狡猾地抓住这些弱点,他们把人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的非理性动物。但不论他们身处何位,保守主义的先驱柏克始终认为人的政治推理能力与他们的工作是完全不对称的。哪怕是相对流行的代议政体,也只是被看作职业政客冷酷地操纵人民冲动和思想的替换办法罢了。在代议政体下,游说者的冲天干劲儿必然会箝制住刚做完一天工作的人们的疲乏的神经……国家、政体处处留有人性的足迹,谁还能否认行为主义的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意义呢?
也许是学以致用,抑或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最终的落脚点总会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呢?是得以充分地发挥还是被某些东西禁锢住了?
从“小平您好”到“什锦八宝饭”的日益盛行,也许反映了我们政坛稍微活泼的气息。但如此大规模的亲民形象宣传,《人民日报》“新华网”不遗余力地报道,是不是也潜藏着总书记的一些无奈呢?昆明市长仇和将市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公布在了《昆明晚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样一种合理合法的举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民众叫好,官场哗然,这样个性的官员确不多见。试思量之,这是某些部门认定其不合情理还是反映了那些机构本身的万马齐喑呢?谈到基层的公务员与职工,总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万里十五年》。他们可能具有些许个性,但与强大的官僚机制相比又太过渺小,仅仅是大体制机器上的零件而已。他们唯一存在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防止发挥有效思想的机会只限于极少数像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生活在不负责任的自由天地中的富人吧!我们公民的被选举权与基层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呢?呵,也许参与者们比我更清楚。
《南方周末》说改革开放30年,人性已然回归。可回归多少,我心里始终存在着大大的问号。
唐老师说我们不应以西方的观点去研究西方的制度,那样我们不会找到出路。只有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来看政治,我们才会真正取得大的发展。在东方,我们强调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又都禁锢在哪呢?
不要把君子宅在一个个办公室里,不要待他们垂垂老矣还要参加繁多无聊而又冗长的会议。
政治中有人性吗?有!
体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了吗?
但愿同样是肯定的回答……
《政治中的人性》读后感(四):政治中的人性
沃拉斯所谓的政治中的人性,不是“你还有没有人性”中的人性,而是人之本性的意思。为什么要提人之本性呢?沃拉斯说,一些政治研究,以人为理性动物,看待事情都出于一种理智上的推理。实际上并非如此。沃拉斯说,人们的政治见解往往包含了无意识的非理性过程。
问题就出在,人性自私,而人的智力又有限。所以沃拉斯反驳布莱斯的话,后者说“在理想的公民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聪明、爱过、大公无私的。他的唯一的欲望,是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现正确的一方,并在多个竞争的候选人中选出最好的一个”。沃拉斯以为这没有任何意义。
人性自私。一方面,民众,出于利益考虑,对于政治活动往往并不热衷;同时,参与政治的民众往往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行事,而是为了个人私利。沃拉斯说,英国对政治有热情的人仅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沃拉斯还说,有些落后的殖民地在实行民主制时,投票的比例非常之低,以至于只能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制度的阶段。美国人投票率貌似超过一半多些。虽然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其他因素,但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是,我印象中奥尔森或弗里德曼曾提到,人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政治对于普通的单个老百姓来说,是属于投资很高收益很低的活动。选举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了解政客和他们的政治观点,这需要个人付出时间和精力上的成本。同时,他们所投出的一票,在达到目的的作用上可能微乎其微。而且,即使是选出来这个政客,他的决策往往是针对大众,而大众会把好处稀释掉。假如说选马云做老大大,马云会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全国人,那么他的1500亿分给13亿人也只有所谓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那些人才开心,认为就是每人分一亿分了之后大家都是亿万富翁而马云还有1487亿。正是出于此原因,可以推想,人们会自然地却少对政治的热情。另一方面,追逐权力的政客,往往也不是出于全心全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动机。就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谈到,虽然说,从才能、品德和智慧而言,让人类当中的圣贤来管理整个社会是最好不过,然而如大卫·米勒所言,实际上圣贤反而不热衷权力,而热衷权力的人往往不是圣贤。
沃拉斯探讨了人的欲望,尤其是私有的欲望,他以为像私有财产对应了人的一种真正本能。当然,这个看法其实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如果要说“本能”,仅仅只能对应人的一些低级智能模块,而且这些模块也只是提供一种驱力,并不提供一种决策。所以,沃拉斯以为,这种私欲本能或许能够通过提供一种“占有”来满足,比如某种“收集”爱好,沃拉斯以为类似给小猫一个毛线球就能满足它的捕捉本能,满足了之后“私欲”就不会再造成人的行为或对社会的危害了。这种想法显然太简单了,有点类似洛伦兹或精神分析中的所谓释放理论,比如“暴力”倾向如果采用某种方式的释放,就如泄洪,放了就不会再造成危险了。这种错误在于,没有弄明白“本能”是干嘛使的。沃拉斯还以为,混杂的情感不如单一的情感强烈。这个说法其实说错了。混杂的感情,假如是一个方向的,可能会增强感情。但是假如有相反方向的,则可能会造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他距离说,候选人最好不要住在自己的选区,原因是什么呢?人们会看到这个候选人作为上层人的生活,从而产生不好的印象。
沃拉斯自己多次参与这种政治竞选活动,所以他谈到自己的一些体验,其中一个是“重复产生厌倦”。他说,反复做同一个演讲,“产生不是实在的感觉,令人苦恼”。他认为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就如我们反复听同一首音乐所会产生的厌倦那样。我平时听音乐非常多。听歌对我来说,是一种把我的注意力保持在读书状态的一种方式。有一种音乐做背景,我往往能够情绪安静下来,能够一直读下去。其他的时候,假如我读的书不够吸引我,我的注意力就会时时从书上转移开。还有一些时候,我内心似乎存在一种焦虑,会让我完全无法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但是假如有了音乐就可能扭转这个局面。或许,是音乐在不断刺激我的大脑分泌多巴胺或其他类似物质,把我的negative情绪调整为positive情绪。你知道,positive情绪能够促进学习,保持大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几乎就跟嗑药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音乐我都喜欢。有些一听就感觉十分喜欢,有些听了感觉还行,有些听了感觉很没滋味,有些就很反感。当我在读书的时候听歌,往往是听“猜你喜欢”这类,然后会出现有时候注意力跳到音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因为音乐动听,就是因为音乐太刺耳。这样,也就是说,或许是因为有些旋律,对我来说是一种中等“噪音”域内的声音。我印象中说,无噪音和大噪音都会引发人的警觉,而影响人的注意力保持在学习上。只有中等程度的持续噪音最能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当然,那些我觉得动听的音乐在我写东西或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动听程度和我思维的顺畅程度成正比。但是往往,就如沃拉斯所说,重复会造成厌倦。对我来说,更像是榨干了这首歌,最初能够引发无数的快感美感和灵感,但是反复听了之后就没有了感觉。我想,这或许是人的一种学习反应,即对新的良好对象有一种positive的好感作为取向,一旦熟悉,就减少这种好感,让人趋向于更新的良好对象。
沃拉斯还谈到群体感情的传染。这种研究也不少了,包括勒庞的《乌合之众》。其他的研究还有在群体中个体的去个体化,去个体化就意味着一是群体力量大,这个时候啥都敢干,同时又有一种责任共担的感受。西安915砸车的蔡洋就是这种本能冲动的牺牲品。另一个沃拉斯注意到的现象是,人们喜欢故事远甚于抽象的推论。这大概是因为,大脑擅长处理故事,但是不擅长抽象推理。故事往往包含了许多情节,因此,如沃拉斯说人的大脑就像一个胡琴,这些情节很容易拨动琴弦。人类内心其实有很多和感情有关的“桥段”琴弦,比如成功、爱情、性、复仇、冒险,所以人们看这种戏剧或电影的时候,往往会被刺激得很动心。我印象中,创业圣经语录似乎也有“首先讲一个好故事”以及一大批教人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的说法。也就是,讲好一个故事是最能拉拢(忽悠)人心的经典手段。所以,沃拉斯说,大众更喜欢安提戈涅,而不喜欢苏格拉底。文化上无与伦比的希腊人都如此,那么还能希望哪国的民众能够更热爱和接近真理呢?沃拉斯还提到,人们考虑事情往往不是纯理性推理,而是感情、欲望、理性一起参与。这就是Pinker所谓的computing。沃拉斯说,只有那些对我们影响小的对象上,我们才能做出理性的决定。他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越接近我们自身的利害,我们的本能作用得越强烈。这个观察很高明,实际上就是利害越相关,驱力越强,这是一种有survival value的适应性。沃拉斯还注意到,我们的智能存在缺陷。比如,我们的视觉有时候会欺骗我们,即使我们知道真相,就如那些视觉错觉图。这就是说,我们的智能处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尤其体现在我们的很多fallacies上,Kahneman和Tversky有对相关主体的详细探讨。沃拉斯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采用一些容易引发错误的方式做出的,有时候人们并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过程。阿伦森的《社会性动物》也谈到了很多种这类现象。
人的智力有限。一方面,民众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往往并不是依靠对知识和真理的掌握,对政客进行审视和选择,他们的政治观点甚至往往也是出于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沃拉斯提到,英国民众对于乔治三世倍感亲切,只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也出生在英国,也因为经常能看到关于乔治三世日常起居的信息。貌似这就是熟悉导致喜欢的例子。当然,这种喜欢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本能因素,即对有权势或财富的人物,人们会产生一种好感倾向,作为动力能够让人趋近资源占有者。但是这种趋近倾向并不排除一种强烈的抑制作用,沃拉斯说,人们见到毕生梦寐以求想见到的国王时,往往就僵住了。我想这和人们见到自己的“神”或要告白的对象时,都会产生抑制时一样的,这种fight or flight的反应肯定不是要fight,大概是出于一种谨慎避免搞糟机会而起作用的机制,就如同Frans de Waal的黑猩猩那样。另一方面,政客从政的动机、手段和目标,往往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个人追逐权力或利益。因此,政治,就如沃拉斯所注意到的一样,和商业是两种尝试操纵人们想法和行为的战场。政客所做的不是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而是尝试打动他们。沃拉斯说,这自然会导致政客在道德上的堕落,因为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抽象的真理很难辨别,同时也让人感到厌倦。正直的政客不愿意采用除了说理以外的其他方式,但是劣质政客不一样,他们会采用各种打动大众的手段,哪怕用夸大、夸夸其谈、许下并不打算兑现的诺言,仅仅为了说些大众喜欢听的而不管其他别的后果,诉诸人们的各种感情如爱国、想国家繁荣自己得好处。总之,就如沃拉斯所说,这种精明的政客只是想赢。或许川普就是这样成功的。沃拉斯注意到,政党、候选人,往往和商品一样,都会打上精美的包装和诱人的宣传语。我印象中有谈到美国竞选的书,谈到美国总统里根,说他获胜的诀窍就在于他做过演员,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候,正是他那和蔼可亲和真诚正直的表情,打动了美国人民。还谈到,人们对于要选举的政客,往往所致甚少,对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就如沃拉斯提到的听起来专业难懂的金融政策,人们往往并不能进行一种准确的判断。因此,人们给竞选人投票的时候,如沃拉斯所提到的,往往根据一些非理性因素做出决定。比如说,长得更高的候选人赢得竞选的可能性大大高于矮的候选人;下巴坚毅的候选人同样常常胜出。也就是说,人们在投票的时候,往往也是根据自己的某种喜好,无论是看面相,还是看高矮,还是看神态,还是看举止,还是看其他各种因素如口音、出身地、家庭背景、学历等等,而并不根据他的能力、品德和学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何况,沃拉斯自己都开始给人相面起来,说“这种人体格强壮,粗下颚、阔嘴巴,能说会道”,神经容易崩溃而不会长寿,和赵本山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一样。郭德纲怕是要点赞。
沃拉斯还提到,人类存在一种符号化象征的倾向。其实就如马林诺夫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中以及其他很多人所注意到的,符号或象征在人类文化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非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动物也有符号和象征,就如雄孔雀做出大屏来展示给雌孔雀,自然界雌性抚育后代的种类,雄性都负责做出一种复杂的信号,包括自身华丽的羽毛、大长角、卓越的筑巢技能、舞技或歌技等等。当然,智能本身就意味着处理信号。所以,信号和象征,实际的作用要追溯到Holland所提到的隐秩序。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象征和符号实际上塑造了一种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社会并不简单等于人类个体的聚集,就是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所提及的整体主义者反复强调的整体不能于部分之和。比如说,一个人的穿戴,其他人对他的态度,他们在一定空间中的位置关系,以及他所出现的地点和场合,都代表了一个人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比如当年人们提到的,宋姓歌手在前一任领导人的时候拍照站在中间,但是后一任时就变成了董。通常,人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之上。现代政治学往往会谈到平等和公正的问题。这个结构自身是不平等的,有的人身居高位,占有大量资源;而大批穷人往往在最底层,并且貌似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剥削,如Jon Telling所言,有时候并不是说是高层人干的,而是这种结构本身在剥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需厌恶哈耶克为资本家和富人做出的辩护,也无需赞成马克思对资本家和富人做出的批判。或许更应该倾向于Rawls所提出的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并不针对富人,而是针对结构来做出调整。人们在这种结构中仅仅是扮演一种角色而已。这种角色的扮演,往往就是通过符号象征体现出来。试想一下,把所有人脱光了放在一起,你看不出来大的差别。但是有了穿衣打扮、住所用具、出入场所,人们就产生了差异。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人们希望在这个结构中,不同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是处于justice。也就是说,是出于merit的标准来确定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存在一定的流动性,但是,实际上人们是出生在不同的位置,而就近进入所能进入的最高位置的。这就是不公正产生的原因所在。
沃拉斯注意到,一个国家也总是努力打造各种象征符号,因为国家本身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有了这个符号,人们就愿意为之献身。那么国家怎么形成的呢?就是通过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尤其是一个政党上层,来造出一个“国家”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疆域、版图甚至国家自身不断变化、灭亡或新生。对人的研究,有人的提法是,把最简单的个人弄清楚,然后叠加起来。这其中的问题是,前人考虑人性,往往是静态的,是固定的,比如善或恶。但假如转变看法为人是智能尝试从环境中获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同样也是个体之间会建立起一种复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群聚,推演起来就变得有些困难。有些人如柏林布鲁克及其弟子迪斯雷利因此就以为,人类是靠感情、欲望的盲力推动产生了文明。相比之下,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参与了这个过程,但是仅仅在各个个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上参与了,整体的秩序和文明还是一种自然过程的结果。但是沃拉斯提出,实际上,人类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给人来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提升。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看法。正如沃拉斯注意到的,人类本性在过去的万年间,恐怕很少变化,但是人类通过积累知识,通过文明的发展,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认识其实有很大的提升。沃拉斯提出,人们通过认识自身智能的局限,就能避免自身的错误,并且识别和避免政治家的操纵。这就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我以为沃拉斯说的很对。但是沃拉斯提到柏拉图所谓理性和本能是否有一天能够和谐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