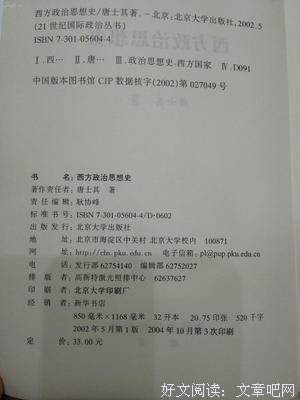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一本由约翰·麦克里兰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8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政治思想史》精选点评:
●艰难地啃完了第一本思想史,对各个理论出现与对话的背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好像体会到了一点某教授说过的一门学科的最佳入门方式就是从思想史读起的意思了
●我竟然看完了?很怀疑.................
●900页能勉强概述西方政治思想,也算不凡了。
●不同于国内政治思想史的声音,一个人多年心血的结晶,不得不看的思想史著作。
●出乎意料的好玩
●终于读完了!作者是个有趣的人
●看书的时候,也会有种自己十分高大上的错觉。
●内容翻译具佳!我看过的翻译最棒的此类著作!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西方所要求和崇尚的民主,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这片土壤。中国的民主改革,不能够太激进,应该适中,在不同与建国时的人民不同,现代中国的新生力量,拥有不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因此,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是长期的和渐进的。不能追求激进的民主而去追求民主形式而放弃民主精神
●为世界理出个意义来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一):写得好,翻译得更好
可能是读了太多味同嚼蜡的翻译书,这本同样是学术著作,读来却富有趣味。
也是读了这本书,让干枯的政治神经开始活跃起来。
谢谢彭教授。你什么时候能来大陆做讲座呢?台湾的政坛一定有些无聊的故事可谈吧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二):翻译的非常非常差
原著的口语感很强,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希望读者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思考方面。而翻译的人,却把书的风格完全变了。
让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拆字组词上面。
好的翻译,应该让读者觉得原文就是中文写成的。
感觉不到隔膜。
而翻译却非常的失败。他故意卖弄文笔。让整个阅读毫无流畅感可言。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三):译者没必要用艰涩的翻译来包装自己吧,难道不应该尊重原文style么?
买了这套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两卷的译本,装帧精美,印刷精良。可是刚看了第一章就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彭先生译得实在艰涩难懂。书的前言美言其译得“文雅”,可是俺实在是才疏学浅,不能欣赏。人家麦先生作为多年高级讲师,深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要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语言将道理讲清楚的,而不是为了用文绉绉的自恋来包装自己的才学的。如果自己做research,大可用自创的各种艰深晦涩难懂的词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译个作品,没必要这样愚弄大众吧?!原书的精要正是在于其采用交谈的方式来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脉络,口语化的方式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可是被彭先生这样一译,顿觉有了距离感。初时以为是自己眼睛有问题,怎么写着写着冒出一句古语,让人丈二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文雅”就体现在什么“夫复何求”中了。哎,翻了第一章,实在费心费力,不是因为不明白人家的思想体系,只是承载道理的文字弄得人很烦心。虽然本人不作翻译行业,当属外行,但是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是分得清什么叫做行云流畅的,幸好识得英文,所以决定还是买本英文原版来读算了!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四):政治 = 处理公共生活
政治,这个词自我小时候,就植入了我的脑袋。这个词是如此抽象而让我从来不能够好好的理解。
于我生活之国度,对人们影响最大的,叫政治运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数的人在领袖的授意下被私下审判。 如果经由法庭审判,罪犯也会被“剥夺政治权利”。于是我一直未搞清楚,剥夺政治权利与人到底有何干系? 难道我有什么东西叫做政治权利?后来,我粗鄙的见解便是,剥夺了政治权利,就是不能当党员;不能当党员,就是不能当官了。
后来,清宫戏越来越多。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叫“搞宫廷政治”。我很明确的知道这种说法只是隐晦的指“宫廷内的权利斗争”。这个时候,“政治”这个词结合了我一贯感受到他的暴力性,就演变成了“权利斗争”的意思。
然后政治这个词出现的几率在某些情况出现得很高,那就是描述某中央领导人的时候。“久经考验的XXX革命家,政治家”。这个时候,政治家的意思貌似就成了,当官的专家。因为在我朝只有政治家全是当官的。
综合我对政治粗陋的理解,他包含着权利斗争和当官的意思。而这一切却离我都非常非常的远。不过,奇怪的是政治这个词却总是围绕在我的周围,一直都会听到他。我想对他一探究竟,看看“政治”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学课本里面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类的句子是在描述政治?于是我翻开了这本书“西方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五):有趣的学术著作
“寡头统治是富人共谋劫贫,民主制度则是贫者共谋劫富。”
“权力之为物,主要用来促进一己的利益,或你所隶属的团体的利益。”
“集合在一起的一般人是一只巨兽,等着安抚、喂食、讨好,然后牵着鼻子走。”
“煽动家知道他只能向人民提出人民已经有心相信的事情,人民则只相信那些告诉他们所求有理的人。”
“世上的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的样子;强者往往不会明白宣布他们所说的正义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意识形态很容易粉饰权力的现实,权力又总是能找到代理人。这国家谁在统治,是个根本问题,想探达这问题的根本,有时十分困难。”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样紧紧把握一个原理:政治不安定的原因是统治集团不团结。但柏拉图添加一个转折:政治稳定的理想方子,是上位者团结而在下者分裂。”
以上是从我正在读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里摘抄的一些语句。这本书没有我们所习惯的规矩,但它是一本实实在在的纯学术著作,全书共80多万字,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直到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记述磅礴大气,但字里行间充满着机敏和愉悦。学术著作让普通读者觉得有意思是一件很难的事,(当然,性学方面的可能例外)但是由J.S.McClelland所写的这本书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西方的学术著作都是这个样子,但我的天,这本书确实让我耳目一新。
看语言风格,我猜想译者应该是台湾人,上网搜了一下,果不其然。这个彭淮栋曾任联合晚报国际新闻编译(不知现在还是不是),因其译著《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台湾版叫做《乡关何处》)而获得当年明报“年度最佳翻译奖”。之前很多种的“国际大学排名”或者“亚洲大学排名”,台湾的好几所学校排在我们的清华北大之前,我一直颇不以为然,认为是不了解大陆只知道台湾的人们制造的偏见。现在看看人家对大部头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准,再想想国内各学科所谓专家们的文化素养,嘿嘿……
不管怎样,这的确是一本好书。并且我正在读它,虽然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