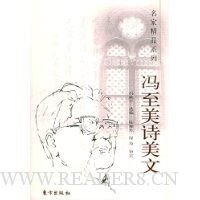
《马拉美诗全集》是一本由马拉美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拉美诗全集》精选点评:
●会感到他的短文比诗还要好哇。
●譯者既然在序言裡說自己受朗松影響,對象征派其他詩人不屑一顧卻獨崇馬拉美,說“感受到了魏爾倫詩歌的膚淺、蘭波詩歌的稚氣,與馬拉美之詩歌內涵相差很多”,那你倒是翻譯的好點啊?啊?啊?
●马拉美是法国一位诗人,写诗非常注重美感,曾经学习过一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天鹅之歌,天鹅在死前会唱出最为动人的歌曲,这个传说是否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异国同心之感呢?
●图书馆借过这版
●没有看懂
●阳春白雪卷翻译的超好,之后就有点儿侮辱诗人了~哎!!!
●第二次重读,前面诗译的十分之烂,但凭着后面的散文,也要给五星。
●翻译得挺美,但是太意译不太适合马拉美这类诗人啊
●造境
●。。。
《马拉美诗全集》读后感(一):「聖女」與沉默的音樂
與馬拉美不少詩歌一樣,《聖女》整首詩是一句長句,這詩與《歎息》一樣,長句由兩部分組成,下半部是上半部的屬句,說的是看不見的世界的景象,而當這景象在從屬句裏,就是以語法作比喻,從屬句裏的是看不見的世界,也是詩人在內心想像的世界。《聖女》一詩描繪了兩個主角,一個是教堂裏供奉的聖女St Cecile,她是一名音樂家,也是音樂家的贊助人,傳說她誓言要守着貞潔,當她被逼要嫁給一名叫Valerian的男人時,在婚禮上暗暗在內心唱着歌,她對Valerian說她有天使守護着她一生,最後Cecile和她的丈夫雙雙殉道。詩中另一主角是彈豎琴的天使,若知道St Cecile的典故,聖女與天使這兩個意象的連繫便不言而喻。
聖女
在藏着 往昔同笛子和曼陀鈴 一起躍彩、褪了色的 舊檀木胡琴的窗前,
面色蒼白的聖女,攤開 往昔晚禱中 流淌着聖母贊歌的 老書:
天使用夜晚的飛翔 散落的嚦嚦琴聲 拂過這聖體 顯供台的窗欞
(葛雷譯)
ainte
À la fenêtre recélant Le santal vieux qui se dédore De la viole étincelant Jadis avec flûte ou mandore
Est la sainte pâle, étalant Le livre vieux qui se déplie Du Magnificat ruisselant Jadis selon vêpre et complie:
À ce vitrage d'ostensoir Que frôle une harpe par l'Ange Formée avec son vol du soir Pour la délicate phalange
Du doigt que, sans le vieux santal Ni le vieux livre, elle balance Sur le plumage instrumental, Musicienne du silence.
ainte
At the window concealing the old sandalwood; its gilt slowly flaking away of her viola sparkling as of old with flute or mandore,
Is the pale saint, spreading out the old book that unfolds; of the Magnificat streaming as of old according to vesper and compline:
At this glazing of monstrance Which brushes the harp of the Angel Formed with its flight of the evening; For the delicate phalanx
Of the finger that, without the old sandalwood Nor the old book, she holds balanced On the instrumental plumage, Musician of silence.
《聖女》此詩只有一句,主動詞是第五行的est(is,「是」),詩人走進教堂看見St Cecile的木製雕像,也有陳舊的長笛和曼陀鈴,聖女無聲地翻開以往的聖歌集。此時這「無聲的音樂」從聖體匣折射出另一形象,並且以冒號(:)分隔下半部平行的屬句,音樂折射到天使的豎琴上(這是過去的天使,而且是傳說,並非與聖女的雕像在同一世界,這也從語法上暗示)。這所謂的豎琴也非真正的豎琴,而是天使的雙翼(第十五行le plumage instrumental,羽毛體形的樂器),點名這一點後,最後一行回到了主句,也即是回到現實——「沉默的音樂家」,在語法上它可以於主句也可以是屬句,也正配合它的語義,聖女與天使也是沉點的音樂家。兩個意象以音樂聯繫,但現實中沒有發出過聲響。
音樂性一直也是馬拉美和其他象徵主義詩人所追尋的理想。而《聖女》裏詩人一步一步地移動,流暢地描繪他所見所想,語句上也一點一點地揭開聖女的身份,猶如音樂的旋律般,而他採用了「無聲的音樂」—靜止的樂器和聖歌集,也是詩人所提出的詩學理想—「無」、「沉默」是最理想的境地。
《马拉美诗全集》读后感(二):天鵝與符號 Le cygne et le signe
天鵝 馬拉美
La vierge, le vivace et le bel aujourd'hui (Will the virginal, strong and handsome today)
Va-t-il nous dechirer avec un coup d'aile ivre (Tear for us with a drunken flap of his wing)
Ce lac dur oublie que hante sous le givre (This hard forgotten lake which the transparent glacier)
La transparente glacier des vols qui n'ont pas fui! (Of flights unknown haunts under the frost!)
Un cygne d'autrefois se souvient que c'est lui (A swan of former times remembers that it is he)
Magnifique mais qui sans espoir se delivre (Magnificent but who without hope gives himself up)
our n'avoir pas chante la region ou vivre (For not having sung of the region where he should have been)
Quand du sterile hiver a resplendi l'ennui. (When the boredom of sterile winter was resplendent.)
Tout son col secouera cette blanche agonie (All his neck will shake off this white death-agony)
ar l'espace infligee a l'oiseau qui nie, (Inflicted by space on the bird which denies space)
Mais non l'horreur du sol ou le plumage est pris. (But not the horror of the earth where his wings are caught.)
Fantome qu'a ce lieu son pur eclat assigne, (Phantom whom his pure brilliance assigns to this place,)
Il s'immobilise au songe froid de mepris (He becomes immobile in the cold dream of scorn )
Que vet parmi l'exil inutile le Cygne. (Which the Swan puts on his useless exile.)
純潔、活潑、美麗,它今天 是否將撲動狂醉的翅膀,撕破 這被遺忘的堅湖,百霜下面 未曾飛翔透明的冰川,在那躑躇!
舊日的一只天鵝想起自己 曾那样英姿勃勃,可如今無望逃走 因為當不育的冬天帶來煩惱的時候 它還沒有歌唱一心向往的天地。
這白色的飛鳥痛苦不堪 它否定太空而成囚犯, 它抖動全身,卻不能騰空飛起。
它純淨的光輝指定它在這裏, 這幽靈一動不動,陷入輕蔑的寒夢, 無用的流放中天鵝擁有的輕蔑
象徵主義詩歌除了深奧難懂、玩弄語言,和到處瀰漫的神祕主義外,其中一樣引人入勝的地方是它的雙重意象。有如兔子與鴨子的圖畫一樣,描述了兩個同時存在的意象,視乎所採用的角度,第一眼看到的圖案,就是你心裏較重視的意念,有些人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若要看到馬拉美的名詩《天鵝》的雙重意象,必須明白馬拉美提出詩學,以至語言學的觀念。馬拉美在他的散文集《流浪集》(Divagations)已闡述了不少他的觀點,符號本來就無所指,它能表達意思必須存在一個網絡,而符號本身是符號之海的一部分,而這些符號必須互相指向,像字典裏的字詞一樣。表意的關係應該是通過暗示、聯想,婉轉地描繪那事物,讓人產生了印象,然後轉瞬即逝,也就是馬拉美提出的名句:paint, not the object, but the effect it produces。
馬拉美解釋他詩學的散文詩裏常提到符號,詩裏也提到天鵝,「天鵝」(cygne)和「符號」(signe)在法語裏是同音字,詩人也就是玩弄這語音的遊戲。
[A Sign! In the central abyss of a spiritual impossibility that says that nothing can belong exclusively to everything, the divine denominator of our apotheosis, some supreme mold for something that doesn't exist in the same sense as other objects. From "Scribbled of the theater"]
馬拉美的詩歌裏大都只圍繞一個主題,就是詩歌和語言本身,尤其是如何達到絕對、理想境界,也就是純詩本身。詩人追求的是純粹從語言的操作來表現詩歌的美,也就是說,詩歌的美來自語言之美本身,通過語言本身的語音系統、語法系統、詞源的追溯等來達到形而上的境界——讓詩歌成為一整個宇宙,而詩人的畢生構想——《書》,也是一首純粹以語言關係來維繫的網絡,它本身就是在紙上的宇宙。
《天鵝》的雙重意象,一面是看到的世界,即天鵝所面臨的困境,另一面是抽象面,也就是無法看到的形而上層面,即是「符號」的意義,只要將cygne讀成signe,還有了解馬拉美的慣用把戲,第二個肉眼不能看見的意象便無所遁形,其實就是詩人對語言符號的糾結,以致他在詩歌裏面臨的困境。這種可見/不可見之間的靈性旅程,正是象徵主義的核心。
《天鵝》裏的5-6行 Un cygne d'autrefois se souvient que c'est lui Magnifique mais qui sans espoir se delivre 最後se delivre,雙重義是解放和傳遞,就是說天鵝解放自己/符號無法傳遞自己的意思
三段體第一行 Tout son col secouera cette blanche agonie "its" 法文son 和son "sound" 相同,符號的發音只引起蒼白的憂傷,這與馬拉美對語言的疑惑一致
同樣的同音字在第12行也有 Fantome qu'a ce lieu son pur eclat assigne, "its pure brightness assigns" 裏隱藏了純音pur son (pure sound),assigne 隱藏了signe 符號這字
最後一句點名了他的結論 Que vet parmi l'exil inutile le Cygne. (Which the Swan puts on his useless exile.) 天鵝要自我流放,也就是符號的無能為力。
《马拉美诗全集》读后感(三):馬拉美《瓶中玫瑰》的虛無過程
關於馬拉美的詩學概念有很多很多,經過了他所遇到的個人低潮,也就是他的「詩歌危機」(Crisis of Verse)(這也是二十世紀初不少詩人所面臨的語言危機),他設計了一套新的語言。詩人有感世界上的語言都無法表現非物質世界的意念,也就是說,很多形而上的或肉眼看不見的東西無法由語言呈現,於是他將語言分為兩類,一類是功能性的日常語言,一類是詩歌語言。詩人重整語言的結構,用他的方式去運用語法,以語音的特點(如雙關語)表現意思,他讓詩歌語言充滿提示,通過聯想去描繪意念,而不用直接的描述去鎖定意思,這使他的詩歌與言像音樂,因為只有音樂才能跳過解碼的步驟,直接將情感寫進人心(而馬拉美讓他的語言像音樂的另一重含意,是他有感音樂給大眾設下了門檻,因為只有曾受訓練的人才能理解,故詩人也將他的語言提升至有相當水平的人才能理解的程度)。
馬拉美通過提示和聯想去描繪意念,也就是他所謂的”to paint, not the object, but the effect it produces” , “To name an object is to remove three-quarters of a poem’s joy… to suggest it, that is the dream”,而對方腦海裏聯想到一個意象,它轉眼即逝,但它在腦海裏留下一個理想的「花」的痕跡。
quot;I say: a flower! and, out of the oblivion into which my voice consigns any real shape, as something other than petals known to man, there rises, harmoniously and gently, the ideal flower itself, the one that is absent from all earthly bouquets." (Je dis: une fleur! et, hors de l'oubli où ma voix relègue aucun contour, en tant que quelque chose d'autre que les calices sus, musicalement se lève, idée même et suave, l'absente de tous bouquets.)
在馬拉美的語言裏,花(或玫瑰)代表意念,裝着花的玻璃花瓶自然是詩歌(「玻璃」verre和「詩歌」vers發音相似),製造玻璃的工匠(verrerie指玻璃器皿,從構詞上也可理解為玻璃工匠)自然是詩歌的工匠。這些意念互想關聯,形成一個網絡,以至事物漸漸被符號化,到某一刻,讀者感悟到,那符號指向一個無法看見的地方,也許是夢裏的事物,也許是想像的世界,也許是形而上的概念。
馬拉美追求純詩(pure poetry)境界,他不斷地追求「理想」、「絕對」、「純潔」,而他所找到的無限,就是「無」,沉默就是無限的境界:「漆黑」、「深淵」,以至柏拉圖式的「空無」(Le Néant)。
馬拉美的十四行詩”Surgi de la croupe et du bond”「瓶中玫瑰」(或譯「花開苦短」)正是這些概念的完美示範。
瓶中玫瑰
從瓶腔裏悄悄地冒出 那幻幻蹦跳的玲瓏, 也沒有繁華辛酸的清醒 ——無知無覺的瓶口像啞然嚴封。
我相信情人和母親 向來未曾親口啜飲 這幻想釀成的香酩 ——我,這從天花板飛來的風靈!
沒有任何飲料的純美花瓶 無盡的孤獨使你暮氣沉沉 並使你越益黯然孤零,
一枝玫瑰在幽暗裏 給了你一個沮喪而天真的吻, 竟劃破了這蕩蕩虛無的幽深。
(葛雷、梁棟譯)
urgi de la croupe et du bond (Rising up from its bulge and stem) D'une verrerie éphémère (of fragile glassware) Sans fleurir la veillée amère (- with no flowers to crown its bitter vigil -) Le col ignoré s'interrompt. (the vase's neglected neck stops short.)
Je crois bien que deux bouches n'ont (I do believe the mouths) Bu, ni son amant ni ma mère, (of my mother and her lover) Jamais à la même chimère, (never drank from the same love-cup) Moi, sylphe de ce froid plafond! (I, sylph of this cold ceiling!)
Le pur vase d'aucun breuvage (The vase untouched by any drink) Que l'inexhaustible veuvage (except eternal widowhood) Agonise mais ne consent, (is dying yet never consents)
aïf baiser des plus funèbres! (- oh naïve funereal kiss! -) À rien expirer annonçant (to breathe out anything that might herald) Une rose dans les ténèbres. (a rose in the darkness.)
全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充滿了否定的詞語,馬拉美擅用「不在」來勾勒出「存在」,而從詩首描述花瓶(詩歌的載體),經過「虛無化」至詩末漆黑中的玫瑰,正好描繪了詩人表現意念的過程,也就是詩歌作為物質化的言詞旨在營造意象,它作為語音最後會消失(第十三行to breath out nothing),只剩下意念(玫瑰)這痕跡。
馬拉美在詩裏的敘事手法正好描述了詩歌如何通過關聯表達意念的過程。第一個四段體描述了一個花瓶,但詩人沒有說它是花瓶(也可能真的不是),第一句先描繪一個含糊的形狀(croupe和bond的意思在此也很含糊),即一個突起和有曲線的形狀,然後描述它的質感(玻璃,還有語帶雙關的詩歌工匠),最後說明它沒有花,和它的頸部是中斷的,提示了物件可能是花瓶。
第二個四段體是詩人的想像(Je crois bien,我相信),從花瓶的口聯想到人的口。詩人進入了幻想,他想到了他媽媽和她的情人,可是他倆都在否認句裏,而詩人在一個冷凍的天花裏。若花瓶是現實中的東西,他媽媽和情人的愛情是不可見和不存在的(愛情不能看見,而且它在詩人想像裏,加上是否定句,還有chimère這神獸象徵了幻像),這兩個意象聯繫之物——口就是現實(可見)與想像(不可見)之間的入口,也就是象徵主義裏的符號,這現實與虛幻中的交界處正是詩人嚮往之地(這交界與後面的天花所象徵的舞台關係馬拉美的戲劇理論)。
六段體裏將兩個意象連結起來,若花瓶就是詩歌,純潔的花瓶就是純詩,純詩裏沒有裝盛任何意念,婚姻(意念)裏也是孤身一人,形式與內容從來不相容,因為彼此沒有自然的關係,它們的結合——親吻也不過是幼稚膚淺的聯繫,詩歌最終也不過是一口呼出的空氣,提示了意念,而這意念到最後像漆黑的玫瑰般殘留腦海中。
六段體的語法結構也極富心思,純潔的花瓶所引申的整個句子都是一個從句,即La pur vase d’aucun breuvage [que l'inexhaustible veuvage agonise mais ne consent, naïf baiser des plus funèbres, à rien expirer annonçant une rose dans les ténèbres.] 意念從屬於那個花瓶的表象,即在句法上也暗喻了花瓶在外,意念在內,而玫瑰花在否定句裏,它是一個形而上存在(在虛無的世界裏)。
《马拉美诗全集》读后感(四):牧神的孤独——对马拉美纯诗世界的管窥
牧神的孤独
——对马拉美纯诗世界的管窥
白色的幽灵、纯洁的风采
注定它以冰雪为伴,
天鹅披着徒然流放中
轻蔑的寒梦不复动弹
——《天鹅》[1]
初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无论谁大概都会被那幽幽的寒意伤到心脾,一个冷冷的孤独的马拉美形象也会立刻树立于眼前。但我得说,请别就这样轻易地为诗人定下素描像。
阅读这本《马拉美诗全集》,我最初惊讶于目录中大量以“赠”、“题”或“题赠”开头的标题。这些字眼后面跟的无非是各类夫人小姐或文化名人的名字。如果说一名诗人向一些文化名人致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的话,那么,全集近百首赠给各类夫人小姐的简短诗作该如何看待呢?这种缺乏才情展现的交际诗让人怀疑这位盛名之下的沙龙主人[2]是否是,或者是否至少曾经是一个依靠混个脸熟的方式博取虚名的诗人?毕竟一般来说,一个有着广泛社交经历的诗人是很难和冷冽孤独的形象统一在一起的。
马拉美给魏尔伦的一封信[3]为我们解决这个疑惑提供了很好的事实材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家庭大革命以后,都相继在政府和登记局做官员;而尽管他们一直处于高官的地位,但我却逃避了从我襁褓中就被注定了的这种官僚生涯。”[4]“我很小的时候——七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先由祖母抚养,她很疼爱我,随后进寄宿学校和中学,我有一颗拉马丁的灵魂,暗暗向往,有朝一日能取代贝朗瑞”[5]从这两段自白中,我不由感叹一个具有官僚基因孩子竟逃避官僚生涯而去做诗人的矛盾性。马拉美出众的交际能力,应该跟这官僚基因不无关系。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选择成为诗人的马拉美认为当时“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它太废旧、太该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6],而生活于其中的诗人必然拒绝与时代同流合污,“这种态度必然给诗人带来孤独”[7]。
但事实上,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所带来的孤独往往是复杂的。比如本文开头所引的《天鹅》,即暗示了一种冰冷环境中的孤傲;又如:
在那缄默的唇上,死寂啊,
你是他们唯一的亲吻。
——《恶运》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一种孤寂,一种渴望。再如:
啊!这个谙尽辛酸的我呀,难道就不会
借重受欺凌的魔怪,冲破这层玻璃,
鼓起无羽毛的双翅倏然而去
冒那在永恒中失足堕地的危险。
——《窗子》
这首诗则传递了以有限之能力探求无限之艺术的无望执念。还有:
让黄昏的秋阳拖着一缕尾光挨过
死寂的水面,那里落叶的萎黄随风悠游,
划出一道冰冷的犁沟。
——《叹》
这首题目常被译为“叹息”的名作,其主题在马拉美的另一首作品《蓝天》中有更明确的表达:
我闭目逃遁,感到苍穹
带着震惊的内疚,忐忑地注视着
我那空虚的灵魂。逃向何处?抛掉何等
惶恐的夜,把它的碎屑抛向这令人伤心的轻蔑?
相比而言,《叹》的表达更为婉曲一些,他通过描述自然的空灵寂美来暗示自己向往自然,以逃避现代文明约束的孤寂心境;而《蓝天》则表达自己在现实理想面前的空虚与无能,而不得不寻求逃避的可能。同样是“逃避”的主题,诗人下笔的角度又不尽相同,但追根究底,我们发现在这统一的主题背后,是一样的孤独柔软的心灵。
种种孤独的变体,在题材并不开阔的马拉美诗作中显得相当突出。但孤独在人类漫长的诗歌史上,属于时时刻刻都会现身的常客,所以其本身恐怕很难成为一名诗人的追求之目的。马拉美的孤独也不过是在种种时代的遗弃与逃避,生存的理想与现实,追求的可望与可及,情爱的神圣与狂野等等矛盾追索中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而无论何种矛盾,马拉美的执着在于对时代的态度始终如一。我们摸索了复杂的孤独形态后,最终又回到前文已述的马拉美自己的观点上去。但这种对时代的拒绝态度,并非是一种划清界线式的断绝关系的结果,而是追求有异的必然结果。马拉美的追求在其令几代人头痛不已的名作《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遗忘和荒芜的冰冷
数不
胜数
在某个空虚而至上的表面
连续撞击
最终幻成
星声的数点
警醒
疑惑
流动
闪烁和沉思
在停留在
某个使之珠光迷离的新点之前
全部思想掷出一把骰子
我们面对这种纯粹的诗性思维的领域时,无法以现实世界的某个因素作为开始读解之门的钥匙,因为诗歌常见的抒情表意功能已经被个体性的自我感觉表达功能所取代,于是他以一种纯粹性的想象力来暗示某种唯心的智性与抽象。正如梁宗岱所说:“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达光明极乐的境域。”[8]在读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只能依凭感觉——尤其是想象——去摸索词与词之间、短语和短语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便能感知到某种梦境般的非逻辑性存在。
上引片段是《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一诗中比较带有连贯性和画面感的一个片段,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想象:无数冰雹在冷寂夜空中坠落,但在半空时就受到一个透明无形的坚硬平面的阻截。它们在这个平面上撞击出火光,像星星一样闪亮,然后弹跳着,发出清脆的响声。而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一切偶然性的因素都可能改变这个状态,甚至哪怕只是某个细微的想法。当然,想法总是很多,于是偶然性的因素也变得无法预料。这样的读解显然是机械而不可取的,但作为一种可能,其在通过想象追寻智性与抽象的方式上,或许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读解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关键问题所在,读解过程本身其实已经跟诗歌写作本身产生了一种同构性,即读解对智性与抽象的追寻或感知,和写作对事理和客观的摒弃其实是一致的。那么,无论是读解还是写作,都不得不进入单独的思维境地,从而在静寂中只能与傲然又痛苦的孤独作伴。
这种对纯粹性的追求,让马拉美诗歌中显现出的孤独也时不时地带上了如水般纯净透彻的质地,除了上引《天鹅》、《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等名作外,《一个牧神的午后》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不,你滞留在昏迷的疲倦中
为压倒凉爽之晨的炎热所窒息;
不要水声呢喃,让我的笛声潇洒
林丛;只有风儿把声音散入淅沥的
霖雨之前,从玲珑的笛管中喷出,
在不被涟漪搅扰的天边,
那充满灵感的嘹呖而恬静的笛声
响遏行云。
……
闲适的话语的灵魂和这变得沉重的躯体,
在这正午自豪的沉寂中迟迟地颓唐下去,
不再需要在对亵渎的遗忘中睡去
在平展变质的沙滩上,当我
向着醇酒般浓烈的阳光张开嘴巴!
情侣,再见,我要看到你们蜕变的幻影。
这首诗是写某个六月的日子里,天空晴朗,牧神在苇塘休憩的时候,来了一群仙女戏水,他醒来看到后便吹响芦笛致意,不料却吓跑了她们,他又想和没来得及跑的仙女拥抱,却被迅速撇下了,一场如梦美幻的情境便在转眼间消失如泡影。法国评论家蒂波岱对这首诗评论说:“诗人试图使其诗章里洋溢着音乐和芭蕾舞的逸韵之美,我们只要读上一页他的诗,心里便会马上感觉出这种美来。牧神的笛子、哀叹和出神所构成的幻觉与影子,围绕着这部作品形成一种被清澈气息和灿烂的金色所幻化成对的云霓:在这部‘思想剧’中,形式和主题、诗和诗意合二为一,使我们在发现它们的无限单纯的同时获得怡悦,甚至忘记了人世间的其它一切。”[9] 上文所引述的两个片段分别描述了牧神吹笛时的情景和牧神在仙女们离开后的情态。前一个片段展现自然物和音乐的纯美,后一个片段则让这种纯美在“醇酒般浓烈的阳光”下充满光亮的孤寂感,我们甚至可以在牧神最后的祈望——“我要看到你们蜕变的幻影”中看到晶亮的水迹溢过孤独的眼神,在落寞的脸庞缓缓划过,像放慢了脚步的流星一样,让沉落的孤寂感和纯净的自然美如酸甜交错的红酒,在人的内心反复激荡。
或许马拉美正像牧神一样,在纯粹的诗歌写作中,无比地靠近着艺术的永恒之美,又因为有限的生命与不可抗拒的人类艺术能力的局限,而永远无法触及这永恒之美。是为马拉美的孤独,亦为牧神的孤独。
注 释:
[1]本文所引马拉美诗作均出自葛雷、梁栋译《马拉美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马拉美每周二晚上,都会在罗马街的寓所接待诗朋文友,然后众人一起谈诗论艺。由于拜访者中包括了音乐家德彪西、雕塑家罗丹、诗人魏尔伦,以及瓦雷里、纪德等后来才成为文坛巨擘的一干人等,所以这个固定的聚会成为文学史上极富盛名的一个文学沙龙,被称为“马拉美的星期二”。
[3]1885年11月16日,马拉美应魏尔伦之邀写下这封自传性质的信。葛雷、梁栋的《马拉美诗全集》中将Verlaine译作“魏尔兰”,本文按照习惯译法,改作“魏尔伦”。
[4]马拉美《自传》,《马拉美诗全集》(附录三)第378页,葛雷、梁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5]同上。拉马丁,1790-1869,法国十九世纪第—位浪漫派抒情诗人。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诗人。
[6][7]同上,第380页。
[8]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
[9]葛雷、梁栋《现代法国诗歌美学描述》,第123-1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马拉美诗全集》读后感(五):穿越時空的冀求——《徒然的請求》馬拉美
馬拉美的《徒然的請求》寫於他詩作生涯的早年,於1887年出版,那時他還在詩刊裏投稿,艱澀的文字常遭到退稿,此作的原名為《請求》,另一寓意是對出版的請求。 葛雷在《馬拉美詩全集》將詩作譯為《小箋寄女友》,他認為詩人之人是雜誌的編輯,但若明白當中的語言遊戲,詩中之人該是馬拉美遙不可及的詩歌理想:
小箋寄女友
公主,嫉妒一位赫柏的命運, (赫柏為希臘神話的青春女神》 她也在留下你高貴之唇的樽邊留下唇痕, 我內心裏燃着熾情卻僅遵着神甫的清規, 即使在這塞弗爾的大地上赫條單身 (譯者認為塞弗爾為南法的地方,但這也指貴族婦女用的瓷器)
因為我不是你長鬍子的小犬, 不是酥糖片,胭脂或伴你嬉戲的三尺頑童, 我知道你已對我瞑目凝心, 去專心在你的金髮上用珠寶顯示自己的神聖!
何所謂…滿臉洋溢着鮮草莓微笑的你, 和我一起竟一時混入了這芸芸的羔羊之群, 一起啃齒這海誓山盟並狂奮地發着這咩咩之聲,
何所謂…為了這羽扇搖搖的愛情, 幽笛數聲洗得我一腔心事平靜, 公主,讓我們作放牧你微笑的主人。
lacet futile
1 Princess! À jalouser le destin d’une Hébé
2 Qui poind sur cette tasse au baiser de vos lèvres,
3 J’use mes feux mais n’ai rang discret que d’abbé
4 Et ne figurerai même nu sur le Sèvres.
5 Comme je ne suis pas ton bichon embarbé,
6 Ni la pastille ni du rouge, ni Jeux mièvres
7 Et que sur moi je sais ton regard clos tombé,
8 Blonde dont les coiffeurs divins sont des orfèvres!
9 Nommez-nous… toi de qui tant de ris framboisés
10 Se joignent en troupeau d’agneaux apprivoisés
11 Chez tous broutant les vœux et bêlant aux délires,
12 Nommez-nous… pour qu’Amour ailé d’un éventail
13 M’y peigne flûte aux doigts endormant ce bercail,
14 Princesse, nommez-nous berger de vos sourires.
Futile petition
1 Princess! Envying the lot of a Hebe
2 Who alights on this cup at the kiss of your lips,
3 My ardour flames, but I have only the modest rank of abbé
4 And won’t be figured even nude on the Sèvres.
5 Since I am not your bewhiskered lap-dog,
6 Not the lozenge, or the rouge or the Supreme Game
7 And since upon me I know your closed glance has fallen,
8 Fair one with goldsmiths as divine hairdressers!
9 Name us… you whose raspberry laughs
10 Group themselves in flocks of gentle lambs,
11 Grazing on the vows of all and bleating their ecstasies;
12 Name us… so that Amor winged with a fan,
13 May paint me there, flute in fingers, lulling the fold,
14 Princess, name us shepherd of your smiles.
一如馬拉美的作風,《徒然的請求》充滿令人困惑的言詞,還有不相關的意象。驟眼看來這是一首尋常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詩(Petrarchan sonnet),描述一位僧侶對不可即的公主懷着強烈的愛意,這種高貴的拍拉圖式愛情和彼特拉克十四行詩慣有的風格相符。可是仔細讀來,詩中行文怪異地讓「你」(tu)和「您」(vous)並用,而公主只有一位,到底「您」是指誰?「你」是指誰?
《徒然的請求》裏充滿強烈的意象:希比女神(Hebe)、瓷器茶具、寵物狗、口紅,還有田園景象,這些象徵符號(也就是象徵主義技法)皆營造着洛可可風格的氛圍。洛可可為十八世紀的繪畫風格,描繪貴族生活、男女情愛,歌頌享樂和愛情,縱慾、情色、現世歡樂皆為重要主題。希比女神——也就是希臘神話中象徵青春的女神為洛可可繪畫中流行的題材,不少貴族女性以希比女神的半祼形象入畫,手執茶杯、烏鴉伴隨在側正是希比形象的標記。這對應了詩中的公主拿着瓷器的杯具,還有有如十八世紀的貴族婦女梳着複雜無比的髮型(Blonde dont les coiffeurs divins sont des orfèvres!/ Blonde whose divine coiffeurs are goldsmiths!)。
洛洛可繪畫中貴族女性的希比女神造型十八世紀貴族女性的誇張髮型若詩中充滿着洛可可的意象,它如何能與彼特拉克十四行詩相融?一為世俗縱情之愛,一為含蓄、不可得的宮廷之愛(courtly love)。若馬拉美終其一生也在尋找詩的絕對,和改革詩歌,《徒然的請求》正暗示了這個願景。此詩以彼特拉克十四行詩的格式寫作,可是每行打破了6+6的亞歷山大詩的韻律。馬拉美本就是自由詩(vers libre)的支持者,此詩用上陳舊的外殼,灌以自由的內心。
這解釋了為何詩中交替地用上「您」和「你」,若公主就是不可即的「絕對」,僧人雖深明自己須獨身的身份,卻仍被引誘靠近。到底公主離僧人有多遠?詩人在十四行的過程中慢慢展現他們的距離和身份。公主自一開始就從希比女神裏得到了女神的身分,她從親吻茶杯這動作接觸了杯裏的世界,也就是僧人嚮往之地(他自嘲自己不能以裸體進入瓷器)。那公主到底是誰?從第二個四段體的描繪,意象充斥着洛可可繪畫的風格,而第七行(全詩的中心點)正是憎人與公主眼神的交會點,也就是最接近彼此的瞬間,同時暗示了——僧人在看一幅畫,畫中的公主(即希比女神的化身)同時在看着自己。
三段體裏是僧人的請求,他請求愛神賜他雙翼,並為他「在那裏」畫上一枝笛子,讓羊群安眠,法文裏強調了「那裏」(”y”),到底他要被畫在哪裏?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到底僧人是誰?
此詩有一個1862年的版本,這版本更直接地描述了主角的身分。
lacet (1862)
1 J’ai longtemps rêvé d’être, ô Duchesse, l’Hébé
2 Qui rit sur votre tasse au baiser de tes lèvres.
3 Mais je suis un poète, un peu moins qu’un abbé,
4 Et n’ai point jusqu’ici figuré sur le Sèvres.
5 Puisque je ne suis pas ton bichon embarbé,
6 Ni tes bonbons, ni ton carmin, ni tes Jeux Mièvres,
7 Et qu’avec moi pourtant vous avez succombé,
8 Blonde dont les coiffeurs divins sont des orfèvres.
9 Nommez-nous… vous de qui les souris framboisés
10 Sont un troupeau poudré d’agneaux apprivoisés
11 Qui vont broutant les cœurs et bêlant aux délires,
12 Nommez-nous… et Boucher sur un rose éventail <==
13 Me peindra flûte aux mains endormant ce bercail,
14 Duchesse, nommez-moi berger de vos sourires.
etition (1862)
1 Since a long time I have dreamt to be, o Duchess, the Hebe
2 Who smiles on your cup kissing your lips,
3 But I am a poet, a little lower than an abbot,
4 And haven’t any positions here on the cup.
5 Since I am not your lapdog,
6 Your candies or your caïman or your precious Games,
7 And with me however you have given way to,
8 Blonde one whose divine hairstyles are goldsmiths!
9 Name us… you whose honeyed peals
10 Are a troop spread in tamed lambs,
11 That going to crop the hearts and bleat in delirium;
12 Name us… and by Boucher on a winged rose,
13 Will paint me flute in hands, lulling the flock to bed,
14 Duchess, name me shepherd of your smiles.
在這版本裡,僧人就是詩人自己,公主是公爵夫人,也就是希比畫像的常客,而愛神不是別人,正是洛可可風格的名畫家布雪(Boucher),也就點出了伯爵夫人(公主的前身)在洛可可繪畫裏,詩人(僧人的前身)希望畫家能將他畫到田園世界裏,和愛人相守。
僧人和公主本就在不同時空,他們只能通過像咒語一般的象徵(親吻茶杯、眼神觸碰、繪畫)來穿越時空。這符合了象徵主義的美學觀,通過象徵來穿越空間,到達肉眼不可見的境界,一切只能用心感受,神秘本身就是美麗。
馬拉美是詩人,他的咒語當然不是意象那樣簡單,他採用語言作為咒語,也就是說,以語言作為動作。代名詞「你」和「您」的使用暗示了僧人和公主的距離。而詩中開端就是對公主的呼喊(Princesse!),這呼喊對應了他的請求——「委任我」(nommez-nous),這語言動作正是祈求公主將僧人的地位提升,僧人用上了「我們」(nous,royal “we”)在他的請求裏,以求和公主平起平坐,而沒有用上「我」(moi)。
僧人的請求成功嗎?從詩中的暗示來看請求是徒然的,在第十四行的終局裏,公主仍是維持「您」(vos sourires),而且在1862年的版本更明顯說明僧人仍是維詩「我」(moi),而非「我們」(nous)的身份。
詩裏不停地轉換角度,以語言遊戲暗示着距離。公主是希比女神的鏡像,本就不存在,正如詩的絕對一樣,任憑詩人怎樣昇華,他也不過是公主在凡塵的另一鏡像,一切如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