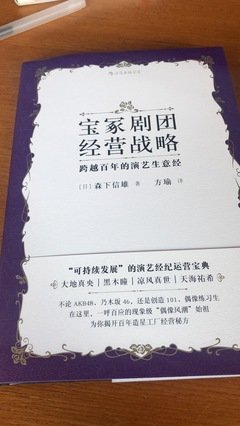
《亲吻神学》是一本由[德] 施皮茨莱 编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页数: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亲吻神学》精选点评:
●除了Abélard et Héloïse那部分不太满意之外其他的做得都很好,这位德国人确实是投入了中世纪的怀抱。绪言是十分精彩的,值得反复揣摩,情爱与信仰的关系值得现代人反思。特蕾莎和葛兰西的选文非常精当,堪称本书的一大亮点。当然最光辉耀眼的那两位还是不太出彩算是全书的遗憾。中译文句有点艰深……尤其是跋的部分不太满意不过总体不错了,明天情人节,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着的@Summer. C小姐〜
●读着读着眼睛就会湿,“爱推动我经历了这一切,走向你” 器官 性别 距离 生死都阻挡不了,人们的确是在通过上帝的存在来爱着一个人,这种遥远又宏大的灵性接触太震撼了,呈现的内在思辨也很有意味。爱的美好是由于隐修的宗教体验,还是来自于它本身的力量?感觉若即若离地能慢慢体会这些书信了,阿贝拉尔和海萝伊斯不多说,更喜欢贝恩哈德信的温度和真挚。信本来就是很美的东西。
●爱欲神秘,强无敌。“因为你和我都在自己和对方的内心感知对上帝的向往,所以,我们的爱教会了上帝用手指在我们心中的语言。”一方面是灵性情谊,另一方面是对遥远“你”的爱和对上帝无限的爱的相似。
●更喜欢原书名“愿你的唇吻我”。爱会永远大于我们的心灵。我们通往爱的道路没有尽头。只要我们相爱,彼总是在中途。在我们的界限之躯。在路上。
●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之间的信是多么不对等呀!他恭顺于上帝,而她恭顺于他。如果他不是极度虔诚和克制,就是极度虚伪。本笃会士的书信优美如散文。特蕾莎致西利娜的信则反映出语言的发展对宗教性表达的影响,相信这一部分也是最令现代读者感到亲切的。绪言也使我受益匪浅:爱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品质;一味强调苦修,而使内心爱的源泉枯涸,将离上帝之道越来越远。以此为前提,“禁欲”的中世纪将给人不同的观感。
●《午夜巴塞罗那》里的萌爷爷说,六千年过去了,人类还是没有学会如何相爱。“爱永远大于我们的心灵。只要我们相爱,彼总是在中途。在路上。” 三世古今,无边刹土,无量光,无量寿。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一个甘心成为心爱男子奴仆的女人照田园女权主义者来看应该十足的愚蠢了--但任何讨论都不应该脱离历史语境与具体情境,全然政治正确的话语实在乏善可陈,毫无美感又面目可憎。与之相类,芸娘的行为可爱至极。
●已读,已忘
●为了阿贝拉尔
●amazing
《亲吻神学》读后感(一):修道男女曾经拥有过的爱
《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四年前读时,感动不已。也因此,在问候旧书箱时,她透过时间的尘雾,继续揪住了我的心。尽管此时我的心境已经和四年前大不同了。那时在意的是神圣的高墙笼不住的人性之爱;现在在意的是真正的人性之爱赖以持存的神谊。
记得当时读到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的情书时,满心忧伤。尤其是为海萝丽丝忧伤。他们大约邂逅于12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的巴黎。阿贝拉尔38岁,极富声望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海萝丽丝16岁,受过良好教育。广泛涉猎拉丁文献并通晓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阿贝拉尔受聘指导海萝丽丝研习哲学。在这对师生之间,产生了炽烈的爱情。授课的时间,成了他们私守的时间。他们不是看着书本,而是凝望着对方的眸子,他的手不是放在书上,而是放在她的胸脯上。他们不知餍足地品尝着爱的欢乐。后来,海萝丽丝怀孕了,他们之间有婚姻承诺,但鉴于阿拉贝尔的学术工作,他们暂时秘而不宣。但也因此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满怀仇恨的海萝丽丝的族人将阿拉贝尔阉割了。从此,阿拉贝尔选择了修道院生活,海萝丽丝也遵从他的意愿,以修女生活终了一生。她给他的信中,一再表达着她对这个人的爱。“我当修女并非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是听从你的要求。”“我心中迸发着青春之火,美德并非指身体的纯洁,而是指灵魂的纯洁。我在上帝面前没有荣光,因为上帝检验人的心,洞察人的隐秘。”“我的目标是使你完全得到满足,‘夫人’之名对别人也许是崇高的、隽永的。但我却认为。所有种种甜蜜的象征永远是被叫作你的情人,或者——啊,请别生气——被叫作你的陪睡者、你的妓女。在你面前忍受最大的屈辱便是对你最崇高的敬意。我的低下地位也绝对遮蔽不了你的熠熠光辉。”她把自己的生命不是献祭给了上帝,而是固执的献祭给了受难的人爱。对于她,没有了他的尘世,再没有了颠倒众生的那些欢乐。
那时,我迷恋海萝丽丝献祭的力量,而没去多想她献祭的意义。还有萨克森的约尔丹与安达罗的狄安娜、阿维拉的特蕾莎与格拉西安,在他们的情书中,充满了相见时难的忧伤。既然相爱了,为什么要选择承受分离的痛苦?为什么不能既满足时空之中的身体之爱又永葆超越时空的精神之爱?的确,修院生活往往因其反人性的禁欲而遭诟病。尽管德国思想家舍勒在其《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曾为此辩护:“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有动物性的方面。” 是受自然本性欲望的支配,还是以精神支配自然欲望——这是区别现代人性观与中古人性观的关键。但问题依然在于,为什么要压抑肉身的欲望才可以仰望神圣?爱欲作为柏拉图式的爱感与美、真、善之间的中介,是通向基督上帝的阶梯,何时成了精神的敌人?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的爱欲本身是那么盲目、易变、常误会、不圆满。修道男女之间的爱之所以那么真挚、持续终生,是因为他们在灵性情谊的爱的生活中效法基督,将精神送往天国的草地上的花丛,让它在那里采集它赖以生存的花蜜。
2008-03-12
《亲吻神学》读后感(二):Heloise的孤勇与纯粹。
在学校图书馆无意间瞥见此书,
带着一种看“朱生豪情书集”的心态借阅来翻看。
特地准备了一个印花的笔记本用以摘录。
结果看了绪言中各种关于“灵性”“情谊”的论述,便觉表述生涩难懂。
爱是活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
不信仰任何宗教,固定唯物主义思想,使我很难理解书信中所表达的“将爱牢牢系在上帝身上”或是“你在主身上寻求安慰,对我亦是安慰”等灵性之爱。
但之于Heloise,她的书信确是她“深情炽热的心房搏动的记录”。
引言称她是一位“伟大的献身于爱的女性”、“以实践证明了纯洁的爱”。
出身名门的Heloise放弃她所留恋的世俗的种种欢乐,进入修道院生活,只为听命于Abaeard的意志。
初看满是不屑,觉得"爱种应无我"?!我擦,姑娘真是傻逼。
仔细看了几遍书信后,便不觉喜欢上这个姑娘。
其看似疯狂缺乏自我主见的行为也是只源于其真实直接的炽热情感,纯粹可贵。
【Heloise用心灵的眼睛看着他,
她看出了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兼教士的理想。
由此而产生对Heloise——她无力摆脱爱的玫瑰——的责任感】
她不需要他的承诺,不需要婚姻的纽带,毫无保留的献出了一切。
“结局证明了,我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始爱你的。”
“通过奉献,我成为你的。”
“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友善的面容,只要你以你之爱报我之爱,以你之微报我之大,以你美言报我饱含牺牲的劳作......”
但是,你没有。
Abaeard并非出于本心走近修道生活,而他一经踏上这条宗教道路便走得十分执著。
“不回信是相信你的聪明,无需向我寻求爱与安慰”
他的回信丝毫看不出曾经的激情与爱,
“首先...... 其次...... 再次...... 最后......”
逐条论述,满是教化与指导。
主题不过论述女性祈祷的种种好处,所以“你应为我祈祷,满怀信心不停地为我祈祷”
谴责Heloise对上帝不顺从的抱怨,“你应该为误解我感到羞愧”
“你应该乐于满足我的要求”
“请别再谈这些空话,停止那些与真正的爱毫不相关的抱怨吧!”
......
如此种种,在我看来,理性到令人发指。
“因为我想让你在一切方面都高兴呀!”
“请求你不要再高喊美德。”
“我也不再发泄抑制不住的痛苦,因为你禁止我这么做”
虽有为自己解释的辩护,但几句小情绪后又是无尽的顺从与痴迷。
在神学体悟方面,他或许早已走在了她的前头,试图提携她。
但她并没有真正投入其中啊!
Heloise将她对Abaeard爱奉为对真理的追求,
产生盲目单纯一腔孤勇的英雄气概。
纵使“我给予你的是安全的凭靠,而我收获的却是不堪忍受的轻蔑。”
纵使“命运将它所有的利箭都消耗在了我身上。”
纵使“疲软无力如一颗心,恰如我这颗心!”
但还是爱你啊。
只是,你日益冷淡的回应,全无情感的指摘能让我坚持多久?
第六封信的最后不再是“我唯一之爱”,
而是“祝平安!”
不知作者的节选摘录,此番安排用意何在。
故事并未完全展开,
有意无意的依据自己最近的情感波动,如此理解.....
Heloise似乎跳出黑色的长袍,中世纪修道院的高墙,单是一个一腔孤勇的少女。
愿你不再被动的跟在他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共同在通向上帝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亲吻神学》读后感(三):“愿你的唇吻我”
听说阿伯拉尔和爱洛依斯的故事是很久以前了,在中世纪哲学课上,来自洛杉矶的教授用好莱坞闹剧的语气讲述阿伯拉尔如何在授课时诱惑爱洛依斯,与她热恋,导致她怀孕,产下一子。他们秘密结为夫妇——秘密是因为爱洛依斯的各种理由——他又被她的家人阉割作为复仇。大概因为先入为主,我总是没法把他们的经历看成悲剧。
书中选编的他俩的通信让人稍感失望。各自进入修道院后十二年,因为阿伯拉尔写给友人的一封信被爱洛依斯看到,他俩在信纸上重新开始联络——尽管他们早已是名义上的夫妻。
这几封信写于他们开始复交之时,爱洛依斯抱怨阿伯拉尔在那么久的时间里完全不抚慰她,哪怕在纸上,用亲切的字句;抱怨上帝为何残忍地让他们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她觉得上帝不公正。阿伯拉尔的信则主要是反驳爱洛依斯的这两个抱怨。
让读者失望的地方在于,并没有从中读出正面力量和超越了常人的灵性的情谊。爱洛依斯的最后一封信已经有了点进入智性话题的意思,可惜本书篇幅有限,还没开始就收了尾。
但编者引言里引用的阿伯拉尔的《受难史》中的一段话很打动我:“我完全失去了理智。爱洛依斯也不愿用更激烈的言词来伤我的心。她只有一边抽泣一边说,‘即便我俩注定要毁灭,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安慰,这便是我们未来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将与我们曾经有过的爱的甜蜜一样深切’。”
我从中读出一种超脱:她把爱的甜蜜与爱所带来的痛苦对等起来——既然都是由爱而来,为何只愿意享受一个而拒斥另一个呢?倘若事先便知晓如今的痛苦,他们是否会因此而不来到彼此?恐怕不会。至少爱洛依斯不会。她抱怨归抱怨,但丝毫不曾后悔,不曾像阿伯拉尔那样把曾经的冲动和柔情蜜意当做羞耻的证据。
这也是爱洛依斯打动我的另一个原因:在修道院里修习了十几年,已经成为女修院长,却仍然一再强调她的不再能够被阿伯拉尔满足的情欲,并将之归罪于上帝。我钦佩她的对自己内心的坚守——她根本不曾把上帝置于爱情之上,不曾把规诫置于内心之上。她的热烈让人看到她的生命力并没有枯萎,而是像扑不灭的火,顽强地窜出美艳的火焰。
人需要一个坚守。无论坚守的是什么。这个坚守是她的支点也是她的根基,让她的生命不再是琐碎的、漂浮的、任凭文明或命运摆布的。她在她的坚守中成为她,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个人。
书中选编的通信还有很多是其他的修士与修女之间的,甚至,诞生于同一个家庭的亲姐妹之间的情书。最后还有二十世纪末的修道院中隐去了姓名的情书。说实话,我并不全然相信修士和修女之间的情谊当真是“灵性”的,越过了性的。即便果真如此,性或许仍然在沉默中驱使着他们在纸上的爱恋,就像身体在沉默中支撑起我们的喧哗的精神世界。
最后说一说永恒吧。一位二十世纪末的修士写给自己的修女恋人:“爱会永远大于我们的心灵。我们通往爱的道路没有尽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便总是在中途,永远在中途。”
友人在阐述他的积极虚无主义时说,爱情并不能一开始就默认是永恒的,但会努力使之接近永恒。我不明白这个观点为何被看成是虚无主义的。我以为这不但是更真实的描述,更体现出看待人事的健康心态。倘若不在发生处便默认永恒算作虚无,那么,虚无便是健康的别名。
有次聚会,友人感慨,人是转瞬即逝的,人生如此短暂,能够构建些什么呢?我问他,假设你是不朽的,你想构建什么?他拒绝进入这个思维实验—或者说,游戏——因为人不是不朽的,假设不朽,相当于从一开始就取消了人,取消了人得以思考的前提。
但我还是很好奇:人究竟想构建些什么?这些被构建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需要构建者是不朽的才能达到?爱情是不是这些东西中的一个呢?人们为什么会希望爱情是永恒的,既然人本身并不永恒?人在生老病死中走完一生,哪有永远那么远 。而,永远又有多远?大概有一个真实的心灵所跋涉的路程那么远吧。
《亲吻神学》读后感(四):天地有大爱而无言
有一种爱,它超越身体、性别、门第、时间、距离和一切世俗的欲望,只因上帝与你我而存在。
最近看《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如清晨的小露珠,在上帝光辉的照耀下,闪烁着圣洁与清新。
浸在书的言语里,其中的感动,我想了很久也无法准确地表达,那是一种自己仿佛要熔掉似的的感动,然而底下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托住。字里行间的美丽,远远超出20年来我对爱的理解和想象。我不无为自己的渺小与庸俗感到悲哀,同时又为自己能够在如此年轻的岁月就有幸窥见这种太阳般的幸福而窃喜(有人到死都不知更不觉有这样一种幸福)。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丝毫不怀疑自己对书中文字的感受。宗教情感是人性中的一股清泉,我有幸被其漫延。
利雪的特蕾莎是整本书最可爱的人,“我的使命”,她说:“就是爱”。她把自己比喻成耶稣的小沙粒,把西利娜比喻成耶稣的小影子。她把自己和西利娜比喻成双生的矢车菊,迎着太阳。她说:“我们要拯救灵魂……灵魂像雪花那样飘逝。”
如果说特蕾莎的纯真让人无法抵挡,海萝丽丝的痛则真真让人潸然泪下。她为了阿贝拉尔献出整个生命,她对他说:“我当修女并非出于对上帝之爱,而是听从你的要求。”她痛苦着阿贝拉尔的痛苦,却换来阿贝拉尔的不理解,甚至是谴责和怀疑。她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没有荣光,在我看来,她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以至真至诚之心面对上帝,这就是海萝丽丝的荣光啊!我非常不喜欢阿贝拉尔,当他手握着笔写下“你不会是在通过逃避荣誉而谋求你的荣誉吧?你不会是口头上谴责你内心希望得到的东西吧!”时,因为怀疑,难道他连一点点对海萝丽丝的愧疚都没有?当他手握着笔写下“避免外表上的诚实,在避免的过程中寻求诚实”时,因为虚伪,难道他连一点点对上帝的愧疚都没有?当他手握着笔写下“……甚至使我更适于做庄重的工作,因为经受不住感官的诱惑会把事情搞糟”时,因为逃避,难道他连一点点对自己的愧疚都没有?(注:此前,海萝丽丝家族的人将他阉割)虽然他对海萝丽丝的言语也是出于爱,虽然是他把海萝丽丝一步步引向主,但他的心显然没有海萝丽丝圣洁,他的灵魂也没有海萝丽丝自由和博大。
在西笃会修士的信里有一段话对我震撼特别大:爱现在不再是像死亡那么强大,而是比死亡更加强大了。上帝的力量因为爱的力量的增长而削弱,直至死亡。然而这被削弱却证明了自己比强大者更强大,它的死亡成为死亡之死亡,啊!死亡。
是啊,其实世界上最强大最美丽最永恒的不就是爱吗?这爱之大用我们人类创造的任何表达方式都不足以诉说,而其中的许许多多灿烂若夜空的星星,温暖如冬日午后的太阳,要我们以自己虽然微小却敏感的心去贴近,去感受与体验。
一直一直,我都那么渴望出现一个人,他(她)可以给予我灵魂的慰籍,而不仅仅是肉身的依靠,这也是为什么《戏梦巴黎》可以让我幻想长达两年之久,至今余温仍未退尽。与中世纪相比,现在肉欲横流,看似人们彻底地摆脱了精神枷锁,其实如德国思想家舍勒所说:“中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真是可悲。
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守住生命的圣洁?
“生命是件瑰宝,每一瞬间都是一种永恒。”如果我们糟蹋了,不是很可惜吗?让我们用自己唯一的爱的胸怀去拥抱整个世界吧!
《亲吻神学》读后感(五):来世也许要天上团聚(韩戍/文)
(原载《文景》2009年第一、二期合刊)
最初读到阿贝拉尔(Peter Abaelard)和海萝丽丝(Heloise)的故事,是在一本名为《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的书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刘小枫组织编译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中的一部。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感叹道,原来基督教思想中也有这样令人震撼的文字和精神。
此言诚是。因为一般人很难将“修道院”和“爱情”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提起修道院,我们想到的往往是离弃世俗,在高墙之内冥思默想的修士修女形象。为了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生活,他们禁欲苦修,把自己的一生都交托给上帝——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凡俗世人的七情六欲呢?
可是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这就决定了一部分人,即使在生活方式上超越了世俗,仍然不能摆脱那些人类专有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何况像海萝丽丝这样集智慧和美貌于一身的富家千金,“遁入空门”原本就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阿贝拉尔,1079年生于法国南特附近的一个骑士家庭,自幼就聪敏好学,对神学、哲学和逻辑学有着天然的热情和兴趣。他曾跟从多位神学名师就学,由于理念不合而又相继和他们分道扬镳。1114年,已经创办了三所神学学校的阿贝拉尔来到巴黎,成为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的校长。海萝丽丝,1101年生于巴黎,自幼饱览各种拉丁文献,又通晓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在修女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117年,已经在神学界盛名颇著的阿贝拉尔接受了巴黎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当地望族富尔贝尔的聘请,担任了其侄女海萝丽丝的私人教师。一方景仰一方的学识和才华,一方爱慕另一方的聪慧和美貌,两人很自然地跨越二十二年的灯火阻隔,爱河中泥足深陷,一发不可收拾。
二人的感情升温,既有阿贝拉尔的主动诱惑,也有海萝丽丝的迁就迎合。前者对后者,既是思想唤醒的导师,也是爱欲启蒙的引路者。他几乎把大半的授课时间用来和海萝丽丝谈情说爱。在1135年写成的《受难史》中他写道:“相互亲吻多于箴言的阐释,我的手往往不是放在书上,而是伸向她的胸脯。我们不看书本,只是相互深情地凝视着对方的眸子。我们从未品尝过这种欢乐,这时却怀着烈火般的倾慕激情不知餍足地享受它,从不感到厌倦。”显然,两人深深沉迷于那种美妙的温柔缱绻之中,以爱的名义肆意享有对方,陷入不可遏止的身体欲望之中,无法自拔。海萝丽丝不幸有了身孕,而堕胎又是基督教最大的忌讳,阿贝拉尔只得把她秘密带到布列塔尼(Bretadne)的姐姐家里生产。随后两人缔结了婚约,海萝丽丝暂时栖身于修道院,阿贝拉尔则重返巴黎执教,出于不打扰阿贝拉尔学术研究的考虑,二人将此事秘而不宣。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事发生了。富尔贝尔家族以为阿贝拉尔诱骗了海萝丽丝,出于羞愤和恼怒,抓住将阿贝拉尔,强行施予最残酷的宫刑。全知全能的上帝,借着世人之手,实现了对阿贝拉尔渎神的惩罚。
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阿贝拉尔已羞于面对世人,只得选择彻底遁入修道院了却残生。海萝丽丝更没有办法,只能披上了那身她从前最为讥笑、鄙视的修女素袍,彻底献身上帝。然而对于修道一事,二人的态度是有着微妙差异的。对阿贝拉尔来说,这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救赎;他将自己的遭遇看成是上帝的惩罚,终身修道,自然是为了洗清罪孽,以求得彼岸的永生。而海萝丽丝自绝尘世,固然是性格中原本带有理想主义的因子,更多的还是出于无奈,出于顺从阿贝拉尔的意愿;她对天国和彼岸世界并不是十分笃信,她不止一次地抱怨上帝的不公:为什么要给他们如此深重的惩罚呢?
生活在当代世界,我们一般很难想象和理解那种纯粹属灵的宗教生活方式。设想若不是生活在神学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有无可置疑的上帝和宗教作为精神支撑,骤然割裂和尘世的一切瓜葛,带着命运的哀叹走进高墙,开始永无止尽的修道生涯,确实是生不如死。阿贝拉尔已年过四十,失去了男子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意味着不会再有对异性的欲求,可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神学研究中去。而海萝丽丝还只是不足二十岁的妙龄女子,青春年少,有着正常的感情需求,另外她还深爱着阿贝拉尔,打算和他共度此生。可她的夫君——阿贝拉尔的形同废人,让她从今以后,连幻想都成了一种奢侈。
二人天各一方,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海萝丽丝的痛楚自不必言。她开始写信给阿贝拉尔,向他索要他示爱的话语,作为精神支撑。她低声下气,自称为他的“妓女”和“陪睡者”,请求他体恤怜悯。可阿贝拉尔已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宗教事业当中,他四处宣教,有了一批追随他的弟子,还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尽管仍是颠沛流离,还是“身残志坚”,身体力行,把执着的宗教信仰发挥到极致。在这极度的宣教热情下面,是对人对事的极端平静和冷漠。他俨然成了海萝丽丝的宗教领导和神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帮助式口吻和海萝丽丝对话。阿贝拉尔答复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语,耶稣上帝新约旧约,避重就轻,异常狡辩,似乎不可理喻。他丝毫不顾海萝丽丝的感受,称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为羞耻器官,认为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无比耻辱,而上帝让他永远失去享受情欲的能力,正是体现了神的大慈大能。他还极力阻止海萝丽丝对上帝抱怨。他说,如果再这样抱怨,就会触怒上帝,就不能和他一起升到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了。为了获得理想中的新生,他甚至宁愿速死,从当前的艰辛生活中解脱。因为生活在深重的苦难中,是远远比不上早些幸福死去的。
后来海萝丽丝已经不再责问阿贝拉尔,而是完全以教内姊妹的口吻向他询问修女制度的源头,并要求阿贝拉尔为自己的修道院制定规章制度。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终于低下了头。因为她知道,再多的怀疑和抵抗,都已经无济于事了。1142年,阿贝拉尔如愿以偿地与世长辞,遗体安葬在至高荣誉的圣灵堂中。二十二年后,海萝丽丝随他而去,同样以榜样教徒的身份,和他安葬在同一个地方。阿贝拉尔比海萝丽丝大二十二岁,也比她早离开二十二年,这样的命运安排,既巧合又充满诡异。二人是否一起相聚在上帝的国度里暂且不问,确定无疑的是,在这个尘世上,二人终于得以永不分离。再也没有什么人或神,能够将他们强行地拆开了。
对于欧洲中世纪,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理解。一种比较修正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关于中世纪“黑暗、蒙昧、专断”的印象,实际上带着一种启蒙的偏见。因为西方学者对中世纪的性质,历来有着两种不同的表述体系。一种是以法国大革命前后启蒙思想家为代表,对中世纪完全否定;认为那是一个极端压抑人性的时代。启蒙,正是要将人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获新生;而另一种是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论述,他们将中古时代的文化视作卓越的典范,认为只有那样的生活,才更接近一种灵性生活的完美理想。而我国“五四”先贤们,在引介西方思想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抛弃了后一种论断,才导致今天我们对于中世纪的样板化认识。
以现代性对启蒙叙事进行解构和除魅,固然是一种可取的认知态度,也是更全面认识历史的必要方法。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中世纪的漫长时段,为人类文化史提供的贡献实在是乏善可陈的。就历史著作而言,不过是多了几部教士编撰的教会编年史。而这些编年史恰恰是克罗齐所说的“死历史”,除了支离破碎的往事记录以外再无其他价值。而就当时的人来说,既然献身于修道院是出于对灵性生活的追求,又何以要在高墙之内苦苦挣扎,为挥之不去、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欲纠缠悲伤忧郁呢?
当然,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个异数。可是这样的异数,若没有宗教神学的阻隔,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吧。生活在一个不能自由选择的时代是不幸的。失去爱人的海萝丽丝最后变成了一个严厉的修道院长,一个禁欲主义的卫道者。她和阿贝拉尔的通信被教会多次出版,既是典型的“反面教材”,又为后来人提供了由世俗转向灵性的好榜样。她献身宗教事业的事迹得到了时人的称赞:“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献身哲学的女性,毅然放弃逻辑转而信仰福音,放弃柏拉图转而追随基督,放弃学院转而投身于修道院……”写到这里,我已经没心情再引用下去了。
浮世短暂,人生如寄,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所以有关彼岸的一切叙事,我一直都不去相信。
2008年12月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