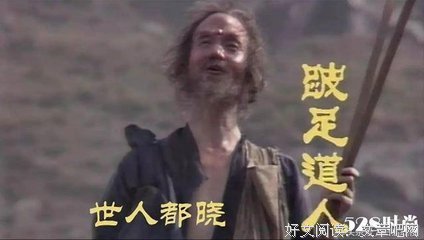
《诗言志辨》是一本由朱自清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页数:1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言志辨》精选点评:
●诗言志辨,重点在于,为何要辨。
●看看~
●开明书店1947年版
●选读
●看的太累。
●似乎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喜作诗言志篇,六朝以降,言志缘情,新旧传统的调和。网上只找到繁体竖版,看的很累,尤其比兴一篇,材料徵引实多,但觉着未说透。
●两遍了,还是没懂。
●有所得。
●没读懂
《诗言志辨》读后感(一):以其昭昭 使人昏昏
朱先生的国学底子本来就有限,但算是比较勤奋的那种。教课之余,可能是根据讲义写的这几本小书。书中颇爱引经据典,但行文逻辑实在是有问题。古义泯灭,讹传纷纭,本来是比较难讲的。经朱先生一讲,搞得我会陷于绝望。本来就不明白,越讲越不明白。当年闻一多先生对朱先生的学问颇多微辞,看来也不完全是文人相轻的原因。不过话说回来,朱先生书中引文甚多,这些引文倒是很有用处。
很喜欢豆瓣网,但是不知道网上这些书的“简介”是从哪里来的。从这本书的简介来看,写这个的人要么是书商或出版社,当然只是说好,要么可能是随便找人写的,矮子看戏,盲人摸象,实有误导之嫌。
《诗言志辨》读后感(二):诗人,诗人
略读朱自清《诗言志辨》。
此书没有传说中那样好,亦没有苛评者说的那样糟。就序而言,一眼就能看出这本书诗人的立意所在:以一种西学而来的文学史观念来看四库集部的“诗文评”。于是我们常见的论述模式呼之欲出:从古代资料中找出许多名词,将这些原本有着特殊语境的名词看做一种有着固定内涵外延的概念术语,抽空其历史意义,赋予其哲学意义,然后用这些名词构建理论体系。
所以,总的来说,诗人就是诗人,目光敏锐,思想较平。很好的问题,很好的角度,也抓住了很有意思的话头。但是总觉得不到位,缺少某种东西。但不管怎样,给人启发甚多。这就是本书最基本的感觉。
《诗教》一篇,我认为还是写得很好的。如对“引诗断案”和“引诗以证事”两部分,分类精当,搜罗颇多,可见其心细。再如讲“温柔敦厚”和“思无邪”之区别,对我启发甚大。清华的孙明君也写过一篇比较“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论文,估计也是受到朱先生此处启发吧,朱先生一眼就看出这里面蕴含的汉宋不同,诗人的敏感的确有过人之处。但可惜他没能站在更为宏观、更有历史基础的地方来看这一区别。他似乎迷失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五彩斑斓的术语中了,他动用了无数的概念和术语,如中庸、平正、和、节等等,但他越想把“温柔敦厚”和“思无邪”的事情说清楚,却越让人迷惑。为什么?因为这些术语并不是有着严格内涵外延的概念,而是在古典典籍中,有着各自的历史语境,在不同典籍中也有着不同意义。探讨基于《诗经》概念的“温柔敦厚”和“思无邪”,却不从《诗经》之为经的角度找原因,只是试图从概念到概念这种想象的逻辑中找到答案,恐怕南辕北辙矣,更不必说其论比兴、诗教、六义等。
《诗言志辨》读后感(三):情志合一——“诗言志”读书笔记
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成员。它诞生的时间最早,但同时也是最不好理解的,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诗言志”这一观念的产生就很好地解释了以上难题。诗言志不仅对诗歌理论有直接的启发,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难怪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说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历经久远,诗言志最初的含义也已经发生改变,但在诗言志中,个人认为是有情有理的,诗言志只有在情与志的完美结合中才能发出更大的作用。
一、历史中的诗言志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帝曰: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古人诗乐不分家的观点。诗,在其初生阶段,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是与歌、舞结合在一起,作为祭祀的一种仪式。然而,许慎的《说文解字•言部》:“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根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诗与志本是一个字,志有三重含义,记忆、记录、怀抱。《诗经》是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理论。如《魏风•硕鼠》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秦风•蒹葭》表现了男的和女的之间如梦的追求。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合一,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二、“情志,一也”
从本质上看,诗从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下降为个体抒情言志的艺术样式。从功能上看,诗从政教功利的教化工具转为个体的生命歌唱。对赋、比、兴的认识,从美刺讽喻的教化手段转为对诗的审美本质的把握。孔颖达认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昭公二十五年)照这种解释,“志 ”并不是人心中固有的、静止的东西,而是 “情动”的产物。情志因人而异,诗亦如此。不论是表现政治、爱情、欢悦、悲痛,不论是士人之所歌咏还是民间的劳动号子,都是言志抒情。《诗经》,原本也是民间的深情之作,只是后为了儒家教化之用,变了风味。那些言志的话语,哪一个不是发自心底的感叹。
诗,只有将缘情、言志相结合,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这样比较平和的观点,既是个人的志趣所在,又能将社会功用凸现出来,不偏不倚,朴实自然,才能品味到中国诗学的恬淡风味,进而拥有更深刻的领悟。
《诗言志辨》读后感(四):从“言志”到“缘情”,一场艰难的分娩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首先有些惶然。从“言志”到“缘情”,如此粗糙地概括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流变,总感到有失恰当。因为,说到“缘情”,似乎就不能不说到“咏怀”,不能不说到“体物”……但“言志”作为古代源远流长的创作观念,在诗歌传统的流变过程中,早就涵盖了“缘情”之外的所有诗歌观念。朱自清先生在“作诗言志”这节中,以翔实的材料和缜密的论证,说明了“诗言志”传统在古代诗歌发展变迁中的牢固存在。与此同时,“缘情”则像言志这条汹涌大河之下的暗流,与“言志”若即若离,虽然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但也从未远离过“言志”。
“诗言志”观念中,“志”的含义几经变化,它从来都未曾脱离“一己穷通出处”,而穷通出处又往往与政教不可分离,这是“诗言志”最原初和最牢固的核心。根据朱先生的论述,“言志”的含义经历了三次变化,这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在屈原宋玉的创作之后,“言志”从上古献诗讽谏为主的窠臼中走出来,第一次做到了歌咏一己之志,穷通出处为主,这是骚人诗赋带来的的一大变化。事实上,在我看来,此时“缘情”也已经初露端倪。“缘情”形成气候是在五言诗的风行之后。“言志”的第二次变化,可以说是“言志”与“缘情”的正式汇合。虽然从六朝开始人们对“缘情”的认可一直都没有敢于明确地独立提出,但把“志”的含义扩展到“情”,无论合适与否,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以及裴子野《雕虫论》的出现,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言志”和“缘情”的界限模糊。即使如此,穷通出处和政教依然是“言志”最正统的含义,“缘情”并未名正言顺地归于“言志”,更没有名正言顺地独立出来。一直到清代,几经曲折,“缘情”终于得以见天日,这是第三次变化。无论把“缘情”看作与“言志”是两条独立的河流,还是二者本为一家,事实上已经不再重要。
那么,古代诗歌传统“言志”与“缘情”的流变,对于现当代诗歌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诗缘情”观念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存在却迟迟不能被认可,细究其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息息相关。“道”为正统,“情”则属于人欲,“存天理,灭人欲”虽则是儒教的极端展现,却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性的压抑。于是,完整意义上的抒情诗自然不会以独立的姿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只能依附于“言志”传统悄悄生长,一直到正式包容于“言志”传统。
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界革命”以及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使得新诗诞生。西方现代派诗歌,则是新诗创作手段的重要借鉴来源。但创作手段上的全新变化,并没有湮没新诗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发展变化之后的“诗言志”作为根深蒂固的诗歌观念,被移植到新诗中。戴望舒的《雨巷》,写作技巧上借鉴了西方象征派的手段,内容可理解为“吟咏情性”。解放后的新时代颂诗,非常接近古代的“政教”传统,算是一次诗歌创作观念的倒退。北岛的《回答》,也用了很多象征的手法,内容则可归于“歌咏人生义理”。“诗言志”传统发展到现今,已经是不仅限于中国诗歌,而是诗歌创作本身的一个原则。所以,学作诗首先要知道“诗言志”,就像要学写小说首先得知道“三要素”。“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前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后者则作为一代代诗人创作观念的拓展、积累、融合,成为诗歌的基本内核。
反观西方诗歌,主要的流变并不是发生在创作传统上(从史诗到抒情诗的变化足以概括),而是发生在创作手法上。西方诗歌史,尤其是近现代诗歌史上,各种流派和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留下了一大批极具特点的作品。与此相比,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段和特点则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和创新,只有各种不同内容风格的出现。这个问题从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对于流派的命名上就看得出来。比如,西方有“象征派”,“自白派”等,区分是创作手法层面上的。中国则有“田园诗”,“边塞诗”等,区分是创作内容上的。“诗言志”这个在中国诗歌史上经历千年流变才得以完善的创作传统,在西方则是自然产生自然存在的。为什么在西方诗歌史上轻描淡写的一个简单概念,却在中国争议许久,嬗变数次,才得到含义上的明确,获得名正言顺的存在?“言志”和“缘情”的纠缠,一直到“言志”的变化和确立,就像一场艰难的分娩,一场本身毫无必要的艰难分娩。我想,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