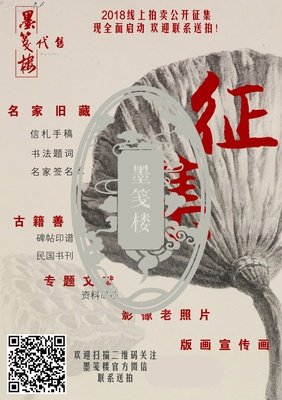
《负暄续话》是一本由11.80元著作,312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1997-1,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负暄续话》精选点评:
●还不错吧。不知道买过没有,回去查查看。
●一共三“话”。可爱老头。不过总体感觉一话不如一话。不能怪人家,实在是没什么人可写 了。
●老家伙有老味道
●写人的文字更吸引我。书确是适合在阳光下随意翻检,似我这般囫囵读完并无多少受益。其中作者与友人应和有一句“安得秋风三五夜,与君对坐话归耕”。深得我心。
●自语系列
●从这一本喜欢上张中行,不过最喜欢的还是桑榆那本
●負暄系列是民國抗戰文革那一代文人的舊聞掌故,負暄意為日下取暖,同瑣話連在一起,是張先生對這本八卦錄的自謙說法。續話的序裏提到了負暄瑣話,其大抵講的都是諸如章太炎胡適之一般的人物,續編講的則更多是算不得出名的故友至交。民國掌故這一年來讀了若幹,那些大儒的癖好多少也都聽聞了一些,但我自己以為,若要找尋一個時代的風骨,莫過於關註那些青史之外的普通國民,與其在面對生死抉擇民族危機時所表現出的大善大勇和超然,畢竟不因此,兩千年血脈不得傳。從這層面上講,續話比瑣話更讓人欣喜。
●给三星不足,四星勉强;这当然不仅仅指的装帧。
●很喜欢他的文笔
●初话、三话的封面装帧也是一样的,只封底颜色不同。
《负暄续话》读后感(一):负暄琐话
最近的兴趣大约薄劣的很。
订了这几本和温源宁的《不够知己》,都是些高雅的名人八卦:自然不乏颊上三毫式的回味辛辣的概括。
前者已经看完了,后者还没有到。
于是淡漠地写:
写东西的兴致大约象香烟,无拘无束地抽上一会,按熄了,过一会还可以再抽--只是距离扫兴也不远了。是,一次比一次更近了。
然后侧头看窗外:绵绵滚滚不断的槐阴,枝叶舒举,饱满的汁液跃跃欲滴,想要挣破这绿。
闷闷地想,看东西的兴致,也类乎此。
袁枚说度客食饱,则脾困矣,须用辛辣以振动之。张中行也写到温源宁,看来确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他的小册子Imperfect Understanding,钱钟书译作不够知己,张译为一知半解--文笔的俏皮流利,张自然较温、钱差了许多。于是象一切穷困无聊的书生一样,对温书有了更迫切的想头。:)
有废名的一段故事,耳熟能详,但不知确切争吵的对象,这回明确了:
“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熊是熊十力。
张并不避讳这些师长辈人物的短处,也经常说到谁的论点,自己并不理解,也不求同:)观察的高度甚妙。
不涉及人物,而转说风土人情的,便不大风趣矣。因此这三本书的目录,都是人物印象在前,其他随笔在后。封面简素,要老实说呢,是有些刻板--跟老爹书橱里的地方县志册子之类大有同源的亲切。
初版是在八六年九月,我不求版本,手头这套是九七年七印的--封面仍然跟县志小册子之流亲切。不由莞尔。
《负暄续话》读后感(二):人生最是难得处
十数小时飞行的光景,最易百无聊赖。临行前,将布衣上的脉望书话八十六篇一一用A4纸打印出来,同Sotheby's: Bidding for Class 一并放入包里,本以为多少能对付过这旅途。不料想大概是昨夜睡得太好的缘故,三四个小时就就匆匆翻完了两个册子。无趣之际便把脉望书话里令人起意的书名钞下来,待日后找寻。钞至张中行先生的负喧琐话,忽然想起似乎之前下载过电子版。拿出电脑,虽然只有其续编负喧续话,却也暗暗欣慰,又可以杀些时间了。
负暄系列是民国抗战文革那一代文人的旧闻掌故,负暄意为日下取暖,同琐话连在一起,是张先生对这本八卦录的自谦说法。续话的序里提到了负暄琐话,其大抵讲的都是诸如章太炎胡适之一般的人物,续编讲的则更多是算不得出名的故友至交。民国掌故这一年来读了若干,那些大儒的癖好多少也都听闻了一些,但我自己以为,若要找寻一个时代的风骨,莫过于关注那些青史之外的普通国民,与其在面对生死抉择民族危机时所表现出的大善大勇和超然,毕竟不因此,两千年血脉不得传。从这层面上讲,续话比琐话更让人欣喜。
张先生的文笔没的说,是我最喜欢的那类旧派文人加上海派路数。书中讲Critique of Pure Reason(259),估计少时也是花大力气读过西学,而英人自傲的那种冷幽默,张先生着实是拿捏的好。试引几段如下:
“可是很对不起梁(漱溟)先生,我没有去商(量他的人生哲学)。责任的一半在我,因为自顾不暇。另一半,我大胆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的,他是不会采纳的”21
“我(向启功)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您见过多少真顾二娘做工的(砚台)?另一个是,譬如从刀法上,风格上,能够断定是不是真出于顾二娘之手吗?启功先生言简意明,只有六个字就交了卷,是“没见过”,“不知道””。 112
“老友寄来一首 高阳台 词请和。信中说明填此调的原因,是听说当年有情人差一点成为眷属的,住在西部某地,已寡居多年。词有真情意,缠绵悱恻。我却为了难,想随着呻吟,可是因为无病,竟几次也呻吟不出来....(集李义山句成诗)交了差,换来了老友的感谢。我,至少也在这短时期,变了对集句的态度,因为它救了我的急,使我无病也能呻吟得像是有病” 203
“启功先生有一种盛德,是你只要把他堵在屋里,他就勇于还账” 248
张先生了身达命,讲述亲友平生亦时不时补上几句自己的评论,于文字中有种造化业力,往往令人唏嘘踟蹰。如讲述与知堂的交往时,写到文革中不得已,烧毁了大多数周作人所赠的手泽玩物,后来觉得自己不免过于敏感,却又说:“这类小损失,也为我换来大获得,是更加明白,人,甚至包括诸有情,为了活命,是什么都可以慷慨舍去的” (65) 活到这个冷暖自知的境界,是最为不易的。
第一次认真写书话,心中满满的赞誉却又不知怎样落在纸上。燕园赋里事,红楼梦中人,那些有王谢气的旧时人物已愈行愈远,留与我们后人评述时,怕也只能像俞平伯讲述李清照一般摇头晃脑地叹几句:“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
《负暄续话》读后感(三):张东荪
1949年后,张中行未再见过张东荪。
有一天再想起他,是因为翻《后汉书》偶然翻到第一百页——《孔融传》。
孔融看不惯曹丕强抢甄宓,便上书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等于是在骂人了。
孔融不会“说话”,后来终于难逃杀身之祸。张中行因此想到“生存与说话的关系问题”,想到了张东荪。他说:“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
我那时读书中《张东荪》这篇的时候,“张东荪”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似乎有点熟悉的人名。张中行先生写得简单又隐晦,我看着没有头绪。更不明白篇首要花那么多篇幅来讲孔融的故事。
后来明白了,不免有些痛心。
从新政府建政伊始被定下扑朔迷离的“叛国罪”之后,张东荪的行踪便开始“迷离恍惚”起来。张中行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他简直像是消失了。”并非只有他一人记忆如此,事实上,张东荪这个人,在49年之后,几乎就不再发出声音,好似被“屏蔽”了一般。同侪后辈,都离他越来越远。
而他,在民国年代,却是一位极为活跃的意见领袖。那时的他,不仅是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张东荪,也是积极透过报刊就公共事务发言、介绍西方文化的报人张东荪,甚至是参与政治活动并担任过要角的政治人物张东荪。
在民国大陆纪元彻底结束前一年,他还举着白旗,领着傅作义出了北平,风光无限。
49年1月,张东荪在西柏坡见了毛泽东。他是主张中国走美苏之间的“中间路线”的,结果与坚持“一边倒”的毛泽东产生了争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张中行所谓“快言快语,得天不厚”例证之一,也难猜测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产生的波澜,我只知道戴晴说,从这场争论之后,他似乎是“失望”了,也开始沉默了。
他与他民盟的朋友们也渐渐拉开距离。他的朋友们知道时代变了,言语做派便也随着变了,似乎只有他,还是旧时代那个倔强的样子,“洗澡”也不愿参加。
49年9月21号,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30号,选举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投票的代表人数是576,计票人员“反复计票”,还是少了一票。
据说后来毛泽东对他许以要职,他却婉拒,还是要做回燕京大学教书。
51年,他据说犯下了“叛国罪”,但罪名并不是法院判下的,而来自权威人物的口中。
顶着这样恐怖的罪名,他从此没有了社会身份,但也似乎没有遭到孔融那样的“杀身之祸”。大约是因为毛泽东很仁慈,要求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把他养起来。
而这些“大事”,张中行这样出世的人,都是不会有兴趣也不可能掺合的,他只是写道:“建国大典过去,知道他荣任了政府委员。我是怀疑主义派,总担心‘一登龙门’,人家会疑为将有所求,于是就连问候信也不再写。又过个时期,断续听到许多传闻:他因什么而隐退了;由燕东园的小楼迁到成府一处平房;受保护的优待,不与垣外人交往;等等。这类事不便探询,渐渐也就淡忘了。”
张中行第一次见到张东荪,是1931年夏天。张东荪当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这年暑假来北大讲演。北大学生张中行看见教授张东荪穿“轻丽的长袍”,“身材不高,洁白清秀”,“讲话清脆,有条理,多锋芒”,是“罗素式的哲学家”。这年张东荪45岁,才刚来北平不久。
40年代后期,还是在北平,张中行开始与张东荪有交往。那时张中行听了张东荪不少上天下地的闲谈,也看出他虽身在书斋,却“不忘朝市”,不甘寂寞。张中行说他“评论性的意见多,附和性的意见少,给人的印象是个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
1949年后,张中行未再见过张东荪。
70年代末,张中行在燕园东门外见到张东荪的女儿(应该是物理学家张宗烨女士吧)。张宗烨做过张中行的学生,两人已30年未见了。张中行只见她眼直视前方,走得很快。张想拦住她,但想及“一言难尽的种种”,一时犹豫,再看时,张宗烨已进了燕园东门。
张中行写道:“就这样,同张先生的情况的消息也最后告别了。”直到80年代写下这篇文章,他仍不知道张东荪在1968年被逮捕进秦城监狱,1973年死在了狱中。
知识人凋零的惨痛,并非任何人的胜利。
《负暄续话》读后感(四):得归——悼念张中行先生
惊闻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辞世,24日凌晨2时40分。
这是自己的一篇关于张先生的旧文字,原来是欣喜于“相逢”,如今,是纪念。
得归
去开明书店,架上有张中行《留梦集》,封面简单却不失雅致,虽价格不菲,亦欣然购之。其时,一老者也买了一本,同去柜台开票时,便有同道之感,与老人相视一笑。
卷首有篇《自序》,文末写道:“最后要谢谢有些读者,书中有不少曾发表的文章,他们也许看过,现在又花一次钱,破费而不怨尤。真可感可敬也。”我是不觉一笑了。先生总是如此周到而幽默,当然就少不得如我之辈“不怨尤”自然也就不觉破费的人在了。
于是想起几年前,我“瞒天过海”逃课去北京游历,从而购的先生《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的事来。
在学校时间长了,人便显得呆了,生活也单调。仿佛是一周的刚开头,想着又是一周的单调,心中正觉无聊,旧友前来,约同去北京。正中我意,当夜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我去北京总是以逛书店为主要目的。读先生《留梦集》中“津沽旧事”一章,对北京和天津的对比,我虽是天津本乡本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北京文苑气浓,天津市井气浓”“卖书的地点也不及北京多”。古城,对我的诱惑是它的古雅的文化气息。
旧友和我是同道,本想此次一行可同过“逛书”瘾,却不知道,她此次出游是有原因的,想是情感上的事不够顺利,想借游走的机会散散心。当时我只是感觉她的目的和我的并不一致,同去王府井书店时,有些心猿。不忍两人都不舒服,让她先回住处。曹丕说过“过屠门大嚼,虽不得食,贵且快意。”对我来说过书店却不能“畅游”,简直难以忍受。好在是神交,相互理解,不致埋怨。
先逛王府井书店,出门奔中国美术馆。道路不熟,便一路走去,见到途中有书店,就进去一看,如此一条长街,倒并不觉得很累。看完画展,天色以近黄昏,怕天黑迷路,决意回家。仍旧是走着,找回去的车站。可是见到路边的书摊还不免驻足,走走停停,不忍匆匆。书摊陈列的书籍大同小异。较之天津,文化气的确更浓,甚至很多专业的书籍,也在其中。
那时我并不知道张中行,但是对于学贯古今,博闻强识的人总是心仪,于是翻看一本《负暄续话》,封面有古雅之趣:左下角三人席地围坐,应该是在“话”,想象中右上角就应该有“暄”。正翻看,卖书的青年热情的向我介绍作者。对有才者赞叹,对有德者景仰,对有情者则几近亲切。翻了几篇,觉得先生三者兼有,便不犹豫,决计买之。摊间遍寻:想有“续话”则定有“前话”或“一话”之类吧。果然,不远处放着先生的《负暄琐话》,封皮一样,只是底色不同,略薄些。二册在手,更觉此行不虚,唯乐与满足。抬头看天,居然好月东升,天已经黑了。
回津细读,更觉美妙。如先生的文章《归》中所说:人生有多种愁苦,心的无所归是渺茫的,惟其渺茫就更难排遣,所以得所归就特别值得珍重。使先生得所归的是现代词人丁宁,使我得所归的是张中行先生,于是也有神游半日,掩卷之后我感谢他,感谢他写了这样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充满温情和美的精神世界,我一旦感到无所归,就仍然可以向他求助,以期漂泊的心能够有所归,就是短到片刻也好。
有如此得归之感,是可以得到安详的心境。一般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才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溶入从而得归。我原是有一位可使我得归的作者的,是俄罗斯的普里什文,如今,又得中国且仍健在的张中行先生的妙文,便觉福分不浅。
几天前,《东方之子》有专家学者专集,尤喜的是,有先生一集。见容貌,听声音,与我想象的差不多,只是更朴厚,声音重而不浊,所谈关于人生观和人生道路不便套用民主一词,即不便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之话语,我以为极妙。看罢电视,重翻旧书,重温旧梦,不觉心中温馨淳厚,仿佛”有所归“了。
张中行先生辞世,想到人称“未名四老”的四位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金克木、邓广铭早已仙逝了,如今张中行先生也走了,不觉心下怅惘,爽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