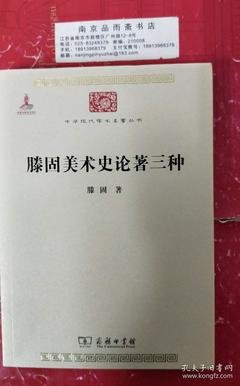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是一本由滕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精选点评:
●論唐宋繪畫史很精當。
●刚好写论文用处很大
●这么好的书啊啊啊!打破了断代史的藩篱来写作美术史和绘画理论,风格分析方法贯穿前两部作品,白话与史料相结合,十分简洁地囊括了大命题。
●汝当效之
●滕固先生可算是以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美术史第一人
●唯有深入艺术史,才能感受到身属同一个文明体是怎样的一种宿命。是内心之源,之本。
●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见识很了不起,对南北宗的反思,将形式分析纳入考量等等,最后那篇是博士论文,同样是把画论作为素材,从美学上探讨,比陈传席不知道高到哪里去,这还是没有太多图像资料作为辅助的前提,滕先生要是活久一些,多看一些画,一定能有更大成就。
●作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家,滕固开了一个好头,对于中国艺术中的核心范畴都进行了关注,从早期佛教人物画到馆阁画到院体画,从士大夫画到山水画到南北宗。
●史学史价值的确很高,且本身也足够精彩。三部对彼时欧陆艺术史观的吸纳各有千秋,《小史》在宏观风格发展的探讨上,《唐宋绘画》在微观时期划分,及取风格相对论来重审南北宗一说上,《画论》则跳到艺术文献和观念的梳理上,参考文献部分不仅有当时德国最重要的一些方法论探讨,也包括施洛塞尔和潘的Idea。诸多方面都尚待进一步挖掘。
●滕固治绘画史的一个初衷是要从从艺术家本位的历史,到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或许囿于当时资料所限,他的研究并未完全践行此想法。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读后感(一):【转】王洪伟:滕固绘画史分期思想分析(外一篇)
每一部绘画史著作必定隐含其研究者对绘画脉络的时间性判断,这是绘画有历史存在的前提。对于绘画是否有历史的问题,在西方艺术史学界是有争论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是独立的个体,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可重复的,艺术作品只有其自身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时间段落中,也只能反映其理解艺术史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代表其真实的历史情境的确立。但是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与目的上,我们又不可能按照这种理解去孤立地看待艺术历史的整体,而总是将绝大部分与我们今天依然相关的作品,转化为一种便于理解的连续的历史现象,使独立的作品转化为必须依赖其产生前的艺术历史和之后被接受的历史状况。确定一种绘画史分期,并非是完全主观与随意的行为,因为一种分期标准的建立,意味着绘画史的脉络在一种新的历史时间结构下产生新的连续发展过程。
【外一篇】 胡新华:滕固如何批判“南北宗”论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读后感(二):【转】薛永年: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
【摘要】本文着重论述滕固作为中国近代美术史学奠基人的学术渊源、治学历程、学术成就,特别是引进西方美术史方法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及其对当下美术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美术史学历史悠久,自唐至清著述不断。但明清两代受鉴藏风气的驱动,著述形式已趋于传记与著录,关注对象更集中于文人墨客,所用资料多回于记载与见闻,治学思想也远离了早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重记载而轻论述,史料价值多了而史学意义少了。世纪以来,由于西学的引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民主精神的倡扬,人文社会科学面目一新,传统的美术史学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标志这一变化的人物,是若干新型的美术史家;反映这一变化的成果,是一些不同于古代的美术史论著与论文。而活动于上半个世纪的腾固,不但以批驳“南北宗论”的《唐宋绘画史》,开始刷新了治学的观点与方法,而且他的《中国美术小史》,实际上也是百年来具有发勒之功的第一本中国美术史。把他视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读后感(三):【转】杨振宇:滕固和中国美术史的现代写作模式
【摘要】滕固素来只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二流作家偶尔被人提及。而身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唯一能够深入理解德语美术史传统,兼得甚深国学造诣的人物,他却遭受历史遗忘达半个多世纪!沈宁先生编辑的<滕固艺术文集>出版,被时人比附为21世纪珍贵文物出土的大事,不是没有道理。清季民初的美术史写作,在滕固这里本该有着令人期待的前景……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读后感(四):《唐宋画论》:一篇尘封多年的美术史论文
整理旧籍,最大的乐事便是发掘尘封多年的名篇名著。为之梳理、编排、校订的过程,仿佛亲手拭去沉积于珍玩的尘土,还以本来的色泽与纹理。于我而言,编辑《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便是这样一次“发现之旅”。
滕固,字若渠,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大家,曾于1938至1940年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滕固先生的最大贡献,是在传统美术史研究中融入了现代学术眼光。现代中国最早一批的美术史,其作者大多是兼授美术史课的画家,而滕固则是为数不多的专业美术史研究者,并且接受了西方艺术史的系统训练。他生前撰有大量学术文章及论著,其中《中国美术小史》与《唐宋绘画史》两种,最为人所熟知。
滕固先生交友甚广,钱锺书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挚友。滕固曾有诗相赠:“十九人中君最少,二三子外我谁亲。”抗战期间,钱锺书离开云南时,也曾赋诗一首相赠。1941年滕固去世后,钱锺书作四首五言古风《哀若渠》以为悼念,“抚棺恸未得,负子子倘知”、“感旧怆人琴,直须焚笔砚”等语尤见其痛。
滕固先生命途多舛,1941年便因脑膜炎而告不治,英年早逝,可惜其著述大都未经结集出版。直到本世纪初才由沈宁先生精心整理,陆续出版《滕固艺术文集》、《挹芬室文存》、《被遗忘的存在:滕固文存》。
本次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除收录滕固《中国美术小史》与《唐宋绘画史》两种知名代表作外,还收录了一篇极为珍贵的论文——滕固在德国学习艺术史所撰写的《唐宋画论》。
1931年,滕固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艺术史,毕业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Chinesische Malkunsttheorie in der T’ang und Sungzeit(唐宋画论)。这篇用德语写作的博士论文长期不为国内学界所知晓,更难获重视。2005年范景中先生将其影印,收录在《美术史与观念史》第IV集。不过,德语原文依旧是阅读的障碍,乃至于有论者认为此篇论文与滕固先生另一部中文论著《唐宋绘画史》在主题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事实上,这篇长期被忽视的论文,意义非同寻常。它呈现出滕固先生接受西方现代考古学、风格学的理论方法后,在研究实践中的巨大转变。简单地说,其中文著作《唐宋绘画史》主要是对画家、画作及流派的分析,而这篇博士论文则进一步讨论了唐宋时期的画论,更偏重于理论与风格的讨论。《唐宋绘画史》虽然出版于1933年,但研究者王洪伟曾考辨此书“底稿”成型年代,应在1926年左右,之后至1930年间进行了增删和扩充,但其整体完成要早于滕固的博士论文。所以滕固的这篇德语论文,可说是其接受西方美学和美术史教育之后最直接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其关于美术史的更为成熟的思考。
滕固在论文开篇处说明了撰写此文的缘由:当时对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上处于探索阶段,且都出自欧洲与汉学家之手,中国本土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他希望能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系统“展示中国唐宋时期的艺术脉络”。为此,他还特意说要与日人金原省吾的《支那上代画论研究》“决一高下”。论文全篇分为五章,分别题为“前史”、“批评家的艺术理论”、“画家的美学理论”、“士大夫的艺术理论”、“馆阁画家与士大夫画家之辩”。文章的谋篇布局与传统的画史画传大不相同。其特点与价值,正如《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一书导读的作者陈平教授所介绍的:“他对理论家个性的生动描述,对理论前后贯通、深入浅出的阐释,以及文化史的联想,使讨论显得十分丰满,远非同时期一般画学著作可以相比。”
这篇论文由柏林国家美术馆屈梅尔教授、柏林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布林克曼亲自审阅并点评。布林克曼在点评中提到:“滕固对于中国画的阐释,具有甚高的价值,在我所读到有关中国画的论著中,他的阐释是最美的。”滕固因这篇论文,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便顺利毕业,也成了当时一大新闻。《艺术旬刊》报道此事时说:“柏林大学考美术史考古学学位本甚谨严,彼邦学者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尚在候选,而滕博士竟以二三年之功获得之,且中国人得此学位者自滕博士始,实为国际无上之荣誉。”
然而这篇重要的美术史论文,因语言的障碍,长期无人知晓。幸而,有心人常有,包括沈宁先生在内的多位学者一直关注此文的翻译工作。后经范景中先生交由时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张映雪,将这篇珍贵的论文翻译成了中文。因为论文中用德语摘引了大量中国古代画论,回译工作难度很大,此次沈宁先生还特地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的毕斐教授担任校订工作。
毕斐教授首先关注到了版本的问题:滕固先生此著为其于193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曾刊于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东亚杂志》)上,后又由柏林Walter de Gruyter出版公司于1935年发行单行本。单行本较博士论文原本略有几处不同,比如文章副标题“一次尝试性的史学考察”,便是单行本有而博士论文无的。张映雪的译文是根据博士论文翻译而成,毕斐教授提出愿以后出的单行本做参照进行补校,以求更准确地呈现滕固先生的原意。
校订工作的最大难度在于引文的回译,这需校订者对传统画论的文献了如指掌。而此书回译的一大难点又在于,由于民国学术引用经典古籍一般不再详细注明版本出处,所以文中所提到的朱景玄、张彦远、荆浩、郭熙、苏轼、韩拙、邓椿等传统画论名家的引文,皆无出处。全文引文的回译,全要靠译者、校订者自己来追根溯源,其中难处犹如大海捞针。毕斐教授专攻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国美术史学史,他撰写的《历代名画记校笺与研究》更是深受学界好评。由他来担任校订工作,大大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除了回译工作外,毕教授还极为细心地完成了不少校勘工作,不仅对原文中关于《后汉书》、《广川画跋》等文献的引文出处进行了校正,也对于滕固先生对《历代名画记》的一处误用进行了说明。校订工作极为繁琐,前前后后共三易其稿。论文共六万余字,却花去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改花了的稿纸上,记录下了一位学者认真、严谨的校订手迹。
如今,这篇被尘封多年的珍贵论文,经由沈宁先生、范景中教授、张映雪女士、毕斐教授、陈平教授的“接力”,终于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它将不仅有助于读者更进一步了解这位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空白,为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美术史学提供了极有分量的一篇研究成果。
(本文刊发于2012年05月2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