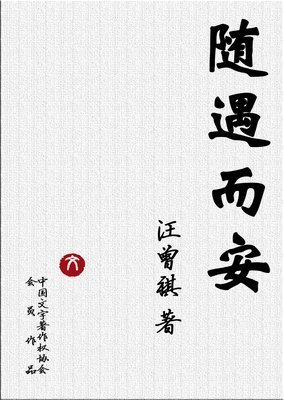
《汪曾祺:文与画》是一本由汪曾祺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页数:1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汪曾祺:文与画》精选点评: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
●万物静观皆自然,四时佳兴与人同。汪老美文冲淡隽永,但此书缺点在于编者选择了太多观点相似甚至内容重叠的文章,读起来审美疲劳。
●字和画都很好, 还是人间送小温的汪曾祺, 可惜文章大多看过, 减了兴味.
●人间送小温~
●疏朗恬淡,适合休息时读。
●是的,有时候我确实需要这种救赎
●促使我再读归有光
●他的文字实在是太美了
●只对排版有点遗憾:文不对画 有重复的内容
●汪曾祺的文章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的散文编的乱七八糟。。进来看了他三本散文集。。重复内容大概都有百分之八十,更无语的是,一本书里为什么还用很多重复的。。真希望有个用心的人,系统完整的把老头的文章再整理出版下。。
《汪曾祺:文与画》读后感(一):文好,画差,是说印刷不好
文章好,画看不清。原来不觉得,汪还是比较自负的,他的确也有可自负之处。
《看画》一篇,“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斗方,画一棵芭蕉,一只五彩大公鸡,挂在他的画室里”,可发一噱。
《汪曾祺:文与画》读后感(二):白云一片汪曾祺
这本小书有一些谈人事的,更多是汪曾祺谈文论画的随笔小品,文字一如既往空疏冲淡,开阖从容。更可喜每篇文章都配有汪曾祺的手笔书画,墨韵十足。文与画间,一位老者的一派天然情致和生活蕴籍立见。以前读黄裳《珠还记幸》,同样文图相间,但也许对书法、包括黄裳所专领域及一些历史人物的隔膜,竟读不到十分快意。再看汪曾祺的书画笔意,照我看,竟可在已经身兼的二美——美文家、美食家前再加一个书画家,但老人却自谦,说他的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只是白云一片而已。”
《汪曾祺:文与画》读后感(三):羡慕所有一手好书画的人
借了两本汪曾祺的散文,更喜欢《文与画》,果然这个老头儿要书画文字一起读起来味道才足。
文字自不多言,没有精巧的结构,行云流水的文章最见功力。不过这次集中读他的散文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往事和八卦,老头儿颠来倒去地在不同的文章里面提到,而且面貌可可相似。对此一点也不恼反倒觉得可亲,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嘛,而且是“我手写我心”的那种。
和文字一样有味道的是老头儿的字画,不习书画的我对个中好处道不出个所以然,只是看到某幅某幅无端会觉得目爽、可亲,尤其辅以那些题画,若干道矮纸斜行就兴味全出。比如: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高邮汪曾祺时年六十三岁,手不战、气不喘”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很喜欢这一条,我觉得能体现一个人生活的兴致情态,就是好的小品。)
“后园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盛,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一九八四年五一偶忆写之。今日作画已近十幅,此为强弩之末矣。”
另外,书末汪朝写的跋也很好,虽然她说自己不很懂书画和自己的父亲。
《汪曾祺:文与画》读后感(四):颜色的世界
这是汪曾祺去世前一年的作品,文字退后,只剩下简单的色彩,这就是本真吧。汪曾祺文、书、画皆通,他喜欢写风俗,写传统,写饮食。他的小说随意如流水,他不拘结构,在意的是语言。他有些鬼异题材又大胆得令人惊异,他是师从沈从文的,沈从文教他们的时候,总是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汪正是沈的高足。老来他的枕边总放着《东京梦华录》,我也打印了一份放在床头。关于《汪曾祺的文与画》一书,难免有许多是重复的,翻翻也就是了,但后记里的这一段,深有同感,故录之。
颜色的世界
—–汪曾祺
鱼肚白
珍珠母
珠灰
葡萄灰(以上皆天色)
大红
朱红
牡丹红
玫瑰红
胭脂红
干红(《水浒》等书动辄言“干红”,不知究竟是怎样的红)
浅红
粉红
水红
单杉杏子红
霁红(釉色)
豇豆红(粉绿地泛出豇豆红,釉色,极娇美)
天竺
湖蓝
春不碧如蓝
雨过天青云破处(釉色)
鸭蛋青
葱绿
鹦哥绿
孔雀绿
松耳石
“嘎吧绿”
明黄
赫黄
土黄
藤黄(出柬埔寨者佳)
梨皮黄(釉色)
杏黄
鹅黄
老僧衣
茶叶末
芝麻酱(以上皆釉色,甚肖)
世界充满了颜色
《汪曾祺:文与画》读后感(五):汪曾祺的灰調子
汪先生的畫我一向喜歡,此書輯入不少,可惜印刷平平,只能看個大概,收進來的文章多數讀過,但再看也還有收穫。比如他論書法,說“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的(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他欣賞徐文長,撰文談其書畫,推崇備至,而徐氏也對宋四家頗多批評,說蘇東坡“老樸,不似其人之瀟灑”,好像也有些道理,我學蘇字,也是瀟灑不起來,看別人寫得飛揚跋扈或者隨心所欲,徒歎不及。汪氏論畫,也時有妙語,譬如他說自己畫的往往是灰調子,比較淡,接著延伸到文藝創作的“淡化”問題,幾乎就是自辯狀,“衰年變法談何易,唱罷蓮花又一春”。他還說自己的願望之一是“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歷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好像最終沒有動筆,至少我是沒有聽說尚有未完成稿存世……惜哉!還有一段我特別同意的文字,見於《自得其樂》那篇文章的結尾,“我很欣賞《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說得何等瀟灑。不知道為什麼,漢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斬了,我一直想不透。這樣的話,也不許說麼?”